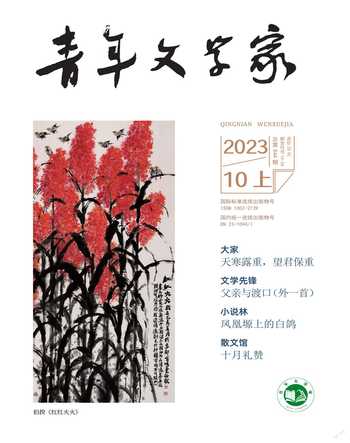蘇軾的閱讀經驗和自我療愈
李德豪

作為北宋文壇領袖的蘇軾,在人生不斷失意,且身心遭受磨難的情況下,仍能保持樂觀豁達、隨緣自適。他在《自題金山畫像》中寫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算是對一生流離的總結。本文試圖從蘇軾生活中的閱讀經驗切入,探析蘇軾的自我療愈過程。傳統經典本身就具有療愈功能,通過閱讀研撰,以及情志之間的互動體悟,消解了蘇軾自我的矛盾痛苦。
一、閱讀療法:書猶藥也
“閱讀療法”是20世紀初西方的心理學家所提出的一個概念,閱讀療法的創始人之一卡洛琳·夏洛蒂認為,閱讀療法是“讀者性格與納入心理學領域的文學文本積極互動的一個過程,它可用于性格評估,改進性格并促使性格成熟”(尼古拉斯·瑪札《詩歌療法理論和實踐》),是將閱讀作為一種輔助心理治療的方法。實際上,“閱讀療法”的認識和實踐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直存在。最早的如孔子所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此時,就已經發現了詩歌對于個人情志的感發和調適的作用。明末清初,李漁的《閑情偶寄·頤養部》直接提出了以書當藥的觀點,讀書、著書等“素常樂為之事”,可以消憂鏟除不平之氣,其功能如藥一般。張潮的《書本草》更是仿照本草體例,備論經史子集的性味功效,如所言:“四書……性平,味甘,無毒,服之清新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心廣體胖。”雖然是游戲筆墨,但依舊點明了中國傳統經典在療愈人心上所具有的“藥性”。可以說,藥石可以醫疾,而書籍則可以醫心。在遇到精神危機時,內斂而通過閱讀傳統典籍尋求解脫之道,從而修正人格缺失,獲得心靈上的拯救,是傳統的儒士所具有的普遍行為。而書,也是蘇軾患難途中最忠實的朋友。
二、閱讀《周易》:對苦難的超越
對于蘇軾的閱讀經驗,南宋的王十朋如此評價:“(先生)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可以說,蘇軾的閱讀范圍相當之廣,這么龐大的閱讀量可以幫助他從多個視角看待人生的各種問題。而且,蘇軾讀書非常之勤。據《春渚紀聞》記載秦少章所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后,不復觀一字矣。”烏臺詩案后,盡管蘇軾內心遭受重創,但并非從此“不復觀一字矣”;而是“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閑窗易粗通”(《次韻樂著作野步》),通過研治《周易》來排遣內心的憂郁和苦悶,化解悲哀,超脫苦難。
作為有經世之志的儒家士大夫,又受到當時盛行的解易之風的影響,蘇軾畢生研撰《周易》。他青年時代就在父親蘇洵的指導下研讀《周易》。貶居黃州時,他有了一定的人生閱歷和閑暇時光,更是投入對《周易》的研究中。比如,他在《黃州上文潞公書》中寫道:“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于《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通過對于《周易》的深思,蘇軾對于其中所蘊含的“變易”思想有了深刻把握。而所謂“變易”,就是指宇宙變動不居,而人也應該隨時宜的不同,積極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并主動適應外部環境。“變易”思想的典型概括便是“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當人生遭遇困難,位于人生低谷之時,要相信有通往坦途的希望和力量。蘇軾曾多次表達這個道理,他在《賀正啟》中說:“伏以物壯則老,肅役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后知天意。”又在《移廉州謝上表》中說:“否極泰遇,雖物理之常然……濯于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擴開云日,復觀于變之時。”這是一種積極正向的心理暗示,將客觀事物的變化看作平常規律的運動,而并非歸咎為命運的無常。這樣不論處于什么樣的境地,都不會使自己的內心陷入一種絕望、窮途之哭的處境。所以,蘇軾在黃州時期,并沒有自我消沉,而是對生活抱有一種熱切的期待,就是受此陽剛精進的“變易”哲學影響。此時,他所展現出的豪放熱切的詞風,如“何妨吟嘯且徐行”等,也是基于這樣的心境,一切總是處于變化之中。對于這種變化的通達認識,無疑正是蘇軾超越困境的心理調節機制之一。
深悟“變易”之理的蘇軾,也對《周易》中的“不易”思想有了透徹認識。“不易”有兩個方面,一是指宇宙秩序的恒常性。在蘇軾登上海南島環視茫茫水天,不知何時能出此島,于是凄然。但轉念便以一種宇宙情懷消解了這樣的痛苦,他認識到“天地在積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之中,有生孰不在島者?”(《在儋耳書》)蘇軾站在宇宙的高度審視,發現不論是中國,還是九州,還是天地,都在水中,于是發現了事物背后恒定的規律,跳出了眼前境遇所導致的惶惶不安。另一個方面是道德價值的恒常性。蘇軾在黃州時期給李公擇的信中就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若見仆困窮便相憐(一作于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可以展現出蘇軾在窮困之時所展現出來的氣度,雖老又窮,但依然秉持著忠義道德和積極的人格精神。而且他被貶海南時期,也積極踐行《周易》的中正觀,立身處世循理無私,正直方正。
三、閱讀陶淵明詩:回歸心靈的田園
如果說易學智慧所建立的是一種樂觀的積極用世觀,那么蘇軾通過閱讀陶淵明的詩集,打開了一條通往精神自由之路。蘇軾對于陶淵明的接受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黃州貶官之前,陶淵明對于蘇軾來講只是一個向往的田園符號;而在烏臺詩案的意外打擊之后,他更深刻地體悟到了陶淵明的人格精神和精神自由。陶淵明處事態度率真曠達,他的詩歌也“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與蘇轍書》),所以蘇軾“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在元豐七年(1084),蘇軾得李江州《陶淵明集》相贈后,余生皆以陶集相隨,他在給程全父所寫的信中說:“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郁,正賴此耳。”(《答程全父推官書》)他在《東坡題跋·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寫道:“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后,無以自遣耳。”他通過閱讀陶淵明,追和陶淵明的詩歌來進行自我療愈,將自身的苦悶和閑適同陶淵明進行互動,沖刷郁積在內心的不良情緒,超越時間的局限,成為心靈的摯友。蘇軾在生死、仕隱、固窮等方面,都繼承了陶淵明不喜不懼、委運自然的思想。蘇軾將生命看作是一種寄寓,人生是短暫的而宇宙是永恒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前赤壁賦》)在宇宙的長度上,人只不過是一瞬間的存在,而世間的一切也沒有長存的,都要歸于幻滅。所以,不再執著于悲喜榮辱得失,不再執著于現世。于是,能夠脫離憂患,超越生死。但蘇軾并非悲觀的虛無主義,而是用一顆平靜之心行入世之事,隨處皆可喜。被貶黃州后,他堅持自己所建立的“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超然臺記》)的生活美學,積極去發現生活,在薪俸微薄而精神高度壓抑時,依舊可以看到“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他能做到很快從悲傷中淡出,回到一種“原初狀態”,也即自己本非淪落至此,而是似乎本來就是如此。化悲為喜,隨處皆喜。這是對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三首·神釋》)人生觀的一種發展,以一種人生如寄的心態安然于塵世生活的百態。另外,蘇軾的用世和出世之間的內心矛盾狀態也通過閱讀陶詩獲得了調和。蘇軾曾高度贊賞陶淵明對待仕隱的態度,評價其為“欲仕則仕,欲隱則隱”。雖然感嘆“長恨此身非我有”(《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看似自己受到朝廷的桎梏,到處遷謫沒有自由,但其實真正的自由應該是內心的自由,應該是保持人格精神的高度獨立,而不是真正去山林隱居。他發展了陶淵明亦步亦趨的仕隱觀,而提出了“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孤館燈青》)的觀點,個體是自我行動的主人,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自己是躡居高位還是耕于農田,自己的內心都可以不為外物所束縛,來往自由,在挫折和苦難中一次次完成超越。但是,放在現實中,仕隱之間的沖突和選擇,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影響因素便是經濟問題。蘇軾的一次次遷謫需要面對的首先便是生活物質上的困境,“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生活上的困頓對于心靈其實也是一種巨大的折磨,在這一點上,陶淵明和蘇軾之間有極為相似的處境,因為饑餓而忍受漫漫長夜。在這一點上,蘇軾繼承了陶淵明“固窮”的觀點,在貧困中堅持自己的操守,“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和陶擬古九首》其二),便是他自我調適的真實寫照。但他并非只是忍耐窮苦,而是用心觀照窮苦的生活而發現生活中的詩意,這是蘇軾精神上高人一等的地方。身處破屋爛房中雨打風吹,但他寫道:“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和陶怨詩示龐鄧》)酣眠自適,完全沒有牢騷滿腹,還有一層釋然祥和,可以看到他的達觀自適。其實,這是和貧困生活的一種和解,用一種真誠的目光看待苦難,盡管物質生活貧乏單調,卻通過內心的調和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充盈。
四、閱讀道釋:消弭界限,物我兩忘
雖然蘇軾是一位傳統儒士,他的思想卻是三教融合后所提煉的產物。我們不能忽略他對于道家和釋家經典的閱讀。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寫道:“(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蘇軾在任密州太守時多次通讀《莊子》來排遣內心的壓抑和苦悶,來凈化內心。莊子的齊物思想對于蘇軾影響頗深,他在《醉白堂記》中云:“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于樂天而已。”從二元論的劃分中超越,用一種相對的眼光看待萬物和人生,將苦難和順境都看作人生的一部分,一切皆順其自然。將萬物看為一體,消除了物我之間的對立界限,生命個體本身才能達到物我合一或物我兩忘的自由境界。基于此,蘇軾超脫于塵世之上,內心獲得一種寧靜且淡泊的恬淡感受。他舍棄了主觀的標準,在《后杞菊賦》中他說:“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這樣的自問顯然是莊子之風,這樣的界限消弭后,內心一派澄明無礙。而蘇軾對于佛教經典的閱讀,初涉《維摩經》,后來與《金剛經》具有頗深的淵源。蘇軾在《〈金剛經〉跋尾》篇中寫道:“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灌流諸根,六塵清凈……應如是觀。”可以看到他對于禪宗的空性觀的深刻體悟。自性本清凈,應如是觀,而不是用五根來尋求解脫。在《和子由澠池懷舊》中他用“雪泥鴻爪”的比喻來表達人生無常、無跡可尋的空性思想,破除聲色迷惘,這也對他曠達無礙的性格產生了啟發。另外,蘇軾繼承了禪宗的“無念無住”的思想,所謂無念,并非指斷絕一切念頭,而是指面對事物的變化而不執著于此,能夠在任何狀態下都可以保持自性清凈,是一種任性自然的狀態。蘇軾在被貶黃州時期所作的《黃州安國寺記》中說:“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是非常困難的,卻是蘇軾內心一瞬的釋然,而且從“孤月此心明”(《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二)等詩句中我們也能體味到他內心那一時的清凈無礙。但值得注意的是,蘇軾從來不是游戲于高深的禪學理論,而是融入生活去參禪體悟。而且他沒有把成佛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只是隨緣隨喜,去獲得禪悅,這是蘇軾獨有的態度。
閱讀是一面鏡子,蘇軾通過這面鏡子,使自己的精神實現了高度自由。不論人生處于何種困厄之中,他都可以積極直面現實人生,觀照自然,體悟生命,打開自己的人生格局。通過對易學的研治,他能夠正面看待宇宙人生的變化,堅守自己的道德。通過對陶詩的體悟,他和陶淵明心靈之間的互動,他可以固守窮困、委運自然。而通過在《莊子》中的遨游,他彌合了是非榮辱、窮達美丑的對立,用一種萬物一體的思想實現了坦然自適。通過對禪學的體悟,他體證了萬物的空性,能夠不執著于外物,從而獲得內心的清凈。可以說,蘇軾通過閱讀實現了精神上的自我療愈,而這一過程必然也是和真實的生活不斷互動的過程,是一個閱讀并實踐的過程。這對于抑郁的現代人來說也是一種寶貴的啟示,傳統經典對于現代人來說也是一劑清涼的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