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鄉村新書寫
周倩
摘要:喬葉的長篇小說《寶水》聚焦中國鄉村在當下宏大時代背景下的轉型歷程與發展新變,力求實現自然、真實、包容的鄉土中國現代化的文學書寫。在主體身份設計、觀照對象選取、結構布局與節奏把握等方面,采取多種富有新意巧思與個性風格的敘事策略,將個人情感體驗實錄、鄉村日常生活記述與對現代化嬗變的觀照統一糅合,描繪貼近現實、著眼當下的“鄉村夢”,書寫變革時期的新鄉村想象,展望傳統鄉村在新時代下激發的嶄新生命力與可能性。
關鍵詞:喬葉;《寶水》;敘事策略;鄉村書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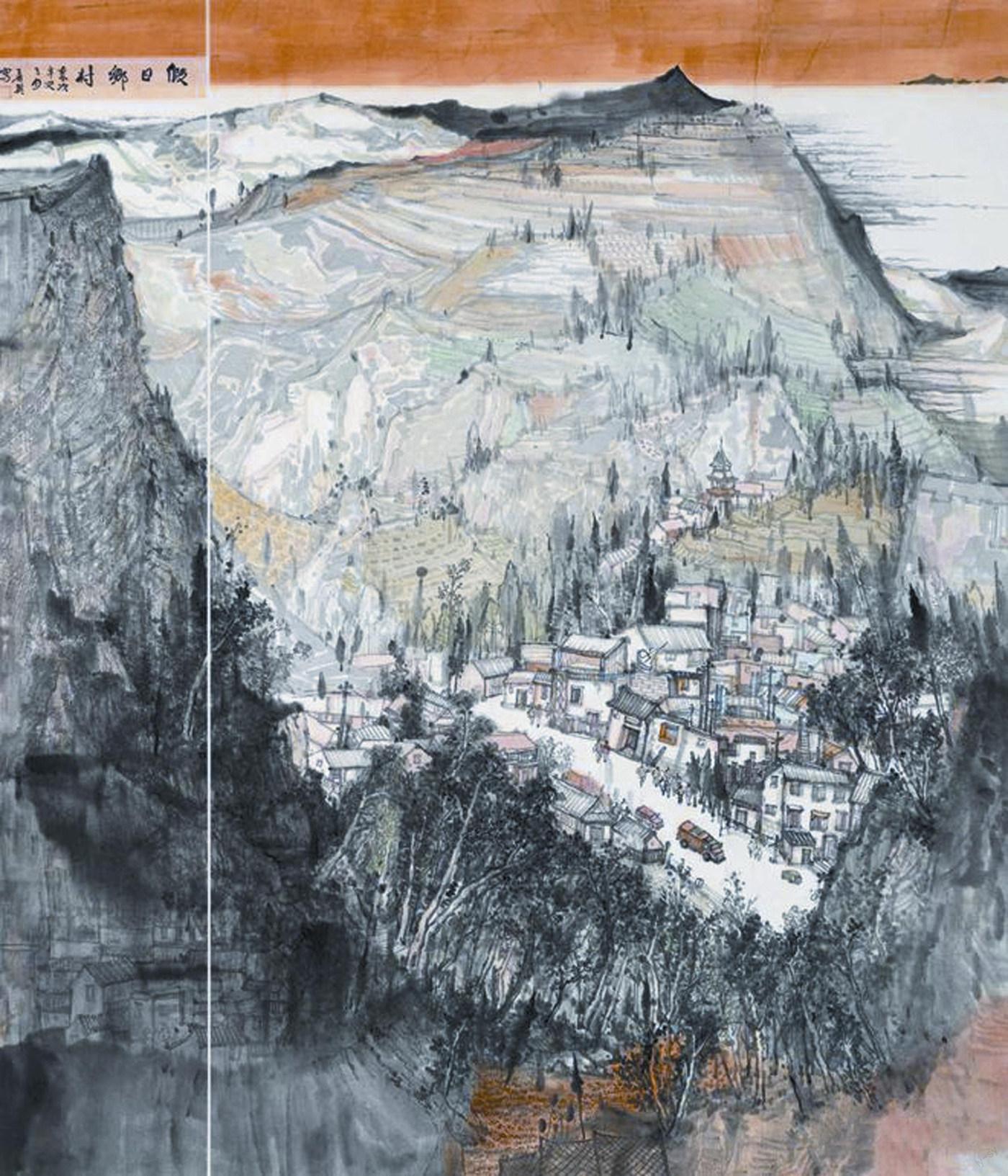
喬葉的長篇新作《寶水》以一種充滿溫情和包容的超越性視角,觀照當下中國社會中一個尋常的豫北鄉村,用細致平和的筆觸描繪鄉村風景、人情與日常生活。作品以貼近土地、還原日常的鄉村敘事,由點及面,真實呈現出新時代背景下伴隨著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與實行,中國千千萬萬鄉村在轉型、建設、發展進程之中的新風景、新面貌、新樣態,展示了當代中國鄉村在延續源自傳統的文化之根與接納時代賦予的現代新變的過程中,激發出新的內生力,以發展取代消亡,再度實現精神家園的存在屬性,構建了一幅面向未來之嶄新可能性的生存圖景。
喬葉所選取的書寫對象“寶水村”具有能夠映射中國廣大鄉村當下真實面貌的普泛性,而寶水村正處于傳統與現代相碰撞交匯的轉型變革期,生產方式、制度建設、觀念意識的新舊交融與沖突以及鄉土人情社會本身的含混性,又使其呈現出繁復駁雜的樣態。為充分發掘與展現其中的復雜性與困難性,喬葉在敘事中采取多種策略,如主體身份的多重設計、一年四季的時間截取,超越性視角、移情式觀照、循環式結構與舒緩型節奏等,生動自然、細致入微地書寫寶水村連接過往與未來的當下發展與變化,深入鄉村肌理,呈現鄉土真實,并對鄉村未來發展寄寓人文關懷與美好展望。
一、觀察與介入:敘事主體的三重設計
對應葉小靈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夢”,喬葉認為在當下迅猛的現代化與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夢”的不確定性逐漸消弭,言說、探討與想象的空間逐漸縮小,因此她將關注的目光投向正在發生新變的中國廣大鄉村,以期描繪“鄉村夢”。在經過“泡村”“跑村”縱橫交織的采風活動與前期考察后,喬葉建構出“寶水村”這一新鄉村想象,依據真實體驗來“寫當下鄉村”[1]。
在敘事中,主體以何種視角、態度和距離觀察與言說所觀照的對象至關重要,不同的設計往往會導致截然不同的敘事效果。在《寶水》中,喬葉針對敘事主體的三重設計,顯示出作家意識所特意選取的出場方式與介入路徑,主體以更自然的方式介入“寶水村”這一空間,在更便于深入展現“寶水”真實全貌的同時,也更易于牽引讀者的情感投入與認同。
身份背景的設置是對敘事主體的第一重基礎設計。主人公地青萍是在省級報社工作多年的記者,在退休前還曾任職于專業學術委員會,擁有對外交流、社會考察、基層調研等履歷經驗,具備典型的城市中層知識分子背景。由于先在的知識儲備、專業視野、職業素養和慣性思維,她在社會、人情、文化等方面必然具備敏銳的觀察眼光、層層剝繭的調查意識和深入透辟的分析能力。身份的設定和交代,決定了主體介入“寶水村”這一敘事空間的基本視角與立場。
《寶水》中第二重較為獨特和精巧的設計是關于主體觀照對象的選取。喬葉并未選擇讓地青萍回歸自己出生地與歸屬的福田莊,而是將寶水村作為一個代償客體。寶水村與福田莊同屬于懷川縣,具備基本相同的文化根基、屬性與語境,但在地理位置上又隔著一段真實的距離,且在具體分類上存在平原村莊與山區村莊的區別——“福田莊在縣西南的大平原上,寶水村在縣東北的大山坳里,隔著足有五六十公里。這段距離完全可以為我建立起一道厚實的心理屏障,讓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2]。因此,寶水村對于地青萍而言熟悉而又陌生,既因與福田莊相似的文化氛圍而使她產生情感體驗上的熟稔,觸發生成文化歸屬感,又排除了以往人情糾葛的干擾,讓她不必過于直接地面對過往,產生過度的排斥感。在這一設定下,寶水村成為一個鏡面性的觀察對象,以寶水為鏡,地青萍不僅能通過鏡面反射成像,間隔安全的心理距離,安心回望始終深藏于內心與回憶中的福田莊,還能因折射的偏差望見中國廣大鄉村具備普泛性的存在狀態。
小說《寶水》曾明確指出地青萍對寶水村的情感生發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對福田莊的彌補性移情”[3],她在排除情緒干擾之后,獲得更加客觀理性的視角。這一主體視角由此具備雙重超越性:一方面是自城市返鄉的生活經驗賦予她的連接和對比城鄉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是在移情式觀照模式下理性與感性兼具的超脫姿態,這讓主體意識能夠以更加溫和而包容的心態去觀照與接納寶水。
這一觀照對象的替換與選取還順勢引出敘事主體的蛻變歷程,讓她前后時期的視角、思維與心態形成對照。地青萍曾抱持不成熟的青春期心態,產生對福田莊的厭惡與憎恨情緒,對于是非對錯進行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決與審定,堅持持有冷峻的夾雜個人情緒的批判態度,以及拒絕認可、抵抗認同、逃離群體的逃避態度。當歷經成長、人至中年的地青萍以成熟的心態重新面對一個新的鄉村時,發現這一對象與福田莊相同又不同,并在現代化的發展中展露新變,于是她的體認與接受態度也隨之發生轉變。此時的地青萍更傾向于對鄉村的自我倫理表示順應、理解與認同,對鄉村語境下特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處事產生包容、認可,不再進行單純粗暴的道德審判和價值判斷。
第三重設計則是女性視角的特寫,這一設計體現出作者自身充滿溫情的目光與飽含諒解的態度,奠定了主體在敘事中一以貫之的情感立場。喬葉曾著重提及其近年來的小說創作在兩個方向上的回歸——“一是越來越鄉土性,二是越來越女性化”,她特意指出:“《寶水》便是女性視角鄉土題材的小說。”[4]邱其濛在分析20世紀末與新世紀初女性作家鄉土小說創作時指出,她們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期待和倡導‘一種充滿溫厚、寬容與混沌的女性愛而自然流露的社會氛圍”,“這種充滿悲憫意識的溫情書寫,不僅僅表現在文本的片段描寫上,而是作為一種敘事策略”,成為她們的共同選擇[5]。喬葉在創作《寶水》時也延續了這種“充滿溫厚、寬容與混沌的”女性愛視角和溫情書寫,她對寶水村的村民抱有充分的共情意識,了解、理解并諒解他們的行為選擇,尤其同情村里部分女性的不幸遭遇與生存困境。但不同的是,她的同情并未上升到悲憫的程度,她只是用溫和包容的目光打量著寶水村的人與事,并非為現代性發展感到焦慮,或為傳統鄉土的衰落而哀嘆。她所持有的心態是積極、樂觀、向上的,她堅信處于現代化轉型中的鄉村蘊藏著化解矛盾、克服困難、向前發展的內生力,因而對寶水抱有尊重、諒解與期待,而絕非憐憫。
例如,當來到寶水村支教的大學生志愿者的教育理念與村民的傳統觀念發生沖突時,大學生以單純的精英意識、高姿態的說教與批判眼光評判寶水:“到底還是小山村,覺悟低、眼界窄、格局小、目光短淺。”[6]當他們尋求身份特殊的地青萍站隊支持時,地青萍勸解他們 :“你注意用詞,不要隨便說人家愚昧落后。”“既然知道這是誰的主場,那就放下身段客隨主便唄。以我的理解,因材施教在這里的意思就是貼著風土人情來做事。哪怕你初衷再好,也不能硬著來。”[7]同時,她明確表示“不站隊”。主人公拒絕站隊的態度,既出于理性判斷的明辨是非,又出于情感立場的不明朗,她不再僅憑表面的是非輕易論斷對錯。地青萍的話語中反復出現“村里的事,就是這”[8]“不能太理想化,這里就是這”[9]之類的表達,實則體現出敘事主體以及作家對鄉村社會規則、人情世態的尊重與包容,也可看出喬葉對此前鄉村敘事中,以現代性的眼光與鄉村對立,站在冷峻的制高點,以過于清高的姿態和犀利無情的言說,批判鄉村之落后這一狀況的隱憂與反撥。
小說采取的女性視角設計還達成另一種特別的效果,那就是便于對豐富、多樣且復雜的女性角色進行塑造。女性視角能夠敏感體察女人的處境,《寶水》對不同代際鄉村女性的命運統一觀照,體察她們幽微隱秘的情感,發現她們個體欲望的訴求。例如,以地青萍視角為引導,對九奶和奶奶的情感世界進行探秘;樹立大英這個能力與魄力勝過男性的典型正面形象,但同時揭示她遏制兒媳的個性發展、潛意識物化女性的“舊社會婆婆”一面;展現雪梅學習繪畫的個性化發展的訴求;揭露嬌嬌的創傷與受害者境遇;述說香梅遵從和伸張本能欲求所進行的悖德與暴力的反抗;記述曹燦在重男輕女的單親家庭環境中的艱難成長及其反抗與獨立意識的萌生。
敘事主體的身份與視角設計,最終使得地青萍的身份呈現多重性與含混性。華萊士·馬丁曾指出:“如果作者想使日常世界陌生化,那么這一世界就必須落入非同尋常的眼中:這就有了利用局外人、非常的或完全天真的人物、小丑、瘋子(堂·吉訶德)或非西方文化中人作為觀察者的傾向。這些人可以震驚我們,因為他們證明,我們認為是自然的東西實際上是慣例性的,或者是不合邏輯的。”[10]對于寶水村這一觀照對象而言,地青萍正是一個漸漸融入其中的“局外人”,在“長客不是客”[11]的集體認同下,她既成為寶水村共同體的一員,又因走出鄉村的經歷和其他身份屬性的復合,具備原生村民所不能擁有的特質,在心理認知上游離于鄉村社群的邊緣。正因如此,她才得到了同樣外來的鄉建專家孟胡子和大學生志愿者肖睿、周寧天然的信任,以及身處某種困境的本村人香梅和曹燦特別的信賴。香梅私會初戀情人時選擇青萍作為幌子打掩護,正是看中她強大的共情能力,以及缺少傳統道德約束的現代性視野和城市人身份。曹燦相信青萍會支持她求學,也是因為她與傳統鄉村人有不同之處,即作為現代城市人表現出的對女性獨立意識的推崇。
喬葉對敘事視角的設計還遠不止集中在主角地青萍身上。對寶水村而言,地青萍并非唯一的女性觀察者,在大學生志愿者周寧和嫁入寶水村的女青年葉青藍這兩個同樣具備一定“局外人”屬性的角色身上,也可窺見作家主體意識的存在。周寧因為童年創傷對鄉村女性產生共情,她更具激進的批判姿態和改變意識,與固守傳統的思想碰撞得更加激烈,而葉青藍在融入鄉村的過程中,同樣與寶水村村民發生觀念沖突,產生雖能共情但無法認可的困惑。
作者在這兩位女性身上傾注了現代意識與鄉土傳統的碰撞與交纏。她們具備與地青萍不同的身份立場、情感態度、生活背景,展現出與其存在分歧的生存體驗、觀點理念和接受態度。在試圖融入寶水村的歷程中,周寧從高姿態的精英意識、“學生”腔調的審視和說教,轉變為采用迂回傳達方式的柔和態度。葉青藍從目睹香梅的暴力行為后堅持報警,不理解、不認同青萍、小曹的維護與包庇,質疑村里的共同認知和道德風尚,到入鄉隨俗,坦然面對與接受村里人為營造熱鬧氣氛的言語調笑,“她的眼神仍歡悅著,和之前相比似乎多了些難以言喻的內容,不再那么簡單,卻也不復雜,在簡單和復雜之間,剛剛好”[12]。這倆人前后所發生的轉變,也與地青萍前后時期的變化形成鏡像對照。
二、循環對照的敘事結構與鄉村倫理書寫
喬葉在創作談中提及,她選取了一年的時間來結構這部小說,而“山村巨大的自然性決定了按照時序敘事”成為她架構《寶水》的“必由之路”[13]。在章節的劃分與安排上,喬葉選擇“遵循四季”,行文間四季流轉、時令輪回。“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14]關注四時之變、陰陽交替歷來是中國文藝理論的傳統。《寶水》的四個章節對應四季,“從冬到春,從春到夏,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從正月十七的過年尾聲到第二年大年三十的新年伊始,從第一節“落花燈、吃落燈面”的“落燈”到最后一節“上墳請祖宗回家過年”的“點燈”,過年時節的結束與開始,一年四季的開端與終結,相互對照、相互接應,形成一個前后照應、首尾接續的圓環式的完整循環。
在《寶水》之前,葉煒的《后土》、付秀瑩的《野望》都曾采取以二十四節氣的時序串聯小說結構的敘事方式,前者以節氣變更推進敘事時空的轉換,加深敘事之真實性與歷史感,傳承“鄉土中國”的百年鄉愁;后者以節氣推移聚焦一戶農家的歲時紀事,以線性敘事折射一個村莊在新時代的滄桑巨變。喬葉坦言曾考慮依據十二月份或二十四節氣架構小說結構,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四季結構,“冬—春”“春—夏”“夏—秋”“秋—冬”,不僅在時間尺度上顯現出四季更替、時令流轉,也更凸顯其中循環、過渡的過程,每個季節首尾相續、重復銜接,連接成一個圓融的輪回結構。相較于《野望》嚴整契合于時令的線性敘事,《寶水》在按時節布局推進講述的同時,穿插主角的回憶與人物曾經的遭遇,將過去與現在的敘事時空打通,使敘事更具有前后貫通、對照、映襯的豐富性與多層次性。當代作家在鄉土敘事中不約而同地選取依照傳統鄉土觀念與知識資源來結構故事,建立一種有別于現代性追求下的非線性敘事的新的敘事結構與秩序,亦可窺見本土性、地方性寫作對現代化潮流的反撥與對抗[15]。
關于章節的安排和敘事的架構,喬葉認為:“其間每個季節的重復銜接也是必然,小說里的樹木莊稼也都需對應季節,因為大自然它就是如此啊。”[16]生長于山水之間、由自然孕育的鄉村,其生存經驗、內在邏輯和文化底蘊的生成也是自然而然的。結合小說中對“萬物啟蒙”式教學方式的描寫,也不難看出喬葉貼近自然、貼近真實的創作意圖。因此,自然輪回的循環式結構將人物命運的回轉、去而復返的循環和恩怨生死的輪回統攝到一起,自然引出最后大團圓式的結局。這一敘事結構也引出和照應著貫穿整部小說的敘事主題——從離鄉到回鄉,落葉歸根。
小說是由地青萍的“返鄉”來展開的,而這里的“返鄉”與以往鄉土文學中反映的返回自己出生的故園和家鄉有所不同。由于作者選取寶水村作為福田莊的代償對象,地青萍的“返鄉”之旅便具有更廣泛意義上的由城市回歸鄉土的意蘊。因此,在更寬泛的視野下,小說中的返鄉者不只有敘述者地青萍,還有因過往的恩怨糾葛決意遠離鄉村的原家父子、攜妻兒下山做生意的大曹、去大城市投奔兒子的老安夫婦等人。最后老原帶去世的父親歸葬,自己也繼承了早已廢棄的祖宅經營民宿;大曹遭遇喪妻的重大變故,只得帶兒子回村,靠祖傳的手藝維持生計;老安夫婦也因在大城市討生活不易而返鄉。人物的離去與歸來形成一種輪回,揭示了鄉村倫理中落葉歸根這一主題。青萍從抵觸、排斥、逃離鄉村群體,到最終抵達“人在人里,水在水里”的圓融之境,也漸漸自覺融入鄉村倫理環境之中。奶奶去世前說的那句以“好”為終結的話,與九奶最后的話“回來就好”相重疊與對應,地青萍的姓、老原的小名“根兒”以及“暖土”“大地色”等細節設定也在一再深化這種土地情結、家園情懷、落葉歸根的文化寓意和倫理意識的表達。
九奶離世、小曹結婚與趙家蓋房,構成對村里婚喪嫁娶、喬遷新居等人生常態的展示,老人的離世與孩子的成長形成生命的回環,村民返鄉過年與送別九奶入葬的重合再次點出“回”的主題。人心回到鄉村尋求歸屬,原家與豆家的和解,地青萍與福田莊恩怨的了結與釋懷,以及“老家嘛……就是等你老了,自然會知道的那個家”[17]的回歸意識,這些循環對照的敘事結構引出以“回歸”為主題的倫理架構,自然揭示鄉村倫理與生命意識。
喬葉在創作時以自然性與原生性為敘事準則,那么小說中所呈現的鄉村倫理架構便自然呈現出一種含混性與真實性。她曾提及:“小說里有新時代鄉村的新風尚和新特質,而這新也建立在舊的基礎上。……而新舊的彼此映襯也讓我覺得格外意味深長。我覺得寫鄉村一定會寫到舊的部分,那才是鄉村之所以為鄉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國之所以被稱為鄉土中國,那一定是因為鄉土性如根一樣。新時代的鄉村固然有新,但舊也在,且新和舊是相依相偎、相輔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慮和浮躁;舊有舊有的陳腐,也有綿長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舊。我在其中不會二元對立地站隊。如果一定要站隊,我只站其中精華的、美好的部分,無論新舊。”[18]在排除了對新與舊的崇拜或批判后,《寶水》所呈現的便是鄉村倫理最本真自然的樣態。
例如,女商人在與農民打交道的過程中得出經驗,他們“不守合同,沒有契約精神”[19],由此揭示鄉村重人情、輕契約的約定俗成的倫理觀。云里村租房做民宿的外客,與村民在送菜與摘樹莓之間發生的齟齬和爭執,表明商品價值與人情價值的不對等——商品價值有高低,但人情價值是平等的。小說進而引出城鄉之間的分歧與摩擦,對城鄉問題作出探討,引導讀者體認雙方對價值觀與邊界感的不同認定,“城鄉之間,就是有這么多難以厘清的東西,這一池渾水,有多少人或深或淺地蹚過?”[20]作為城鄉之間的聯結者與協調者,村干部為上傳下達、推行政策、公正處事,在維護外客正當權益和維系本村村民情誼之間不斷進行權衡。
以大英這一典型人物為例,雖然作家在創作中并未有意樹立與區分正面與反面人物,但大英仍舊是作為帶有理想色彩的正面人物出場的。她深諳鄉村人情倫理,由此磨煉出完備的鄉村治理之道,行事有主見能決斷,顯示出超越男性的執行力與魄力。但她的行事風格并非完全意義上符合現代制度標準,而是自覺順應鄉土民情,例如,為修建停車場,她以風水為借口誆騙大曹遷祖墳,讓出地盤。恰恰是不死板、使巧勁,貼近鄉土的鄉村治理之道讓新時代的政策得以在寶水村順利推行,并逐步使傳統鄉村煥發出新面貌。
與此同時,大英自身的形象也存在復雜性,在她身上,聰慧獨立、有勇有謀的女強人特點與封建守舊的“舊社會婆婆”形象并存。至于衣錦還鄉的趙順,他偷養情婦的行為并未受到道德譴責,甚至比起遙遠都市中的那位富貴而陌生的原配,村里人更認同這位較為熟悉的情婦。九奶去世后,老原作為原家的孫輩,給來自張家的九奶送終,村里人卻自然而然地接受這一有悖常理的行為,這印證了原家的隱情早已成為村里人共同保守的秘密與留存的集體記憶,在充滿善意、感恩與包容的集體情感面前,任何源自道德常理的理性規約都只能做出讓步。正因如此,香梅以暴制暴的反抗行為得到了青萍和小曹的支持和默許,在法律與倫理產生分歧時,“不是啥事都得靠法律”,香梅利用看似野蠻原始的方式達到“履險如夷的微妙平衡”,從而維護自己的權益。這種“小環境的自凈功能”[21]正表征著鄉村倫理中自我化解、自我調和、自我平衡的內生力。
“官方規則和民間道德向來是兩個系統。”[22]鄉村倫理之所以體現出含混性、模糊性與復雜性,正是由于在鄉村中,認同的達成、規則的建立往往是由情感生發的。在相對封閉的小環境里,聚居于此的人們大都具備血緣、親緣的牽連,他們在觀念意識上本就最為重視人情關系,缺乏對既定規則的理性恪守。這種長期留存、根深蒂固的境況,既導致鄉村傳統意識與現代化理念的難以兼容,同時又因其靈活性而具備自我調節的功能,這對鄉村的現代化轉型既可能形成阻礙,又可能提供突破口。例如,寶水村在大學生志愿者的倡導與組織下,向村里的少年兒童推行生命意識教育與性教育,在因傳統與現代的觀念矛盾引發沖突與齟齬時,一向受人敬重的九奶主動站出來,在觀念上表示支持,增強說服力,在勸說村民的過程中,她又以嬌嬌曾經遭受侵害的慘痛教訓為例,從情感角度出發使人產生共情,從而贏得道義上的認同,使性教育課程最終被村民默許。這便反映出在鄉村中普泛存在的,由情感的孕育和激發為起點,推衍至文化、上升至道德,塑造并建構鄉村意識共同體的這一運作機制的本質。
小說對鄉村倫理的含混性、模糊性的展現,描繪出具有自在性、本真性的真實鄉村生活。對福田莊的童年回憶與對寶水村的發展觀察,這兩條敘事線穿插進行、互為對照。奶奶的“維人”的處世原則與方法,“人情似鋸,你來我去”[23]的生存智慧,與九奶的“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這一輩子,哪能只顧自己”[24]的人生哲學形成對照。奶奶的“維人”與九奶的助人兩相照應、殊途同歸,揭示出鄉村倫理中最本真的互相幫助、扶持、依賴的生存實境與傳統道德。
“傳統鄉村共同體是以人倫關系為依托,以‘近距離為特征建構起來的禮治社會,以親仁善鄰為道德態度,以相鄰和睦為價值目標,以相容相讓為基本原則,以相扶相助為倫理義務,既有‘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情結,也有‘趨福避禍的傳統民間信仰,既有‘烏鴉反哺,羔羊跪乳的慈孝道德觀,也有‘出入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良善交往原則。”[25]遵循這一鄉村共同體的原則,奶奶依靠“維人”,讓自己這個拖著兩個孩子的寡婦,依舊能在村里的社群中擁有勸人的話語權,不僅做到了支撐門戶,保住體面,還為自己的兒子謀得好前程。九奶依靠助人,為十里八鄉的鄉親無償接生,讓自己這個喪夫喪子的苦命人與“掃帚星”成為廣受敬愛的福星,離世后配享巡山。九奶在特殊時期保護原家,為原家延續子嗣,即便這一悖德的秘辛被全村人知曉,他們也因九奶的恩情而自發保守這個秘密。
奶奶“維人”的生存智慧,九奶助人的人生信條,大英順應民情的鄉村治理之道,都屬于依據鄉村倫理、民風民情而自然內生的民間智慧。地青萍從曾經的不理解、不認同,否定、厭惡、逃離鄉村,到以成熟的心態自發融入這種鄉村倫理環境之中,真正認識與理解其功能與價值,由此從對“人情似鋸”的恐懼、厭惡、抵觸、背棄,到最終抵達“人在人里,水在水里”的圓融之境,讓自己成為在情感、精神與文化層面架構起來的這一鄉村共同體中的一份子。
三、細水長流的敘事節奏與鄉村現代化觀照
不論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意圖使然,不可否認的是,《寶水》的創作是被置于新時代、新山鄉、美麗鄉村、鄉村振興等宏大的時代背景主題之下的,喬葉認為評論員李國平的理解是精準的:“《寶水》不是命題作文,如果說有領命和受命的意思,也是領生活之命、文學之命、尋找文學新資源之命,作者面對文學、面對生活,反映現實、表現生命的理解的自覺之命。”喬葉認為《寶水》的寫作正是“個人的自覺性邂逅了宏闊時代的文學命題,如同山間溪流匯入江河”[26]。
或許正是因為“個人的自覺性”與“宏闊時代的文學命題”的邂逅,個人的生活經驗、情感體認自覺而自然地融入時代主題書寫,因而即便是展現新時代鄉村新變的長篇著作,喬葉在書寫時仍選取一種平和舒緩的敘事節奏,并延續了此前創作中關注個人、關注情感的風格傾向。于是宏大的時代背景與平緩的日常敘事完美結合,在半封閉半開放的小山村中,當地人依據時令、節氣自然輪回的循環平常的生活節奏,主人公漸漸生發遞進的情感節奏,以及寶水村作為新時代的美麗鄉村,展現的滴水成河、轉型變革的發展節奏,相互穿插貼合,對應個體情感敘事與鄉土敘事,總體營造出細水長流般的敘事節奏,給讀者以近乎靜態且緩慢流轉的時間體驗。
喬葉經由三種路徑來營造這種平和舒緩的日常敘事節奏。其一是“極小事”的交互穿插、串聯與糅合。小說中每一章都有一節內容以“極小事”來命名與構成,統觀整部小說,也基本是由“極小事”連綴而成,經由“極小事”以小見大,反映大變革,由此日常生活敘事與鄉村現代化嬗變書寫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小說在敘述的推進上并未刻意追求一波三折、緊張刺激的戲劇性情節設計,而是如細水長流一般,平淡地從地青萍的視角出發,細細講述寶水村這一年來鄉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以及“美麗鄉村”建設與文旅發展事業的林林總總,沒有出現主要人物的個人生活發生重大變故,鄉村發展事業遭受嚴重挫折,最終眾人齊心協力、合力解困的程式化敘事。地青萍與老原結合的個人情感歸屬,返鄉者回歸并融入鄉土的釋懷與轉變,九奶的離世以及最終促成原家與豆家的和解,在吊唁與巡山中呈現全村人的情感與記憶共同體,這些重要的線索與情節點都融于日常生活敘事中,情節推移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而然地引出最后大團圓式的、對未來充滿希望的結局。敘事模式不顯老套、陳舊,而舒緩的敘事節奏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跟隨敘述主體的視角,如魚入水,自然融入故事情景之中,未有生硬、牽強、格格不入之感。
其二是碎片化的對話與口語記錄。小說通過大量基于當地風俗習慣、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扯云話”的對話形式及內容,以及對方言俚語的記述與闡釋,推進情節發展,鋪展人物故事的講述,表達人物情感的變化,展開對生活體驗的紀實并進而推動主線敘事,時時穿插主體意識影響下主人公碎片化的所思所感以及內在的心靈對話。這種多聲部的對話形式充分貼近于日常生活體驗與真實鄉村生活情境,方言的熟練運用更使讀者身臨其境地感知與體認豫北鄉村的風土人情與文化語境,地青萍內心的無聲言說與自我對話,進一步發掘并呈現出她幽微的內心世界、搖擺的情感立場與漸趨明朗的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寶水》以主人公地青萍的心靈療愈之旅為線索,而其敘事風格本身也營造出輕松、和諧、自然的充滿療愈意味的氛圍,缺少文化批判的冷峻和道德審視的重負,在對集體生活的觀照中,也同樣關注個人、關注情感。
其三是主干故事敘事與地方性知識交錯互構,這也使得《寶水》具有一種內在的地方文化屬性。小說中隨處穿插對與各種節氣相關的民俗活動的描寫,如正月十九小天倉,喝油茶敬倉神,正月挖茵陳,驚蟄吃懶龍,“立秋風,山楂紅。白露到,打核桃”[27],“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軟棗”[28]。在主體記錄與講述之外,依據時令和節氣的推移插入對地方風俗、景觀、植物、吃食的詳細描述與介紹,使得小說敘事日常而不瑣碎、平淡而不無聊,充滿貼近鄉土氣息的真實性和生動性。如上文所述,《寶水》并未如《野望》的嚴整結構一般,嚴格按照節氣的對應劃分敘事,而是將節氣融于敘事的自然推進中,仿若隨意地在鄉村日常生活記敘中引入二十四節氣的習俗,在對吃穿住行的細節描寫中不經意顯現時節的更替與推進,少了形式安排的精巧與刻意,但多了貼近生活的樸素與真實。
正是這種平和舒緩的日常生活敘事,在點滴之間自然而真切地描繪出一個新舊參半、接續傳統與面向未來并行的當代村莊,深入肌理地觀察、剖析、呈現出寶水村在這一年時間中,由構想發端到步入正軌的現代化嬗變歷程,展現出這一處于現代化轉型中的普通鄉村,在生產與生活方式、鄉村治理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新變。
寶水村選擇以發展旅游文化產業作為現代化轉型的路徑,其發展正是根植于當地的風土人情、地方色彩,小說通過民宿的起名——“山明水秀”“小村如畫”“我家院子”“老原家”等,暗含寄情山水的情懷,以及回歸自然、淳樸、本真的鄉村生活的返鄉意識。大曹回村后重拾祖傳的編荊手藝,在工業化沖擊下失去實用價值的傳統器具,通過在村史館展出后,得到縣長乃至副市長的贊賞與肯定,轉而依托藝術價值重新順應市場需求,由此可管窺喬葉對民間手藝傳承問題的關切與思考。對依據時節而行的傳統民俗、口耳相傳的民諺民謠和民間故事的融入,蓋房喬遷、婚喪嫁娶、節日祈福等儀式活動與地方風俗的嵌入,大量“百科全書”式的地方性知識的注入,顯現出鄉村連接過往與當下的本土性、傳統性。
《寶水》忠實地還原了一個普通豫北山村的原貌,如實反映村莊根植于傳統的一面,與此同時,喬葉也通過細致的筆觸書寫寶水村一年之中的變化,耐心地講述鄉村的現代化發展與革新。老宅改建民宿、土特產制作與販賣方式的推陳出新、網絡視頻的營銷手段,揭示鄉村產業結構調整與生產方式變革。村干部依靠與鄉民的親緣關系來開展工作,靈活借助“村官”乃至上級領導的影響力,經由新聞傳播發揮名人效應,對內向村民進行政策宣講,對外向整個社會進行廣泛宣傳,引發輿論關注,傳播鄉村名氣,展現鄉村治理模式的現代化轉換。寶水村依托鄉賢文化與鄉土情懷建立城鄉鏈接,吸引精英人才返鄉,助力鄉村活力復蘇。在文教方面,寶水村吸收大學生志愿者入村開展支教活動,在他們的倡導與組織下,向村里的少年兒童普及生命意識教育、性教育和“萬物啟蒙”的新型教育理念模式。這都體現了新舊調和、交融的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發展。
結 語
《寶水》將個人情感故事、傳統的鄉土故事、新時代下的鄉村振興故事相糅合,從而兼具情感、現實、時代與政治的敘事意義。重識自我的個體敘事、互助群像的群體敘事與普泛存在的時代敘事結合在一起,由一個人、一群人上升到一代人,使小說的鄉土書寫具備普遍的社會意義和指導價值。過去鄉土敘事中“離鄉—還鄉—又離鄉”的經驗模式與心路歷程,轉變為“離鄉—還鄉—留鄉/建鄉”的新體驗、新方向、新出路,由曾經加劇失望、決意舍棄的悲劇性體驗記敘,轉向心靈療愈、精神激勵的充滿希望與可能的開放式展望,在對新鄉村的想象與書寫中,凸顯鄉村補足、療愈城市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淵源,發掘新鄉村在新時代背景下所煥發的原生力量。小說以由城市返鄉的療愈之旅作為發端,也更貼近當代都市人的心理癥候,更契合他們的精神困境、情感訴求和生存體驗,更具有針對性、具體性、實踐性的啟示意義。
在《寶水》的第一章第十五節里,青萍跟隨大英去挖茵陳,一開始“別說是茵陳,連別的一絲綠影兒都沒看見”,大英叮囑 :“走慢些,仔細看,啥都有。”“蹲下去貼地去瞧。”隨后青萍真的看見了茵陳、山韭和榆樹的小花。“回去的路上,再看周邊,滿眼里已經處處都是點滴的綠,許多干枝也滲出了隱隱綠意……當視覺的焦點和重心發生變化時,看到的東西居然能和之前如此不同。”[29]喬葉在創作談中特意提及這段描寫,“我把自認為的深意都埋在這些敘述中,希望讀者能夠讀到,也相信一定有人能夠讀到。”[30]
尋找茵陳這一件小事中所體現的因視角變化,體驗、認知與心態也都隨之而變的心路歷程,似作為小說的文眼,照應并指代著青萍在喪夫后會找到新的人生伴侶和情感歸屬。她在融入寶水之后理解并認同曾經排斥的鄉村倫理準則與生存經驗,與失去父親的痛苦、對奶奶和福田莊的埋怨與憤怒、詛咒奶奶的愧疚和解,最終得以療愈心病,揭示出離鄉的人在回歸鄉土后,不僅得到心靈療愈與歸屬,還擁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如獲新生這一主題。小說充分展現寶水村在現代化轉型中的向好發展,呈現新山鄉的新面貌,同時建立對鄉土、鄉村、鄉民、鄉風的重新認知。中國傳統鄉村正如“經冬不死,春時因陳根而生”[31]的茵陳一樣,依靠文化與情感的根基,憑借內在的精神力量與文化積淀,經受住現代化潮流的沖擊,在新時代鄉村現代化的驅動下進行社會轉型,萌發新的內生力,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1]喬葉.跑村和泡村[J].長篇小說選刊,2022(06).
[2][3][6][7][8][9][11][12][17][19][20][21][22][23][24][27][28][29][31]喬葉.寶水[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10,345,315,307,307,373,50,478,330,413,416,453,384,185,417,359,451,57,57.
[4]喬葉.皆為寶水[J].小說選刊,2022(10).
[5]邱其濛.新世紀轉型期女作家的“新鄉土敘事”[J].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04).
[10][美]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當代敘事學[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49.
[13][16][18][26][30]喬葉.寶水如鏡 照見此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05).
[14]劉勰.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4.
[15]謝喬羽,蔣述卓.《野望》的節氣美學[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03).
[25]周永康,陸林.鄉村共同體重建的社會學思考[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2).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