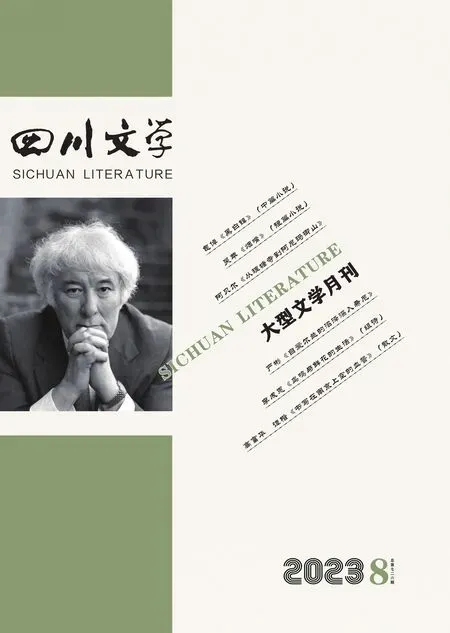胡萊的秋分
□文/龐驚濤
一
一大早,胡總照例在遇仙山莊巡視的時候,驚訝地發現荷塘正中嬌嬌出塵了一朵花蕾飽脹、盈盈欲放的荷花。
時令已過秋分,這個位于山莊中心位置的數畝荷塘中的荷花早就謝絕,綠翠如傘蓋的荷葉也大都有了頹敗之色,再過一段時間,就是一塘殘荷的意境了。這朵荷花卻在這個時候執意抽條蓄勢,在眾人不經意間長成了一個荷塘乃至一個度假山莊的焦點。
負責荷塘日常維護和管理的花工老趙也嘖嘖稱奇,連忙電話請教花卉協會的專家。專家說,此等泥中長出的花木,錯了季節和物候開花的也常有,不過秋分之后尚能觀荷,這對山莊來說到底是個好事,旅游業現在這么不景氣,這朵荷花不失為一個話題,對外好好宣傳一下,小概率如果做出大影響,說不定也能吸引一些游客。
胡總連忙用手機拍了幾張照片,發到朋友圈,并激動地用了一個“勾引”的手勢。發完朋友圈,他才反應過來,因為山莊相鄰的安置小區確診了一例陽性,這片區域在昨天就被列為中風險地區進行封控管理了。
微信發出不到五分鐘,住在畫家村的畫家沈白山打來電話。胡總連忙接了。還沒說話,沈白山的聲音就在電話里炸了出來,連一旁的趙工都被震住了:“你這朵荷花有點怪哦,人家都謝完了,它才開。”
胡總連忙應道:“沈老師,那你還不來畫幾張,作品的名字我都給你想好了,就叫秋分。”其實是明知故說,畫家村雖然在山莊所屬的城郊接合部有特殊地位,但還是一樣列為封控區域,任何人都出不來的。
沈白山道:“老胡,你倒是懂完了,我構思的畫面就是枯萎的荷葉和盛開的荷花在一起,熱烈與冷寂相對,繁華襯托落寞,黑白反噬粉彩,既是季節與氣候的陰差陽錯,也是人間萬象的陰陽顛倒。只是現在這個情況,只有等幾天解封后才能過來畫了。”
“幾天后?這個誰說得清楚,你曉得的,這荷花一開就謝,等你幾天后過來,怕只剩下冷寂和落寞了。”胡總惋惜道。
沈白山問:“老胡,你是不是有辦法?”
當著趙工的面,老胡只能說:“我能有什么辦法,我現在還不是跟你一樣,封控在山莊了。”他邊說邊往荷塘深處走,顯得若無其事但是其實有意避開了趙工,然后他壓低聲音對沈白山說:“老莫你認識吧?他現在在社區當領導了,昨天我看到他戴著個紅袖章,在各個小區和路口來來往往,指揮調度,這事找他或許有戲,反正你有每天都是陰性的核酸檢測證明。”
“我跟他不熟,要不,你幫我給他說說?”
胡總一口應了,反正關著無聊,沈白山能來山莊畫畫,既是個消遣,也是個宣傳。剛要掛斷電話,沈白山又補充了一句:“小羅也要來,她不在,我畫不好。”
小羅是沈白山去年才娶的“小”老婆,足足小他二十四歲,是他去美術學院上課時認識的崇拜者。自打娶進門,他就一時半刻也離不開她,沒有她在身邊,他畫畫通常沉不住氣,幾下起筆就會胡亂收尾,畫到最后更是經常打個大紅叉,撕了重來。
胡總沒好意思說多一個人多一份麻煩,也只好一口答應。
轉身,他就給老莫打電話。誰知電話剛通,就被老莫掐了,如是者三次,胡總就不打了,只在微信里給老莫留言,囑他幫忙把沈白山兩口子搞過來。
過了半個小時,老莫才回過來消息:“忙死了,晚上再說。”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七點,胡總估摸著老莫該吃完晚飯了,就打電話過去想問下他的態度,誰知老莫又是掐斷電話。不過這回很快回了個信息:莫催嘛,我正想辦法呢。
老莫有兩個音同字別的外號,其中一個是“莫吹”,因為大多數時候吹牛不打草稿和少數時候的辦事不力;另外一個是“莫催”,顯示他一貫大事臨頭不慌張的從容氣派。在胡總面前,老莫是“莫催”,生意人見官矮三級,雖然他只是個社區干部,但好歹有個副主任的頭銜,胡總經常用好煙好酒等小恩惠巴結著。這回為了幫沈白山夫婦“通關”,胡總明白一碼歸一碼,為求得個踏實,只好額外又補充了一句話:“明天過來的時候,順便到我辦公室拿兩瓶茅臺。”
不知道是兩瓶茅臺起了作用還是胡總催得恰到其時,晚上九點過,老莫給胡總打來電話,慢悠悠地給胡總說:“明早九點,我去接他們兩口子過來,你給他說一聲。”
二
沈白山內心是看不上老莫的。
什么具體原因,沈白山說不出來。或許就是藝術家和小干部天生的氣場不對,所以在一個轄區生活多年,低頭不見抬頭見,但他從不正面跟老莫說話。在胡總眼里,沈白山這種高雅藝術傍身的人,對老莫這種無一技之長的街頭混混怎么都好感不起來,即便老莫后來當了社區副主任,他也照樣不給好臉色,甚至于更增嫌惡,究其因,或許就是老莫身上體現出來的“莫吹”和“莫催”雙重人格。
而老莫對沈白山呢,也怎么都親近不起來。藝術家本來就不大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因此老莫也認定他不通世故,不過到底是一枚可以牽線搭橋的棋子,所以表現得便十分中性,既不“吹”,也不“催”,是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的態度。
門口候著沈白山夫婦和老莫,胡總連忙報喜說:“那荷花又打開一些了,真真是好看。”其實早上起來他還沒來得及去荷塘,但他仿佛已經看過了一樣,并且對這朵荷花的美全然有數,那夸張的表情好像一個夏天整個荷塘的荷花現在都還開著似的。
可誰都沒想到打臉來得如此快,四人走到荷塘邊時,荷塘中心那朵才有尖尖角的荷花卻不見了,入眼全是接天連葉的無窮碧綠。
“老胡,你這個玩笑開大了。”沈白山看著一臉驚詫的胡總,有些調侃,也有些埋怨,表情里是對他昨天“自導自演”的輕嘲。
老莫不等胡總解釋,忙出來打圓場,也是給自己帶沈白山夫婦過來找理由:“畫家嘛,不和農民一樣,幾天不下地就活不舒坦?沒了荷花,畫荷葉也是一樣的。我忙去了,改天再去你辦公室。”說完一徑走了,連招呼都不給沈白山夫婦打一個。
沈白山看著老莫的背影,沖胡總說了一句:“他懂個錘子,陰陽調和,天下至理,只有陰,沒有陽,畫出來就不是那個味了。”
在沈白山夫婦和老莫面前丟了面子,胡總心里很不是滋味,現在他腦子里盤旋的,全是一個個巨大的問號:這朵昨天都還開得好好的荷花,為什么一夜之間就不見了?究竟是誰那么心狠手辣,對這么一朵不能說話的花都要下此狠手?
他把趙工喊來,一頓劈頭蓋臉地訓斥。趙工看著“空蕩蕩”的荷塘和怒發沖冠的胡總,以及膩歪在一旁看笑話的沈白山夫婦,一臉的茫然懵懂之后,迅速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他脫下鞋子,挽起褲腿,踩進剛好淹沒腳踝的荷塘,分開荷葉,往荷塘中央深一腳淺一腳地尋去。
他躬身在荷塘里扒拉尋找了半天,卻生不見荷花、死不見荷花,不僅看不到半點荷花的花瓣,就連葉柄也遍尋不著,仿佛這朵荷花就從來沒在這荷塘生長過。
趙工上岸,垂頭喪氣地給胡總報告了這個消息。
“這也太邪了。”胡總坐在鄰近荷塘邊的咖啡座上,一言不發,沈白山稱奇道:“老天爺也要這荷塘一片陰,所以一朵陽也不行。”
此時,秋雨下得有些纏綿起來,小羅忙拖沈白山回到咖啡室。胡總叫趙工把封控在山莊的值班人員全部叫來,他決意要把這個摧花的辣手找出來。
看到這個場景,沈白山知道他們留在這里實在有些多余,于是索性給胡總打了個招呼,挽了小羅的手回畫家村。走之前,他不忘交代胡總:
“你昨天那條微信莫刪,照片還有用。有它作為基礎素材,加上我的想象,這個秋分陰陽的畫面我還是可以完成的。不過,我現在好奇的是,這朵妖艷的荷花究竟去了哪里?”
三
客房部、餐飲部、保安部等部門留守人員全部到齊了,胡總壓低了聲音,指著荷塘,恨恨地說:“老天爺好不容易照顧我們遇仙山莊,開了這么漂亮的一朵荷花,竟然被人活生生地給摘了。山莊就這么幾個人封控在這里,誰干的并不難查,自己坦白交代,免得查出來大家都難堪!”
客房部劉經理是個頗有幾分姿色的少婦,她心里對胡總抓小做大的管理很不了然,于是半開玩笑半認真地道:“不就一朵荷花嘛,胡總,用不著這么較真吧,明年夏天不又是一塘一塘地開了,誰還在乎……”
胡總不等她說完,就打斷了她半含撒嬌半逞媚態的話:“我胡萊可是要面子的,客都請來了,你招呼都不打一聲,就自作主張把席撤了,你說我在不在乎?”
劉經理碰了一鼻子灰,明白胡總今天是不查清楚不收兵的架勢,便不再吭聲,埋了頭耍手機,以掩飾剛才的尬局。
眼見最為受寵的劉經理都碰了胡總一鼻子灰,剩下幾個干脆都傻站著。胡總沒奈何,心想只有祭出撒手锏了。
于是他開始懸賞:“哪個發現有重要的線索,這個月獎金加一倍。”
保安部平時最是看不慣客房部和餐飲部的人油水多、居高臨下的氣勢,此時值班的小保安王權率先向胡總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我昨晚八點巡邏的時候,看到客房部二樓靠里那間客房有燈光。”
正在耍手機的劉經理一個激靈,連忙黑了屏,故作鎮靜地回答道:“我例行檢查一下房間不行啊,難道我該摸黑進去,神經病。”
王權卻沒有就此收兵的跡象,看他猶豫了幾秒,又扔出來一句:“早上從后門出去的一對中年夫婦是誰?我可是看著他們從客房里出來的,有人還給他們送了一口袋的牛奶面包。”
胡總威嚴的眼光掃過來,劉經理已經感受到了一種威壓,她明白,繼續裝傻風險太大,自己無論如何無法搪塞了,舍卒保車是她目前唯一的出路,于是她迎向胡總冷酷的眼光,坦白道:“對不起,胡總,我確實收了兩個老鄉住店,他們出差三天了,住不到酒店,也是沒辦法,才找到我的。”
“你收了他們多少錢?”胡總問。
“非常時期,他們也理解,比掛牌價多收了五百元。但多的,我原計劃全面復工后上繳。”自知理虧,劉經理的頭埋得更深了。
“你膽子不小,不僅隱瞞賬目,還敢在非常時期帶人住店。劉經理,你想過沒有,這是違法行為啊,萬一帶進來個陽性,我們大家跟著遭殃。”胡總恨恨道。
劉經理想轉移話題,于是辯白道:“不過胡總你放心,他們絕對沒有時間和心思去荷塘摘那朵荷花,我可是把他們接進來又送出去的,全程都沒有離開過。不過要說到山莊昨天進人的事,餐飲部昨晚也有嫌疑。”
胡總忙將目光轉向餐飲部經理邵爭:“不是說了嗎,天王老子都不接待,你們把防疫政策當耳旁風啊?!”
邵爭明白辯解無益,索性坦白交代:“我錯了,胡總,我舅舅他們住隔壁安置小區,昨天沒搶到菜,擔心封控久了挨餓,昨晚我給他們拿了一些,菜錢我一定如數上交。至于那朵荷花,我以人格擔保,他們壓根就不知道荷塘里還有荷花在開這回事。”
幾個人攻來攻去,還是沒有眉目。胡總不甘心,問王權:“你們平時怎么監控的,連餐飲部有人來拿菜都不知道?”
王權告訴胡總,山莊的監控點位都是按照保安部當時的設計安裝的,不排除他們有意避開了監控點,至于荷塘,四角都有攝像頭,處于荷塘中央的那朵荷花究竟是誰摘的,相信攝像頭能監控得到。
于是胡總命令王權,盡快把監控調出來,他要抓出那個摧花的辣手狂魔,也替萎靡不振的山莊經濟出口惡氣。
四
胡總山莊所在的區域,是這個城市的城郊接合部,混雜著未拆遷的原住村民、農家樂和安置小區,地理環境復雜,經營業態交纏,居住人口混雜,很難做到規范化封控。街道和社區限于標準化封控需要的投資過大、戰線過長等因素,因此封控初期也沒有任何有效措施。
作為片區中高檔水準的農家樂,遇仙山莊一直以來都是街道和社區經濟活躍的命脈所系,上上下下對山莊多少都有些優待,起因自然是上上下下多少都能從山莊得到一些好處。那朵荷花開出來的前兩日,隨著封控的風聲日緊,胡總已做好關門歇業的準備。可是金九銀十的旺季,他哪里甘心就這樣坐以待斃呢,仗著地利人和,在天時不允的環境下爭取一個活口子,這就是他全部的心思。那朵荷花的錯季開放,更像是對他這個想法的成全和助力,這就看得出他為什么對那朵荷花的出現和消失如此上心了。
胡總的山莊也不是沒有競爭者,相鄰的八條山莊生意后來居上,據說憑借的除了餐飲口碑,還有比胡總更可靠的后臺支持。說起八條名字的得來,老板辛六連忙解釋“跟麻將無關”,其實來源于國畫傳統里的九鯉圖。鯉魚躍龍門,這是吉兆,而八這個數字呢,在做生意的人看來,諧音發財,也是吉祥的,兩吉加持,所以便選了這個名字,另外一方面,也是回歸他早年做河鮮的本行。八條的經營面積雖然沒有胡總的山莊大,但更精致。由于彼此的停車場相鄰,休閑食客每每將兩家搞混,車輛出入穿插于兩個山莊是常有的事。辛六心眼小,為了保持獨立性,后來干脆在兩家之間扎起一道竹籬笆,兩家才真的井水不犯河水了。
辛六和胡總一直保持著面子上的同聲相應,內心里對胡總經營上的長袖善舞、局面大開不大了然。一聲封控令下,兩家一起歸零,看上去大家都是平等地關門歇業,但暗地里誰沒個小九九,幾乎是在胡總找老莫的同時,辛六也打起了小心思,找老莫探口風。
胡總微信里曬那朵荷花的時候,辛六內心里是生起過嘲笑的,可當他知道老莫要幫胡總帶畫家沈白山去畫畫時,他猛然發現自己實在有些淺陋和幼稚了,比起無時無刻不在想法子找路子搭梯子的胡總來,這一次他辛六比胡總確實慢了半拍。
“不就一朵荷花么?未必他還能還出一個夏天來?”微信里,辛六對胡總的陰施倒陽大為不然。
“你懂個錘子!”老莫回給他一個粗口,語氣卻是很友情的。“他托我帶沈白癡兩口子去畫畫。你曉得的,白癡的朋友不少,那絕對是個很好的宣傳!”
“那你幫我也帶幾個人來啊!”辛六不平道。
“八條又沒球得荷花看,哪個來嘛?”老莫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一朵荷花,還整成金包卵了?我明年也挖個荷塘種上荷花,看誰開得過誰!”辛六恨恨道。
“你啊,遲了,還是想想眼面前的法子吧!”老莫回完辛六這條信息,正準備收住話頭,不料辛六卻把電話打過來了:“聽說他的山莊還在偷偷住人?”
老莫心想,狗日的消息靈通呢,怎么知道劉經理瞞著胡總偷偷找他帶人住店的事情?于是打了個馬虎眼:“不曉得呢?他那個山莊要偷偷溜人進去也容易,管不了的地方那就只有隨其自然了。”
“莫主任,我敢打賭,他那絕對還會有動靜,要不,你幫我關注一下,我也學學?”
辛六的小心思,老莫是懂的,只是他不好有明確的態度,于是不知可否地說了個“再說嘛”,就掛掉了電話。
五
王權在監控室眼睛都不眨地快進和慢倒折騰了幾個小時,最后還是一無所獲。
他看到了鏡頭里按時巡邏的自己,也看到了劉經理帶進來的住店夫婦。此外,大多時候,監控里是隨時間和天氣變化的天色。
那朵荷花雖然隔了很遠的距離,但他依然能清楚地看見:有時候它靜若處子,有時候它又迎風擺動,身姿動人。王權注意到,監控鏡頭下的荷花,有一種朦朧的美,是超越了眼面前所見和花瓶中偶爾目及的。
他沒有放過監控中的一分一秒,像等待一個美人兒突然進入鏡頭,以至于他有一陣老是懷疑自己是看花了眼,又不得不反復倒回去重看。最后,他確認沒有任何線索,便給胡總打了電話。
胡總從客房部留給他的房間走過荷塘時,下意識又看了一眼荷塘:除了越來越陰沉衰敗的荷葉,荷塘中央什么奇跡都沒有出現。夏天的陽光、荷花的陽光真的過去了。
王權問胡總:“要不要再親自看一下監控?”
胡總搖了搖手:“算了,我相信你。”
看來查監控這事只能到此為止了,王權向胡總表示,他會再去找線索,一定要找到摧殘荷花的“兇手”。
“王權,你是不是隱瞞了什么?”胡總要離開監控室前,意味深長地問了一句。
“沒有啊,胡總。”王權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提示你一下,你最近是不是耍女朋友了?”胡總忽然笑瞇瞇地看著王權。王權一下恍然大悟的樣子,于是承認道:“我確實和八條的春花在耍朋友,但她這幾天都沒有來過,根本不可能來偷摘荷花!”
“我指的不是這個。你耍朋友我不反對,但是,山莊的任何經營動態和信息,你以后不準講給她聽,明白嗎?”
昨晚,劉經理向胡總打小報告,說了王權跟八條的服務員春花耍朋友的事情。競爭對手之間,這種關系非常微妙,劉經理提醒胡總的目的,是希望胡總在一氣之下炒了王權的魷魚,以報她被王權當面告密的仇。
但胡總有胡總的考量。他決定利用春花,打探八條的消息,于是,他索性借機點撥了王權一下:“當然,你女朋友可以多了解一下八條的情況,將來到山莊一起工作也是可以的。我們私營企業,不搞避嫌那套。”
王權一瞬間領會胡總的意圖,于是連連點頭,極度服從的樣子。
胡總繼續提示道:“尤其是封控期間,注意他們搞小動作。”
王權借機邀功道:“我聽春花說,他們辛總這幾天老是請老莫去吃飯。”
“老莫嘛,就那德行。”胡總雖然心知自己的小恩小惠買不斷老莫的絕對“忠誠”,但聽到王權的消息,他還是隱隱不爽。看來對老莫,他還得留一手。他不知道老莫是否幫八條帶了人,或者,幫八條疏通了上面,偷偷為八條開經營的口子,但他明白,王權提供的這個信息實在太及時太重要了。
“胡總,這封控的時間萬一拖得太長,我們是不是也找老莫想想辦法,帶點人來?”
“你以為人就那么好帶,再說了,風險太大了,一旦進來個陽的,大家跟著遭。”胡總對王權的討好并不買賬,他覺得王權在經營上出點子,是越界了,這不是一個保安應該操心的事情。但王權的話最后還是點醒了他,讓他決定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他貼耳對王權說:“這幾天八條如果有人聚餐,就讓你女朋友拍下來傳給我,明白了?”
王權心領神會,點頭如儀。眼看胡總要離開,于是不忘請示道:“荷花那事,還查不查?”
“查,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胡總毫不猶豫地吩咐道,那語氣倒不像是給王權說的,而是說給他自己的。
六
封控狀態下無所事事的三天,熬得像是漫長的三年。到第四天,胡總實在覺得無聊,就打電話給老莫說,他準備帶些凍庫里的肉菜,去畫家村看幾個畫家朋友。
“想都別想!”老莫果斷地拒絕了他:“上級批評我們這個片區管控得太松,要求從嚴,商戶和安置小區之間馬上要安裝鐵皮護欄了,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待著,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
王權提供八條的情報沒什么新變化,荷花被摘的事,查來查去也沒什么新的進展,連胡總都覺得每天問王權有些多余。所有人最大的困擾變成了在不可預知的漫長封控狀態下如何安頓肉體和消遣精神,至于有沒有生意做,已經退居其次。
下午胡總正準備午睡,老莫突然打來電話,說安置小區的十多個家長托他把關在家里的“神獸”送到山莊的圖書館來,管個三餐,再安排個服務員看守著,每天每人50塊錢,問胡總愿不愿意?
胡總反問老莫:“你咋不往八條帶?”
老莫恭維道:“方圓幾里范圍,不是只有你胡總有個書店嗎?再說,他那里隔三岔五還得管社區干部和志愿者的伙食,動靜太大了也不好。”
十多個學生娃和社區干部、志愿者,哪頭的肉最有油水,胡總還是清楚的,可此時他失了比較和嫌隙的動能,現在,他心下雖然是愿意的,可電話里還是要故作試探地忸怩一番:“這樣做不犯錯?”
老莫作為“莫吹”的氣質一下子就流露出來了:“犯錯賴我行不?”
胡總借坡下驢,答應了,回頭把每天照顧學生們伙食和日常監護的工作安排給了劉經理。路過荷塘的時候,他發現其實那朵荷花在與不在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可胡總剛準備放下誰摘了荷花這事,王權卻向他報告了一個重要線索,其實也不是線索,是王權忽略了一個細節,其實也不是細節,是當天的一個意外。
這個意外就是封控的頭一天,山莊所在的片區在下午6點到8點之間停了兩個小時的電。
“你檢查監控的時候就沒注意到?現在才告訴我?”胡總很生氣,他忘了他其實也知道山莊停電這回事,甚至,所有封控在山莊的人應該都知道停電這回事。所以,當王權居然理直氣壯地拿這個頂他的時候,他竟然無言以對。
“那就是說,很有可能,這個人是利用停電這兩個小時來作的案?”胡總故意把“作案”這兩個字說得很重,此刻,他懸停了幾個小時的追查興致又被重新吊起來,而且這個興致甚至是刺激,在隨著他和王權的大眼瞪小眼吊得越來越高。“這太好玩了,一朵荷花,值得他這么處心積慮、大費周章?”
王權似乎也被胡總的情緒感染,他對胡總說:“這個人很有可能是內鬼!”
“你又沒證據,可不能亂說。”胡總嚴肅地看著王權,一轉念,他又問,“你覺得誰最有可能?”
“趙工啊!”王權幾乎毫不猶豫地說。
“說說你的理由。”胡總的興致越來越高了。
“胡總你看啊,他是八條跳槽過來的對不對?雖然三年了,但誰知道他跟辛六有沒有私下交流?”王權的興致似乎比胡總還高,保安隊長不在山莊,這幾天他幾乎成了胡總的貼身保鏢,他有一種被重用的向往和期待,加之胡總全權委托他追查荷花被摘這個“案件”,又把女朋友發展成了打入八條的內線,他沒有理由不感到受器重。這種備受器重的感覺,讓他可以在此時隨意懷疑山莊的任何人,不管他是老員工,還是部門經理,甚至是胡總的相好。“再說,趙工最清楚山莊花卉草木的生長狀態,也掌握每個員工的生活規律。”
“動機,他這么做的動機是什么呢?”胡總百思不得其解。
“老話不是說,恨人富怨人窮,不許人家的花比我家的紅。他幫辛六搞掉山莊的吉祥之花,可不是幫辛六出了口氣?”王權覺得自己的分析實在不亞于辦案的警察,說完之后討賞一般看著胡總。
“你娃是不是想多了?”胡總猶疑不定地看著王權,幾乎有五秒鐘,兩個人就這么對視著。最后,他向王權發號施令:“這幾天你盯著他一點。”
七
第二天,老莫分三批把十多個學生娃帶到了山莊。
離開山莊之前,他對胡總說:“現在生意難做,萬一要打持久戰,你這十多間客房,干脆就近做隔離酒店算了。”
“聽你這口氣,似乎還要封下去?”胡總有些忐忑,一面盤算著做隔離酒店的收入能不能應付日常的水電氣和人工開支。
“你都是老江湖了,隨機應變吧。”老莫邊往外走邊說,“沈白癡的畫還沒畫出來?我還等著看呢。我不相信,一朵荷花,他能畫出天仙來!”
胡總知道他們兩人不對付,連忙打圓場:“你還別說,按他的構思,真要畫出來,說不定可以跟莫奈的名畫媲美!”
“誰?摸奶!”老莫笑了,“我就知道狗日的沈白癡不正經,不然五十多歲了怎么找個二十多歲的黃花大閨女。胡總,我勸你一句,這沈白癡也畫不出什么天仙來,別把他當神仙供著。”
胡總也笑了,笑得幾乎收不住。莫奈跟摸奶有球關系啊,老莫這樣張冠李戴,太好玩了。
送走老莫,王權來了,向他展示女朋友傳來的三張微信圖片。圖片里,一些人在八條的餐廳胡吃海喝,胡總沒有留意的是:這三張照片上其實都沒有看見老莫。
“膽子太大了嘛!”王權添油加醋地說。
胡總沉思有頃,終于下定決心一般對王權說:“你把這三張照片傳到網上去,再打個12345,讓他辛六吃不了兜著走!”
王權一下慌了神:“胡總,萬一他們曉得是我們干的呢?”
“沒有直接證據,他們即便懷疑,也拿你沒辦法。你放心,你女朋友隨時可以過來上班。”胡總的話讓王權終于吃了一顆定心丸,他下定決心,用山莊的座機去打12345。
八
胡總剛回到房間,趙工來了。
“我有個情況給胡總反映。”趙工說。
胡總想,未必他要投案自首?胡總想起這幾天追查荷花被摘“案件”的起伏與轉折,真心覺得這太有意思了。現在,究竟是誰摘的荷花,終于要水落石出了。
“封控頭一天,王權脫崗了有好幾個小時。”趙工猶豫了一下,還是勇敢地說出來了,這讓期待是他投案自首的胡總大感意外。
“你咋曉得的?”胡總問道。
“我親眼看到的,山莊一停電,他就從山莊跟八條之間的一條隱秘通道過去找春花了。晚上九點過我才見他回來。”趙工說。
“人家耍朋友,也正常嘛。”胡總松了口氣,為趙工的小題大做大為不滿,準備就此打發他。
“問題是,這幾個小時,山莊進進出出了哪些人,就沒人監控了,說不定就給人鉆了空子,來摘了這朵荷花!”趙工的話,將胡總的興致又吊了起來。他明白,趙工來反映情況,是想向胡總表明,他絕沒有摘荷花的動機和條件。
“大家都在封控期,還有鬼大爺進來啊!”胡總對趙工說,“如今你說這些有啥用?王權不在,停電那兩個小時,即便有人進來,也沒有人發現了。”
趙工聽出胡總的口氣,是不打算追究王權脫崗的責任。但他不想失去證明自己的機會,或者說提供線索的機會:“胡總,我還真看到有人進來。”
胡總一個激靈,坐正了身姿,問道:“你看見誰了?”
趙工說,吃完晚飯,他閑得無聊,就去保安室找王權閑聊,結果看到王權從保安室出來,順著竹籬笆中間的一個小洞,拐進了八條。他心下還在嘲笑王權:“狗日王權食髓知味,又去偷腥了。”然后,他進了保安室,臥在一張已經千瘡百孔的沙發上看電視。天還未黑透之前,他看見一個人氣宇軒昂地閃進了山莊,從背影里,他一眼就看出來那個人是誰。
他拿出胡總的左手,在他的掌心里寫下了一個字。
九
胡總被山莊臨馬路邊的喧鬧聲吵醒時,已經是封控第七天的上午九點過了。
透過客房的落地玻璃,他看到一輛警車,后面跟著幾輛魚貫尾隨的大巴,它們都打著應急燈。警車和一輛大巴上,陸續下來無數個大白,很快便站滿了臨近山莊的馬路。
他被這一幕震撼到了。
他意識到王權昨天的匿名舉報發揮作用了,但看到這個大場面,他不禁為自己的“下作”感到羞愧,同時也為八條不可預知的“命運”感到擔心。
打敗對手理應讓他高興,但他現在的感覺是驚懼。
他正準備打電話給王權,王權卻心急火燎地闖了進來:“胡總,不好了,我們收學生娃的事情被人舉報了。”
六神無主的胡總被劉經理和王權簇擁著,一路小跑著奔向山莊大門。他看見老莫正帶著一群大白走向山莊,后面,還跟著幾個警察。
不知道什么時候,劉經理把剛剛到圖書館的十一個學生也帶了出來。
老莫看也不看胡總,而是對著劉經理大聲指揮:“所有人,全部上大巴,集中隔離。”
后面一個警察走過來,大聲問:“哪個是山莊的老板?”
胡總連忙上前:“我是!”
“給你十分鐘收拾東西,跟我走,其余人,聽社區的統一調度。”
胡總聽到趙工在問老莫:“莫主任,發生啥子事了?”
老莫一副居高臨下的口吻:“發生啥子事了?就是你們不聽招呼,這里發現了兩例陽性,這下安逸了?”
十
胡總回身往客房走的時候,下意識地又看了一眼荷塘。他驚訝地發現,荷塘中心又有了一朵鮮艷綻放的荷花,不對,不是一朵,而是三朵,它們高低錯落地開放在荷塘的中央。
這三朵荷花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打開了花瓣,淺粉帶紅的顏色,煞是好看。胡總似乎看到它們中心還有未散盡的露珠,他一下子呆住了。
胡總揉了揉眼睛,發現這三朵荷花雖然開得艷麗,但它們開放的整齊劃一和由粉到紅的層次實在有些詭異,他總覺得有哪里不對,但是一時又說不上來不對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