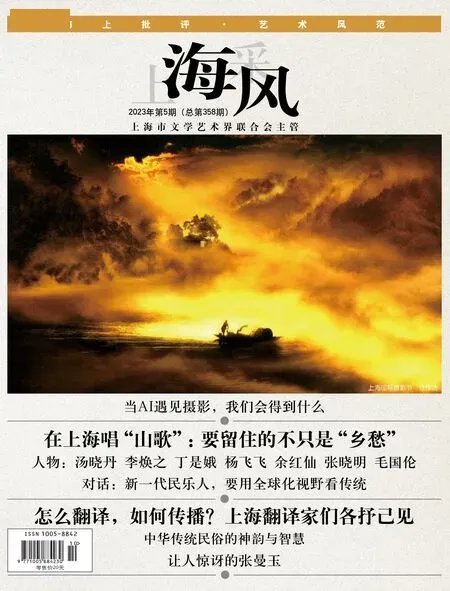尊古開今 守正創新
——毛國倫、毛冬華父女求藝之道
■ 馬信芳
1960年秋,上海大同中學高二學生毛國倫迎來幸福的一天,剛成立的上海中國畫院在全上海招收五名學生,毛國倫幸運地成為其中一位,自此開啟了他的求藝生涯。
圓丹青夢,鑄筆墨魂
毛國倫,浙江奉化人,1944年生于上海。雖然家里沒有人從事過文藝這一行,可他自小就愛畫畫,癡迷地做著丹青夢。在那個沒有電視節目的年代,他從香煙牌子、小人書中了解武松、楊家將、諸葛亮和岳飛等歷史人物,甚至夜里打著手電筒在被窩里看歷史小說,如癡如醉。一開始他是照本臨摹,受到了鄰居們的夸獎,興趣倍增。那時,劉繼卣的《武松打虎》、劉旦宅的《木蘭辭》和程十發的《畫皮》,是他最喜愛的連環畫。
家住老城廂小西門的毛國倫,最愛去文廟和老城隍廟,那里有許多他喜歡的畫。1950年代初,第一屆南市區國畫展在文廟舉行,他省下零用錢,竟買票連看三場。老城隍廟里有不少賣畫的店,他時常目不轉睛地欣賞櫥窗里陳列的畫。后來,他開始即興創作,并嘗試投稿了。1958年6月1日,他的《快馬加鞭日千里》竟上了《解放日報》的“兒童畫專刊”。畫作雖稚嫩,但處女作的發表無疑給了他極大的鼓舞,令他在求藝道上加快了腳步。
大同中學有位教美術的張文祺老師,發現學校里有不少可培養的美術苗子,便組織起美工組,毛國倫是其中一員。老師的用心、學生的努力,讓美工組大出風頭,學生的畫作在市里畫展中連連獲獎,引起了上海《青年報》的重視,專門撰文作了報道。也許是這個原因,當上海中國畫院正式成立急需培養新人時,招聘人員按圖索驥來到大同中學,一眼相中毛國倫。于是,他成為上海中國畫院的第一批學生。
1960年12月29日晚上,汾陽路150號上海中國畫院二樓的大廳里舉行了拜師儀式。時任上海市文化局領導方行、畫院院長豐子愷,以及文藝界近兩百位嘉賓到會。毛國倫和陸一飛、邱陶峰、吳玉梅、汪大文等首批學員分別站在吳湖帆、賀天健、唐云、樊少云、程十發老師面前。儀式由時任畫院黨支部書記、副院長湯增桐主持。
上海中國畫院1956年籌建時聘請有69位專職和兼職畫師,平均年齡超過63歲,且每年時有畫師謝世。為了使這些老畫師的技藝后繼有人,畫院參照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的教學方法,同時結合中國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模式,為學生制定了“五寫”的國畫教學方法:臨寫、寫生、速寫、默寫、寫字。還要學生學古文詩詞,并且開設山水、花鳥、人物、篆刻等課目,讓學生能夠全面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
初學階段,老師安排臨摹北宋李公麟的《五馬圖》和《八十七神仙卷》、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孫位的《高逸圖》以及明陳洪綬的《歸去來圖卷》《隱居十六觀》等。除了這些指定內容,凡在畫院資料室看到中意且能借到的畫作,毛國倫都會借來臨摹一遍。三年的臨摹,讓他打下了筆底功夫,這正是日后他創作中國畫的筆墨基礎。
毛國倫并不亦步亦趨。他感到臨寫的內容,在唐宋元那些畫風較為嚴謹工整的作品之外,還可以加入明清的寫意畫和大寫意的作品,這樣更能鍛煉用墨、用筆、用水的技藝和寫意的膽魄。這也使得他日后的作品能含精微于奔放之中。

毛國倫作品《歡樂歌》
要對中國畫的特征、特色與創作理念加深理解,學習中國古代的畫論極為重要。南齊謝赫的“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經營位置、隨類賦彩、傳移模寫”的六法,東晉顧愷之的“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的妙論,南朝宋宗炳說的“以形媚道”,唐代張彥遠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以及司空圖說的“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還有宋代歐陽修所云“忘形得意”……毛國倫認真學習,細細體會,并一一運用到他的創作中。
除了課堂學習,畫院每年安排學生兩次去工廠、農村參加勞動,并展開寫生、速寫和創作活動。1964年,赴寶山縣羅店公社深入生活后,毛國倫和來楚生先生合作了人物畫《雙生犢》,這幅畫入選第四屆全國美術展覽,后被上海美術館收藏。這是毛國倫進畫院后一次成功的創作實踐,讓他至今不能忘懷。
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毛國倫拜的是樊少云、程十發兩位老師。請樊少云做導師是程十發提議的。樊少云(1885—1962)字浩霖,上海崇明人,他是晚清畫壇名家陸廉夫的學生,兼擅山水、花鳥、人物。他善于用羊毫筆在生紙上作畫,表現出山水滋潤渾厚的效果。可惜樊少云先生只教了兩年便仙逝了。所以,程十發足足當了毛國倫47年的老師。
發老離世已經16載,談起自己的老師,毛國倫唏噓之余,依然感激不盡。
他清楚記得,拜師第二天,程十發先生就講了中國古代兩個畫院學生及他們作品的故事:一是五代南唐畫院學生趙幹的《江行初雪圖》,二是北宋畫院學生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這兩幅畫被稱之為千古絕唱。很明顯,這是老師借題向學生提出的努力方向。毛國倫心領神會,決心不負老師期望,努力攀登畫壇的“珠穆朗瑪峰”。
程十發的教學,貫穿在他的言傳身教中。他對祖國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抱著非常虔誠、敬畏之心,對古代的優秀藝術品和繪畫作品的面貌、特點如數家珍。在教學上,則通常是根據學生學習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授業方式。平時,他大多是平和地啟發,點到為止,而必要時,他也會及時棒喝,使人猛醒。
每次檢查作業,程十發都會從一整疊作業中挑出幾幅比較好的給予講評,甚至曾親自為學生補筆、修改——
1963年,老師發覺毛國倫畫的一幅《走遍山村》中有個年長的貨郎少了一條腿,畫中毛驢的眼睛周圍也沒有留白,就親自動手為之補上,還在毛驢的眼睛周圍加上了白色。
1978年,老師看到毛國倫畫的《祖沖之》,高興地說:“恰到好處。”
1983年,毛國倫從長江三峽深入生活回來后,創作了兩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彩色連環畫《秭歸》《巫山神女》。老師翻閱后,只說了一句:“不容易。”
1992年,蘇州古吳軒出版了毛國倫的第一本個人畫冊《毛國倫畫選》。老師看了之后,指著畫冊中的一幅《達摩圖》說:“這張不錯。”
印象特別深的,是當老師發現毛國倫某一個階段的人物畫用筆拘謹、畏縮,不由大聲地對他說:“小毛,你要吃一個老虎膽,壯壯膽了!”一聲棒喝,頓時把他叫醒。
“程家樣”是程十發先生獨創的繪畫藝術。老師的繪畫之道也成了程門弟子毛國倫極寶貴的財富。
1950年代,中國繪畫藝術面臨新時代“轉型”的課題:如何繼承傳統藝術之精粹,并表現出藝術個性和情感。這時的程十發已創作了大量有影響的連環畫,令畫壇刮目相看。但他心里明白,他的藝術還沒有抵達他所夢想的自由之境。
1957年春,程十發隨文化部組織的美術工作團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寫生。他發現,云南少數民族的服飾特別適宜用中國寫意畫瀟灑多變的筆墨線條來表現,這不僅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藝術個性和才情,同時又符合表現新中國生活的要求。
程十發先生說了他首次用國畫手法創作的《召樹屯》:
在一次晚會上,一個端莊秀麗的芒市小學的女學生進入我的眼簾,她的形象正符合我創作《召樹屯》連環畫中孔雀公主的模樣,我就請她當模特兒,并在這基礎上加以想象和夸張。
從創作《召樹屯》以后,我感到中國畫和西洋畫的構圖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便不再拘泥于解剖、透視的束縛,而設法表現我從生活中感受到的意境,也注意到如何渲染和夸張形象等問題。
這時,一首幽婉的民歌竟讓我癡迷:“月亮出來亮旺旺,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我聽著,哼唱著,一種用靈魂來演繹的愛情絕響和用生命來詮釋的曠世戀歌的感覺油然而生。
1959年10月的一個晚上,程十發聽著歌,欣然揮毫,如有神助……一個戴著斗笠,挑著擔子和陶罐蹚過小溪的傣族姑娘,怕水沾濕裙子,回頭用手輕輕拎起裙擺,栩栩如生,躍上畫面。這就是后來讓人過目難忘的佳作《小河淌水》。就這樣,程十發找到了表達自己真性情和真筆墨的自由之境。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人物畫《小河淌水》,正式宣告其獨創的“程家樣”繪畫藝術的問世。他開拓的少數民族題材作品在畫壇一炮打響,成為當代中國畫的一大流派。
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程家樣”藝術得到了打造與提升。“文革”結束后,程十發迎來了第二個春天,創作熱情空前釋放,藝術理念也日趨開放。一批人物畫的精品力作問世,如《橘頌》《禮忠魂》《東坡撥琴圖》《鐘馗嫁妹》《游園驚夢》《金玉滿堂》等。這批畫標志著“程家樣”繪畫藝術的最終確立。
程十發的繪畫藝術,是打破古今中外藝術的鴻溝而深深植根于民族藝術審美的產物,是人物畫壇聳起的一座別樣高峰。毛國倫從老師的身上感受到了大時代的脈動。在以后的幾十年中,毛國倫也用這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描繪他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美好事物,創作了《小站新風》《游春圖》《晚晴圖》《歡樂歌》《苗家歡歌》《苗寨嫁女》《草原輕騎》等一批受歡迎的作品。
以形寫神,以神寫形
毛國倫是上海中國畫院的一級畫師。賞讀他的人物畫作品,那種隨意揮灑的筆觸,常常讓我們有一種“畫得毫不費力”的錯覺。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當他談論自己畫作時,我們發現,在看似逍遙的筆墨背后,卻別有一番辛苦。
“人人都可以走出一條路來,但這條路你不能忘記中國的筆墨傳統。”毛國倫一直謹記著老師程十發的教導:筆墨筆墨,筆中有墨,墨中有筆。民族繪畫的結晶是筆法,筆墨是中國畫民族性的根本。無論現今的畫壇如何日新月異,對筆墨傳統的傳承是萬萬不可丟棄的。
毛國倫的人物畫承襲了程十發描寫生動的特點,而有意識地弱化了老師筆墨上的大開大合。毛國倫的畫中對比強烈的線條和墨塊并不多見,更多的是依靠熟練飛動的線條構形搭物,支撐畫面,加上他擅長的空白背景處理,使得畫面在寫實之余,又多了一份輕靈的動感。他的人物畫近來越發趨向于清新明快、筆墨暢達的境界,這是他數十年繪畫功力積累水到渠成的結果。

毛國倫作品《游春圖》
毛國倫的人物畫大致可分三部分:古代圣賢名士、戲曲人物和現代人物。
從諸葛亮到王羲之,從杜甫到李清照,無不形象生動,而如諸葛亮之閑定、王羲之的灑脫、杜甫之憂思、李清照的浪漫,都在他的畫中巧妙直觀地得到體現。平時,毛國倫手不釋卷,讀老莊經典,背禪語偈句,頌唐詩宋詞……雖不求甚解,但每有會心,便把這種感受融入畫作,題上紙面。
理性地對待繪畫,嚴肅地對待創作,是毛國倫一貫的藝術態度。他對中國人物畫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不管藝術家有怎樣的理念、怎樣的觀點,都必須以自己的繪畫實踐體現出來,只有以實踐為基礎的理論才能令人信服,而中國畫理論的最直接載體就是筆墨。
如他的《孔子》《岳飛——池州翠微亭詩意》《諸葛亮》等人物畫作品著意于筆墨意趣的闡發,而這種意趣絕不是憑空無依或者純粹地玩弄技巧,它是緊緊依附于物象的表達。
敦厚樸實的毛國倫早期畫風嚴謹寫實,亦能于筆墨間抓住人物的姿態和表情,以形寫神。而在近年的創作實踐中,他有意更加主動地將書法筆意摻入畫面,在人物畫的線條處理上使之更具有書法的意味。抑揚頓挫間起承轉合,勾搭呼應,筆勢流轉,有一氣呵成的痛快感,令人蕩氣回腸。尤其是他的寫意戲曲人物畫,如《宇宙鋒》《斷橋》《齊天大圣》等,不僅將角色的動作姿態刻畫得惟妙惟肖,就連他們的身份、性格及情狀,也躍然紙上,這庶幾稱得上是以神寫形了。
為此,饒宗頤大師看了毛國倫的畫,不由在香港的報紙上撰文《筆墨性情 大家風范》,其中寫道:“毛國倫先生十分尊重中國寫意畫的審美傳統,他能以一種灑脫不羈的筆墨傳達出一種精妙入微的精神,筆墨的張力被他舒展到了一個無限寬廣的境界,這是一種大手筆傳達出來的大氣魄。”“先生對傳統中國寫意畫的造詣頗深,他的線條運用得非常精彩,他能深刻地體察到畫面意境中的線條運動,且將它賦予了一種詩化的處理,使其韻律感十足,神采飛揚處,情致德操盡顯其中,以有形的筆墨傳達出無形的內在精氣。”
薪火相傳,筆墨傳承
1971年12月,毛家喜事降臨,女兒毛冬華出生了。現在已是上海美術學院副院長的毛冬華接受筆者采訪時回憶道,作為出生在這個畫家家庭的獨生女兒,父親沒有放任自流,而是引導她對繪畫產生興趣,努力將其培養成有用的人才。
對此父親毛國倫沒有否定。他補充道,當時自己也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大概是女兒兩三歲時,一天,他用毛筆畫了一面紅旗的輪廓,讓女兒在線條里面涂紅色。毛冬華像模像樣還真完成了。夫婦倆嘖嘖稱贊女兒:“筆握得真好!”被表揚的毛冬華喜笑顏開。
自此毛冬華的藝術啟蒙之路開始了。父親讓女兒臨摹連環圖畫,《草原英雄小姐妹》《楊門女將》等小人書,她看得很起勁,畫得也認真。后來便逐漸進入實物寫生。九歲時,她速寫一個放在桌上的梭子蟹,畫得生動且細致。當她被稱贊時,高興之情溢于言表。她對畫畫越發熱愛了。此外,書法也列入了她的課程。一本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她足足寫了六年,后來在此基礎上又學魏碑。
自然,報考上海美術學院附中成為毛冬華努力的目標。在父親的傳授下,她在中國畫的白描勾線、寫實能力等方面,已經有了一點基礎。然而,學校要考的是用明暗方法處理的素描和水粉畫一類,她從沒學過,無疑敗下陣來。但毛冬華并不氣餒,開始全身心地補學素描和色彩。每天上下午加晚上的素描和水粉畫課,不管風霜雨雪,她從不缺席。第二年,毛冬華竟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上海美院附中,畢業后又直升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
毛冬華對我說,因家學的影響,她從小受正宗中國畫的筆墨練習,中學又開始接受學院的繪畫基礎學習,經歷了東西方兩種模式的繪畫基礎訓練,這使她更明確什么是屬于自己的繪畫理念。
現代性轉型,創造性轉化
毛冬華是幸運的。自小有在上海中國畫院當畫師的父親的親授,而后又有專業學院的老師和領導的指導。北京《美術》雜志主編尚輝是毛冬華藝術道路上的一位重要的貴人。2009年,與毛冬華素不相識的尚主編慧眼識珠,將毛冬華的中國畫作品《多云轉晴》用在了當年12月號雜志的封面上。這位中國美術理論權威,稱這幅作品為“中國畫現代性轉型的一件成功范例”。
毛冬華稱尚輝是她的貴人,正是由于他的發現和引導,讓她在守正中國畫傳統基礎上,開創了傳承與發展積墨沒骨語言的中國畫現代性之路。
2018年9月,由上海民族樂團、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組委會共同委約德國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Christian Jost)創作的民族音樂會《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獻演于上海大劇院。音樂會由《東方韻味》(Oriental urban perfume)、《浦江明珠》(Pearls reflecting Towers)、《伊甸園之橋》(The Garden Bridge)、《中華第一街》(East Nanjing Road)及《外灘》(The Bund)五個篇章構成。充滿律動和畫面感的音樂,跳脫出民族音樂的慣性表達思路,以一種新的色彩和活力盡情展現中外文化的交相輝映及現代和傳統文明的兼收并蓄,也讓聽眾在有限的聲場空間得到無限的遐想與陶醉。
毛冬華的中國畫《外灘心影》是音樂會的主要視覺呈現之一。這也是外灘主題當代繪畫與民樂的首次結合,外灘和上海其他的經典建筑以及人文印象,通過她手中的畫筆一一呈現在觀眾面前。樂團將毛冬華的《外灘心影》制作成多媒體全景版,具有中國傳統工筆和寫意的畫風,其精細的線條勾勒精至毫發。多媒體制作團隊將《外灘心影》作為主線視覺,通過技術手段虛實結合,使靜態的繪畫藝術,隨著音樂的流動起伏變化,盡情舒展,體現了上海符號,彰顯了工匠精神,以經典與當代元素表達上海人文創新之城的建設理念,引起觀眾強烈共鳴,他們紛紛表示,這場音樂會給他們帶去的是耳目一新的視聽覺體驗。
玻璃幕墻引來的新視角
《外灘心影》中,毛冬華用筆墨致意京華古今經典建筑,通過玻璃幕墻這一中國畫里的全新視角,用“觀海”與“望京”兩組作品為主線,來表現北京古建筑和上海外灘萬國建筑群,呈現這兩座中國最重要城市所承載的歷史人文意涵。

毛冬華在畫《誕生地》
2018年11月8日,《觀海望京——毛冬華水墨作品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展覽共展出毛冬華作品60件,以“觀海”與“望京”兩組作品為主線,作品借用傳統山水畫積墨法和花鳥畫沒骨畫法來表現北京古建筑與上海外灘萬國建筑群。這是上海中青年藝術家首次赴中國美術的最高殿堂——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也是上海美術學院院長基金一號項目。
我問毛冬華,怎么會想到用玻璃幕墻這一新視角來豐富自己的創作?
作為畫家的毛冬華是個有心人,上海街頭的玻璃幕墻遍地皆是。她發現,或陽光普照,或雨過天晴,或風花雪月,或華燈初上……高大的建筑在玻璃幕墻里變化無窮、精彩紛呈。有時透過玻璃幕墻,那些熟悉的建筑平添許多陌生感,這為藝術家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和內容。毛冬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看到了“轉視”的豐富畫面,發現了中國畫的線面結合的新手法,從而開創了中國畫的新視界。
“觀海”系列,是毛冬華內心濃郁的上海情結的厚積薄發。而“望京”系列,則是毛冬華欲將筆墨情懷深化、延展的新課題。為此她幾次赴京寫生,嘗試用其個性化水墨語言進行更多延伸,由此開始了“京華煙云”的創作。通過《雍和鐘聲》《劇院魅影》《蟬鳴白塔》《正陽夕照》《天壇希音》《殿堂祥云》《紫禁清影》《雪漫京華》等8件直徑達2米的圓形作品,向經典建筑致敬,探索將建筑與環境相融,用水墨表現建筑在云影、天光、雪景、水景、夜景中的諸多變化,并由此獲得歷史的感悟。
父女攜手,藝路求索
毛冬華說,現在還擔任著松江區程十發藝術館館長的父親,是程十發先生授教時間最長的學生之一,父親總結了老師的畫藝之路,一篇《十發畫語》發表后影響很大,他又將自己對老師為人為藝的深刻體會寫成了《守望中國畫的精神家園——重讀程十發畫語錄有感》等多篇文章發表。
父親毛國倫曾說,照搬老師的路子,不可;模仿別人優秀的作品,不可。一定要接受優秀傳統的真命脈,抒發自己的真性情,尊重自己的真感受,才能走出屬于自己更為廣闊的藝術之路。所以,毛冬華認為,幾十年來父親能形成自己的畫風,正是他孜孜追求和努力的結果。
毛冬華與父親房子買在了一起,一梯二戶,她就住在父親的對面。為藝術問題爭論是經常的事。如關于玻璃幕墻的視角,毛國倫帶著傳統的眼光不習慣這樣的表現方法。后來,在專家和觀眾的稱贊中才慢慢作出了修正。
而對于未來,兩人的看法倒趨于一致。
對優秀傳統的敬畏,理性地對待繪畫,嚴肅地對待創作,是毛國倫一貫的藝術態度。他說,有了謙遜寬忍的胸懷,就能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熔鑄風格;有了知己知彼的明智,就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堅守自我。毛國倫已有多部畫冊問世,但他認為,藝術是沒有盡頭的,所以他的求索將一如既往。
毛冬華表示,她的“觀海系列”是為獻給上海這座生她養她的城市而作。從2009年完成第一件作品,到2020年完成第六幅,歷經10余年,可以說這個系列的創作伴隨著上海的發展。她希望這系列作品從題材(徽派傳統建筑、石庫門、外灘西式花崗巖大樓和摩天大廈)到藝術語言(沒骨法和積墨法)體現更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在這基礎上,發展成了她的三個大系列:“觀海”系列、“望京”系列和“外灘”系列,而今也還在繼續擴大和發展,通過它們,她將繼續拓展中國畫的藝術之路。另外她還有“記憶”“城市樂園”“冬日暖陽”等系列,未來也還將不斷補充、完善之。
父女倆都有一個共同愿望:不久之后,帶上各自的水墨中國畫走出國門向世界述說上海故事和中國故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與各方人士盡情地對話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