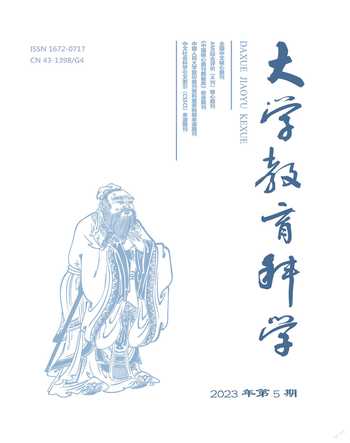論未來主義運動對電影藝術的影響
潘曉霞【作者簡介】 潘曉霞,女,湖北武漢人,河北科技大學影視學院講師,動畫系副主任,主要從事影視、動 畫、電影色彩學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電影色彩語言在影視創作中的運用研究”(立項 編號:SQ14115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潘曉霞,女,湖北武漢人,河北科技大學影視學院講師,動畫系副主任,主要從事影視、動畫、電影色彩學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電影色彩語言在影視創作中的運用研究”(立項編號:SQ141158)階段性成果。
未來主義20世紀初興起于意大利,由詩人、藝術家與先鋒主義者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1909年首先提出。馬里內蒂號召歐洲的藝術家們摒棄以文藝復興與羅馬帝國文化的舊文化,在資本主義現代技術的基礎上建立充滿激情的新社會與新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對交通運輸、通訊設備等現代機械化速度與力量的贊美和謳歌。在對現代技術的狂熱崇拜之后,支撐許多意大利藝術家率先投入這一運動的是意大利對土耳其戰爭的勝利及其迅速發展的國家實力。出于相似的理由,上升時期的歐洲國家普遍具有對新科學新技術的激情,因此未來主義迅速向英、法、德乃至剛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蔓延。同時,一些未來主義者還將熱情傾注到瘋狂的戰爭中,通過宣揚革命之美和戰爭之美號召對“舊文化”的進一步“清洗”。這種對戰爭的熱衷無法贏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因此,在意大利未來主義運動只是曇花一現。但作為20世紀初第一個全球藝術運動,這種將生活熱情投入未來生活的美好愿望迅速在文學、繪畫、雕塑、電影等領域傳播開來,它的理念深刻且持久地影響著包括電影藝術在內的諸多藝術創造領域,為人類文明史貢獻了關于技術性思維的精神財富與文化遺產。
一、對歐洲20世紀20年代先鋒電影運動的影響
未來主義是一場革命性的現代主義運動,它始于馬里內蒂在1909年公開發表在報紙上的《未來主義宣言》。在這份未來主義綱領性的文件中,馬里內蒂以具有畫面感的文字描述了他在想象中見到的諸多華麗繁復的意象:他的思想如同寺廟的“黃銅賀頂式吊燈”一樣熠熠發光,而心臟如同燈絲般燃燒并放出光芒,“我們踐踏著祖傳的惰性,在華麗的東方地毯上長久地來回踱步,在邏輯的極限內高談闊論,同時揮筆寫下許多憤激的言詞。我們的胸中充滿極大的自豪感,因為我們感到此刻惟有自己頭腦清醒,昂首挺立,猶如面對從淡藍色的營地里向外做敵意窺探的點點繁星而傲然屹立的燈塔和穩步前行的哨兵……”[1]未來主義“歌頌追求冒險的熱情、勁頭十足地橫沖直撞的行動”對應在同一時期的許多文學與繪畫創作中,甚至出現了文學領域、繪畫領域與建筑領域中的“未來主義宣言”。然而,由于這一時期電影尚處在“吸引力電影”的原始階段,導演與剪輯師還未能發掘出電影本身表意的功效與美學內涵,因此這些華麗的場景、光亮四射的想象性場景并未第一時間出現在電影的表現之中。反而是在20世紀20年代之后,以好萊塢敘事電影為代表的故事片成為商業電影的主流,許多感到危機的電影藝術家才從未來主義的美學主張中尋求與其對抗的方式。
首先是抽象主義陣營對抽象造型節奏感與韻律感的把握。盡管黑白無聲電影時期的畫面還不具備未來主義繪畫中明亮飽滿的色彩,但導演往往通過三角形、斜線、有序圖形的快速不斷變形來體現內心的沸騰。在瑞典,維京·愛格林(Viking Eggeling)先后拍攝了《對角線交響樂》(1921)、《平行線交響樂》(1924)、《地平線交響樂》(1924)等帶有實驗性質的抽象動畫短片,這些短片從未來主義與達達主義中找到靈感,畫面主要是由螺旋、平行線、直線、銳角等線條和圖形組成。導演熱衷于絕對抽象化造型的節奏和美感,并試圖用這些抽象的線條、圖形或物體的造型來圖解在無聲電影時期難以表現出來的“旋律”和“節奏”。在法國,雷內·克萊爾(Rene Claire)、曼·雷伊(Man Ray)、費爾南德·萊熱(Fernand Leger)與達德利·墨菲(Dudley Murphy)等導演將畫面造型立體化,帶著浪漫的詩意和樂觀的幽默感拍攝了《機器舞蹈》(1924)、《回到理性》(1923)《幕間節目》(1924)等作品。《幕間休息》利用現實生活中的素材進行抽象化的表述:紙船飄蕩在巴黎屋海上空,穿著輕盈舞裙起舞的并非花季少女,而是滿臉胡茬的男人,香煙變成支撐希臘神廟的柱子,降格攝影將莊嚴的送葬隊伍“戲弄”一番。《回到理性》則以相對抽象的物件與運動剝離附著在其上的現實性,導演將釘子、紐扣等物放在光源上方,神秘的輪廓光照射中透露出反理性的主張。
其次,20世紀20年代路易·德呂克(Louis Delluc)及其友人阿貝爾·岡斯(Abel Gance)、謝爾曼·杜拉克(Germain Dulac)、馬塞爾·萊皮埃(Marcel L'Herbier)、愛浦斯坦(Jean Epstein)等人所創立的印象主義電影攝影和剪輯均具有一定的形式感,畫面中的機器被用作現代化的象征,將未來主義對速度與機械的狂熱展現了出來。阿貝爾·岡斯的《鐵路的白薔薇》(1923)中頻繁出現鏡頭遮罩、大特寫、疊印、快速剪輯、多重視域等多種電影手法,“車輪”象征命運與欲望的輪回,開場以快速剪輯的蒙太奇表現火車事故,極具震撼力;讓·愛浦斯坦的《紅色旅店》(1923)《忠誠的心》(1923)將鏡頭的節奏跟音樂相吻合,越來越快的鏡頭拼接甚至單格鏡頭的出現、快速推拉搖移的運動攝影等電影技法,都在強烈的運動節奏中調動起激烈的觀看情緒。同時,荷蘭的伊文思(Joris Ivens)憑借《橋》(1928)、《雨》(1929)等紀錄片作品贏得了國際聲譽。《橋》表現了鹿特丹室內馮斯河上的一座火車、汽車并行的鐵路橋,伊文思通過長期細致觀察,選擇最富有表現力的角度,準確地掌握拍攝時刻,合理設計物體運動和攝影機之間的關系使鐵橋構成的運動和聲音對比形成了鮮明的節奏關系;《雨》長達4小時拍攝,以攝影機的眼睛觀察雨中的漣漪蕩開、水花四濺、積水表面的塵埃漂浮等細微有趣的情景。
再次,主要盛行于20世紀20年代初的德國,其表現主義影片在以夸張、變形的甚至怪誕的形式表現藝術家內心世界的方面與未來主義具有直接的關系。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和其他先鋒派最大的區別在于它強烈的現實主義意義,這與未來主義基于現實需求而向往未來、否定過去的觀念不謀而合。以卡爾·梅育(Karl Mayer)與羅伯特·韋恩的經典之作《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1920)為例,這部影片打破了靜態感性的表現方式,在傾斜構圖、濃烈的膠片染色與夸張強烈的幾何圖像中包含著濃重的主觀心理因素,故事中的科學狂人與變態實驗也摻雜著某種病態心理與夢幻意識。
最后,超現實主義電影在否定了視覺認識的現實性和繼承性的同時,展現出人類潛意識中迷狂、無邏輯跳躍的一面。它以創造幻覺場景與虛幻的超現實世界的方式,對未來主義者所持的立場與思想體系進行有效的繼承。在謝爾曼·杜拉克創作的《微笑的布德夫人》(1922)、《主題與變奏》(1928)、《僧侶與貝殼》(1928)等一系列電影中,客觀物象的表現與運動被賦予了非理性化的精神愉悅感與象征意義:從教堂向外的窺視代表暗地里的嫉妒,用巨型海貝擺弄黑色液體的教士象征宗教勢力與世俗勢力的媾和,將軍用刀劈開貝殼象征破除權威的阻礙,教士手捧的紙質城堡在疊印中顯現,將軍面部的變形、分裂和破碎水晶球的扭曲畫面暗示權威的壓抑和欲望的釋放等。超現實主義電影將影像魔術和心理深度相互結合,帶來了極具視覺震撼的虛幻破碎化空間。
二、對俄國構成主義電影運動的影響
盡管在一戰后由于國家沙文主義傾向逐漸滑向軍國主義的深淵,但未來主義仍然對英國旋渦派、歐洲先鋒派等藝術流派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美學價值最高的,便是從1912年開始的俄國未來主義美學運動。與歐洲藝術精英們領導的先鋒潮流不同,俄國未來主義是在工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通力合作中前進,并意圖創造一個藝術、機械和勞動合一的社會主義新社會。俄國未來主義美學運動是俄國20世紀現代設計的新開端,它提倡與傳統決裂,篤信技術和意義的變化,結合具有不同視覺感知的形式元素,令工業和藝術兩者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變融合。革命前的俄國藝術運動受歐洲現代主義藝術抽象形式的影響,主要以立體主義和未來主義為代表,通過運用幾何、抽象圖形,綜合現代光學、美學以及心理學等諸多領域,并將藝術與工業結合起來,對現代設計的形式語言、藝術表現等方面做出突破性嘗試,為這一時期的藝術創作提供源源不斷的新觀念和設計要素。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俄國未來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刺激之下采取了一種革新實驗性的方法和形式,那就是將勞動、無產階級與未來主義運動結合為一體的構成主義運動。在未來主義于意大利產生之時,激進的意大利藝術家看到技術中存在著社會變遷的巨大潛力,抱有對工業化社會秩序的希望而宣布與舊秩序劃分界限;而十月革命不僅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引進了根基于工業化的新技術,還提供了信奉文化革命和進步的觀念。“革命的巨變亦反映在蘇聯建國初期的藝術創作中,摧毀資產階級藝術及其布爾喬亞意識形態成為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鞏固其統治的必然要求。帶著革命的激情和青春的叛逆,在革命風暴中登上歷史舞臺的年輕一代強烈要求與傳統藝術徹底決裂。……藝術上的‘弒父沖動既是年輕一代長大成人的必經階段,也是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創建一種嶄新的革命藝術的內在要求。”[2]因此,未來主義中對舊秩序終結與新時代誕生的理念順理成章地在相似的社會環境中被俄國無產階級所接納的,從而在革命之后獲得在美學、文學、建筑學、電影等方面和設計實踐的機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大背景下,俄國未來主義以構成主義的形式展現出來。
俄國的未來主義者把借鑒自歐洲的、一種實驗和革新的方法引入藝術語言當中;而電影創作者則將其以構成主義電影的形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在電影領域中,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鼓舞了青年一代電影導演與理論家的創作與研究,他們注重電影風格和技法方面的實驗,希望借助電影的宣傳效果來傳播“全體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捍衛新生蘇維埃共和國的統一體”的信息。舊有的電影作品以電影理論被認為是僵化落后的,維爾托夫、普多夫金和愛森斯坦等新一代電影學者為了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與理念展開了漫長的論戰,其辯論的核心便是“影像如何反映客觀事物,影像的運動又如何生成新的客觀事物,更重要的是這種經由影像生成的新事物如何為革命所用”[3]。其中,愛森斯坦注重場面調度、主張利用剪輯技巧干預影像生成;他的創作理念被“電影眼睛派”的維爾托夫與馬雅可夫斯基等人批評是在將革命“戲劇化”,是一種背叛了歷史真實的行為。對“電影眼睛派”來說,活動的電影影像提供了一種捕捉各種真實世界運動發展的媒介,當事物被刻寫為一幀幀的影像時,影像與影像之間的運動潛能在理解客觀事物的存續上就變得尤為關鍵。與將人類行為與其周圍的物的世界比作機械的運動,從而構成人與機器世界隱喻的歐洲電影相比,無論是愛森斯坦還是維爾托夫,其理論主張的大方向相對一致仍是指向現實意義的。其中的區別更多在于維爾托夫與馬雅可夫斯基立足于影像之間統一化的間隔,通過不同鏡頭之間的排布與運動,激發出影像之間的相關性;而愛森斯坦則以沖突性的蒙太奇構成新的運動影像與美學特質。兩者的本質都是通過對現實素材的拆分、還原與重組生成新的物質形式——這與20世紀20年代興起,將藝術視為生產的觀念,以及構成主義者對于蘇維埃革命的構想一致。其中的典型之作,便如《罷工》(1925)與《戰艦波將金號》(1925)中顛倒錯位、象征隱喻、主觀視角的運用、鏡面反射與曲面鏡帶來的變形、眼睛與面部的大特寫等“雜耍蒙太奇”顯示出敘事中的批評力度與革命節奏感;不斷升起的炊煙和不斷旋轉的車輪象征著工人們如火如荼的反抗;全速前進的波將金號在海面上留下一道道水痕,輪機在特寫中高速運轉,冒著濃煙的煙囪與破開浪花的船頭,儀表盤特寫顯示船只正在全速前進……一系列節奏越來越快的鏡頭組成了節奏蒙太奇,也留下了關于革命故事近乎完美的影像表述。在構成主義者所主張的新秩序中,藝術、科學與技術將結合起來一同協作;而工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則在共同的勞動與創造中富含激情地展現出一種新的社會景象。
三、對電影美學的影響:打破物象,進入感覺領域
時至今日,再對未來主義的畫作與電影進行觀察,會發現其中許多作品似乎“沒什么看頭”:白色畫布上簡單的黑色方塊、連續旋轉或對稱的軌跡留下的圖像、小孩子游戲般留下的夸張圖形等,在今日都是可以用電腦自動繪圖工具快速畫出來的圖形;而“未來藝術宣言”中貶低傳統藝術、貶低女性、鼓吹國家沙文主義的部分也早已飽受批判。的確,就表現技法和藝術理念而言,未來主義藝術與其后繼起的諸多美學流派相比過于簡單,顯得感性有余而深度不足。但藝術不是比較技法的東西,盡管未來主義本身時間短暫且具有各種限制。它是20世紀首個對以寫實為主的傳統電影美學發起沖擊的現代美學運動,未來主義的作品專注于藝術的純潔性,在簡約的外表下蘊含著智慧、現代性和精密性的象征。從美術設計到電影創作,未來主義作品在引導人們去發現具體物象之外的事物,在感覺層面啟發創作者向內探索現代生活的激情。這樣的思想與新生的電影技術觀念混合在一起,改變了歐洲一些地區的美術、建筑、設計領域和電影美學的面貌,也促成了“純電影”或“快速電影”的產生。
“純電影”又稱“完整電影”,這一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由法國先鋒派電影理論家杰爾曼·杜拉克提出。它與20世紀諸多成熟的美學流派相比更接近于一種獨立制作、帶有動畫性質的電影范疇。這一理論認為電影并非敘事藝術,而是“形狀的電影”與“光的電影”的匯合;它在敘事上“借助于各種節奏和運動中的形狀,更能創造和構成一個形象,然后與其他形象相協調”,這樣的電影與僅僅是運用了電影手段的類型片相比才是真正的電影。[4]例如由立體主義畫家轉而成為導演的萊謝爾就多以機械的圖案和城市生活景象為主題,在其代表作《機器的舞蹈》(1924)中,便將具體物象的現實性打破,亮白色反光的機器零件、白色的圓圈和三角形、來回擺動的球體、搖彩的輪盤、棱鏡折射的光線、齒輪、草帽、數字、雜技表演中的馬術場面等內容在快速組接中完全摒棄敘事的可能,轉而展現為富于節奏與機械性的純粹運動,即成為了一種“眼睛的音樂”或“視覺交響樂”[5]。未來主義深刻地影響著20世紀20年代的許多先鋒電影,繼而在純粹的非敘事實驗電影觀念中不斷地延續了下去。不僅后世的“藝術電影”在對感覺的依賴中找到了新的影像表達,就連敘事電影乃至商業主流大片都汲取了未來主義觀念中的養分,例如喬治·盧卡斯就深受歐洲實驗電影運動的影響,他在《星球大戰》(1977)、《星球大戰1:魅影危機》(1999)、《星球大戰2:克隆人的進攻》(2002)等電影中所展現出的無限想象力,以及先鋒美學與科技成果的融合,完全可以追溯至百年之前的未來主義時期。
結語
20世紀初誕生的未來主義運動是現代藝術史上第一次大范圍內的美學運動,它旨在倡導基于現代技術的藝術實驗與革新精神,這種藝術思潮從美術領域發展到電影領域,使這一時期的電影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風格樣式。未來派電影藝術通過分析的、同時也是心理性的選擇及綜合象征地表現運動中的造型,在歐洲的多個國家引起了抨擊美國故事片的先鋒派電影運動。未來主義風格的電影與繪畫為這一時期的電影領域帶來了充沛的激情與創作經驗。盡管由于敘事性與商業性較差,得不到發行商支持的先鋒主義影片漸漸被有聲電影所取代。然而,它繼承自未來主義美學的形式美學仍然被傳承在后世的電影中。
參考文獻:
[1][意]薩布麗娜·拉法格羅.未來主義之路[ J ].中國美術,2010(02):153-157.
[2]莊沐楊.物的革命潛能與自反:維爾托夫、愛森斯坦與蘇聯先鋒派動畫觀[ J ].電影藝術,2021(04):118-124.
[3]賈斌武.“革命的孩子”與他們的藝術革命——重訪蘇聯早期先鋒藝術宣言《丑怪主義》[ J ].藝術百家,2020(06):145-151.
[4][5][法]馬塞爾·馬爾丹.電影語言[M].何振淦,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