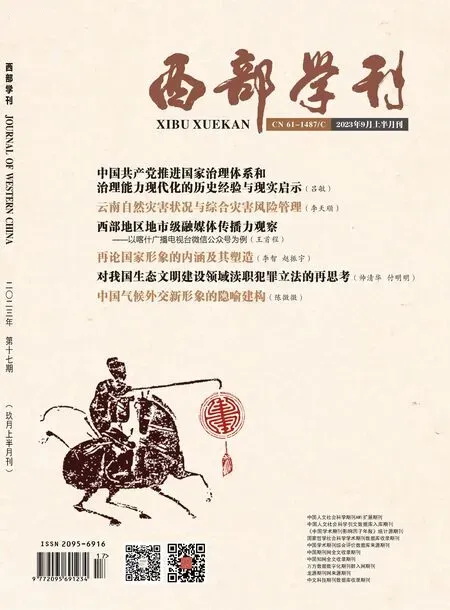淺析莊子的生死觀
張 迪
(黑龍江大學(xué) 研究生院,哈爾濱 150000)
在莊子看來(lái),道是世界萬(wàn)物的本原,也是一種至高無(wú)上的存在。 氣就是一種具體化的道,道通過(guò)氣的凝聚產(chǎn)生了生命,隨著氣的彌散,生命迎來(lái)了消亡,回歸到道本身。 無(wú)論怎樣變化,這都是一種必然的造化過(guò)程。 莊子從本體論出發(fā),闡述了他對(duì)待生死的看法,提倡消除生死界限,保持豁達(dá)樂(lè)觀的態(tài)度。
一、莊子生死觀的形成
(一)社會(huì)背景
莊子生活在戰(zhàn)國(guó)中后期,周王朝東遷象征著天子的權(quán)威衰敗,禮樂(lè)征伐大權(quán)下落到了諸侯大夫手中,展開了幾百年的割據(jù)兼并戰(zhàn)爭(zhēng),各國(guó)都通過(guò)變法來(lái)增強(qiáng)本國(guó)的實(shí)力,可是斗爭(zhēng)越激烈,人民的生活也就越艱難,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當(dāng)中。 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戰(zhàn)火連天、民不聊生的社會(huì)環(huán)境,莊子在書中多次描繪過(guò),在《莊子·在宥》篇中,他寫到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的慘狀,“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1]287,到處都是被處死者的尸體、戴著枷鎖的人擠滿整個(gè)道路,一眼望去都是遭受刑戮的人。 與莊子同時(shí)期的孟子對(duì)當(dāng)時(shí)動(dòng)蕩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和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自己欲望、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的行為進(jìn)行了有力地抨擊,“爭(zhēng)地以戰(zhàn),殺人盈野;爭(zhēng)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2]統(tǒng)治者為了一己私欲,不斷發(fā)動(dòng)兼并戰(zhàn)爭(zhēng),死傷戰(zhàn)士和百姓的尸體鋪滿了整個(gè)戰(zhàn)場(chǎng),死亡的恐懼籠罩著每一個(gè)人。
能夠躲戰(zhàn)火、僥幸活下來(lái)的百姓,也沒(méi)有辦法擺脫勞碌和憂辱,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爭(zhēng)名奪利的風(fēng)氣彌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1]250從上至下,人為物累,終日奔波勞累,忙忙碌碌追逐外物,內(nèi)心充滿虛名浮利,最終淪為物欲的奴隸,回首一生,身心俱疲,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1]51莊子對(duì)于生命流逝的感嘆,更是蒙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他感嘆道“方今之時(shí),僅免刑焉”。 在這種極端惡劣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當(dāng)中,莊子對(duì)這個(gè)無(wú)道的社會(huì)和生命流逝的過(guò)程感到完全的失望,他沒(méi)有選擇與統(tǒng)治者同流合污,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百姓的遭遇和痛苦抱有極大的同情,思考如何化解生存危機(jī),這引發(fā)了他對(duì)于個(gè)人的生死存亡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理論基礎(chǔ)
道是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一個(gè)最基本的范疇,也是莊子人生哲學(xué)的基礎(chǔ)。 關(guān)于什么是“道”,老子在《道德經(jīng)》中給了一個(gè)定義,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dú)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3]“道”是宇宙萬(wàn)物的本源,是天地之根、萬(wàn)物之母,雖然我們感知不到它,但是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而是永遠(yuǎn)的存在,世間萬(wàn)物循道而生、復(fù)歸于道,事物的產(chǎn)生、發(fā)展、滅亡都是遵循道的規(guī)律。
莊子繼承了老子“道”這一思想并賦予了它更多的含義,在《大宗師》篇中,他對(duì)“道”的性質(zhì)進(jìn)行了完整的論述:“夫道,有情有信,無(wú)為無(wú)形;可傳而不可受……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zhǎng)于上古而不為老。”[1]189“有情有信”說(shuō)明道雖然不被我們所感知,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真實(shí)存在的;在天地還沒(méi)有產(chǎn)生之前,它已經(jīng)存在了,并且還會(huì)無(wú)限地存在下去;它的運(yùn)轉(zhuǎn)從不依賴萬(wàn)物,萬(wàn)物的生化卻脫離不了它。 無(wú)論是從時(shí)間的跨度還是空間的跨度來(lái)看,道的地位都是至高無(wú)上的。
莊子對(duì)于道的理解,更多地落腳到了精神境界上,把道看作是一種最高的認(rèn)識(shí)。 《齊物論》中講到:“物無(wú)非彼,物無(wú)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 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wú)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1]60每個(gè)事物真的都有兩個(gè)方面嗎? 還是因?yàn)槲覀兯^察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樣的? 莊子談了自己的看法,此也是彼,彼也是此。 彼此之間沒(méi)有差別,“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既然彼此之間沒(méi)有差別,也就取消了彼此對(duì)立的關(guān)系、消除物我之間的差距,這樣就能像是進(jìn)入到了太極中間的圓環(huán)一樣,以不變應(yīng)萬(wàn)變。 沒(méi)有了是非對(duì)錯(cuò)之分,那么生與死也就沒(méi)有差別,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莊子從道的角度出發(fā),消解事物之間的區(qū)別,通過(guò)這樣的方式,化解人們對(duì)于生死的憂慮。
二、莊子生死觀的本質(zhì)
(一)以道觀之,生死齊一
“道”作為萬(wàn)物之母,它是永恒存在的。 “道無(wú)始終,物有生死”,一切人和事物的存在都是暫時(shí)的、相對(duì)的。 “道”普遍地存在萬(wàn)物之中,內(nèi)化成為事物運(yùn)動(dòng)變化的動(dòng)力。 從宇宙中“道”的角度來(lái)觀察一切,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所有事物的變化都是表面變化,其內(nèi)核是不變的,“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wú)成與毀,復(fù)通為一。”[1]67
在莊子看來(lái),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事物有成的理由,也有毀的原因。 同樣的,反過(guò)來(lái),事物有不成的原因,也有不毀的道理,沒(méi)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莊子還舉了個(gè)例子,無(wú)論是纖細(xì)的小草還是粗壯的大樹,無(wú)論是相貌美麗還是相貌丑陋,世間一切細(xì)小的差別、千奇百怪的事物,在道看來(lái),都可以是渾然一體的。 舊事物中蘊(yùn)含著新事物,其分解意味著新生,反之亦然,所以所有事物的成與毀并沒(méi)有差別。 回歸到人間的生死問(wèn)題上,生也就是死,死也就是生,本質(zhì)上并沒(méi)有什么區(qū)別,都是大道流轉(zhuǎn)上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人們之所以會(huì)樂(lè)生悲死,會(huì)對(duì)死亡產(chǎn)生恐懼,是因?yàn)閷?duì)待事物的一切認(rèn)識(shí)都受限于自己的感知經(jīng)驗(yàn),莊子對(duì)待生死的看法顯然是超脫現(xiàn)實(shí)的。
(二)氣化生死,四時(shí)行也
在《知北游》中,作者認(rèn)為宇宙萬(wàn)物源于“氣”,人的生死也是因?yàn)闅獾木凵ⅰ?從道的角度來(lái)觀察人的生死變化,都是氣的變化。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 故萬(wàn)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1]565所以人之生死,物之生滅都是源于氣的形態(tài)變化,氣聚則萬(wàn)物生,氣散則歸于道,這是一個(gè)循環(huán)反復(fù)永不停歇的過(guò)程。 在《至樂(lè)》篇中,莊子妻死,他沒(méi)有表現(xiàn)出悲傷,反而鼓盆而歌。 惠子不解,于是莊子感嘆到:“察其始而本無(wú)生,非徒無(wú)生也而本無(wú)形,非徒無(wú)形也而本無(wú)氣……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1]462世界上本沒(méi)有氣,也沒(méi)有生命,氣的存在就是來(lái)表示無(wú)法感知的道,道通過(guò)氣不斷變化形體,凝聚而生成萬(wàn)物,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彌漫而萬(wàn)物消亡,回歸到了道最開始的狀態(tài)。 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的這一個(gè)過(guò)程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輪轉(zhuǎn)一樣自然平常,冬去春又來(lái),循環(huán)往復(fù),生生不息。 你會(huì)因?yàn)樗募镜淖儞Q而感到傷心嗎? 我的妻子只是遵循自然變化的規(guī)律,又回到了原本最初的狀態(tài),安然地躺在天地之間,為什么又要感到悲傷呢? 通過(guò)氣的聚散,衍變出來(lái)了不同的形態(tài),事物之間相互轉(zhuǎn)化,這樣一個(gè)過(guò)程也是“物化”的過(guò)程。
“昔者莊周夢(mèng)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mèng)為胡蝶與,胡蝶之夢(mèng)為周與?”[1]98莊子在夢(mèng)里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了蝴蝶,醒過(guò)來(lái)發(fā)現(xiàn)自己還是莊周,在夢(mèng)醒之間迷迷糊糊也搞不清自己原本是蝴蝶還是莊周。 人生就像一場(chǎng)夢(mèng),在懵懂之間,泯滅了物我之間的界限,實(shí)現(xiàn)了物我之間的轉(zhuǎn)化,也將生死融為一體。 所以對(duì)于終極本源的“道”和物質(zhì)基礎(chǔ)的“氣”來(lái)說(shuō),生死只有形態(tài)上的差異,并沒(méi)有本質(zhì)上的差別,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這都是大道周流上的轉(zhuǎn)化環(huán)節(jié)。
(三)不生不死,薪盡火傳
在莊子看來(lái),看待生死的最高境界莫過(guò)于跳出大道的循環(huán),最終達(dá)到不生不死的境界,從而超越生死。在《大宗師》篇中,“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后能外天下……無(wú)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1]192莊子認(rèn)為通過(guò)“外天下”“外物”“外生”三個(gè)修養(yǎng)過(guò)程,最終就能跳出時(shí)間的循環(huán),破除對(duì)生死的執(zhí)著,就能體認(rèn)大道,到達(dá)“不知說(shuō)生,不知惡死”的真人境界,真人與道融為一體,超越生死界限,一切都隨順自然,游于“逍遙”之境,追求一種無(wú)待無(wú)己的狀態(tài),在精神上追求永生。 正如徐復(fù)觀在《中國(guó)人性論史·先秦篇》中提到的“指窮于為薪,火傳也”的“火”,亦當(dāng)指精神而言,而“薪”則比喻作人的形骸。 單個(gè)的薪是有盡的;但薪里的火,則由此已盡之薪,而傳至其他方始之薪。 人的形骸是有盡的,但形骸里的精神,則由此已盡之形骸而回到道那里去,再化為其他方生的形骸,所以他才說(shuō)“不知其盡也”。 “不知其盡也”,乃是他“安時(shí)而處順”及“物化”的真正根據(jù)[4]373。
所以,莊子也是借舉“薪火之喻”來(lái)將個(gè)人的生死融入宇宙大化的流行之中,從而在宏觀層面上消解個(gè)人對(duì)于生死變化的恐懼,最終實(shí)現(xiàn)精神層面的“不生不死”的境界。
三、莊子對(duì)待生死的態(tài)度
(一)生死有命,隨順自然
莊子把生命的流逝看作是一種遵循大道流轉(zhuǎn)的必然過(guò)程,所以關(guān)于我們出生、死亡的一切,都不是個(gè)人能決定得了的,這背后是“道”在起作用。 在《大宗師》篇中,作者提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莊子認(rèn)為,一切事物的生滅就像日月永恒交替一樣,是一種不能違抗的自然現(xiàn)象,人是改變不了的,只能坦然接受“道”的安排。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198大道的陰陽(yáng)造化就像親生父母一樣,賦予了我形體,讓我生存、衰老以至于死亡,這個(gè)過(guò)程就是自然造化的規(guī)律,既然以生為樂(lè),就應(yīng)該坦然地接受死亡,以死為樂(lè)。 莊子借以“大冶鑄金”的例子來(lái)詮釋:把自己比喻成為將被鑄造的金屬,把大道比作鑄鐵的工匠。 金屬本身是不知道自己將要變成什么的,也沒(méi)有什么追求和欲望,金屬形態(tài)的變化完全隨著工匠的冶煉而自然變化,如果被鑄造的金屬大呼,我一定可以被鍛造成名劍,那它一定會(huì)被認(rèn)定是不祥的金屬,是因?yàn)樗米约旱闹饔^欲望代替了大道的安排,從而違背了順隨造化這一道理。 同樣的,人的喜生悲亡如果也違背了這一點(diǎn),就會(huì)被視為“不祥之人”。 人只有坦然接受命運(yùn)的支配,讓形體隨著自然造化而變化。這背后體現(xiàn)了莊子對(duì)于生命造化的悲觀和無(wú)奈,所以落實(shí)到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莊子秉持安之若命的生活態(tài)度,安然接受一切的變化,保持內(nèi)心的平和。
莊子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列御寇》中有記載: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 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wàn)物為赍送。吾葬具豈不備邪? 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1]848在莊子即將去世的時(shí)候,弟子們給莊子準(zhǔn)備了豐厚的陪葬品。 莊子都拒絕了,他認(rèn)為面朝青天,背靠大地,世界萬(wàn)物都是他的陪葬,又何必特殊準(zhǔn)備什么呢? 人的生死都是自然變化,那么死后被鳥或者螻蟻所侵蝕,也是天地的安排,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不要用人為的方法去回避自然的變化。 莊子身體力行、超脫生死,達(dá)到了一種徹底自由的境界。
(二)死歸至樂(lè),善生善死
莊子以人的樂(lè)生而惡死,實(shí)系精神的桎梏[4]370。在莊子看來(lái),命是大道掌握的,人是沒(méi)有辦法決定各種變化的。 從大道的角度來(lái)看,一切變化都是有意義的,存在有存在的意義,那么消亡也有其合理性,所以我們既然以生為樂(lè),那么也應(yīng)該以死為樂(lè)。 艾地戍守疆界之人的女兒在被俘獲還沒(méi)有得到榮寵之前也是悲傷大哭的,“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哪會(huì)知道死了的人會(huì)不會(huì)后悔臨死之前的求生欲望呢? 每個(gè)人的人生體驗(yàn)只有一次,死后的事情并不可知,沒(méi)有經(jīng)歷過(guò)的事情并不能貿(mào)然評(píng)價(jià),所以莊子反對(duì)那種先天代入的主觀意識(shí)。 在《至樂(lè)》篇中,莊子借用寓言故事,通過(guò)骷髏之口說(shuō)出了人活著所得到的世俗快樂(lè)并不是真正的快樂(lè),只有死后才獲得了至樂(lè):莊子途經(jīng)楚國(guó),見路邊一枯骨骷髏,便問(wèn)其為何而死?莊子入睡后,骷髏便和莊子分享死后的快樂(lè):死了之后也沒(méi)有君臣的束縛,也沒(méi)有了四季的操勞,可以安然自在地與天地同化,“雖南面王樂(lè),不能過(guò)也。”[1]465莊子不信,便打趣要恢復(fù)骷髏的形體,骷髏憂郁地表示怎么能放棄真正的快樂(lè)而回到人間受苦呢? 在這里,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消失,而是對(duì)人生負(fù)累的解除,死亡因此有了生命的價(jià)值[5],當(dāng)死亡來(lái)臨時(shí),欣然接受。 莊子以生為苦,以死為樂(lè),死歸至樂(lè),善生善死,其實(shí)最終目的是把生命看作成為一個(gè)自然造化的過(guò)程,死并不代表著人生意義的終結(jié),而是一個(gè)全新的開始。 生命回歸其本然的狀態(tài),也是一種快樂(lè)。
四、結(jié)語(yǔ)
莊子把“道”作為世界的本源,把“氣”作為連接道和萬(wàn)物的中間的橋梁,“道”通過(guò)掌握氣的各種形態(tài)上的變化從而把握世間萬(wàn)物的生死,所以世間萬(wàn)物從本質(zhì)上來(lái)看都是一樣的,由此莊子認(rèn)為生死齊一、隨順自然。 其實(shí)不僅對(duì)待生死我們要用順乎自然的態(tài)度,對(duì)待人生更是如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guò)隙,忽然而已”[1]575,人的一生很短暫,從出生、衰老、死亡,不過(guò)幾十年。 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人們糾結(jié)于太多自己無(wú)法改變的事情,深陷苦惱不能自拔,與其這樣還不如改變對(duì)待生活的態(tài)度,用一種順其自然不強(qiáng)求的方式去對(duì)待生活,這也是莊子生死觀教給我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