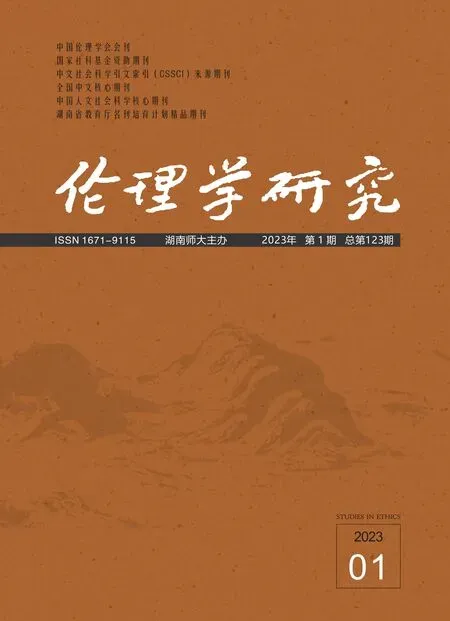論孔子之“樂”
劉立夫,黃小榮
據統計,“樂”字在《論語》中一共出現48 次,頻次僅低于“仁”“君子”“禮”等字詞。其義項有三:一是音樂,即禮樂之樂;二是喜愛,此用法只有一例,即“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①下引《論語》只注篇名。;三是快樂或與快樂相關的意義。對于第三種意義上的“樂”,楊伯峻、李澤厚、錢穆等人幾乎都譯為“快樂”。這可能會引起誤會,因為快樂一般指短暫的、感官或物質的享受,比如以快樂主義著稱的伊壁鳩魯哲學就被認為(雖然是誤解)是豬的哲學而飽受批評。與庸俗的享樂主義相對立,孔子之“樂”具有明顯的道德意味。陳來認為孔子之“樂”就是幸福[1],但問題是孔子時代還“沒有直接出現西方或者現代意義上的‘幸福’詞語”[2](13),亞里士多德也說“那最為平庸的人,則把快樂和幸福相等同”[3](5),可見,快樂和幸福不宜等同。在先秦時期,與“幸福”最接近的概念是《尚書》中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概念,但孔子在《論語》中卻未提到“福”。還有學者認為孔子之“樂”是一種“來自生命追求與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是一種“自得之樂”與“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4](157)。這種“向上一路”的說法雖然高明,卻不接地氣,不能呈現孔子之“樂”的全部內涵。雷永強提到“在孔子的音樂世界中,音樂情感實包括藝術情感、道德情感和自由情感等三重境遇”[5](32),孔子之“樂”也有三個層次,其中既有感官快樂、物質快樂,也有精神上的快樂,還有實現了生命追求與道合一的精神自由。學者們之所以對孔子之“樂”有不同的理解,蓋出于此種概念的多義性。大致來說,孔子之“樂”的第一層次即感官快樂、物質快樂相當于日常所說的快樂;第二層次即精神快樂相當于倫理學所說的幸福,尤其是道德幸福;第三層次即精神自由,作為一種與道合一的至善至美境界,其本質上仍然屬于一種道德境界。可見,道德是理解孔子之“樂”的關鍵,而道德性則是孔子之“樂”的根本特征。對孔子來說,快樂之路即成德之路或向善之路,他由此開出了以弘道為核心,包括順性、節情、成教和游于藝等方面在內的快樂之方。
一、孔子之“樂”的層次
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穆勒說過:做一個不滿足的人勝于做一只滿足的豬;做不滿足的蘇格拉底勝于做一個滿足的傻瓜[6](12)。他認為快樂有高低優劣之分,高等快樂比低等快樂更值得追求。孔子雖然沒有明確地區分快樂的等級,但他所提到的快樂也是有層次的,包括感官快樂、物質快樂,精神上尤其是與道德相關的快樂以及生命回歸到仁的狀態下的精神自由[7](153)。不過,與功利主義強調以快樂作為指導人生的根本原則不同,孔子的快樂觀更強調回歸道德本身,二者的立場有根本性的差異。
孔子之“樂”的第一個層次是感官的、物質的快樂。最典型的就是食、色之樂。孔子曾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鄉黨》),如果有條件的話,他認為在飲食上越精細越好。他還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也承認好色是人之常情。此外,孔子還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可見他對物質享受并非不追求,只是認為應該有所節制,不能過分,更不能越過道德底線,比如喝酒,就不能為酒所困,更不能喝到亂性。孔子還談到“損者三樂”: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季氏》)。他認為這三種快樂本身就不可取,談不上節制不節制的問題。所以,孔子并非禁欲主義者,他對正常的感官和物質享受都是認可的,只是貶斥庸俗而荒誕的縱欲主義和享樂主義。
孔子之“樂”的第二個層次是精神上的快樂。《論語》開篇就提到兩種精神快樂:學習之樂和友誼之樂。他說的學習和友誼都與道德有關,因為通過學習道德知識和與有道之士交往能提升個人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能力,孔子稱為“學以致其道”(《子張》)和“以友輔仁”(《顏淵》)。這兩種快樂本質上都是一種道德滿足感或者道德幸福[8](26-34)。同時,與“損者三樂”相對,孔子還提出了“益者三樂”,即“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季氏》),這三種也是精神上的快樂,而且也都跟道德有關,這表明孔子所講的精神快樂是有道德性的。孔顏之樂作為先秦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2](13)是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快樂。所謂“孔顏之樂”,即“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述而》)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的那種快樂,其核心要義是安貧樂道。首先,其道德性不言而喻。其次,孔顏之樂超越了感官和物質以及外在的生存境遇層面的快樂,其精神性凸顯。孔顏之樂后經周敦頤闡發而成為理學的重要議題。如程顥指出,“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9](352),認為顏回樂的是仁。但程頤卻認為“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乎,則非顏子矣”[9](1237),否認顏回是以道為樂。朱熹指出,“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個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后樂。見得這道理后,自然樂”[10](801)。程顥的“樂仁”說尚有仁我之分,而程頤和朱熹則認為孔顏之樂是一種“與道為一”[11](48)的境界。王陽明更是直接將天理、良知和孔顏之樂融為一體,創造性地提出了“樂是心之本體”“良知即是樂之本體”[12](293)等命題,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孔顏之樂的道德性和精神性。
孔子之“樂”的第三個層次是實現與道合一的精神自由,是一種超越的生命境界。精神自由也可以理解為道德自由或道德自覺。達到這種境界的人將道德視為生命的內在訴求,即孔子所謂的“仁以為己任”(《泰伯》),在道德實踐中是自覺、自發和自由的。孔子晚年達到的“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種道德自由境界。從心所欲說明他是自由的,不逾矩則表明他心之所欲是契合大道仁義的,也即與道合一。當一個人達到精神自由境界時,他就會將道德義務覺解為不可推卸的責任,以至于用生命去捍衛道義,即“殺身以成仁”。對他而言,實現其內在的道德生命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對于外在的生存境遇尤其是逆境往往表現出隨遇而安與豁達的態度。以此而論,精神自由又體現為一種憂樂圓融的生命境界,即在憂患的現實當中始終保持精神的超脫和自由。其要義可分為三點:第一,外在境遇之“憂”與內在德性之“樂”的圓融。正如塞涅卡所言,“幸福的人是無論當下境遇如何,都滿足于自己的境況并與之友好相處的人;幸福的人是得到理性對他所有的境況的認可的人”[13](41)。精神自由者是擺脫了外在境遇的束縛的人。第二,“憂道”和“樂道”的圓融。達到精神自由或道德自由境界后以弘道為務,一方面從弘道中感受到精神上的滿足和快樂;另一方面也為現實中的弘道受阻而擔憂。第三,個人之“樂”和天下之“憂”的圓融。莊子曾斷言諸子百家共同追求的終極目標都是內圣外王,這意味著個人的精神自由必須放在更廣闊的天下視域中加以審視。只有那些真正心憂天下者,才可能致力于天下太平,充分履行其所背負的天命,實現其精神自由。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都是這種精神境界的表達。
孔子之“樂”的三個層次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首先,感官、物質快樂是由感官享受或物質上的滿足引起的快樂,精神快樂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感。其次,精神快樂是指某種行為所帶來的精神滿足感,而精神自由則是精神上的自我實現。再次,在孔子特殊的語境,三個層次的快樂都與道德相關。精神快樂和精神自由都是以道德為前提,而感官快樂和物質快樂也離不開道德規范。最后,不同層次的快樂可能相互交織甚至有時候可能體現在同一種快樂中。比如曾點之樂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進》)就是這樣。其中既有感官享受、精神享受,也有精神自由。朱熹評曰:“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14](124)陳慧認為這種“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性,處在自然而然的圓滿狀態之中”[15](66+107)就是理學家向往的政教理想。他還指出,理學興起之后,儒家政教理想發生了內在轉向。所謂“內在”并非只著眼于精神或心靈層面,否則便成了朱子批判的流于佛老,而是將原本作為外在規范的倫理道德內化于個體生命,實現心靈秩序與生活秩序的一貫,達致內外無別、體用一如的境界[15](107)。可見,曾點之樂已臻精神自由之境。程顥則將此描述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境,其實質就是以極開放和宏大的道德心胸包容和擁抱天地萬物。張載、朱熹、王守仁等人對此也有過類似論述。
二、孔子之“樂”的特征
關于快樂,哲學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論。比如伊壁鳩魯認為快樂是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無煩惱,亞里士多德認為“快樂是自然品質的現實活動”[3](158),功利主義認為快樂是可以量化的,莊子強調精神自由才是真正的快樂,佛教將快樂視為彼岸的理想,等等。那么孔子所講的快樂是什么,有何特點?這需要對孔子思想進行整體觀照。孔子所謂的快樂最根本莫過于節禮和為仁的快樂。由此,孔子之“樂”的特征可概括為兩條:
第一,強調禮對快樂的節制。禮的本義與宗教祭祀有關,具有神圣性。又因宗教祭祀重視儀式,所以禮也有規范之意[16](123-131,216)。中國至周代始有所謂制禮作樂之說,實際上凸顯了禮的人文意義,禮由宗教祭祀的儀式變成了人倫規范。孔子非常推崇禮樂制度,他一生都以恢復周禮為己任,主張“以禮讓為國”和以禮立身行事,其快樂觀也打上了以禮節人的烙印。第一,孔子提出對某些享樂行為應該以禮節之,比如在飲酒方面他就劃出了兩條底線:不為酒困和不及亂。其他享樂行為也是一樣,也都應該守禮和講規矩。第二,孔子提出追求物質上的富貴應該正當合禮。他雖然不排斥或敵視富貴,但是他提出人們追求富貴的手段應該合乎道義精神。對不以正當手段攫取的富貴他嗤之以鼻。“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第三,孔子將“節禮樂”本身當成一種快樂。所謂“節”即意味著限制,是對人的欲望的某種抑制,很難說是快樂的。他為何將節禮樂當成一種有益的快樂呢?究其原因,一是他認為禮是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學禮知禮節禮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社會;二是他所說的禮其實并不苛刻,節禮并不等于抹殺人們正常的感官享受。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學而》),禮的運用是講究和諧的。就此而論,似乎“禮節樂和”的分工也并不是絕對的。第四,孔子反對統治者窮奢極欲,強調社會財富應該得到公正分配。他雖然認為快樂的根本在于德性,但是同時他也認為財富、地位、友誼和名聲等外在善對于快樂來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湯云指出:“用制度保障快樂的物質條件屬于‘正義’的范疇……制度處理與正義相關的問題,包括自由、資源和機會等與個人快樂息息相關的資源的分配。”[17](141)因此,正義是快樂的外在維度。孔子重點談到的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他認為富民和惠民是當政者應有的德行之一。孔子不僅明確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堯曰》)的富民主張,而且還將“養民以惠”視為君子之道。總之,孔子認為當政者有富民惠民之責,應該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特別是在稅收政策上要體恤百姓,這是治國之大經,也是當政者應當去遵循的行為規范即禮。尚建飛指出,作為政治、道德行為規范體系的“禮”,能夠確保人類社會在親疏、尊卑之別的社會結構中公正地分配財富、地位、榮譽等外在善[18](67)。由此,他認為禮展現了孔子所謂幸福的外在向度。
第二,強調快樂的根本在于對仁的追求。禮和仁是孔子思想中的兩個核心范疇,禮是外在規范,仁是內在原則[19](48-58),因此,從根本上說約禮即為仁。但約禮只是為仁的一個方面,不能代替為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如果只是徒守外在形式的禮而內心絲毫無仁義之實,這種節禮就顯得行為者處處受到限制和不自由,很難說是快樂的。孔子以節禮樂為樂,顯然是以自由為前提的。對于那些真正將節禮當成快樂的人來說,禮并非限制,而是責任,他們在踐禮的過程中是自由的。這種責任不是外來的,而是人的本性之仁對我們提出的要求。由此,尚建飛將仁視為孔式幸福的內在向度。這表明,孔子所謂的快樂或幸福根本在于對仁的追求,而不取決于諸如財富、地位等的滿足。這就是快樂的內在維度,即反身性[17](143)。快樂的根本之所以在于對仁的追求,原因有三:其一,只有仁者才能獲得那種最為持久和鞏固的快樂。普通人往往追逐感官享受和物質上的滿足,這種快樂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但是君子在學道和弘道中尋找到的快樂卻是穩定持久的。其二,仁者不憂。有仁德的君子不僅能獲得更為持久鞏固的快樂,而且他們也能更從容地面對生活的困苦,在艱難的人生境遇中保持樂觀、豁達和超脫。正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越是艱難處,越見君子的操守。其三,最高的快樂是實現與仁合一的精神自由。這決定了孔子不得不強調為仁的根本性。只有為仁,才可能實現這種終極快樂。仁德不是天生的,人們只有在長期的道德實踐中才能養成,只有仁人才能達到與仁合一的精神自由境界。
強調節禮和為仁充分體現了孔子之“樂”的道德性,說明孔子對快樂的理解包含深刻的道德關切。孔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面對這種社會現實,他認為只有道德才能拯救世界,因而他以推行道義視為自己一生的使命。他畢生的愿望就是百姓得到教化、社會歸于有道。正如趙法生所指出的,“孔子對于儒家人性論乃至于儒家文化的開創性貢獻,是他對人的道德性的發現與首肯”[20](57)。孔子肯定人的道德性,等于承認道德完善是人的自我實現的必然,人應該過道德的生活,追求道德上的完善。正因為孔子之“樂”具有明顯的道德性,有人將它視為與幸福等同的概念。“幸福來自目的論的傳統(若用尼采的表達:來自仍舊持有最高價值的傳統),它指向先于個人意志的目的。這個目的在道德或倫理上表現為德性(virtue),而幸福可以理解為德性的實現。”[17](139)應該說幸福這個概念確實比較接近孔子之“樂”,但是,孔子之樂不僅包括幸福的層次,還包括快樂和精神自由的層次,二者不能簡單地等同,只能說幸福是孔子之“樂”的題中之義。
三、孔子之“樂”的踐行之路
塞涅卡說:“所有人都想幸福地生活,然而對于看清楚是什么創造了幸福的生活,他們卻處于迷霧之中。”[13](29)雖然人們都渴望幸福的生活,但是幸福不是神賜的,不會像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嗎哪那樣從天而降①根據《圣經》記載,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在曠野中沒有食物可吃,耶和華于是將嗎哪從天降下賜給以色列人食用。嗎哪是一種食物,“樣子像芫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摻蜜的薄餅”。,幸福是奮斗出來的。我們想獲得幸福,就必須知曉什么是幸福以及通往幸福的正確道路,也就是塞涅卡說的“首先把我們追求的目標放在面前,然后環顧四周,看看經由哪一條路才能夠使我們盡快趕往那里”[13](29)。從邏輯上說,有什么樣的幸福觀就會采取什么樣的行動追逐幸福。愛財的人求財,愛道的人行道。孔子和塞涅卡都認為真正的快樂和幸福是建立在德性的基礎上的,因此,只有有德性的人才能創造并享受幸福的生活。由此,孔子所謂的快樂之路實際上也就是向善之路和成德之路,具體包括弘道、順性、節情、成教和游于藝等不同方面。
首先是弘道。道即天道,是中國哲學中表示最高存在、真理和價值的哲學范疇。道在孔子思想中居于最高地位,大致相當于西方德性幸福論中的至善,是以“仁”為本質、“禮”為形式的一種道德價值和理想。弘道,也就是過道德的生活,包括學習道德知識、進行道德思辨和道德踐行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踐行,因為道德總是關乎行動的。其一,學習道德知識。孔子所講的“學”,舉其大端,主要有詩、書、禮、樂、書、數等方面,特別強調的是詩和禮兩項。之所以強調詩、禮,是因為二者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他認為《詩》可以激發人們的道德情感,而禮則是人們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其二,道德思辨。包括兩點:第一是自省,即從道德方面自我反省,比如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第二是辨惑,即在容易產生困惑的事上加以辨別,從而達到“不惑”的境界。子張和樊遲都曾問過孔子辨惑的問題。以子張之問為例,孔子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顏淵》)同一個人,當我們喜歡他的時候就希望他活著,而當我們討厭他的時候又恨不得他馬上去死,這就叫做迷惑。辨惑就是要認識、克服和走出這種迷惑。其三,道德踐行。包括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個人層面即個人道德實踐的層面,目標是明明德、修己,是內圣。社會層面即以道德教化民眾,目標是親民、安人、安百姓,是外王。根據《大學》所說,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其實是相通的。從修己以敬、行己也恭到為國以禮與為政以德,可以看到孔子所說的道德踐行也是貫穿于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儒家道德實踐的最高理想就是實現內圣外王的統一。總之,弘道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包括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的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弘道的展開既是成就德性的過程,也是獲得快樂的過程。
其次是順性,也就是按照人的本性生活。正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的本性是上天賦予的,人依照自身的本性生活是對天道的遵循和踐行,由此順性就成了弘道,成了為仁,成了通往道德完滿和幸福生活的道路。關于人性,孔子留給后人的只有“性相近,習相遠”這一句話。陳德述認為“孔子實質上是堅持人性善的”[21](58),曹大中認為“孔子基本上是一個性惡論者”[22](17),趙法生則認為孔子的人性論包括自然性、道德性和超越性三個向度[20](55-61)。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性善論,但他肯定人性中有向善的可能,用西方哲學的話說,就是按照理性生活,讓理性支配欲望和激情。孔子的順性可分為三種情況。其一,克己復禮。克己就是克制私欲。順性絕非由著性子為所欲為,而應當盡可能地克制私欲,以使行為符合禮的規范。禮所代表的就是與人之本性相一致的理性,后來宋明理學中才有“禮者理也”的說法。其二,忠恕,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兩方面。忠恕之道都是從“欲”出發的,即都是基于人性的。當然,這種欲望已經不是一己之私心、私欲,而是一種擴大的欲望或者說共同的欲望,也可以將其稱為同理心。只有擁有這種同理心我們才能夠理解別人,關心別人,才能夠從仁的立場出發去真正愛人。其三,從心所欲不逾矩。這里的“欲”實際上是指天理,即人性能達到的最完滿狀態。從心所欲不逾矩是順性的最高境界。當一個人達到了這種境界,他的行為就會有極大的自由度,同時又能處處合禮中節,《中庸》稱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這就是圣人氣象,也是一種道德化境。
再次是節情。情即情感,是指人們對事物所持的態度體驗,比如好惡等。節情也就是使情感的表達符合一定的原則或規范。性跟情都是中國傳統人性論中的概念,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孔子沒有嚴格區分性與情,他與孟子一樣有“以情論性”[23](27)的傾向。儒釋道三教在處理情感問題上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是滅情派,主張情惡當滅,如李翱的“滅情”說,老子的“無知無欲”說及《壇經》中說到的“能斷百思想”的臥輪禪師都屬于這一派;一是無情派,主張物來順應,不為情所累,莊子、以慧能為代表的南宗禪和理學都屬于這一派。孔子既不屬于滅情派,也不屬于無情派,或可稱為節情派。其主張主要包括:(1)節情須用實情。“情”字在《論語》中一共出現了兩次,一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二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兩個“情”都有“真實”的意思,可見情感的表達最貴真實,不能刻意偽裝。(2)節情須正情。實情強調的是情感的真實性,正情則強調情感價值取向的正確性。以“好”為例,“好德”就比“好色”的價值取向更積極更正向,故孔子有“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之嘆。(3)節情以中和為目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中和指的是情感在還沒表現出來時無所偏向的狀態,表現出來之后又要符合相應的規范,恰到好處。要做到中和,可以通過“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來避免某些極端的情感傾向。
復次是成教。所謂的教主要是指道德教化,以成德為目標,其內容包括文、行、忠、信等。君子成教的實質是作出道德表率,也就是立德,唯其如此,成教才能成為所謂的快樂之路。但成教不限于立德,還包括立功,即成就一番事業。古人所講的事業即平治天下,如《易經》所說“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孔子說的成教主要包括三方面。(1)教化者必須品行高潔。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答云“政者,正也”,明確指出當政者自己要品行端正,才能教化百姓。(2)先富后教,以富帶教。孔子認為富民是教民的前提,只有人民富裕起來才能更好地接受教化。孟子就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為民制產的觀點。(3)軍事教育。孔子曾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在亂世中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讓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的人上戰場是真正的暴虐。孟子后來繼續發揮了孔子的成教思想,他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上》)當作君子三樂之一,更明確了成教是快樂之路。在“君子三樂”外,孟子還提到一種快樂即“王天下”,就是以王道教化天下,這也可以歸結為弘道或者成教。
最后是游于藝。所謂的藝主要是指“六藝”,是當時貴族子弟學習的六種科目。游于藝,也就是以六藝為游樂。朱熹注曰:“游者,玩物適情之謂。”[14](91)君子在閑暇之余以此來適當地放松身心。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1)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認為藝術與道德是相通的,學習藝術的根本目的在于成就道德,也就是徐復觀所講的“為人生而藝術”[24](14)。如詩可以興發人們的道德情感,禮可以為人們提供為人處世的原則,音樂可以涵養人們的性情等。(2)游于藝以志于道和據于德為前提。要做到游于藝,除了要精通六藝,更重要的是要在道德修養上用功,達到較高的道德境界。在“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的序列中,孔子將游于藝放在最后,道理就在這里,他是在強調學藝先學德。(3)藝是成人之德。雖然在孔子的藝術觀中道德是第一位的,但并不意味著孔子只把藝術當做工具看待。子路問孔子如何是成人,孔子答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可見,藝也是一種德性,就跟智慧、勇敢和廉潔等德性一樣。追求藝術既是成為成人之路,也是快樂之路。
孔子所謂的快樂之路,一言以蔽之,就是成為一個有道德的君子。首先,擁有德性或過有德性的生活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快樂,而且是一種比聲色犬馬更好的快樂。其次,德性的快樂是自足的,無需附加別的條件,也不會因為其他因素的改變而消亡。最后,追求道德的完善并不意味著禁欲主義或徹底拋棄感官、物質享受。孔子主張合乎理性地或有節制地享受這些快樂。這樣做不僅是有益處的,而且可以避免附帶的痛苦。那些在享樂方面不懂得節制的人最終將被享樂本身淹沒和毀掉。這就是為什么孔子將過有德性的生活視為真正的快樂之路的原因。在這條快樂之路上,弘道無疑是根本和核心,其他四個方面多是補充。弘道要求人們成為有道德的君子并且盡可能地用道德去引導和教化天下百姓,從而讓生活的世界變得更加公正和有序,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屬于自己的快樂。但是,道畢竟是外在的,以此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無法凸顯人自身的價值,因而在天道和人道之間必須有一個通道,這就是性。順性由此成為快樂之路。中國哲學超越而內在的性格之形成也與此有關。同時人的本性與情感本來就很難剝離,節情就是用理性引導感情,使之得到更真誠和恰當的表達以致中和。相比于弘道,順性和節情也為正當的欲求和情感需要留出了空間,可以彌補其不足。成教和弘道雖然都是講成己成人的,但弘道偏重成己,而成教偏重成人,二者正好相資為用。至于游于藝,其根本目的是陶冶人的性情,讓人在潛移默化中受到道德感化,最終成為道德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