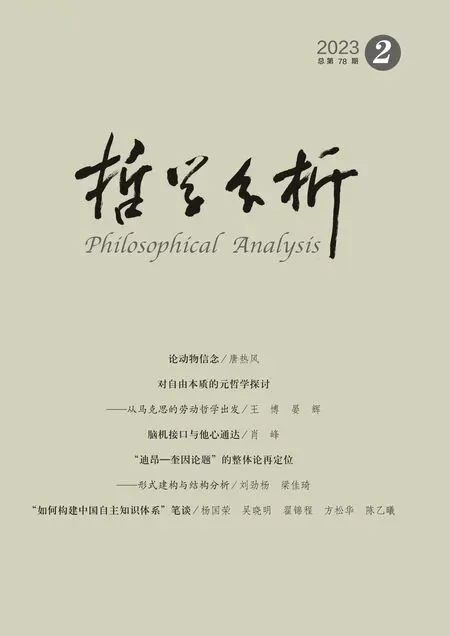海德格爾和阿倫特對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卷的解讀
王寅麗
阿倫特在雅斯貝爾斯的指導(dǎo)下完成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 (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 年在柏林出版,這是她1951 年發(fā)表《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之前出版的唯一著作。1996 年出版的英譯本《愛與圣奧古斯丁》 (Love and St.Augustine),是在此書的英譯稿和阿倫特1960—1961 年對英譯稿的部分修訂的基礎(chǔ)上編輯而成的。在1920—1930 年的德國學(xué)界,奧古斯丁是一個持續(xù)的熱點,被視為存在主義的先驅(qū),引起了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天主教哲學(xué)家瓜爾蒂尼(Romano Guardini)、新教神學(xué)家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的研究興趣,阿倫特那一代青年學(xué)子也沉浸在此學(xué)術(shù)氛圍中,紛紛以奧古斯丁為論文選題。①海德格爾1921 年夏季弗萊堡講座以“奧古斯丁與新柏拉圖主義”為題,該講座已收入海德格爾全集第60 卷,即《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 (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雅斯貝爾斯為他的未完成的《大哲學(xué)家》寫了《柏拉圖與奧古斯丁》兩章;瓜爾蒂尼1935 年發(fā)表了《奧古斯丁的皈依》 (The Conversion of Augustine);漢斯·約納斯的首部著作(1930 年)是《奧古斯丁與保羅主義的自由問題》 (Augustin und das paulinische Freiheitsproblem)。在圍繞著奧古斯丁展開的思想激蕩中,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的關(guān)聯(lián)無疑十分重 要。
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的全面解讀開始于1921 年夏季學(xué)期在弗萊堡大學(xué)開設(shè)的講座。在以“奧古斯丁與新柏拉圖主義”為題的初步考察中,他首先批判了19 世紀德國思想界對奧古斯丁的種種歷史主義闡釋進路,表明他真正關(guān)切的是宗教的“事實生命經(jīng)驗”(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卷的解讀,是他的“實事詮釋學(xué)”(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形成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①James K. A. Smith, “‘Confessions’ of an Existentialist: Reading Augustine After Heidegger: Part I”, New Blackfriars,Vol. 82, No. 964, 2001, p. 273.,并引向了《存在與時間》中對于此在的生存論分析。海德格爾的《奧古斯丁與新柏拉圖主義》和阿倫特的《愛與圣奧古斯丁》都以對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卷的解讀為重點,他們都從“事實生命經(jīng)驗”的角度來解讀奧古斯丁,都堅持他們的解釋是現(xiàn)象學(xué)的而非神學(xué)的。②Hannah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Joanna Vecchiarelli Scott& Judith Chelius Stark (ed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4; 中譯本參見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王寅麗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年版,第39 頁;Martin Heidegger, 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210; 中譯本參見海德格爾:《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歐東明、張振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 年版,第234 頁,譯文略有改動,下同。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的闡釋已得到較多研究③例如:Frederik Van Fleteren (ed.), Marti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s of Saint Augustine: Sein und Zeit und Ewigkeit,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2005; Daniel Dahlstrom, “Truth and Temptation: Confessions and Existential Analysis”, in S. J. McGrath & Andrzej Wierciński (ed.),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Rodopi B. V., 2010;中文研究主要有李成龍:《從幸福生活到實際生活:論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闡釋及其得失》,載《道風(fēng):基督教文化評論》,第54 期,2021 年,第462—501 頁;邵鐵峰:《海德格爾與奧古斯丁的恐懼詮釋》,載《哲學(xué)與文化》2020 年第9 期;王堅:《奧古斯丁的自我生命——海德格爾對〈懺悔錄〉第十卷的現(xiàn)象學(xué)闡釋》,載《科學(xué)·經(jīng)濟·社會》2013 年第1 期。,阿倫特的奧古斯丁解讀也隨著她的博士論文英文版的問世而受到重視,但是阿倫特與海德格爾這兩部論奧古斯丁作品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卻鮮有討論。阿倫特的研究者多數(shù)認為她在政治上對“現(xiàn)象學(xué)存在主義”的發(fā)展是對海德格爾的批判和超越,卻鮮少關(guān)注他們之間的分歧更早產(chǎn)生的這一起源。④例如Villa, Dan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Martin Jay, “The Political Existentialism of Hannah Arendt”,in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7—256; Lewis P.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In Heidegger’s Shadow: Hannah Arendt’s Phenomenological Human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No. 2,1984, pp. 183—211。本文大致依照海德格爾對《懺悔錄》第十卷所作的章節(jié)劃分,將第十卷主要內(nèi)容分為四部分:第1—7 章的引言部分,第8—19 章對“遺忘”和“記憶”的分析,第20 —39 章對“欲望”和“實際生活”的分析,第40 —43 章為結(jié)語。我們首先討論海德格爾和阿倫特在解讀引言部分時提出的不同解讀路向,然后比較他們對記憶和欲望部分闡釋的要點;最后基于以上指出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說明阿倫特在揭示人們組成的“共同世界”方面與海德格爾的“共在世界”的分 歧。
一、《懺悔錄》第十卷第1—7 章引出的解讀路向
奧古斯丁出生于公元354 年,《懺悔錄》寫于公元397 年至401 年間,講述了他從出生直到33 歲皈依上帝為止的生活歷程,被譽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精神自傳。“懺悔”(confession)在書中有認罪、皈依和見證三層含義:對背棄上帝的前半生所犯下的罪過表示悔恨,請求上帝的寬恕;“懺悔”同時也是作者對自己的反省,以回憶的方式從現(xiàn)在之“我”的角度觀看過去之“我”:“但現(xiàn)在我站在你面前,通過這本書向人們既懺悔現(xiàn)在之我,也懺悔過去之我。”(X,3:4)①Augustine,Confessions, Albert Cook Outler (trans.),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4.中譯本參見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0 年版,以下此書引文僅在括號中用羅馬數(shù)字標出卷次,用阿拉伯數(shù)字標出章和節(jié)。這個不同于“過去之我”的“現(xiàn)在之我”在懺悔中呈現(xiàn)出來;另外,“懺悔”(Confessor)在拉丁文中也有“見證”的意思,奧古斯丁在第十卷開篇表示要以文字的形式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的過錯,見證上帝在自己身上的作為:“因此我愿意透過我的懺悔,在你面前在我心中,同時在許多見證人面前這樣做。”(X, 1:1)“懺悔”的言說首先是“在上帝面前”,其次是“在眾人面前”的言說,向著上帝的懺悔喚醒了被遺忘的“內(nèi)在之我”,對眾人見證的目的則是“履行真理”(veritatem facere),揭示真理,希望讀者從中獲得益處。以《懺悔錄》的自傳性質(zhì)來說,本書到第九卷已經(jīng)結(jié)束,第十一、十二、十三卷是從神學(xué)上對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記》開篇的解釋。但第十卷卻是全書最有哲學(xué)性的一卷,是從前九卷的懺悔文學(xué)向神學(xué)主題的轉(zhuǎn)折。在這卷中奧古斯丁提出著名的“自我之問”(“quaestio mihi factus sum” [I have become a question to myself]),并將自我理解為存在于永恒上帝中的“記憶之我”,使得個人生命通過記憶的中介與永恒生命匯合。前九卷的自我敘事匯入后三卷更為宏大的圣經(jīng)創(chuàng)造敘事之中,自我的故事在創(chuàng)造故事中獲得意 義。
正如J. K.史密斯指出的,奧古斯丁主題對存在主義傳統(tǒng)最深刻的影響之一是自我對于理解存在或生存的優(yōu)先性。②James K. A. Smith, “‘Confessions’ of an Existentialist: Reading Augustine After Heidegger: Part I”, p. 275.在第十卷開篇講述了“懺悔”的含義和目的之后,奧古斯丁自問作為懺悔者的“我”是誰,既然我在上帝面前是完全袒露的,為何還要向他懺悔?別人聽我談?wù)撟约海荒苷J識過去的我,卻不認識現(xiàn)在的我,“而這方寸之心才是真正的我”(X. 3:4)。在奧古斯丁看來,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誰”,真正的我既不是我的人生故事,也不是別人眼中的我,而是這個“內(nèi)在之人”(ipse intus)。就像莎士比亞創(chuàng)造了哈姆雷特,從而了解他的全部一樣,“我是誰”的問題,即我的存在和意義的問題,要從他存在的源頭、創(chuàng)造主那里得到回答。阿倫特評論說,奧古斯丁這種轉(zhuǎn)向自身存在的源頭,從“造物主—受造物”(creatorcreature)的語境下來理解人之存在的方式,隱含著一種根本的人類依賴性(human dependence):“人非自造,乃是被造,這個事實意味著人存在的意義感既在他自身之外,又先于他自身。”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49, p. 50;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第98 頁、第100 頁。
在《懺悔錄》第十卷第6 章,奧古斯丁從對自我的發(fā)問轉(zhuǎn)向?qū)ι系鄣陌l(fā)問:我愛上帝,究竟愛的是什么?(X. 6:8)海德格爾認為奧古斯丁在懺悔態(tài)度中所傳達的所有現(xiàn)象都處在“尋求和擁有上帝這一任務(wù)之中”,“重要的是指出經(jīng)驗上帝得以付諸行動的真正條件”。②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 S. 283;海德格爾:《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第335 頁。如同《存在與時間》中對此在的發(fā)問從屬于存在是什么的根本問題一樣,在這里他指出“我”通過愛的經(jīng)驗行為獲得對“上帝”(存在)的領(lǐng)會。海德格爾以現(xiàn)象學(xué)方法解讀“神之愛”:“當他活在神之愛(the love of God)中時,有什么向‘充實性直觀’(fulfilling intuition)呈現(xiàn),什么東西滿足和充實他在對神之愛中所意指的東西”③Ibid., S. 178—179;同上書,第192 頁。。奧古斯丁把人分成“外在之人”和“內(nèi)在之人”(homo interior),外在之人從物質(zhì)對象的經(jīng)驗(形貌的秀麗、暫時的聲勢、肉眼所好的光明燦爛等)中不能把握上帝,上帝也不在大地海洋、飛禽走獸、日月星辰當中(“我問這一切事物,它們皆回答‘我們不是你所尋求的上帝’”)。但我經(jīng)驗到我內(nèi)在擁有另一種“內(nèi)心的光明、音樂、馨香、飲食、擁抱”。這類經(jīng)驗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在上帝那里永存。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個“內(nèi)在之人”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人之靈魂,也不能以希臘—羅馬哲學(xué)中的理性靈魂來理解,因為內(nèi)在經(jīng)驗到的上帝是“我的上帝”,這個內(nèi)在者“被經(jīng)驗為在人之中滲透身體、驅(qū)動和為之貫入生機的東西”④Ibid., S. 180;同上書,第194 頁。,從而上帝被經(jīng)驗為“越—出”(ek-static)我的靈魂者,表明靈魂本身有待被超越。海德格爾因此區(qū)分了奧古斯丁尋求上帝的兩種路向,一種是把上帝視為經(jīng)驗的最高“對象”,存在者的最高秩序來尋求,一種是進入此在的具體歷史—生存分析。“通向秩序關(guān)涉和對象關(guān)涉的生存上的突破之進路(Ansatz)——心理學(xué),或者對于以具體的歷史的—生存的方式來自實際生活的問題之解釋和領(lǐng)會。”⑤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S. 181;《 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第196 頁。接下來他將《懺悔錄》第十卷第8—19章闡釋為第一種尋求上帝的路向,第20 —39 章闡釋為第二種尋求上帝的路向。⑥參見Ryan Coyne,Heideggers Confessions: The Remains of Saint Augustine in“ Being and Time” and beyon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p. 63—64。
阿倫特在《愛與圣奧古斯丁》中對奧古斯丁的解讀,著重于分析“上帝之愛”與世俗社會生活的“鄰人之愛”(neighborly love/N?chstenliebe)之間的張力。⑦阿倫特在博士論文德文版中輪流使用“鄰人”(der Nachbar/der N?chste)和“他人”(der Anderer),第二章第3 節(jié)標題為“近人之愛”(Dilectio proximi)。既然“愛鄰如己”的要求包括在基督教“愛上帝”的命令中,她追問這兩種愛在奧古斯丁關(guān)于愛的概念中是否內(nèi)在一致。“自愛”(amor sui)是將“上帝之愛”與“鄰人之愛”聯(lián)系起來的樞紐,但她發(fā)現(xiàn)奧古斯丁的“自愛”實際上有兩個并不一致的意涵:一種是在“愛作為欲求”的概念語境中以希臘哲學(xué)的自足、無依賴性來定義的,在那里,真正的自愛是從無欲求的“絕對未來性”(absolute futurity)角度否定現(xiàn)實自我,并從“愛的秩序”出發(fā)合宜地、冷漠地愛每個人。對奧古斯丁而言,“這種自忘(selfforgetfulness)和對人之存在的徹底否定的最大困境是,它使基督教愛鄰如己的核心命令變得不可能了”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27, p. 28;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第69、71 頁。。另一種是在“造物主—被造物”的概念語境中來定義自愛,“自愛”始于人的自我追問(quaestio mihi factus sum)。“正是這種對自我的尋求,讓他最終轉(zhuǎn)向上帝。”②Ibid, p. 25; 同上書,第66 頁。在人轉(zhuǎn)向上帝的同時,上帝之愛(amor Dei)將人的生命“喚入存在”,讓人的生命不再是無。后一種“自愛”概念肯定人的依賴性,因為人從無中被造,人的存在從無到有,介于存在與不存在之間,這種變易、不確定的存在方式需要和絕對存有相連,即人的存在過程始終依靠上帝之愛的扶持。她認為這個自我就是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十卷揭示的“內(nèi)在之人”,造物主內(nèi)在于我的居所。這個“內(nèi)在永恒”(internum aeternum)是我所缺乏、所不是者,但它卻是上帝之愛和鄰人之愛的深奧核心,“人本質(zhì)的‘居所’,這個肉眼不可見的‘內(nèi)在之人’正是不可見的上帝工作的領(lǐng)域”③Ibid, p. 26; 同上書,第68 頁。。在她看來,正是自我和上帝之間的愛的關(guān)系——我愛“我的上帝”和上帝的覓人之愛,體現(xiàn)出人與上帝的相似性,人所具有的獨特“上帝形象”(imago Dei)本質(zhì)上是一種建立愛的關(guān)系的能力。這個我在愛中把握的“我的上帝”,我的渴求和愛的正確對象,是奧古斯丁內(nèi)在自我的核心,其“心靈的本質(zhì)”。人心隨著時間變換,心靈的本質(zhì)卻超越了時間,“我可以憑借愛而歸屬于這一本質(zhì)存有,因為愛賦予其歸屬”,超越于我的永恒本質(zhì)在我自身之內(nèi),“因為你就是你所愛”。④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26;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第67—68 頁。可見,阿倫特與海德格爾都嘗試對奧古斯丁的上帝觀作出區(qū)別于古希臘式的,特別是新柏拉圖主義上帝觀的“宗教生活經(jīng)驗”闡釋,海德格爾將尋求上帝引向此在(自我)的生存分析,阿倫特則引向?qū)圩鳛槿酥嬖诘臉?gòu)成性活動的分 析。
二、《懺悔錄》第十卷第8 章的“遺忘難題”
《懺悔錄》的作者在自我見證中對“我是誰”的發(fā)問,也是對“我的上帝”為何的發(fā)問。站在基督教立場上,奧古斯丁認為上帝是人的創(chuàng)造者和生命本源,人對自身的探索必須在上帝之內(nèi)進行,而人要洞見本源性的上帝,就需要靈魂的內(nèi)在轉(zhuǎn)向。在他那里,靈魂向內(nèi)的探索同時是一個靈魂上升的過程:“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層級上升趨向我的創(chuàng)造主。我進入記憶的領(lǐng)地,那里是儲藏感官對一切事物所感受而進獻的無數(shù)影像的府庫。”(X, 8:12)正如吳飛指出的,記憶有“連接自我與上帝之存在的功能”①吳飛:《奧古斯丁與精神性存在》,載《哲學(xué)動態(tài)》2018 年第11 期,第51 頁。。在《懺悔錄》第十卷第8 至19 章,奧古斯丁對上帝的尋覓從自身以外轉(zhuǎn)回到心靈記憶中“自外而內(nèi)”的找尋。記憶里包含著無數(shù)事物的圖像,以及我們關(guān)于它們同時想到和感受到的一切,經(jīng)過思想的收集、加工、增損都儲備在里面,隨時聽從我們的召喚,構(gòu)成“一種廣闊而無限的內(nèi)在”(penetrale amplum et infinitum)②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 S. 182; 海德格爾:《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第196 頁。。奧古斯丁依次考察了五種記憶類型:第一種是感性對象的影像,包括顏色、聲音、氣味、味道等;第二種是非感性的知識,如文學(xué)、論辯學(xué)以及各種知識問題;第三種是數(shù)理對象,包括數(shù)學(xué)和邏輯;第四種是內(nèi)心的情感,如對快樂、希望、憂愁、恐懼的記憶,以至于人能喜悅地回想曾經(jīng)的悲傷,或憂傷地回想往昔的快樂;第五種是“對遺忘的記憶”。在論及最后一種類型時,他闡述了著名的“遺忘”疑難(aporie)——遺忘是記憶的缺失,既然遺忘,便無從記憶,但我們又怎么會記得我們忘記了什么呢?比如我們常常忘記了什么東西,但當別人問是不是這個或那個時,我們又能說是這個或不是這個,可見并非全然忘記。③對“遺忘疑難”的分析,參見保羅·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5—126 頁。“遺忘疑難”表明記憶的“內(nèi)在”空間有著自身不可觸及的深層性,自我與永恒上帝之間存在著深不可測的距離。奧古斯丁一邊感嘆記憶的廣大深邃令人敬畏,一面繼續(xù)向上帝發(fā)問:你在哪里,我到哪里去找你?——“我將超越記憶而尋找你。但在哪里尋見你,……如果在記憶之外尋找你,那么我已不記得你。如果根本不記得你,那么我怎能找尋你呢?”(X, 17:26)可見心靈更根本的遺忘是對上帝的遺忘。奧古斯丁遍歷記憶的角角落落找尋上帝:“我進入了心靈的最內(nèi)室,這是記憶專為心靈而設(shè)的——因為心靈也回憶自身——你也不在那里,因為你既不是身體影像,也不是活人的情感(如我們歡樂或悲傷時感受到的,或我們愿望、恐懼、回憶、遺忘,諸如此類時感受到的),又不是我的心靈本身;你是心靈和所有這一切的主宰,而你永不變易地居于這一切之上”(X, 25:36)。人的心靈中所有關(guān)于物質(zhì)、情感、思想的記憶,都不是對上帝的記憶,后者居于人的心靈之中,卻超越人的心靈之上。對奧古斯丁來說,上帝正是透過心靈的內(nèi)在空間向他顯露:“到哪里能找到你以便認識你?只能在你之內(nèi),在我之上”(X, 26:37)。
奧古斯丁用“遺忘難題”揭示出心靈的內(nèi)在廣闊空間,也引出人有著對“幸福生活”(Beata Vita)的回憶,以及幸福求而不得、人生無法免于被試探誘惑的困境。他在早期作品《論幸福生活》中就表述了幸福在于擁有上帝、享受上帝的觀點,不僅因為在他繼承的古典的至善幸福論中上帝是最高善,以及在新柏拉圖主義的存在序列中上帝是至高完滿存在,還因為奧古斯丁從基督教立場指出人有一種根本的存在性缺乏——如《懺悔錄》開篇所嘆:“我們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懷中,便不會安寧”。在第十卷第20 章,他說:“我尋求你,就是在尋求幸福生活。”他指出,人人都意愿幸福,卻并不擁有幸福。可是沒有幸福,人們又是從哪里知道幸福呢?也許它存在于我們的記憶中,我們總有過一些幸福生活的模糊影像,對幸福生活的記憶最終讓我們渴望幸福本身,即歸向作為完滿存在的上帝。“幸福生活就是朝向你、在你之內(nèi)、為了你而歡樂,這就是幸福,此外無他。”(X, 22:32)在考察幸福生活時,奧古斯丁不得不正視人的欲望享樂的問題。在塵世生活中,自我本有被世間欲望所吸引而“消散在萬物中”(X,29:40)、靈魂又總是受“習(xí)慣”的牽引而下墜;他在第30 —39 章依此分析了“眼目的情欲”“肉體的情欲”“今生的驕傲”這三種貪欲,并深深認識到人靠自身能力無法抵擋心靈的混亂失序狀況,“我對我自身成了一個謎”(X,33:49),而上帝則是自我之謎的真正答案。第十卷卷末(第43 章)指出只有上帝之愛才能拯救人脫離罪惡重壓下的生活,呼應(yīng)了后三卷關(guān)于圣經(jīng)的創(chuàng)世主 題。
三、“誘惑”和“愛”的現(xiàn)象學(xué)闡明
奧古斯丁關(guān)于靈魂在記憶的內(nèi)在空間上升的觀念,受到新柏拉圖主義的普羅提諾的影響。普羅提諾主張靈魂的自我轉(zhuǎn)向和逐級上升運動,靈魂轉(zhuǎn)向之所以能夠發(fā)生是因為至善、絕對或上帝的理念已經(jīng)存在于靈魂記憶之中。不過與普羅提諾不同的是,奧古斯丁的記憶回轉(zhuǎn)之路始終受一個“覓人的上帝”的引導(dǎo)。①參見章雪富:《救贖:一種記憶的降臨——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卷至第十三卷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35 頁。海德格爾在這里批評奧古斯丁的記憶概念仍受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不是關(guān)注歷史性此在贏得“幸福”的生存運動,而是受永恒不變的“持存”的規(guī)整:“記憶(memoria)沒有徹底地、生存地付諸實現(xiàn),毋寧說,按希臘的講法,它在內(nèi)容上是下墜的,不是它如何‘曾是’與他同在以及在‘曾是’中如何‘是’。”②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 S. 247;海德格爾:《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第286 頁。相比于記憶,他更為重視奧古斯丁的“遺忘”在生存運動中的地位。“遺忘”是記憶的不在場,作為當前未進入掌握之中的東西,但這里的遺忘不是記憶的徹底缺失,而是“遺忘的記憶”(即我記得遺忘本身)。在他看來,奧古斯丁的遺忘讓所關(guān)涉意義的“不在場”得到了把捉,“先把握”(Vorgriff)得到了非當下的呈現(xiàn)。海德格爾指出了它在現(xiàn)象學(xué)上的兩層含義。第一,它與當下呈現(xiàn)之物的意向性關(guān)涉意義——原本的擁有和可能會失去的擁有,來到隱而未現(xiàn)的把握之中:“遺忘不是回憶的徹底缺失,它有著意向性關(guān)涉意義。從關(guān)涉上理解就是我們在失落某物時,我們?nèi)匀弧畵碛小雹費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 S.191; 海德格爾:《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第208—209 頁。。第二,“遺忘”喚起更深層次上的存在論遺忘:在尋找的時候,還有什么是可供我資用的?我在為著什么尋找?什么東西在逃離我而去?在奧古斯丁那里尋找發(fā)生在對上帝之為真實生命的失落和找尋中,在海德格爾看來,奧古斯丁意義上的上帝經(jīng)驗并不是孤立的具體行為或理論構(gòu)型,而是“存在于本己生活的歷史實相(der historischen Faktizit?t des eigenen Lebens)的經(jīng)驗關(guān)涉中”②Ibid., S. 294; 同上書,第360 頁。,故而,“在我對上帝的尋找中,在我之中的某物不僅得到了‘表達’,而且構(gòu)建著我的事實生命和我對它的關(guān)切”③Ibid., S. 192; 同上書,第209 頁。。
近代以來,笛卡爾的“我思”通常被視為“奧古斯丁式自我”的繼承,但海德格爾在《奧古斯丁與新柏拉圖主義》中明確批評說,笛卡爾的主體理論把自我研究帶到了錯誤的方向,他主張:“奧古斯丁意義上的自身確定(self-certainty)和自身擁有(self-possession)完全不同于笛卡爾的‘我思’(cogito)的明證性。”④Ibid., S. 298; 同上書,第356 頁。自我不是具有明證性的“我思”,而是始終處在不確定、不安、對自身的“不擁有”的開放性生存過程中。海德格爾對此的分析集中于后半部分的“誘惑現(xiàn)象學(xué)”。他指出,在奧古斯丁那里,自我流散于萬物,在自身之外尋求意義。當上帝的召喚臨到它,它被命令對抗流散,對抗生命的分崩離析來“集聚”自身。“將你所命賜予我,并依你所愿來命令我。”(X, 29:40)但這個對抗流散的反向運動在自身中并不能一勞永逸的贏獲,生命不斷地將自身向反方向拉扯,從而奧古斯丁式的自我始終具有一種“越—出”(ek-static)的特征。“我永遠不能訴諸一個靜止的時刻,在其時我貌似看透了我自己;總是有下一個時刻能讓我跌倒,并暴露出我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我。出于這個原因,只要擁有—自身畢竟是可以實現(xiàn)的,它就總是處在朝向和遠離生命的拉扯之中,一種來來回回。”⑤Ibid., S. 217; 同上書,第244—245 頁。在海德格爾看來,試探、誘惑(tentatio)是據(jù)以理解宗教經(jīng)驗生活的本質(zhì),他以奧古斯丁引用的《約伯記》名言——“整個人生是一場試探”——來概括“此世生活”的特征。接著也依照“肉體的貪欲、眼目的情欲、世俗的驕傲”⑥奧古斯丁關(guān)于世間欲望的三種劃分來自《新約·約翰一書》2 章16 節(jié)。的順序分析了誘惑的三種形式,對他來說,這不是自我與世界、肉體與靈魂、“愛世界”與“愛上帝”之間的搏斗,而是作為生命實際生活基本特質(zhì)的“關(guān)切”(curare/care)的三種形式。誘惑的前兩種形式分別來自周圍世界(感覺和認知)引起的愉悅、好奇,感覺是與某物打交道(Umgehen)的欲求,認知是在各種不同的范圍和領(lǐng)域里的尋視(Umsehen),前兩者指向“周圍世界”(Umweltlich)。第三種形式“世俗的驕傲”(ambitio saeculi)則來自與他人共在的世界,因為我們從那里獲得對自身價值和自我意蘊的關(guān)切,正是與“周圍世界”和“共在世界”(Mitweltlich)的無休止對抗,讓信仰生活成為真實的生命。如李成龍所指出的,對誘惑的存在論分析是《存在與時間》中分析“沉淪”概念的基礎(chǔ)。①李成龍:《從幸福生活到實際生活:論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闡釋及其得失》,第488 頁。另參見《存在與時間》中的論述:“此在為它自己準備了要去沉淪的不斷的引誘,在世就其本身而言是充滿誘惑的。”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6 年版,第250 頁。
阿倫特仍然通過分析愛的概念來說明奧古斯丁對古典幸福論的超越,愛者的最終目標是他自身的幸福,但他并不擁有幸福,而是在其所有活動中被非他自身的某種東西所引導(dǎo),被驅(qū)向自身之外。她認為讓奧古斯丁擺脫斯多葛學(xué)派和普羅提諾影響的,正是他對人之為人的“依賴性”(dependency),非自足性的體驗,也是促使他歸向上帝的經(jīng)驗,即人必須與自身之外的他人、世界或上帝建立聯(lián)結(jié)。阿倫特以愛的兩種“概念語境”(conceptual context)——希臘哲學(xué)和新柏拉圖主義的“愛作為欲求”語境和基督教的“創(chuàng)造主—被造物”語境,來分別闡釋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十卷所描繪的“欲望”和“記憶”的尋求模式。在“愛作為欲求”的定義中,欲求規(guī)定了愛者和愛的對象:“欲望介于主客體之間,通過把主體轉(zhuǎn)化為愛者,把客體轉(zhuǎn)化為愛的對象,消除了它們之間的距離。……既然人非自足,總是要渴求在他自身之外的某物,那么他是誰的問題就只能通過他欲望的對象來回答,而不是像斯多葛學(xué)派認為的,通過對欲望本身的壓抑、消除來回答:‘因為你就是你所愛’。”②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18;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第57 頁。貪愛(cupiditas)和圣愛(caritas)在此的區(qū)別在于愛的對象不同,前者是對屬世對象的愛,渴求塵世中能帶給人的滿足之物,卻總是伴隨著對喪失的恐懼(fear of losing),并最終落在對死亡的最大恐懼中。這種根本的恐懼只有當我們所欲求的對象是永無喪失之虞的“永恒”時才會消除。在此語境下,“圣愛”尋求永恒的“絕對未來”或“無未來的現(xiàn)在”,“這個無未來的現(xiàn)在——不再關(guān)注具體的善,因為它本身就是至善(summum bonum)——就是永恒”③Ibid,p. 13;同上書,第50 頁。。“圣愛”的永恒視角建立的秩序,規(guī)定了任何人或任何物都不能“因其本身的緣故”而被愛或被渴求,而應(yīng)當“為著上帝的緣故”被愛,只有上帝才能“因其自身”被愛,簡言之,人對世界的恰當態(tài)度是“使用”(usi)而不是“享受”(frui),只有上帝才是享受的對象。由此,人自身的生命被設(shè)定為一種欲望相關(guān)物時所必然呈現(xiàn)的死亡恐懼,通過圣愛概念得到了解決,但阿倫特認為,使用和享受的區(qū)分再次讓“鄰人之愛”的概念陷入矛盾:“一個生活在絕對未來之期盼中,并且把世界及其上的一切當成使用物(包括他自己和鄰人在內(nèi))的人,為何應(yīng)當重視和建立這種在所有愛中都隱含的關(guān)系,并且明確地聽從基督教命令:‘汝當愛鄰如己’?”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39;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第85 頁。
在“愛作為回憶”的語境中,對幸福生活的尋求從“期待的未來”(anticipated future)轉(zhuǎn)向“記憶的過去”(remembered past),這里,愛不是以“指向”(aiming at)未來的方式,而是以“回轉(zhuǎn)”(referring back to)到過去的方式關(guān)涉對象:“奧古斯丁將喚回那些逃離我記憶之物的方式,等同于我認識的方式,以及我愛或渴求的方式。”②Ibid, p. 94.我們對所欲之善的看法,依據(jù)自身對幸福生活的知識,因而我們總是多少知道一點幸福生活,才會尋求和渴望它。對幸福生活可能存在的知識,是在先于一切經(jīng)驗的純粹意識中被給定的,它保證了我們一旦在未來跟它相遇,就能認出它來。在自我從“消散”中聚攏,收斂心神的回想(recollection)中,過去被回憶帶入當下,他也同自身的整個生存聯(lián)合。記憶的性質(zhì)超越當下經(jīng)驗返回過去,正如欲望的性質(zhì)是超越當下和指向未來:“鑒于記憶提交的知識必定在每個特定過去之前先以存在,它實際上就指向一個超越的、超出塵世的過去,即人類存在本身的源頭。”③Ibid, p. 48;同上書,第97 頁。記憶的回返最終指向一個先于所有塵世經(jīng)驗可能性的過去,人們回轉(zhuǎn)到他們的源頭,即作為造物主的上帝。作為回憶的愛同樣區(qū)分為“欲愛”和“圣愛”,“欲愛”返回到我們一出生就進入的、我們所屬的世界中,把這個世界當成自己的源頭,“反認他鄉(xiāng)是故鄉(xiāng)”,隨從習(xí)慣(consuetudo)的力量而屈服于世界;“圣愛”返回到世界“之前”的亙古源頭——它真正的“所來自”,認識到世界也是被造而有的。阿倫特認為在“愛作為回憶”的語境中,奧古斯丁最終超出了希臘式的存有概念,轉(zhuǎn)向基督教的“造物主—受造物”的存有概 念。
四、“對世界的懼”和“愛世界”
阿倫特在1946 年的《什么是存在哲學(xué)》一文中批判了海德格爾的基礎(chǔ)存在論,1958 年的《人的境況》更以人們在世的“協(xié)同行動”(act in concert),來回應(yīng)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孤獨此在的本真決斷。人們以往認為,阿倫特對海德格爾的批判主要是她在納粹上臺后積極介入政治的思想產(chǎn)物,但通過前面的分析就發(fā)現(xiàn),其博士論文(1929 年)在主題和方法上已受到海德格爾的奧古斯丁講題的影響,同時她已通過奧古斯丁開啟了與海德格爾的批判對話,從強調(diào)人離開世界的“有死”轉(zhuǎn)向人在世界中的“誕生”,從對這個世界的“懼”轉(zhuǎn)向?qū)@個世界的“愛”。
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們都把奧古斯丁尋求上帝的核心解釋為對自我存在的尋求,并通過奧古斯丁論幸福生活的闡釋,引向“誘惑”和“愛”的實際生活定向問題。海德格爾所謂的“誘惑”也是出于愛,出于欲求的愛。他說:“愛的傾向是對自身的關(guān)切。真正的amor sui是對自己的愛,正是這一點導(dǎo)向了誘惑,也因此產(chǎn)生了嚴重的愁煩(Molestia)。”①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sen Lebens,S. 294;海德格爾:《宗教生活現(xiàn)象學(xué)》,第350 頁。海德格爾將沉迷于世界誘惑而消散自身、遺忘自身的“自愛”,解釋為“對世界的畏懼”,并以奧古斯丁“奴性之畏”來闡釋,真正的自愛或畏懼則是“圣潔之畏”。“第一種畏懼(奴性之畏)即‘對世界的畏懼’(出自周圍世界和共同世界的畏懼),是攫住和壓倒一個人的不安。相比之下,timor castus(圣潔之畏)是由真正的希望,由它自己所激發(fā)的信任所驅(qū)動的’自我畏懼’。”②Ibid., S. 297;同上書,第355 頁。如邵鐵峰分析指出的,奧古斯丁的“奴性之畏”對應(yīng)著海德格爾作為“現(xiàn)身情態(tài)”(Befindlichkeit)的“焦慮”,此在消散于常人和共同世界的非本真存在方式,奧古斯丁的“圣潔之畏”對應(yīng)著召喚此在回到最本己的存在方式的本源畏懼經(jīng)驗。③參見邵鐵峰:《海德格爾論奧古斯丁的畏》,載《哲學(xué)與文化》第47 卷第9 期,第138 頁。這里的“懼”和“愛”既是道德和心理上的情感,也是人經(jīng)驗世界的實際指引。不過在阿倫特那里,愛有著更積極的內(nèi)涵,借助對愛作為記憶而非欲求的定義,她將真正的“自愛”定義為對“記憶之過去”的回返,并在論文最后找到了“鄰人之愛”的真實基礎(chǔ)——鄰人是與我擁有共同命運和共享歷史“事實”的共同體伙伴。阿倫特在英文修訂版中還特地增補了一句對《存在與時間》的批評:“是記憶而非期待(例如,在海德格爾的進路中對死亡的期待)賦予人的存在以統(tǒng)一性和整體性。”④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p. 56;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第108 頁。
阿倫特晚年將其政治思想概括為“愛世界”(Amor mundi /love for the world),實際上,“愛世界”的表達最早出現(xiàn)在她的博士論文中。⑤Ibid.在那里,她指出奧古斯丁所用“世界”一詞的雙重含義:既指作為受造物的世界,也指居住在其中的愛世界者(die dilectores mundi)。對于奧古斯丁“世界”含義的同樣說明也出現(xiàn)在海德格爾1929 年《論根據(jù)的本質(zhì)》一文中。⑥“我們也用世界來稱呼那些由于愛世界而居住在世界中的人”——參見海德格爾:《論根據(jù)的本質(zhì)》,載《路標》,孫周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0 年版,第170 頁。阿倫特在博士論文的注釋中引用了此文,并指出了她與海德格爾在世界闡釋上的共同點和分 歧:
在海德格爾對世界概念的歷史概述中,奧古斯丁式的世界概念是被提及的其中之一。海德格爾也區(qū)分了奧古斯丁的mundus[世界]一詞的兩種含義:世界一方面是ens creatum[受造物] (對應(yīng)我們這里的神圣作品,天和地),另一方面世界被設(shè)想為愛世界者。海德格爾只在后一種意義上闡釋:“世界,因而意味著在整體中的存在,是作為決定性的如何,據(jù)此,人的生存關(guān)聯(lián)到存在(ens),向存在行動。”他的解釋因此僅限于把世界闡明為“本質(zhì)上與世界的共在”,而他提到的另一個世界概念卻仍未得到闡釋,我們的闡釋目標正是使這兩方面得到理解。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66, note 80;相同注釋段落參見Hannah Arendt, 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 Berlin: Julius Springer Verlag, 1929, S. 42。
奧古斯丁批評那些“愛世界者”,即逗留、沉溺于世界之人,被世界的“習(xí)慣”牽引。對于海德格爾來說,世界是施加意義的“存在論構(gòu)造”,也造成了“此在”與世界的共在,“沉淪”從生存論上規(guī)定著在世。但如同奧古斯丁貶低“俗世”一樣,海德格爾也用“非本真存在”“閑言”“好奇”“兩可”來標識這種“沉淪”、跌落于世的存在方式。阿倫特認為海德格爾“提到的另一個世界概念卻仍未得到闡釋”,即作為受造物的世界概念未得到闡釋,暗示海德格爾受奧古斯丁影響而對世界采取了消極評價。借助“圣愛—貪愛”的框架,阿倫特實際上區(qū)分了兩種對世界的愛,兩種“愛世界者”:一種是沉溺于世界,被欲望和喪失的懼怕所支配的“愛世界者”,一種是響應(yīng)上帝的創(chuàng)造之愛的“愛世界者”。“圣愛”在她后來的思想中轉(zhuǎn)化為對持久共同的人造世界的照料維護,對人們之間“共同世界”的關(guān)愛。②參見王寅麗:《探索阿倫特“愛世界”的奧古斯丁起源》,載《道風(fēng):基督教文化評論》第52 期,2020 年,第63—83 頁。
五、結(jié)語
奧古斯丁的“自我問題”開啟了西方思想史上對自我存在的重要探索,海德格爾和阿倫特都將其在神學(xué)語境下展開的自我追問解讀為對人與世界、與他人關(guān)系的“生存處境”現(xiàn)象學(xué)分析。對他們來說,奧古斯丁的存在主義神學(xué)和他繼承下來的與新柏拉圖主義的張力,以潛伏的形式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主體經(jīng)驗與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的對抗。海德格爾對“誘惑”的現(xiàn)象學(xué)闡明強調(diào)欲望在自我真實生命經(jīng)驗中的地位,他對誘惑的存在論分析演變成了他在《存在與時間》中對“沉淪”概念的分析。阿倫特的“愛”則重視記憶帶來的反思和自我構(gòu)建,通過對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的批判闡釋,她在博士論文中初步探討了確立“鄰人之愛”可能性的新原則,即以“記憶之過去”形成的共享命運和共同歷史事實基礎(chǔ)上的共同體伙伴關(guān)系。本文對海德格爾的奧古斯丁解讀與阿倫特的博士論文的比較,既顯示出他們思想共有的奧古斯丁式存在主義的背景,以及他們對奧古斯丁論題所作的世俗化轉(zhuǎn)換,也顯示出他們在“世界”概念上的進一步分歧。與海德格爾提出的“對世界的畏懼”不同,阿倫特在她的奧古斯丁論文中為 “愛世界”的思想作了準 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