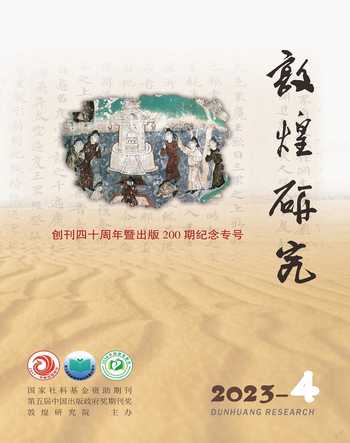敦煌彌勒經變圖中戒壇與戒場
湛如



內容摘要:在廣律、戒本的記載中,諸部派有關戒場與戒壇的記載有不明之處,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對出家受戒儀軌以及戒壇的形式做出了補充且明確規定。通過對敦煌莫高窟與榆林窟彌勒經變中戒場受戒實際情況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圓形帷幕剃度受戒場景,認為戒場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幾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道宣對戒壇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對僧尼受戒的嚴格管控。
關鍵詞:戒場;戒壇;道宣;敦煌;彌勒經變
中圖分類號:K87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3)04-0126-10
The Ordination Platforms and Ordination Settings in
Maitreya Sutra Illustrations
ZHAN R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Among the Buddhist canons of precepts, the records taken down by different schools of Buddhism regarding the settings and platforms suitable for ordination are either unclear or inconsistent. Therefore, the text Sifenlü Shanfan Buque Xingshichao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A Revision of the Vinaya in Four Parts Created through Simplific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written by the Tang dynasty monk Dao Xuan provides a highly pertinent supplement to these regula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ctual practices and places by which monks were ordained by examining depictions of these ceremonies in the Maitreya sutra illustrations in both the Mogao Grottoes and the Yulin Grottoes; the painting of being ordained behind a semicircular curtain in Mogao cave 445, for example. The results poin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that can explain the changes in ordination ceremony practices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irst is that the famous monk Dao Xuan began widely recommending the use of ordination platforms; the second is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ordination of monks and nuns through official laws.
Keywords:ordination setting; ordination platform; Dao Xuan; Dunhuang; Maitreya Sutra illustr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引 言
佛教作為一種異域的宗教,自從進入中土之后就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適應與本土化過程。在此進程之中除了佛教的語言與經典、佛教教義與思想之外,佛教制度的本土化與中國化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層面。這其中既包括比如佛教寺院制度、宗派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在地化,在佛教僧團內部的規章制度上,也呈現出一個緩慢但堅定的演化過程。本文通過以圖證史的方式,來試圖從佛教制度的一個側面,即佛教僧人受戒儀式發生的場所——戒場到戒壇的轉變,來探討在中國中古史上極為重要的轉折期之中佛教教團內部所產生的深刻變化。這其中既反映了印度本土宗教元素所具有的強勁生命力與影響力,同時也看到,在中土背景之下的政治、文化要素對印度原始宗教元素的不斷侵蝕,并最終讓中國佛教以一種全新形式實現了脫胎換骨式的轉變。
自曹魏嘉平二年(250),曇摩迦羅(Dharmakāla,活躍于222—250年間)翻譯出《僧祇戒心》并為中國僧人受戒后,一部分中國僧人便開始追求戒律的正統性,以獲得“如法如律”的宗教生活。法顯(342—423)西行開啟了向印度求取律典的篇章,到唐代這種熱情仍在持續,義凈(635—713)在前往印度求取廣律的同時,還寫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了當時前往西域求法高僧的盛況{1}。在這些高僧前往印度以自己的親身見聞,為唐代的受戒儀軌帶來印度樣本的同時,唐朝本土的高僧則開始通過對經文律典的鉆研,試圖復原出佛陀在世時受戒的儀軌。道宣(596—667)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通過對文獻的鉆研,繪制出了他想象中祇園精舍的樣式,以及戒壇的樣式和受戒儀軌{2}。中國的受戒儀軌在這兩股潮流的沖擊下,呈現出眾多形態,但是隨著時代變遷,道宣學說成為了中國律學的主流觀點{3},其他受戒儀軌漸漸悄然淹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
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印度文明流向中土時在此留下痕跡,中華文明西出陽關時也在此打下印記。從這個角度而言,敦煌現存的資料是還原唐代受戒儀軌的最佳切入點,因此本文以敦煌壁畫中彌勒經變中所描繪的受戒場景為基礎,對唐代的受戒場所進行探討。
彌勒經變是指以《彌勒下生經》的內容進行繪畫創作的敦煌壁畫,其中含有大量的受戒場景。壁畫所描繪的眾多場景中,受戒場所包含有兩種狀態:一是在地面為僧人受戒而建造的方形壇,即有戒壇的受戒(以下簡稱為戒壇受戒);二是在平地上用布圍起來的場所,即無戒壇的受戒(以下簡稱為戒場受戒)。而戒壇、戒場的稱呼,可追溯到《四
彌勒經變雖然是從經典演變而成的壁畫,但是關于其中受戒的場景,必不可能是畫工憑空想象,而是依據現實才能進行創作構圖,因此經變中的場景雖然無法完全和文獻對應,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代的受戒儀軌。如武德九年(626)至貞觀四年(630),道宣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其中第八《受戒緣集篇》對世俗人出家時的條件和相關儀程做過詳細描述,其中提及出家時“在于露地香水灑之,周匝七尺四角懸幡”{2},和彌勒經變中的受戒圖像無法一一對照,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由此,彌勒經變可以作為唐代受戒場所研究的一份可視資料{3}。對此本文從受戒場所這一畫面中的細小場景進行探討,以求反映唐代受戒場所的變化,并對這一變化的原因進行一些推測:戒場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幾近消亡{1},根據現有史料推測,應與道宣對戒壇的推崇,以及朝廷對僧人出家受戒的嚴格把控有關。
筆者關注到在《彌勒下生經》的受戒畫面中,受戒場所這一表現形式有所差別,因此本文從下述兩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彌勒經變中的剃度受戒場景之方形帷幕場所問題,指出該場景象征的應是戒場受戒;二是唐代的受戒情況。本文雖然利用《彌勒下生經》中有關受戒畫面的記載,試圖厘清唐代的戒場受戒,但因資料缺乏,只能確定唐代存在這一事實,無法詳細分析戒場受戒在中國傳播的過程。盡管如此,戒場受戒作為從印度流傳至中國的受戒制度,較少受人關注,所以本文試圖用有限的資料對這一制度進行探討。
一 彌勒經變中的剃度受戒場景再探討
彌勒經變中關于剃度受戒的場景眾多,與本文有密切關系的有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圖1、2);榆林窟第25窟(中唐,圖3、4)、莫高窟第202(中唐,圖5)、361窟;莫高窟第138窟(晚唐),莫高窟第61、100窟(五代、宋)。有學者曾以盛唐第445窟,榆林窟第25窟為例,對整個場景構圖進行分析[8-10],此處以此為基礎展開一些討論。
首先,第445窟的壁畫的出家受戒場景中,在俗者坐在半圓形帷幕中,帷幕有人出家受戒。有學者認為第445窟布局中的半圓形帷幕是與唐代帷幕相類似的物品,作用為杜絕女性出家者被偷窺,而男性場景中同樣的帷幕是為了畫面布局對稱而畫上去的,不符合出家受戒的實際場景[10]26-36。這一布局雖然成為盛唐以后彌勒經變的主要形式,但無法將該結論推廣到所有彌勒經變,理由有兩點:一是第445窟的帷幕為半圓形,除此之外莫高窟第202、361、138、61、100窟,所見眾多圖像基本為四方形,因此將第445窟的半圓帷幕作用擴展到方形帷幕,似有不妥。二是第445窟帷幕內人物全為在俗者,其他圖像中,如第202窟的兩個方場有僧有俗和唯僧無俗,分別代表出家和受戒場景,因此簡單的將帷幕作用解釋為隔絕偷窺,男性出家受戒的帷幕是為了布局對稱,則太過牽強。簡而言之,第445窟雖然能代表一部分洞窟的壁畫場景,但方形帷幕應另有含義。
其次,設置方形帷幕的含義與功用為何?雖然眾多彌勒經變中,所見剃度受戒的場景基本一致,即在圍三缺一的方場中完成僧俗身份的轉換,但在具體表現上仍有差別,其中莫高窟第361、138、61窟,榆林窟第25窟,都只描繪了一個方場,莫高窟第202、100窟則描繪了兩個方場。這些畫面中,當以第202窟(圖5)最能傳達方場的具體含義。該畫面呈左右對稱分布,分別描繪男女出家受戒的場景。以男性為例,在畫面靠中間的方場中,站立眾多僧俗,眾人面前跪一人,此當為剃度場景。稍右側方場中,有十位僧人,前跪一僧,此當是“三師七證”為僧人傳授具足戒。受戒過程中,對求戒者的安置是方形帷幕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圍三缺一的作用是為了滿足受戒條件中的“眼見耳不聞處”{1},即在律典中明確規定要將求戒者安置在眼睛能看見戒壇受戒情形,耳朵聽不見受戒羯磨法的地方。當然,若是在寬敞的場所中,連圍三缺一的帷幕也不必要。這應當是某些彌勒經變中不畫帷幕的原因。
二 唐代的受戒
敦煌做為中印文明的交接點,壁畫的畫面極可能同時含有中國和印度兩種元素。因此在探討壁畫中的受戒場景時,不僅僅要關注本土的高僧著作,還需要關注戒律原典以及求法高僧的見聞記錄。通過圖像與文本的對照,可以發現,彌勒經變中所畫的帷幕是戒場受戒,接下來對戒場進行探討。
戒場是受戒場所的簡稱,在律典中有具體的設立儀軌。在以往的研究中{2},并未有人注意到戒場受戒,而是將戒壇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現有文獻較少,難以知曉戒場受戒的具體操作流程,只能從彌勒經變的場景予以推測。筆者以為在平地上設立用帷幕建成的“圍三缺一”的方形場所,是唐代戒場受戒的實際狀況。
(一)戒場的具體狀況
現存的唐代律師文獻中,關于戒場受戒的記載較少,此處以道宣的《關中創立戒壇圖經》為主,輔以唐代其他律師的相關記載,利用這些戒場的相關文獻,從戒場的定義、戒場的設立兩個部分進行探討,試圖將戒場的具體情況復原。
受戒是成為正式僧人必經步驟,所以唐代律師在眾多文獻中都描述了戒場受戒。從律典的記載來看,受戒最主要的條件是“白四羯磨”(四次表白詢問),即在僧團中將要舉行受戒之事稟告,而后進行三次詢問,若無反對者,則受戒成立{1}。為了讓“白四羯磨”不被僧團外的沙彌和在俗者竊聽,因此需要結戒場,規定受戒場所范圍,除儀軌相關人員外他人不得進入該范圍。戒場結法的相關文獻較多,五分律師愛同(生卒年不明)在他的《彌沙塞羯磨本》中,詳細地將結戒場到解戒場的作法列出[11]。四分律師道宣在《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中,同樣對戒場的設立有所說明[12]。此外,懷素(624?—697?){2}、定賓(生卒年不明)等律師都對戒場有不同程度的記載{3}。這些文獻的存在說明唐代戒場受戒廣泛存在于各個律學流派中。
雖然眾多文獻中都有戒場的記載,但是真正對戒場做出具體定義的是道宣的《關中創立戒壇圖經》。《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是道宣對自己在凈業寺設立戒壇的經過以及戒壇樣式的記載。在文中,道宣對“戒壇”和“戒場”進行了說明:戒場是在平地上的場所{4}。而道宣之后,義凈在他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提及他在印度所見的受戒方式,除了小壇(戒壇)外,大界(一般指寺院范圍)或自然界(一般指某個自然場所范圍)內受戒也可以得戒{5}。其中大界和自然界就包含了戒場受戒。此外,《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中說,若是受戒過程中下雨,可以將戒場解除移到屋根(屋檐)下{1}。綜合這些記載,戒場受戒是在平地上舉行的受戒儀式。
設置在平地上的戒場也并非毫無范圍,在律典中有明確的結界規定。在受戒的準備過程中,最重要的前提準備工作就是結界,即規定戒場的范圍。在律典中戒場的結界方法是先結戒場界,再結大界{2}。結界的過程十分繁瑣,此處簡單總結為先派遣四位僧人站定四個角落,高聲說明戒場的具體范圍的四個角落,而后以石塊、木頭等物標記范圍{3}。除了人為劃定范圍外,以醒目的場所區分標記為界的自然界也是設立戒場的常用手段。在道宣的記載中,自然界有四種,即聚落(村落)、蘭若(寺院)、道行(行走范圍)、水界{4}。這種自然界中,在船上(水界)進行的傳戒儀式就是一個極具有代表性的例子{5}。
現有資料中,未能見到戒場受戒的具體記載{6},但不論是道宣還是義凈,或其他律師的記載中都承認不需要戒壇的戒場受戒,因此盡管資料缺乏,唐代存在戒場的受戒形式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二)唐代的戒場受戒衰退原因推測
戒場受戒之所以淹沒在歷史中無人知曉的具體原因不明,可以推測的原因之一是,隨著四分律宗的興盛,戒壇在寺院中漸漸增多,而國家對度僧資格的嚴格把控,導致受戒場所集中在有限的戒壇內,戒場受戒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道宣以前戒場和戒壇并存于世,而后關于戒場受戒少見于文獻記載,可以推測隨著四分律宗的興盛,以及對戒壇的推崇是戒場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敦煌戒壇,土橋秀高、姜伯勤都曾做過深入研究{7},近年大谷由香以東大寺的現存戒壇為基礎,結合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的記載,對唐代的戒壇樣式進行探討[13]。故而此處不再探討戒壇的樣式,而以《關中創立戒壇圖經》為基礎探討道宣對戒壇受戒的推崇。《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中,道宣對戒壇和戒場的主要討論集中在《戒壇立名顯號第二》,文長煩引,略說如下:首先,道宣提出“壇”和“場”二者并不一致,中國人混淆了其中含義{1}。其次,道宣引用《別傳》中迦葉對阿難的詰問證明“壇”才是受戒的場所,并對戒壇進行說明{2}。最后,道宣總結戒壇之名始于佛世,后因文本過多而混亂,因此他遵阿難所說而立戒壇{3}。此外,《關中創立戒壇圖經》還記載了中印度大菩提寺釋迦蜜多羅見到道宣所造戒壇,認為其符合印度戒壇的形制{4}。從道宣的這些說明來看,雖然其沒有否定戒場受戒,但是他更推崇戒壇受戒,認為這才是從佛世傳承下來的正統。中唐后,四分律學為正統通行天下[14],道宣被推為南山律祖,因他對律學的深遠影響,其所推崇的戒壇受戒應是戒場受戒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社會角度而言,隨著李唐王朝佛教制度的完善,度僧作為統治佛教的一個重要手段被朝廷掌控,這是戒場受戒衰退的另一個原因。從唐初開始,朝廷對僧團治理的法規在不斷加強{5},剃度受戒則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一方面,僧人出家受戒需要有度牒,度牒是由朝廷頒發并定期核查,記載了僧人的籍貫、身份、出家年齡、背誦經典、剃度受戒時間等一系列詳細信息的文牒[15-16];另一方面,朝廷又規定了剃度受戒的地點,凡未曾得到允許而私自剃度受戒的僧人被視為違法的私度{6}。對于受戒地點的要求,圓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記》中記載大和二年(828),全國只有兩所戒壇能舉行受戒儀式{7}。雖然圓仁的資料較晚,但是也可以看出當時對受戒地點有嚴格的規定。簡而言之,朝廷為了統治僧團,對受戒的戒壇進行嚴格規定并定期核查度牒,因此推測相較于能夠簡單的在平地上結界舉行的戒場,有實體建筑物的戒壇則更容易為朝廷掌控。當然,法律的規定與實際操作有所區別,特別是唐后期中央政權逐漸喪失對藩鎮的控制后,由藩鎮私自舉行的剃度受戒屢見不鮮{8},這也可能是敦煌壁畫中不斷出現戒場受戒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因文獻不足,戒場衰退的原因難以完全清楚。此處試圖從佛教內部道宣對戒壇的推崇,以及佛教外部朝廷對佛教掌控的事實來解釋這一現象的產生,但是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將來更深入的挖掘。
三 結 語
佛教從最初的東來傳道發展到西行求法,這本身也是一個宗教向域外傳遞,并且最終實現形式轉換的絕佳案例。佛教傳入中國,并最終與中土文化融合無間,這中間所經歷的漫長演變過程不僅具有歷史研究價值,同時也對當前宗教治理具有重要啟示。
從佛教制度層面來看印度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也是研究此一歷程的一個重要側面。雖然歷史上不斷的有人將印度儀軌傳入中土,但中土高僧,不會只是被動地接受這種外來的制度性規范,他們也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在不斷的調整各種制度。而受戒作為佛教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得到眾多高僧的矚目。在受戒過程之中,為了確保隱私性而確立的戒場與戒壇設立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歷史資料的發掘,可以發現早期印度僧侶的受戒儀軌主要是在戒壇以及自然界中所設立的戒場之中實行,在此期間戒壇至少并不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在最近的一個千年之中,中國僧侶的受戒地點則主要是以戒壇為主。這其中轉換的關鍵階段就在于中國唐宋變革的這一時期內。不僅唐宋整個社會出現了全面轉向,即使是在佛教方面也有了諸多前所未有,并且對于后世有深遠影響的轉變。而從戒場與戒壇并行,再到戒壇獨盛,則是其中的一個過去不為學界所注意的側面。這一轉換過程漫長而細微,現有文獻材料無法將其一一呈現。在此,筆者另辟蹊徑,通過敦煌這個華戎交匯與中印文化匯聚之地,以圖證史的方式,以敦煌石窟彌勒經變所反映的中古受戒實景逆推還原這被歷史的塵埃所掩蓋的一面。因此,本文的研究,就不僅對于研究佛教制度史有所發明,或者也可為今后拓展歷史研究之中的圖像史料有所貢獻。
在拙文中,通過對彌勒經變中的方形帷幕含義與作用進行再探討,可得出至少如下初步的結論:
第一,筆者對莫高窟第445窟以外,壁畫所見的方形帷幕作出解釋。“圍三缺一”的方形帷幕,是為了能讓后面的求戒者既能看見前一個受戒者的受戒儀軌,又不至于聽見“三師七證”傳授時的羯磨法。此外,對榆林窟第25窟中的剃度受戒無戒壇的情況可能是表示戒場受戒,而并非不符合戒律的規定{1}。
第二,以往的研究中未曾注意到戒場受戒,筆者通過唐代眾多律師的記載指出,在唐代存在通過在平地上結界即可舉行受戒儀式的戒場。而之后戒場逐漸消失,其原因可能是道宣對戒壇的推崇,以及封建王朝對于僧團各項制度性限制所導致。從后者之中,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具有規律性的結論。即佛教內部的制度性轉換,往往要受制于政、教勢力在更寬廣背景下的互動。中國佛教的在地化,其中一個最為明顯的推手,還是來自政治權威的不停頓的壓力。它會持續直接地推動中國佛教的本土化進程,即使是在看似細微之處,也往往會潛藏著來自王權的暗力。
以圖證史,為文獻之不足征者。雖然如此,但傳世文獻之不足,依然還是一個莫大的缺憾。因此,本文雖然通過圖像資料,來恢復中古佛教制度上的一個側面,但不過即是拋磚引玉。對具體的受戒細節以及其他具體情況,則仍有待來賢。
參考文獻:
[1]平川彰.戒壇の原意[J].印度學佛敎學硏究(20),1962:276-296.
[2]McRae John R. Daoxuans Vision of Jetavana:The Ordination Platform Mov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G]//William Bodiford. Going Forth:Visions of Buddhist Vinay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68-100.
[3]Thomas Newhall. The Development of Ordination Platforms (jietan 戒壇) in China: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īm?觀 in East Asia from the Third to Seventh Centuries[G]//Jason A,Carbine,Erik W Davis. Simas:Foundations of Buddhist Relig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22.
[4]佛陀耶舍,竺念佛.四分律:卷35[G]//大正藏:第22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8:819c.
[5]僧伽跋陀羅.善見律毘婆沙:卷2[G]//大正藏:第24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8:682a.
[6]定寶.四分律疏飾宗義記:卷8[G]//續藏經:第42冊,京都:藏經院,1912:248a.
[7]比丘尼傳:卷1:晉竹林寺凈撿尼傳[G]//大正藏:第50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8:934c.
[8]沙武田,李玭玭. 敦煌石窟彌勒經變剃度圖所見出家儀式復原研究[J]. 中國美術研究,2018(1):26-36.
[9]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9-19.
[10]石小英. 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5-57.
[11]愛同. 彌沙塞羯磨本[G]//大正藏:第22冊. 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8:214c-215a.
[12]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1[G]//大正藏:第40冊. 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7:16a-c.
[13]大谷由香. 大寺戒壇院の塔[G]//東栄原永遠男,佐藤信,吉川真司. 東大寺の思想と文化(東大寺の新研究3). 東京:法蔵館,2018:112-115.
[14]王建光. 中國律宗通史[M].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89-193.
[15]孟憲實. 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J]. 文物,2007(2):50-54.
[16]池田溫.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M]. 龔澤銑,譯. 北京:中華書局,1984: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