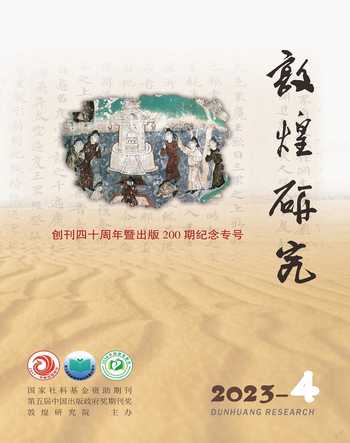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
內(nèi)容摘要:對(duì)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進(jìn)行比較與思考,重點(diǎn)從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內(nèi)涵之比較、學(xué)術(shù)歷程回顧、前景展望及設(shè)想等四個(gè)方面來進(jìn)行探討。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皆是高度綜合性的學(xué)問,以大型建筑群作為承載空間,研究對(duì)象中均有數(shù)量巨大的藝術(shù)品、文物及獨(dú)樹一幟的文獻(xiàn)。二者的研究歷程都肇始于20世紀(jì)初國寶文物、文獻(xiàn)的流散以及外國學(xué)者的搶先研究,激發(fā)了中國有識(shí)之士奮起直追的意愿;經(jīng)過篳路藍(lán)縷、披荊斬棘的努力,建立起中國學(xué)界自己的研究隊(duì)伍,并最終成立了專門研究和保護(hù)敦煌石窟與故宮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遂將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研究一直引領(lǐng)至今。展望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前景,故宮是中華文明源遠(yuǎn)流長的見證,敦煌是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故而應(yīng)當(dāng)從中國文化整體的視角來研究和發(fā)展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此外,還應(yīng)加強(qiáng)基礎(chǔ)研究與綜合研究,重視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與公眾普及。
關(guān)鍵詞:敦煌學(xué);故宮學(xué);比較;中國文化;中外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hào):K87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4106(2023)04-0012-12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Comparison,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WANG Xudong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Abstract: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mparative review and historical retrospect on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of these two fields: comparison of their research objects and academic findings, review of their academic historie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oposals for the advancement. Both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are highly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s concerned with huge, extremely complicated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s that contain a large amount of artworks, cultural relics and unique documents. The academic histories of both fields began at a moment when precious national treasures and documents were being dispersed abroad, and when foreign schol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ad already begun advanced study of these objects. Both sets of circumstances stimulated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aspiration to conduct academic study along their own lines of thought. After pushing through decades of hardship, Chinese academia established itself, along with var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specialized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Dunhuang Caves and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se institutions and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can now be recognized as inaugur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future of these disciplines, it is the belief of the author that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Palace Museum bears witness to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unhuang is a central lo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Finally,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basic,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ffor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while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blic popularization still require greater development.
Keywords:Dunhuang studies; Gugong studies; comparison; Chinese culture;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今年是《敦煌研究》創(chuàng)刊40周年,上距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已123年,而距離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中國學(xué)術(shù)界正式提出“敦煌學(xué)”的概念{1}也已過去93載。迄今為止,經(jīng)海內(nèi)外一代又一代學(xué)者前赴后繼的不斷努力,敦煌學(xué)已取得極其豐碩的研究成果,并且從陳寅恪先生口中的“世界學(xué)術(shù)之新潮流”,發(fā)展為今日國際學(xué)術(shù)界的一門顯學(xué)。
2003年鄭欣淼先生首次提出“故宮學(xué)”的概念,至今正好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故宮學(xué)在故宮博物院以及中外學(xué)者的共同推動(dòng)與探索之下,也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績。盡管故宮學(xué)概念的形成比敦煌學(xué)要晚七十多年,然而與故宮學(xué)相關(guān)之研究(如故宮古建筑及各類館藏文物、文獻(xiàn)研究)的學(xué)術(shù)歷程則十分久遠(yuǎn)。
本文擬對(duì)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進(jìn)行一番比較與思考,重點(diǎn)從二者的研究對(duì)象、內(nèi)涵之比較、學(xué)術(shù)歷程回顧、前景展望及設(shè)想等四個(gè)方面來進(jìn)行探討,并著重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當(dāng)從中國文化整體的視角來研究和發(fā)展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
一 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
1. 敦煌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
敦煌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
一是著名的“敦煌文書”,即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的文獻(xiàn)及文物{2},數(shù)量約5萬件,內(nèi)容異常豐富,分藏于英、法、日、俄、中等國的圖書館、博物館及其他機(jī)構(gòu)或私人藏家手中。對(duì)敦煌文書的研究,是敦煌學(xué)得以建立的起因,也是狹義上的敦煌學(xué)研究的內(nèi)容。敦煌文書中有確切年代記載的文獻(xiàn)從公元406年至1002年,時(shí)間跨度近600年[1]。其內(nèi)容更是包羅萬象:除作為主體的佛教經(jīng)典之外,還包括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的經(jīng)典,還有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史子集四部的典籍(以上多為寫本或曰卷子的形態(tài));另外還有官私文書、俗文學(xué)作品(如曲子詞、變文、小說)等;漢文文獻(xiàn)之外,還包括藏文、梵文、于闐文、回鶻文、粟特文、巴利文、西夏文、龜茲文、突厥文乃至敘利亞文等所謂“胡語文獻(xiàn)”。此外尚有拓本、刻本、星圖、云圖、信封、經(jīng)帙等。藏經(jīng)洞還出土了一批藝術(shù)品,如木版畫、紙畫、絹畫、麻布畫、絲織品、剪紙等。廣義的敦煌文獻(xiàn)研究,往往還外延至敦煌漢簡以及吐魯番、和田、庫車、黑城等地出土的文獻(xiàn)。
二是敦煌石窟本身,主要指莫高窟,廣義上還包括敦煌的西千佛洞,瓜州(原安西)的榆林窟、東千佛洞,以及肅北的五個(gè)廟石窟。敦煌莫高窟現(xiàn)存735個(gè)洞窟,其中有壁畫、彩塑的洞窟共492個(gè),內(nèi)有彩塑2400余身,壁畫約45000平方米,主要分為北朝、隋、唐、五代、宋初、西夏、元等幾個(gè)發(fā)展階段。此外,榆林窟存41個(gè)洞窟,西千佛洞存16個(gè)洞窟,東千佛洞存23個(gè)洞窟,五個(gè)廟石窟存4個(gè)洞窟。敦煌石窟包括洞窟及窟檐建筑、窟內(nèi)彩塑與壁畫(包含文字題記),此外還有窟外一些附屬文物等。對(duì)敦煌石窟的研究與保護(hù)是敦煌學(xué)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
除上述兩部分主要內(nèi)容之外,敦煌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史(包括敦煌研究院的歷史)也是敦煌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敦煌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除敦煌文書和石窟之外,還包括敦煌學(xué)理論、敦煌史地等[2],更廣義的看法則認(rèn)為敦煌學(xué)是研究敦煌古代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的學(xué)問{1}。
2. 故宮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
故宮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主要包含三大部分:一是故宮古建筑群,二是故宮博物院的各類館藏文物(包括文獻(xiàn)),三是故宮博物院的歷史——故宮學(xué)將以上三者視作一個(gè)有機(jī)的文化整體。鄭欣淼先生曾在《故宮學(xué)述略》一文中,將以上三大部分內(nèi)容細(xì)分為六個(gè)方面:1. 紫禁城宮殿建筑群;2. 文物典藏;3. 宮廷歷史文化遺存;4. 明清檔案;5. 清宮典籍;6. 故宮博物院的歷史[3]。其中第2—5條是對(duì)第二大部分即故宮博物院館藏文物(包括文獻(xiàn))的細(xì)分和具體化。章宏偉先生在《作為學(xué)問的故宮學(xué)》一書中則指出故宮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主要包括故宮建筑學(xué)、故宮文物學(xué)、故宮文獻(xiàn)學(xué)、故宮歷史學(xué)和故宮博物館學(xué)五個(gè)主要方面”[4],與上述研究對(duì)象基本對(duì)應(yīng)。
故宮是全世界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宮殿建筑群,占地面積達(dá)7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約17萬平方米,擁有近千座明、清木結(jié)構(gòu)建筑,是中國古代宮殿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建筑學(xué)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國建筑史》一書中稱贊故宮“整齊嚴(yán)肅,氣象雄偉,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筑所不及”[5]。
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文物(包括文獻(xiàn))逾180萬件(套)。鄭欣淼先生稱:“其文物品類,一應(yīng)倶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 金銀器皿以及其它歷史文物等等,可以說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shù)寶庫。”[3]王素先生在《故宮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初探》中將館藏文物分為五大類、十八小類:一、書畫(包括法書、繪畫、碑帖);二、器物(包括石刻、雕塑、銅器);三、宮廷文物(包括織繡、漆器、文具、家具);四、工藝文物(包括陶瓷、玉器、琺瑯器、金銀器);五、其他文物(包括宗教文物、外國文物、鐘表儀器、雜類文物){2}。故宮博物院藏有古籍文獻(xiàn)37萬冊(cè)。此外,現(xiàn)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位于故宮西華門內(nèi))的原故宮內(nèi)閣大庫檔案(約800萬件),也是故宮文獻(xiàn)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文物之外,完整意義上的故宮文物,還應(yīng)包括臺(tái)北故宮的館藏文物(約68萬件/套),以及流散于國內(nèi)外各處的清宮舊藏文物(包括圓明園舊藏):國內(nèi)如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沈陽故宮博物院等處的相關(guān)藏品;國外如大英博物館、法國楓丹白露宮(中國館)、美國大都會(huì)博物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xué)美術(shù)館等處的相關(guān)藏品;此外還有大量中外私人的收藏——兩岸故宮以及流散各地的清宮舊藏文物,皆應(yīng)作為故宮學(xué)研究的內(nèi)容。
故宮博物院,既是近代中國社會(huì)政治變革的典型產(chǎn)物,也是推動(dòng)當(dāng)代中國文化轉(zhuǎn)型的重要力量,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重要見證。對(duì)故宮博物院院史的研究,也是故宮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1}。
二 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內(nèi)涵之比較
從上述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已可看出,二者均是具有高度綜合性的學(xué)問,皆有極其豐富的內(nèi)涵,既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各自的特點(diǎn)。以下從四個(gè)具體方面對(duì)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內(nèi)涵進(jìn)行比較與分析。
1. 高度綜合性的學(xué)問
由于研究對(duì)象的豐富性,敦煌學(xué)成為學(xué)術(shù)界公認(rèn)的一門綜合性的學(xué)問。李正宇的《敦煌學(xué)導(dǎo)論》一書列出敦煌學(xué)的“分支學(xué)科”包括:史地學(xué)、考古學(xué)、民族學(xué)、藝術(shù)學(xué)、宗教學(xué)、民俗學(xué)、文學(xué)、語言文字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古代科學(xué)技術(shù)、文物保護(hù)科學(xué)以及“敦煌學(xué)學(xué)”[6]138。劉進(jìn)寶在《敦煌學(xué)通論》中也指出敦煌學(xué)所涉及范圍極廣,“大凡中古時(shí)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藝術(shù)、歷史、地理、語言文字、文學(xué)、哲學(xué)、科技、經(jīng)濟(jì)、建筑、民族關(guān)系、中西交通等各門學(xué)科,都可以利用敦煌學(xué)資料”[2]3。根據(jù)現(xiàn)有研究粗略統(tǒng)計(jì),敦煌學(xué)所涉及的主要學(xué)科至少包括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特別是石窟寺考古)、藝術(shù)史(以及藝術(shù)學(xué)、美學(xué)等)、建筑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古代經(jīng)學(xué)、宗教學(xué)、語言文字學(xué)、民族學(xué)、地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文學(xué)、民俗學(xué)、醫(yī)學(xué)、科技史、文保科學(xué)等。
與敦煌學(xué)類似,故宮學(xué)也是包羅萬象的綜合性學(xué)問。鄭欣淼先生在《故宮學(xué)述略》一文中曾指出“故宮學(xué)很顯然是綜合性學(xué)科,在研究中需要運(yùn)用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建筑學(xué)、文藝學(xué)、美學(xué)及相關(guān)的自然科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故宮學(xué)“涉及歷史、政治、建筑、古器物、檔案、圖書、藝術(shù)、宗教、民俗、科技、博物館等諸多自成體系的學(xué)科”{2}。王素先生在《故宮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初探》中則進(jìn)一步對(duì)故宮學(xué)所涉及的12個(gè)學(xué)科即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文物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宗教學(xué)、出版學(xué)、民族學(xué)、醫(yī)藥學(xué)、圖書館學(xué)、博物館學(xué)、古建筑學(xué)、文保科學(xué)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
由上可知,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不僅都是綜合性極強(qiáng)的學(xué)問,而且二者所涉及的學(xué)科有大量重合,如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建筑學(xué)、藝術(shù)史、文獻(xiàn)學(xué)、宗教學(xué)、民族學(xué)、醫(yī)學(xué)、文保科學(xué)等。
2. 以大型建筑群作為承載空間
敦煌學(xué)和故宮學(xué)的另一個(gè)重要共同點(diǎn),是二者的研究對(duì)象中都包含一組大型建筑群,即敦煌石窟和故宮古建筑群,它們既是研究對(duì)象,同時(shí)也曾經(jīng)或者依然是承載其他研究內(nèi)容的空間“容器”——敦煌文書曾經(jīng)密封在藏經(jīng)洞內(nèi)近千年之久,彩塑與壁畫則一直以石窟建筑空間作為依托;故宮的館藏文物及檔案文獻(xiàn)在流散之前皆分藏宮中各建筑內(nèi)。
但敦煌石窟與故宮古建筑群亦有著顯著的差異。以敦煌莫高窟為代表的石窟寺建筑,以石構(gòu)洞窟為主(當(dāng)然也留存有一批木結(jié)構(gòu)窟檐{3}),是通過在崖壁上“開山鑿巖”獲得空間,可謂一種“負(fù)建筑”,在中國古代建筑中別具一格[7]。而故宮古建筑群則是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即由一座座木構(gòu)建筑通過院落式布局形成組群。當(dāng)然故宮也有少量磚石結(jié)構(gòu)建筑,典型者如浴德堂;此外,故宮古建筑的臺(tái)基大量使用石構(gòu)件,其中最宏大的工程即三大殿臺(tái)基的欄桿、欄板和御路等。因此,敦煌石窟和故宮古建筑在研究與保護(hù)方面存在很大的互補(bǔ)性,可以互相借鑒。
3. 數(shù)量巨大的藝術(shù)品及其他文物
敦煌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畫是無與倫比的藝術(shù)杰作,考古學(xué)與藝術(shù)史研究的大宗,毋庸贅言。需要注意的是,敦煌的壁畫、彩塑與石窟的建筑空間,構(gòu)成“三位一體”的整體,三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共同營造出石窟寺特有的宗教氛圍。巫鴻先生的近作《空間的敦煌:走近莫高窟》[8],即在他此前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藝術(shù)品之“原境”(context)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探究作為空間整體的莫高窟。因此對(duì)莫高窟壁畫、彩塑與石窟建筑的研究應(yīng)該納入整體視野進(jìn)行深入探討。
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文物種類極其豐富,除了藝術(shù)品之外還包含大量其他類型的文物,它們大多屬于清宮舊藏,宮廷文物承載著中國古代悠久的歷史、文化與藝術(shù),作為中國歷代文化之載體的性質(zhì)與故宮古建筑群相同,它們同屬于故宮這一“文化整體”的組成部分。正如壁畫、彩塑與石窟建筑空間共同形成敦煌石窟的“原境”一樣,大量宮廷文物與故宮的建筑空間同樣構(gòu)成故宮的“原境”或“原狀”(典型者如皇帝寶座與太和殿、皇帝鹵簿與太和殿廣場、《四庫全書》與文淵閣的關(guān)系等等),應(yīng)被視作整體來進(jìn)行研究。
4. 獨(dú)樹一幟的珍貴文獻(xiàn)
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中,均包含獨(dú)樹一幟的珍貴文獻(xiàn),即敦煌文書與故宮內(nèi)閣大庫檔案,二者皆位列近代中國古文獻(xiàn)“四大發(fā)現(xiàn)”之中,與殷墟甲骨和居延漢簡齊名。與敦煌文書分散收藏在中外諸國的境況類似,故宮內(nèi)閣大庫檔案也被分散收藏,主要部分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tái)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其余分散藏于國內(nèi)外一批博物館、檔案館和圖書館{1}。
這兩種文獻(xiàn)性質(zhì)迥異,前者年代在5—11世紀(jì)(十六國時(shí)期至元代)之間,且內(nèi)容龐雜之極,既有佛、儒、道之經(jīng)典,又有官私文書及俗文學(xué)材料,既有漢文文獻(xiàn),又有大量“胡語文獻(xiàn)”。內(nèi)閣大庫的檔案則以明清時(shí)期(尤其是清朝)為主,且主要是宮廷檔案,對(duì)治明清史、宮廷史意義重大。二者在年代及性質(zhì)方面,恰呈互補(bǔ)的局面。
故宮文獻(xiàn)除了著名的明清檔案之外,還有大量宮廷典籍(現(xiàn)存故宮圖書館),后者除了經(jīng)史子集四部書之外,也包括宮廷刻印的佛教《大藏經(jīng)》,還有尺牘、少數(shù)民族文字文獻(xiàn)等,頗可與敦煌文書比較、對(duì)照研究。此外,故宮收藏的出土文獻(xiàn)包含甲骨、金石和敦煌吐魯番文獻(xiàn)等——其中的敦煌吐魯番文獻(xiàn)則是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共同的研究對(duì)象[9]。此外,珍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處的專為清代皇家服務(wù)的建筑世家“樣式雷”的建筑圖檔,也是故宮檔案文獻(xiàn)的重要組成部分,對(duì)于故宮古建筑的研究具有無可替代的巨大價(jià)值。
三 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學(xué)術(shù)歷程回顧
每個(gè)學(xué)科的研究都離不開對(duì)其學(xué)術(shù)史的回顧與整理,特別是像敦煌學(xué)和故宮學(xué)這樣浩瀚博大,由多學(xué)科的大批學(xué)者進(jìn)行過長期耕耘的學(xué)問,其學(xué)術(shù)史本身也是學(xué)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研究的重點(diǎn)之一。
如果對(duì)敦煌學(xué)和故宮學(xué)的研究歷程進(jìn)行一番簡要回顧,便會(huì)發(fā)現(xiàn)二者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中國學(xué)術(shù)界開始對(duì)敦煌學(xué)和故宮學(xué)(盡管早期尚未形成“故宮學(xué)”的清晰概念)進(jìn)行研究的歷史背景,都是20世紀(jì)初左右珍貴國寶文物的流失——即陳寅恪先生所言“吾國學(xué)術(shù)之傷心史”;之后由于外國學(xué)者的搶先研究,更激發(fā)了中國有識(shí)之士奮起直追的意愿;經(jīng)過這些先賢們篳路藍(lán)縷、披荊斬棘的努力,建立起中國學(xué)界自己的研究隊(duì)伍,并最終成立了專門研究和保護(hù)敦煌石窟與故宮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遂將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的研究一直引領(lǐng)至今。
1. 敦煌學(xué)簡要?dú)v程
眾所周知,敦煌學(xué)的誕生緣于1900年6月22日(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園祿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以及隨之而來的敦煌文書流失海外。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分別于1907、1908 年抵達(dá)敦煌,并帶走大批珍貴藏經(jīng)洞文書。1909年伯希和赴京,向北京的學(xué)者展示若干藏經(jīng)洞珍貴文獻(xiàn),以羅振玉為首的一批學(xué)者先后前往伯希和寓所參觀、抄錄。同年9月25日羅振玉發(fā)表《敦煌石室書目及發(fā)現(xiàn)之原始》,首次公布了敦煌藏經(jīng)洞的重大發(fā)現(xiàn),敦煌文書遂引起中國學(xué)者高度重視。盡管之后羅振玉提請(qǐng)清學(xué)部收集藏經(jīng)洞剩余文書,得以將部分殘卷運(yùn)回北京并入藏京師圖書館,可是緊接著日本大谷探險(xiǎn)隊(duì)及俄國奧登堡考察隊(duì)又分別于1911—1912年和1914—1915年從敦煌帶走大批文書。1923年,面對(duì)空空如也的藏經(jīng)洞,美國人蘭登·華爾納又將一批精美壁畫、彩塑從石窟中揭取、盜走(現(xiàn)藏哈佛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對(duì)莫高窟造成極大破壞。
以上外國探險(xiǎn)家最早開啟了對(duì)敦煌石窟和文獻(xiàn)的研究。1907年,斯坦因?qū)δ呖叩慕ㄖ⒌袼堋⒈诋嬤M(jìn)行調(diào)查攝影,并對(duì)南區(qū)的18個(gè)洞窟編號(hào),做了文字記錄和平面測繪。1908年,伯希和對(duì)莫高窟大多數(shù)洞窟進(jìn)行編號(hào)、記錄、攝影,繪制了南區(qū)石窟立面圖和該區(qū)下層洞窟平面圖,抄錄了部分壁畫題榜,后出版《敦煌石窟圖錄》(六冊(cè),1920—1924)。1914—1915年,俄國人奧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記錄的基礎(chǔ)上,對(duì)莫高窟做進(jìn)一步調(diào)查,增補(bǔ)部分洞窟的編號(hào),逐窟測繪、記錄、拍照,抄錄部分題榜并摹寫部分壁畫,在測繪南區(qū)單個(gè)洞窟平、立面圖的基礎(chǔ)上,最后拼合出總平面圖和總立面圖。1924—1925年蘭登·華爾納考察敦煌石窟,對(duì)榆林窟第5窟(今編號(hào)第25窟)壁畫做了專題研究;1925年北京大學(xué)陳萬里隨華爾納一同調(diào)查敦煌石窟,其后來所著《西行日記》是我國學(xué)者對(duì)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學(xué)考察記錄[10]。
彼時(shí)的中國學(xué)者們奮起直追,投入對(duì)敦煌文書多角度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包括羅振玉、王國維、蔣斧、曹元忠、王仁俊、陳寅恪、陳垣、向達(dá)、王重民、姜亮夫、劉半農(nóng)、鄭振鐸、劉師培等。至1930年,陳寅恪在為陳垣《敦煌劫余錄》所作序文中正式提出“敦煌學(xué)”概念,并指出研究目標(biāo)為“內(nèi)可以不負(fù)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世界之學(xué)術(shù)于將來”——此亦可謂中國治敦煌學(xué)者之共同心聲。
與之前中國學(xué)者大多從事敦煌文書研究不同,抗戰(zhàn)期間,一批學(xué)者及藝術(shù)家(如張大千、謝稚柳、常書鴻、何正璜、向達(dá)、石璋如等)紛紛前往敦煌石窟進(jìn)行實(shí)地調(diào)查研究。特別是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xué)先后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tuán)、西北科學(xué)考察團(tuán)兩度赴敦煌考察。向達(dá)運(yùn)用傳統(tǒng)文獻(xiàn)、敦煌文書和實(shí)地考古調(diào)查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完成了《莫高、榆林二窟雜考》等4篇系列文章{1},為我國學(xué)者敦煌石窟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石璋如按照張大千編號(hào),對(duì)莫高窟逐窟做了文字記錄,繪制平、剖面圖,拍攝圖版照片,后出版《莫高窟形》(三冊(cè))。
1944年,國民政府成立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1950年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擴(kuò)建為敦煌研究院)。此后,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學(xué)人扎根當(dāng)?shù)兀硇耐度氲蕉鼗褪叩难芯颗c保護(hù)之中,取得豐碩成果。1982—1987年,由夏鼐、常書鴻、宿白、金維諾與日本學(xué)者長廣敏雄、岡崎敬、鄧健吾任編委會(huì)委員,匯集中日兩國多位敦煌石窟研究專家共同編寫的《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冊(cè))陸續(xù)出版;1999年起,由敦煌研究院組織編寫,段文杰任主編、樊錦詩任副主編的《敦煌石窟全集》(共26冊(cè))由商務(wù)印書館(香港)陸續(xù)出版;2011年,敦煌研究院編,樊錦詩、蔡偉堂、黃文昆編著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bào)告》(系多卷本考古報(bào)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第1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以來,敦煌學(xué)在學(xué)術(shù)界日益成為顯學(xué)。《敦煌研究》《敦煌學(xué)輯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等雜志陸續(xù)創(chuàng)刊。1983年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huì)”。一系列敦煌學(xué)研究的專著及論文紛紛出版與發(fā)表,蔚為大觀;中外各國收藏敦煌寫本的大型圖錄也陸續(xù)出版。此外,1980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敦煌學(xué)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在中國或海外召開。
2. 故宮學(xué)簡要?dú)v程
2003年10月,鄭欣淼先生在慶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的“博物館館長論壇”上正式提出“故宮學(xué)”概念。盡管學(xué)科概念的正式提出要晚于敦煌學(xué),但故宮學(xué)相關(guān)研究的肇始則要早得多。
與敦煌類似,對(duì)故宮古建筑及文物、文獻(xiàn)的研究,也伴隨著清宮文物與文獻(xiàn)的流散(主要因英法聯(lián)軍劫掠圓明園、八國聯(lián)軍庚子之役以及清遜帝溥儀“小朝廷”的盜運(yùn)等),以及外國學(xué)者對(duì)故宮古建筑的實(shí)地調(diào)查研究。
1901年,在八國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之后,日本學(xué)者伊東忠太成為首個(gè)進(jìn)入故宮進(jìn)行調(diào)查測繪的建筑史學(xué)者,他測繪了故宮的總平面并拍攝大量照片。之后,瑞典學(xué)者喜龍仁、德國學(xué)者鮑希曼、日本學(xué)者常盤大定與關(guān)野貞等,均得以考察故宮古建筑并發(fā)表相關(guān)圖錄{1}。
1921年,北洋政府出售大批內(nèi)閣大庫檔案(即所謂“八千麻袋事件”),之后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成立“清代內(nèi)閣大庫檔案整理會(huì)”(后更名“明清史料整理委員會(huì)”),陳垣任主席,沈兼士、鄭天挺、馬衡等學(xué)者參與其中,整理幸存檔案,此為中國學(xué)者整理研究故宮檔案之緣起。
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館藏文物和檔案的保護(hù)、整理與研究遂納入正軌。陳垣任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又分圖書部(專管清宮舊藏圖書)和文獻(xiàn)部(專管清宮舊藏檔案),沈兼士主持文獻(xiàn)部(1929年從圖書館分出,改稱文獻(xiàn)館,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之前身)。1929年博物院創(chuàng)辦《故宮周刊》, 連續(xù)出版510期,影響深遠(yuǎn)。為學(xué)術(shù)研究之需要,193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了書畫、陶瓷、銅器、美術(shù)品、圖書、史料、戲曲樂器、宗教經(jīng)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設(shè)計(jì)等10個(gè)專門委員會(huì),聘請(qǐng)一批知名學(xué)者擔(dān)任委員。
1930年中國營造學(xué)社成立,我國學(xué)者開始對(duì)故宮古建筑及相關(guān)文獻(xiàn)進(jìn)行系統(tǒng)研究:如朱啟鈐、陶湘、闞鐸、劉敦楨、梁思成等結(jié)合故宮所藏“故宮本”“四庫本”等古籍校勘北宋《營造法式》,陶湘依據(jù)內(nèi)閣大庫檔案中發(fā)現(xiàn)的《營造法式》宋本殘葉刊印陶本《營造法式》[11]; 梁思成結(jié)合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與故宮古建筑實(shí)例研究清代建筑,撰成《清式營造則例》(1934),為研究故宮古建筑及清代建筑之入門書;朱啟鈐、闞鐸、朱偰、王璧文(璞子)等先后進(jìn)行元大都宮苑(為明清故宮及西苑三海之前身)之專題研究{2};單士元長期從事明清北京及故宮建筑史研究{3},終成一代大家。從1934年起,受中央研究院委托,梁思成與中國營造學(xué)社同仁開始有計(jì)劃地測繪故宮古建筑,可惜此項(xiàng)工作因抗戰(zhàn)而中輟,不過仍然留下數(shù)以千計(jì)的照片、測稿及測繪圖,成為故宮古建筑研究與保護(hù)之珍貴史料。此外中國營造學(xué)社還參與了故宮角樓、文淵閣,景山五亭等建筑的維修與保護(hù)工程或計(jì)劃。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以及抗日戰(zhàn)爭期間,故宮博物院文物的南遷與西遷,歷時(shí)十余年,行程數(shù)萬里,寫下了保護(hù)中華文化珍寶可歌可泣的篇章。而在抗戰(zhàn)時(shí)期的北平,中國營造學(xué)社社長朱啟鈐委托基泰建筑事務(wù)所的張镈建筑師(梁思成在東北大學(xué)建筑系任系主任時(shí)的學(xué)生)主持測繪了故宮等北京中軸線重要古建筑群,繪圖七百余幅,又是抗戰(zhàn)中保護(hù)文化遺產(chǎn)的一樁壯舉。這套圖紙(分藏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及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至今仍是研究故宮古建筑的珍貴一手資料[12]。
建國以后,故宮博物院的故宮學(xué)相關(guān)研究成果甚豐,古建筑及館藏文物各領(lǐng)域皆專家輩出,不再一一列舉。1979年復(fù)刊的《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創(chuàng)刊的《紫禁城》和1983年建立的紫禁城出版社(后更名“故宮出版社”)成為故宮學(xué)術(shù)成果重要的發(fā)表、出版陣地。1990年以來先后成立了“中國史學(xué)會(huì)清代宮廷史研究會(huì)” 和“中國紫禁城學(xué)會(huì)”,進(jìn)一步拓展了故宮相關(guān)研究的力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故宮博物院除了主要的研究、保護(hù)與管理部門之外,與故宮學(xué)密切相關(guān)的一系列研究機(jī)構(gòu)得以逐步建立:古建筑方面有古建筑研究中心及“明清官式建筑保護(hù)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diǎn)科研基地”;各類館藏文物方面有古書畫、古陶瓷、明清宮廷歷史、藏傳佛教文物等研究中心及“古陶瓷保護(hù)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diǎn)科研基地”等。2005年6月,故宮舉辦第一次故宮研究、“故宮學(xué)”座談會(huì),此后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不斷延續(xù)。2009年正式設(shè)立故宮學(xué)研究所,將故宮學(xué)的理論探索與實(shí)踐應(yīng)用提升到新的水平。故宮出版社陸續(xù)出版“故宮學(xué)視野叢書”,包括鄭欣淼《故宮學(xué)概論》、章宏偉《作為學(xué)問的故宮學(xué)》、王素《故宮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研究初探》等。
以上扼要回顧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在中國學(xué)術(shù)界發(fā)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學(xué)術(shù)歷程,未涉及國外的研究情況。但由于二者皆以文物、文獻(xiàn)流散海外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重要緣起,因而從發(fā)軔之時(shí)便具有了國際化的特點(diǎn)。此外,由于學(xué)科內(nèi)涵包羅廣大,二者皆具有高度的可持續(xù)性,未來發(fā)展仍有巨大空間。
四 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前景展望及設(shè)想
1. 從中國文化整體的視角研究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
不論是敦煌石窟還是故宮,其古建筑、壁畫、彩塑以及各類文物、文獻(xiàn)收藏,都是一個(gè)巨大的文化整體,而這一文化整體又是更為廣大的中國文化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決定了對(duì)敦煌學(xué)、故宮學(xué)的研究,必須首先從中國文化整體的角度來進(jìn)行探討{1}——其中敦煌學(xué)更加偏重于討論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的融合,而故宮學(xué)則更聚焦于中國古代文化的溯源及其傳承、發(fā)展等內(nèi)容。
1.1 故宮是中華文明源遠(yuǎn)流長的見證
故宮學(xué)研究,應(yīng)注重從中華文明探源的角度探討中國古代以“觀象授時(shí)”為基礎(chǔ)的農(nóng)業(yè)文明,是如何通過都城、宮殿的營建與一系列宮廷制度的確立{2},將那些與文明息息相關(guān)的知識(shí)與思想加以記錄和傳承,并最終沉淀在故宮的古代建筑群中,凝聚在故宮收藏的浩如煙海的歷代文物、文獻(xiàn)之中,使故宮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中華文明源遠(yuǎn)流長的偉大見證”。
故宮首先是中國古代宮殿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對(duì)故宮古建筑的研究,理應(yīng)與中國歷代都城、宮殿遺址的考古學(xué)研究相結(jié)合,以探索都城、宮殿營建傳統(tǒng)的傳承、發(fā)展與演變。特別要關(guān)注與故宮密切相關(guān)的明中都宮城遺址、明南京宮城遺址以及沈陽故宮等。此外,故宮自成立考古部以來,已陸續(xù)進(jìn)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對(duì)元大內(nèi)、明北京故宮等相關(guān)遺址均有重要發(fā)現(xiàn)。結(jié)合歷代都城、宮殿考古以及故宮自身的考古工作來研究故宮古建筑,應(yīng)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故宮古建筑還體現(xiàn)了儒、釋、道文化的充分融合。除了主體宮殿建筑群之外,還包含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建筑群,如中正殿、雨花閣、寶華殿、寶相樓、吉云樓、佛日樓、梵華樓等40多處佛堂;道教建筑群,如欽安殿、玄穹寶殿等;此外還有祭祀薩滿的坤寧宮,祭祀城隍的城隍廟等,不一而足。各種宗教建筑與宮殿建筑構(gòu)成完美交融的和諧整體。梁思成先生在其《中國建筑史》一書中提出了“結(jié)構(gòu)技術(shù)+環(huán)境思想”的理論體系,對(duì)于環(huán)境思想,他尤其強(qiáng)調(diào)了“政治、宗法、風(fēng)俗、禮儀、佛道、風(fēng)水等中國思想精神”對(duì)于建筑群平面布局的深刻影響[5]7-15。今后對(duì)故宮古建筑的研究,更要從文化層面著眼,探索上述環(huán)境思想因素對(duì)故宮古建筑群以及宮廷制度的影響。
故宮所藏各類文物(如玉器、青銅器、陶瓷、書畫等),皆為中國歷朝歷代物質(zhì)與精神文化之精髓,與故宮古建筑一同見證了中華文化之傳承有序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故宮又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見證:其前身為元大都之大內(nèi),清代又作為滿族王朝之宮殿,內(nèi)藏大量藏傳佛教建筑及文物,凡此種種,皆是民族融合的例證{1}。
故宮博物院藏有2000余件從西方引進(jìn)的科技文物,包括天文學(xué)、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地理學(xué)、機(jī)械鐘表及醫(yī)學(xué)六大類。此外還藏有郎世寧等西方傳教士的大批畫作。它們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故宮博物院院史,則與近現(xiàn)代中國歷盡艱辛的文化轉(zhuǎn)型息息相關(guān)。
從中國文化整體觀之,故宮學(xué)的研究可謂對(duì)整個(gè)中國文化史的研究——誠如單士元先生所言“故宮是一部中國通史”[13]。
1.2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
從中國文化整體的角度研究敦煌學(xué),一方面應(yīng)關(guān)注佛教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相交融的重大主題;同時(shí)還特別要注意的是,敦煌實(shí)際上是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佛教的傳入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大變遷。在敦煌,佛教藝術(shù)的中國化得到充分體現(xiàn),如:石窟外面?zhèn)鹘y(tǒng)的木構(gòu)建筑窟檐;莫高窟早期洞窟的雙闕形龕與敦煌當(dāng)?shù)赝瑫r(shí)期墓葬中雙闕形象之密切關(guān)聯(lián);大量壁畫的傳統(tǒng)線描畫法、粉本之運(yùn)用(有的粉本據(jù)學(xué)者推測直接來自長安),與莫高窟早期洞窟受西域龜茲石窟影響而采用的“凹凸畫”技法形成鮮明對(duì)照;敦煌壁畫與漢代畫像石(磚)之傳承關(guān)系及與唐代宮殿、寺觀壁畫的關(guān)系;畫中的“凈土世界”實(shí)為中國北朝或唐宋宮殿、佛寺乃至住宅建筑的摹寫;佛教造像為中土與印度、西域藝術(shù)的融合,等等。以上內(nèi)容皆有大量學(xué)者曾加以討論。
藏經(jīng)洞文獻(xiàn)除了佛經(jīng),還有大量儒、道經(jīng)典。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學(xué)概論》中指出,藏經(jīng)洞出土的《道德經(jīng)》卷子(寫本)多為高僧抄錄[14]。以上皆佛教與中國文化交融的例證。
與故宮類似,敦煌亦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見證:十六國、北朝、吐蕃與西夏時(shí)期,皆為少數(shù)民族所統(tǒng)治。而敦煌文書中所存各民族語言的文獻(xiàn),各外來宗教的典籍(有的甚至在其發(fā)源地、母語國都已絕跡),至為珍貴,它們正是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一座重要的國際化都會(huì),匯聚東西方多種文化并最終將其融合的明證。
1.3 從中國文化視角看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研究的交流互鑒
從中國文化整體視角審視,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研究有不少可以展開交流合作的地方。
例如結(jié)合歷代都城與宮殿營建來研究故宮古建筑時(shí),敦煌壁畫中所表現(xiàn)的北朝至元代的建筑形象,尤其是唐代的宮殿、佛寺等建筑圖像,便是極其重要的資料。在中國現(xiàn)存唐代木構(gòu)建筑僅有三座完整實(shí)例(即山西五臺(tái)山佛光寺東大殿、南禪寺大殿,芮城廣仁王廟大殿){2}的情況下,敦煌壁畫中數(shù)以百千計(jì)的唐代木構(gòu)建筑圖像,尤其是表現(xiàn)大型宮殿、佛寺建筑群的巨幅經(jīng)變畫,顯得彌足珍貴,是研究唐代木構(gòu)建筑群最重要的形象材料。梁思成先生在《中國營造學(xué)社匯刊》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1932)[15],即是借助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中所刊印的壁畫照片,對(duì)唐代建筑進(jìn)行初步研究。此后,敦煌的學(xué)者們對(duì)此課題進(jìn)行了更深入的探索[16-17]。通過對(duì)敦煌壁畫中建筑圖像的研究,來探討唐代宮殿建筑群營建的情況,將會(huì)大大推動(dòng)以故宮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宮殿建筑的研究——可以說是在敦煌尋找唐代的故宮;反過來看,敦煌大量經(jīng)變畫中所表現(xiàn)的唐、五代時(shí)期宏大壯偉的建筑群,均是以二維平面來表現(xiàn)三維建筑空間,但是如果結(jié)合對(duì)故宮建筑群的真實(shí)空間體驗(yàn),則能更好地幫助今天的人們建立對(duì)唐代宮殿、佛寺等大型建筑群宏偉氣魄的想象與認(rèn)知——又可以說是在故宮尋找敦煌壁畫中唐代宮殿的“影子”。
無論是“在敦煌尋找故宮”,還是“在故宮尋找敦煌”,未來均大有文章可作。以上僅是舉古建筑研究為例,其實(shí)從各類文物、文獻(xiàn)的角度出發(fā),均能在中國文化層面找到不少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交流互鑒的方向。
2. 加強(qiáng)基礎(chǔ)研究與綜合研究
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目前皆已取得豐厚的研究成果。展望未來,還應(yīng)持續(xù)加強(qiáng)基礎(chǔ)研究,這是每個(gè)學(xué)科賴以發(fā)展的根本。此外,基于二者高度綜合性的特點(diǎn),應(yīng)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整體的綜合研究。
2.1 考古、測繪與修繕報(bào)告的編纂
對(duì)敦煌石窟、故宮古建筑進(jìn)行系統(tǒng)的實(shí)地調(diào)查測繪,是中國敦煌學(xué)、故宮學(xué)學(xué)者進(jìn)行相關(guān)研究的巨大優(yōu)勢(擁有近水樓臺(tái)之便),同時(shí)也是重大的責(zé)任。敦煌石窟考古報(bào)告集、故宮古建筑測繪圖集以及修繕報(bào)告集的編纂,依然是敦煌學(xué)、故宮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重大工程,也是中外學(xué)者對(duì)敦煌石窟與故宮古建筑進(jìn)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前提。正如樊錦詩先生指出的,科學(xué)、完整而系統(tǒng)的考古報(bào)告集,“將成為永久保存、保護(hù)、研究和弘揚(yáng)敦煌石窟信息,乃至全面復(fù)原的依據(jù)”[10]41。
敦煌石窟考古報(bào)告的撰寫是一項(xiàng)艱巨、浩繁、長期的系統(tǒng)工程,仍然任重而道遠(yuǎn)。目前考古報(bào)告已于2011年出版第1卷,但距離規(guī)劃中的100卷(包括莫高窟86卷,西千佛洞3卷,榆林窟10卷和總論1卷){1}的宏偉藍(lán)圖,還有漫長而艱辛的道路要走。
與敦煌的情況類似,故宮也有數(shù)量巨大的古建筑,目前公開發(fā)表的測繪圖僅是少部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1940年代張镈主持完成的測繪圖。大量1990年代以來陸續(xù)完成的測繪資料尚未整理發(fā)表,此外還有不少建筑未測。可以說,從1934年中國營造學(xué)社計(jì)劃全面測繪故宮開始,迄今已過去近90年,故宮的測繪大業(yè)尚未完成,更遑論全面出版測繪圖集。因此,故宮古建筑的測繪及整理出版(如計(jì)劃中的《故宮古建筑實(shí)錄》叢書{2}等),依然是未來故宮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
2.2 文物及文獻(xiàn)資料的整理、出版及網(wǎng)絡(luò)公布
敦煌文獻(xiàn)方面,目前散落各處的敦煌文獻(xiàn)絕大部分已經(jīng)發(fā)表,可供研究者使用。未來的一項(xiàng)重要基礎(chǔ)工作,應(yīng)當(dāng)致力于分類目錄的編寫(目前各收藏機(jī)構(gòu)僅有帶序號(hào)的總目,編目時(shí)未作分類,給學(xué)術(shù)研究造成極大不便),為各學(xué)科學(xué)者提供基本的文獻(xiàn)檢索平臺(tái)。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此項(xiàng)工作比過去更具備實(shí)現(xiàn)的可能。
故宮方面,各類館藏文物已出版大量精美圖錄(如《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冊(cè)等),除了繼續(xù)進(jìn)行文物、文獻(xiàn)的整理出版之外,也應(yīng)借鑒敦煌文獻(xiàn)的做法,編纂故宮館藏文物、文獻(xiàn)目錄,以及流散文物、文獻(xiàn)目錄等。此外還應(yīng)借鑒英、法等國敦煌文書收藏機(jī)構(gòu)的經(jīng)驗(yàn),為各類文物、文獻(xiàn)(如明清檔案)建立更加開放的數(shù)據(jù)庫、信息平臺(tái),供中外學(xué)者更加方便地開展研究——這項(xiàng)工作應(yīng)該聯(lián)合收藏故宮文物、文獻(xiàn)的海內(nèi)外機(jī)構(gòu),共同實(shí)現(xiàn)資源共享——這是故宮學(xué)邁向國際化的重要舉措,也是全面研究故宮收藏的必由之路。
2.3 整體的綜合研究
敦煌學(xué)和故宮學(xué)的研究,皆應(yīng)注意研究對(duì)象的整體性,宜將流散海外的珍貴文獻(xiàn)、文物,以及分散收藏在中國其他機(jī)構(gòu)的文獻(xiàn)、文物,結(jié)合敦煌、故宮本身的收藏,以及石窟與古建筑本體進(jìn)行綜合研究,以期獲得對(duì)文化整體的充分認(rèn)識(shí)。
以故宮為例,故宮的古建筑、館藏文物和故宮博物院是文化上的有機(jī)整體,因而治故宮學(xué)者,應(yīng)重視三者之內(nèi)在聯(lián)系,比如注意宮廷收藏之文物與宮廷制度之關(guān)聯(lián);各類文物與宮廷的政治、禮儀、宗教活動(dòng)、日常生活以及各建筑群空間之關(guān)聯(lián);各類文物、建筑空間與明清宮廷檔案記載之關(guān)聯(lián);各類宗教建筑空間與館藏宗教文物之關(guān)聯(lián)等等。例如結(jié)合兩岸故宮所藏康熙《皇城衙署圖》、乾隆《京城全圖》等珍貴的古代測繪圖(輿圖),可以對(duì)故宮古建筑的歷史沿革進(jìn)行更加深入的探討,還可以和現(xiàn)狀測繪圖進(jìn)行比較研究;結(jié)合故宮所藏宮廷繪畫如《萬國來朝圖》《康熙南巡圖》《京師生春詩意圖》等,可對(duì)畫中不同時(shí)期的故宮古建筑群及其現(xiàn)狀進(jìn)行比較研究,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總之,學(xué)者在專研各自專業(yè)領(lǐng)域的同時(shí),應(yīng)能對(duì)文化整體進(jìn)行觀照;各不同專業(yè)之間更應(yīng)加強(qiáng)交流,包括國際間的合作交流,逐步邁向整體的綜合研究。
3. 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與公眾普及
敦煌莫高窟與故宮都是1987年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的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chǎn)。對(duì)這兩處偉大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工作仍充滿挑戰(zhàn),是未來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研究的重要使命。兩處遺產(chǎn)的保護(hù),牽涉到木構(gòu)建筑、石構(gòu)建筑、壁畫、彩塑,以及種類豐富的文物、文獻(xiàn)的保護(hù)、修繕或修復(fù)等復(fù)雜的工作。不僅如此,兩處遺產(chǎn)地目前已同時(shí)進(jìn)入到以預(yù)防性保護(hù)為主的中國文物保護(hù)的新時(shí)代。面臨上述多方面的情況,對(duì)敦煌石窟與故宮的遺產(chǎn)保護(hù)工作,需要探索更加科學(xué)的保護(hù)理念,積極運(yùn)用當(dāng)代先進(jìn)的保護(hù)科技,并加強(qiáng)國際交流協(xié)作。在此方面,敦煌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也應(yīng)積極展開多方面的交流協(xié)作,如壁畫、彩塑、彩畫保護(hù)、木構(gòu)建筑與石質(zhì)文物保護(hù)、等等。
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既要充分運(yùn)用當(dāng)代先進(jìn)的理念和科技,同時(shí)要做好公眾普及工作,以便更好地弘揚(yáng)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近二十多年來得到充分發(fā)展的 “數(shù)字敦煌”與“數(shù)字故宮”建設(shè),都是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和公眾普及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新成果,它們一方面是敦煌學(xué)、故宮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重要手段,如運(yùn)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對(duì)文化遺產(chǎn)(不論是古建筑群還是各類藝術(shù)品、文物、文獻(xiàn)等)進(jìn)行信息采集、存檔、分析、研究與保護(hù);同時(shí)又以高度可視化的多媒體成果架起文化遺產(chǎn)與社會(huì)公眾之間的溝通橋梁。不斷發(fā)展中的“數(shù)字敦煌”和“數(shù)字故宮”必將對(duì)未來敦煌學(xué)和故宮學(xué)的發(fā)展起到更大的推動(dòng)作用。
以“數(shù)字故宮”為例,其總體目標(biāo)是利用先進(jìn)的信息技術(shù),遵循真實(shí)、完整、可用的數(shù)字資源長期保存原則,更好地保護(hù)和展示古老的故宮文化遺產(chǎn),助推文化資源的全人類共享,是21世紀(jì)故宮博物院發(fā)展建設(shè)的重要目標(biāo)之一。結(jié)合故宮學(xué)立足于中國文化整體的視野,未來“數(shù)字故宮”也將在“文化大數(shù)據(jù)”戰(zhàn)略指引下,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豐富內(nèi)涵和元素符號(hào),秉持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理念,充分利用數(shù)字資源開展更為多樣性的線上線下數(shù)字傳播、展示與服務(wù)[18]。
五 結(jié) 語
既充分尊重與繼承傳統(tǒng),又以開放包容、博大的心胸吸收外來的優(yōu)秀文化,并將其成功融入中國固有文化之中,在敦煌石窟和故宮身上皆有著強(qiáng)有力的表現(xiàn)——這也是中華文化之所以源遠(yuǎn)流長、生生不息,具有無窮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研究與發(fā)展敦煌學(xué)、故宮學(xué)這兩門博大精深、包羅萬象的學(xué)問,同樣要具有尊重傳統(tǒng)又開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以及繼往開來的氣魄。
與敦煌學(xué)目前所具備的國際化程度相比,更年輕的故宮學(xué)尚有一定差距,應(yīng)充分借鑒敦煌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更加注意吸收海外學(xué)者的故宮學(xué)研究成果,并與之積極展開交流合作。敦煌學(xué)與故宮學(xué)未來更大的發(fā)展,皆有賴于中外學(xué)者的共同努力、交流互鑒,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敦煌在中國,敦煌學(xué)在世界”——未來故宮學(xué)亦如是。
參考文獻(xiàn):
[1]榮新江. 敦煌學(xué)十八講[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6.
[2]劉進(jìn)寶. 敦煌學(xué)通論[M].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9:4-5.
[3]鄭欣淼. 故宮學(xué)述略[J]. 故宮學(xué)刊,2004(1):8-35.
[4]章宏偉. 作為學(xué)問的故宮學(xué)[M]. 北京:故宮出版社,2019:1.
[5]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1:179.
[6]李正宇. 敦煌學(xué)導(dǎo)論:第8章[M].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138.
[7]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M]. 香港:商務(wù)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3:5.
[8]巫鴻. 空間的敦煌:走近莫高窟[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2:前言4-10.
[9]王素. 故宮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初探[M]. 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57-60.
[10]樊錦詩.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bào)告編撰的探索[J]. 敦煌研究,2013(3):40-46.
[11]梁思成. 營造法式注釋:卷上[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3:8.
[12]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shí)測圖集[M]. 北京:故宮出版社,2017.
[13]中國紫禁城學(xué)會(huì)論文集:第2輯[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386.
[14]姜亮夫. 敦煌學(xué)概論[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0-23.
[15]梁思成. 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J]. 中國營造學(xué)社匯刊,1932,3(1).
[16]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畫卷[M]. 香港:商務(wù)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
[17]蕭默. 敦煌建筑研究[M]. 北京:機(jī)械工業(yè)出版社,2002.
[18]王旭東. 數(shù)字故宮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J]. 科學(xué)教育與博物館,2021(6):52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