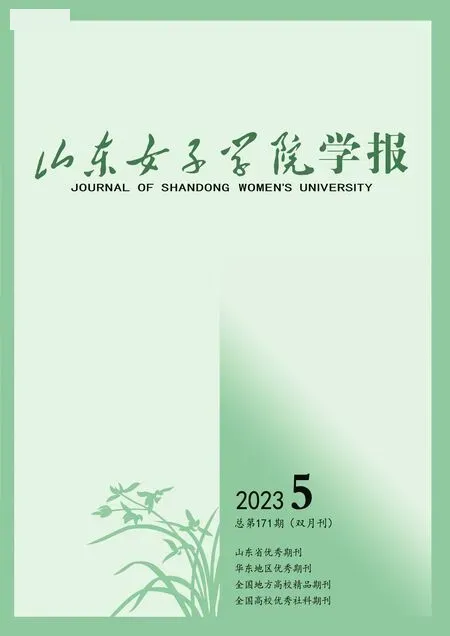面向人口高質量發展的農村生育形勢分析
王記文
(農業農村部 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北京100810)
一、引言
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的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至今已逾60年。根據世界人口展望(WPP)數據,1991年中國大陸總和生育率(TFR)驟降至1.93,跌至更替水平以下,開啟了人口內在負增長。在過去的10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制定實施了單獨兩孩生育政策、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和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但仍未扭轉總和生育率下降的勢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于2022年開始人口負增長,而農村人口在區劃調整和就地城鎮化[1]的作用下早在1996年就已開始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95年農村人口達到頂峰的8.59億人,而后連年下降;2022年農村人口降至4.91億人,不足頂峰時的六成。不同于總人口和城鎮人口,農村地區人口減少經受了人口外流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在連續數十年人口城鎮化和人口外流不可避免的狀況之下,人口老齡化所牽涉的一系列問題對農村人口生育提出了更加迫切的期望。
人口學界對于全國生育水平的估計非常多。例如,有學者回推估計過往15年的生育水平,發現2017年之后出生人口數和生育率大幅下降[2]。具體到農村生育的研究,以往文獻主要是對個體層面的調查數據進行的微觀分析。一方面是對農村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進行的分析。有研究分析了甘肅省農戶生育水平的變動趨勢[3];還有研究對比了25歲以下育齡婦女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城鄉差異[4]。另一方面是對農村生育影響因素進行的分析。有研究者對比分析了東中西部農村居民二孩生育的影響因素[5];另有研究發現,農地產權[6]和社會養老保障[7]對農村生育有影響;還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動降低了農業戶籍人口的生育水平[8],而戶籍城鎮化在一定條件下也可提高生育率[9]。此外,也有文獻分城鄉比較了生育率的變動趨勢。相關研究發現,1965年以來,城鄉生育水平均呈整體下降趨勢,但農村生育水平始終低于城市[10]。20世紀80年代,農村總和遞進生育率相對平穩,并且遠高于城市;1990年初急劇下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11]。盡管許多鄉—城流動人口已常住城市,但當時計劃生育政策仍按戶籍區別管理,因此,農業戶籍人口的生育率始終高于非農戶籍人口[12]。從孩次結構看,城鄉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源于一孩生育率下降。2005—2015年間,一孩總和生育率從0.990下降至0.607,而二孩總和生育率下降趨勢不明顯[13]。受生活壓力等因素的影響,流動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極低。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的城鎮化、非農化和大流動,成為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影響因素[14]。并且,城市流入人口的生育水平既低于當地農村人口,又低于當地城市人口[15]。盡管2005—2015年間流動婦女和非流動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均在下降,但2015年流動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不足0.9[13]。
在以往研究對農村宏觀生育趨勢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使用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公布的2000、2010、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匯總數據,從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的角度,使用一般生育率(GFR,即出生人口與15~49歲育齡女性人口之比)、年齡別生育率(ASFR)、總和生育率指標描述農村人口的生育變動趨勢。本文接下來的安排如下:首先,從城鄉對比的視角,通過生育高峰(即生育率曲線的最高點)和峰值生育率(即生育率曲線最高點對應的年齡別生育率)的位置移動,揭示農村生育的變化趨勢;其次,為了探尋出生人口的主要來源,本文分別分析農村生育的孩次差異和區域差異,并與城市和鎮進行對比分析,以便發掘農村生育的深層特點;再次,本文基于農村生育形勢,就如何從生育角度應對人口負增長展開相關思考和政策討論。
二、鄉村生育率始終高于城鎮,呈現出推遲和分散的特點
在鄉村地區人口率先開始減少后,鄉村出生人口仍然是全國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鄉村的生育率在2000—2020年間始終高于鎮和城市地區,說明鄉村家庭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或者生育意愿得到了較好的滿足。因此,在全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后,比以往更加需要依賴農村人口轉移補充城鎮人口。然而,鄉村生育模式在21世紀也發生了強烈的變化,出現了生育率下降和生育推遲的共生現象(見表1)。

表1 分城鄉的一般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
進入21世紀以來,全國生育率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同期鄉村地區的生育率也經歷了類似過程,但相對穩定。無論鄉村和全國生育率如何波動,鄉村生育率始終高于全國生育率。2000年鄉村地區一般生育率為40.93‰,同期全國一般生育率為36.11‰。2000—2010年間,鄉村和全國生育率均經歷了下降過程。2010年鄉村地區一般生育率略降為39.04‰,而同期全國一般生育率降為33.31‰。2010—2020年間,鄉村和全國生育率均經歷了回升過程。2020年鄉村地區一般生育率緩慢回升為40.58‰,同期全國一般生育率回升為37.26‰。雖然鄉村的一般生育率發生了先下降、后回升的現象,但鄉村的總和生育率從2000年和2010年的1.43和1.44增長為2020年的1.54。這說明鄉村育齡女性的年齡結構在此期間發生了改變,尤其是2010年作為生育主力的25~29歲育齡女性占比明顯低于2000年和2020年,導致鄉村一般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呈現出不一致的變動趨勢。
第一,鄉村生育水平波動的背后是其生育模式的變化。2000年鄉村地區的生育高峰更為集中,而2010年和2020年的生育高峰后移且更為分散。2000年鄉村地區的生育高峰落于23歲,高峰生育率為171.7‰。2000—2010年間,鄉村生育高峰僅推遲1歲,但高峰生育率下降明顯。2010年鄉村地區的生育高峰推遲至24歲,高峰生育率驟降為125.1‰。2010—2020年間,鄉村高峰生育率略微下降,但生育高峰推遲2歲。2020年鄉村地區的生育高峰推遲至26歲,高峰生育率略降為120.1‰。以25歲為節點,可以將鄉村地區年齡別生育率大致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25歲前,年齡別生育率主要呈逐年下降趨勢;在25歲后,年齡別生育率主要呈逐年上升趨勢。上述結果表明,鄉村人口的生育模式同時呈現出“晚育”和“分散”兩個特點。
第二,鄉村和鎮的生育模式逐漸靠攏。2000年鄉村和鎮的生育高峰分別落于23歲和24歲,對應的高峰年齡別生育率分別為171.7‰和140.1‰;此時城市的生育高峰落于25歲,對應的高峰年齡別生育率為115.1‰。2000—2010年間,鄉村和鎮的生育高峰年齡逐漸接近,但峰值生育率仍存在一定差距。2010年鄉村和鎮的生育高峰均落于24歲,對應的高峰年齡別生育率分別下降為125.1‰和106.2‰;此時城市的生育高峰落于28歲,對應的高峰年齡別生育率下降為83.2‰。2010—2020年間,鄉村和鎮在保持生育峰值年齡接近的同時,進一步降低了峰值生育率。2020年鄉村和鎮的生育高峰均推遲至26歲,對應的高峰年齡別生育率分別為120.1‰和117.1‰;此時城市的生育高峰依然落于28歲,對應的高峰年齡別生育率回升為96.3‰。此外,2000年鄉村生育率在28~32歲之間有一個明顯高于鎮和城市的“隆起”,該隆起在2010年有所弱化,直至2020年幾乎完全消失。至此,鄉村和鎮生育高峰年齡和峰值生育率高度接近,二者的年齡別生育率在生育高峰之后幾乎完全重合,差別僅存在于生育高峰之前。
三、鄉村生育地區差異明顯,東北鄉村生育率遠低于其他地區
雖然鄉村整體的生育水平高于全國整體水平,但受限于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鄉村生育水平存在更大的區域間差異,并非所有區域的鄉村生育水平都高于全國整體水平。就全國整體和城市地區而言,生育率的區域差異并不明顯;問題在于鎮和鄉村,特別是鄉村的生育率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東北鄉村的生育率遠遠低于西部、中部和東部鄉村,而西部鄉村的生育率遠高于全國和其他地區鄉村(1)參照國家統計局對經濟地帶的劃分方法: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0個省(直轄市);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個省;西部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東北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個省。。
除東北鄉村總和生育率略低于東北總體水平外,其他區域鄉村的總和生育率均高于區域整體水平。202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3,其中西部和中部最高,分別為1.5和1.3;其次為東部,為1.2;東北最低,僅為0.9。2020年,鄉村總和生育率為1.5,高于全國整體水平。其中,西部鄉村最高,為2.1,恰好處于更替水平,遠高于西部整體水平;其次為中部鄉村和東部鄉村,均為1.5,高于中部和東部整體水平;東北鄉村最低,僅為0.8,低于東北整體水平。
相比于城市和鎮,鄉村的年齡別生育率具有更明顯的區域差異。無論東、中、西部,抑或東北,鄉村生育高峰均落于25~29歲年齡組,生育高峰對應的年齡別生育率呈現出“西部>中部=東部>東北”的格局。2020年,西部鄉村25~29歲年齡組的生育率最高,為142‰;其次為中部鄉村和東部鄉村,均為111‰;東北鄉村最低,為62‰,僅為西部鄉村相應年齡組的一半左右(見圖1)。

圖1 分城鄉年齡組別生育率的區域差異(‰)(2020年)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匯總數據。
四、鄉村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占比提升,呈現出年輕化和鄉鎮同質化特征
在人口減少時期,不但鄉村整體的生育模式發生了變化,鄉村的多孩生育模式也發生了明顯改觀,并與城鎮的多孩生育模式逐漸接近。一個突出的變化是低齡產婦生育多孩的比例明顯上升,這是城鄉的共性。所不同的是,多孩生育占比在城鎮各年齡段育齡女性中均有提升,而在鄉村僅年輕女性選擇多生。
進入21世紀以來,鄉村地區一孩出生占比降低,而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經歷了持續上升過程,占比從四成增至六成,與全國情況類似;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始終高于全國。2000年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為38.56%,同期全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為31.95%。2000—2010年間,鄉村和全國的二孩出生占比均小幅提升。2010年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上升為44.61%,同期全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上升為37.83%。2010—2020年間,鄉村和全國的二孩出生占比均大幅提升。2020年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達到60.00%,同期全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達到54.23%,其中鎮和城市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達到57.17%和48.20%。
第一,鄉村地區二孩及多孩生育呈現年輕化特點。以28歲為節點,可以將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大致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28歲之前,2000—2010年間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變動不大,2010—2020年間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明顯上升。相反,在28歲之后,2000—2010年間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有比較明顯的下降,2010—2020年間鄉村地區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變動不大。
第二,鄉村和鎮的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亦逐漸靠攏。2000年,30歲及以上鄉村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有約9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30歲及以上鎮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有約70%~8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30歲及以上城市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有約50%~6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2000—2010年間,30歲及以上鎮育齡婦女所生育的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下降明顯。2010年,30歲及以上鄉村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有約70%~8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30歲及以上鎮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有約60%~7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30歲及以上城市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有約30%~5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2020年,30歲及以上鄉村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仍有約70%~80%為二孩及以上孩次,但鎮和城市30歲及以上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中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大幅上升,其中鎮的占比已接近鄉村。不過,在30歲之前生育多孩次方面,鄉村育齡婦女仍然保持一定的領先優勢(見圖2)。

圖2 鄉村地區年齡別二孩及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比重及歷次普查城鄉差異(%)(2000—2020年)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匯總數據。
五、思考與討論
在農村受人口外流和區劃調整影響而先于全國26年開始人口減少的背景下,農村生育水平和模式需要得到比以往更多的關注。為此,本文結合歷次人口普查匯總數據,從年齡結構和孩次結構兩個維度分析了農村生育在21世紀的變動趨勢,得出一些重要結論。
第一,農村在21世紀發生了生育時間的推遲和生育水平的下降。本文發現,雖然農村生育率高于城鎮,但農村生育高峰年齡從2000年的23歲后移至2020年的26歲,同時峰值生育率也在20年間下降了5個百分點。鑒于生育文化觀念短期內難以改變,需要從外部經濟社會環境發力,不能任由社會壓力繼續降低農村家庭的生育意愿或者限制其生育意愿的滿足,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必須著力關注農村生育環境。應仔細梳理現有農村政策措施,在治理高價彩禮等問題的基礎上,出臺針對農村地區的生育激勵政策,讓有意愿生育的農村婦女得償所愿;或者在今后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強調優先在鄉鎮布局托幼撫育設施,解決嬰幼兒看護問題,避免農村夫妻對隔代照料和留守兒童的擔憂,幫助農村育齡人口更好地實現生育意愿。
第二,農村一孩出生占比下降。本文發現,2000—2020年間,農村出生人口中一孩絕對數量和占比急速下滑,相應的是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上升。治本之策是改變農村人口的外部生存環境,切實解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產生的社會根源。然而,養育一個孩子與多個孩子的精力付出和經濟支出是不同的。相比20年前,2020年農村二孩占比和三孩及以上占比均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農村多孩家庭可能會面臨經濟窘境。對于鄉村年輕女性多生現象,相關政策應及時給予充分支持,避免在遭受外部環境沖擊的情形下生育率再度下跌。例如,隨著受教育程度的逐年提高,農村年輕女性多生的現象可能會再度發生推遲。為了保證農村女性及時完成自主生育,需要對有生育意愿的農村家庭進行經濟補償,并切實保障育齡女性各項權益。
第三,對于低生育率問題需要分城鄉看,警惕東北農村人口急劇下滑風險。本文發現,生育率的區域差異在農村更明顯,2020年西部農村25~29歲年齡組的生育率相當于東北農村的2倍,而且東北農村的總和生育率甚至不及東北整體。在全國人口負增長和低生育率時代,需要針對不同地區分層施策,以達到精準提升生育率的目的。本文認為,要穩固西部農村生育水平,提振東北地區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