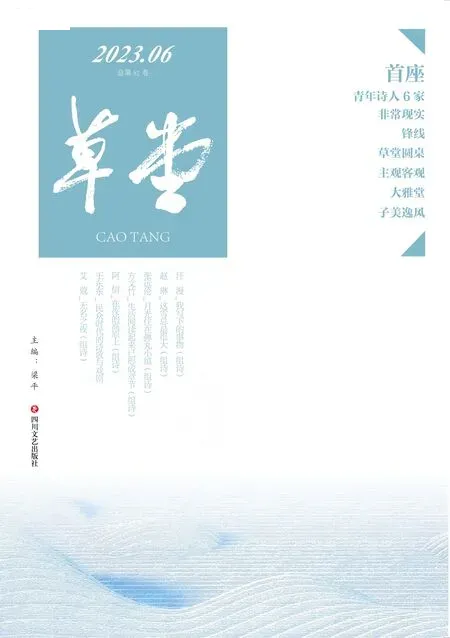趁著晨霧未散,且說阿信
◎唐 欣
阿信是我在西北師大上學時的學長,我是84級中文系,他高我兩屆,是82級歷史系,在校時并不太認識,來往不多,我們當時還挺熱鬧的詩社,他也沒有參加,真正熟悉起來,是畢業以后的事了,那時他已是甘肅詩界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了。我在西安讀研時,他帶學生來訪學考察,我跑去旅館看他,他正半開玩笑地叮囑那些純樸的學生。
我還記得第一次去甘南州府合作的情景。早晨,天剛蒙蒙亮,我在蘭州七里河,上了長途班車,一路翻山越嶺,經過田野和牧場,成群的牛羊、三三兩兩的毛驢和狗,還有大片的林區。一條河流始終在車旁奔流,山上的巖石閃耀著金屬之光,全車的旅客都已昏昏欲睡,我們也慢慢從黃土高原登上了青藏高原。下午時分,轉過一座山,就能看見下面安靜的,有些塵土飛揚的小城。剛一下車,我立刻感到充滿涼意,有些粗糙的風,在夏天真是少見。我還想,這兒可真遠,真有些荒蕪啊(那會兒甘南還沒有成為現在的旅游熱點,單位出差,沒人愛來,只能打發一些混不清楚的邊緣人員前去,我倒也得以數次來到這里,不但暢游了過去從未到過的草原、喇嘛廟,與朋友歡聚,在充滿馬圈氣息的電影院看武打片,其間牧民們搖晃著長條木椅,爆發出陣陣狂笑,我還在此留下了自己的詩作,后期阿信還在學校給我安排過詩歌講座)。安頓完公事,就是去找朋友報到了——阿信,還有他的同學、詩人桑子。他們所在的合作民族師范學院(當時還是師專)位于小鎮的近郊,要走好一陣子,似乎也要高一些。好像到了這里,就過了三千米海拔線了(對心臟和肺活量似有要求,我四十多歲后再到這里,開始出現氣短和失眠的癥狀)。學校挺新的,條件也還不錯,坐在他們的宿舍喝茶,看看周邊的風景,我突然覺得這兒也挺好的(現在阿信在此都住了快四十年了)。我們寫作的詩歌路數不同,但這一點都不重要,校友加詩友,彼此欣賞,那就是江湖兄弟的情誼了。文學青年消磨時間的方式估計都差不多,喝酒,吃肉,沒完沒了地聊天,講笑話,四處閑逛,我們度過了難忘的快樂時光。某年暑假他來我所在的干部學校小住,正好蘭州要搞什么中國藝術節,我有個師兄在籌備組,硬是要攬下開幕式解說詞的活給我們,他大概想,詩人妙筆生花,這點文案還不是小菜一碟。這也是我和阿信唯一的一次合作,我們還挺重視的,但辛辛苦苦弄了半天交上去,等到盛會開幕,詞兒當然有,但不是我們的。看起來,我們不是干這號事兒的人啊,倒也好,以后就再也不碰這種事情了。阿信脾氣溫和,為人厚道,總是帶著微笑,和他相處非常舒服。詩歌反倒談得并不多,頂多說說詩壇逸事什么的。各自的詩都在那兒放著,作品就是最好的詩論,所以也無須多言。我的第一本詩集出來,最早寫評論鼓勵的朋友就有阿信。那會兒聲名不顯,出頭不易,還只能發在天水的一家小報紙上。反過來,我可能也是比較早研究阿信的人之一,而且,后來很多人討論的阿信的若干詩歌品質或者特點,諸如孤獨、安靜、緩慢、謙遜和感恩等,好像正是本人先總結出來的。寫詩的人很多,但能寫出自己的地域或境界的詩人很少,阿信就是這少數人之一。他創造出的詩歌的甘南草原(后來他的領土有所擴大,涵蓋了西部乃至全國,但都是他特有的筆觸和色調),跟我見到和感受到的并不太一樣,可能我只是個浮光掠影的匆匆過客,而他已經與這片高地水乳交融了吧。但在這里祖祖輩輩生活的人多了,別的人也并沒有寫出來呀,況且,即或是寫了(我想起同樣待在那兒的詩人桑子、扎西才讓、敏彥文、李志勇等),也跟他的完全不同。這就是每個詩人自己特別的詩學了。 阿信筆下這個自足的世界,清冷,寂寞,略帶憂傷,也飽含溫暖和柔情,氣質很像我看過的某些俄羅斯小說,特別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這是情境,也是意境,更是詩人的心境,他要在這里安頓自己,徜徉和休憩,出發并返回,這是他獨有的、專屬的詩歌家園,非常迷人,吸引著無數的讀者,我也時常沉浸并沉醉其中,獲得久違的寧靜和感動。我忘不了他一首寫藏羚羊的詩,“它們從藏身的巖穴出發,踩著草莖,碎石,/薄薄的月光,沿河谷走向庫賽湖湖畔。/湖面的反光,路邊一絲輕微的風吹草動/都會讓它們感到心驚。”真是令人戰栗,這不光是那些可憐的動物,也是大部分人類的寫照吧!小心翼翼地活著,真不容易啊,我們怎能不彼此珍重?很自然地,阿信那里就成了甘南的詩歌中心,圍繞在他身邊的年輕人不少。記得有一次我到合作出差,去阿信他們學校玩,碰上一位從山里來的,看上去還很靦腆的小伙子,敲門進來,拿著一本《詩刊》,挺興奮地跟他們說,他的作品又發表了。我看阿信和桑子的神情都不太自然,有點尷尬,支支吾吾的,拿過來一看,果然,明明標注著是洪燭的詩嘛!小伙子還拿著個大本子,把洪燭發布的作品都粘貼在上面,看來他是把洪燭當作自己的筆名了,就陶醉在自己的幻覺里。哎呀,這可真是有點凄涼。但恐怕阿信他們看他那么真誠,又那么高興,誰也不忍心揭破他吧。還有一次,一個冒名的詩歌騙子跑到了甘南,主要是蹭吃蹭喝,順帶著也偷點東西之類。阿信給我講他是怎么識破這個家伙的——晚上他們在看電視,正播中國的小提琴獨奏《梁山伯與祝英臺》,大家都全神貫注,這小子不知趣,兀自東張西望,說個不停,雖然這人對詩壇還有些了解,掌握著聯絡圖上的很多信息,但對美如此無感,完全絕緣,他當即斷定,此人必是騙子。有點道理,我心里暗想,阿信也夠天真簡單的。甘南的雪下得早,結束得晚,雪天很多。雪天是否更適宜寫詩呢?我覺得肯定是的。還有,阿信常年生活在這里,對當地的生活態度耳濡目染。這都成了他詩里獨特的底色。但命運的安排誰也不會想到,又過了幾年,老實巴交的阿信居然成了學校的領導,上面自有慧眼,他的品行和能力經得起公論。見面發現,阿信作為一位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的大學副校長,確實也沒有絲毫的違和感。2006 年我調到北京,學校對面,俗稱校長大廈,是教育部培訓高校領導的專門機構,阿信正好在此學習。好嘛,我又去體驗他們的伙食,比方西安羊肉泡饃,做得還真是地道呢。 又是長談, 看到我的近作,他回去后,還用電腦寫出模仿的詩體來唱和調侃。有一年的五一節左右,他來北京,我們在三聯書店附近的一個飯館喝啤酒。還有一次,是在新疆烏魯木齊的某個酒店,我們因為兩場完全不搭界的詩歌活動相遇。當然,工作的變動,并沒有影響他的寫作。沒準他比以前,更需要詩歌的支撐和平衡。詩人,真的是一個特別的種族,其感受方式和表達欲望,構成了很難擺脫的身份和情結,他的熱情和樂趣就在這個地方。對詩歌的忠誠終生不渝。職務只是一時,詩歌和詩人才能長久。后來阿信的詩反而更多了。“有人說,馬在這個時代是徹底沒有用了/牧人也不愿再去牧養它們/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許/神還需要/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我看見它們在那里,我可以把它們一匹匹牽出來”。確實如此,我看到他的詩越來越好,也越來越受到歡迎,各種大獎紛紛收入囊中,這是詩人成熟期自然收獲的結果了。
雖然相距遙遠,朋友圈交集也不多,但作為青年時代的朋友,心理沒有距離,時常還是惦念。如他所說,“我始終對內心保有詩意的人充滿敬意”,是的,我們方向不盡相同,但想象并體會這樣的旅程,永遠有著并肩向前的親切感,“黑馬涂炭,紅馬披霞,栗色夾雜著雪花。/我們的皮袍兜滿風,腰帶束緊。/人和馬不出聲,頂著風,在僵硬的裸原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