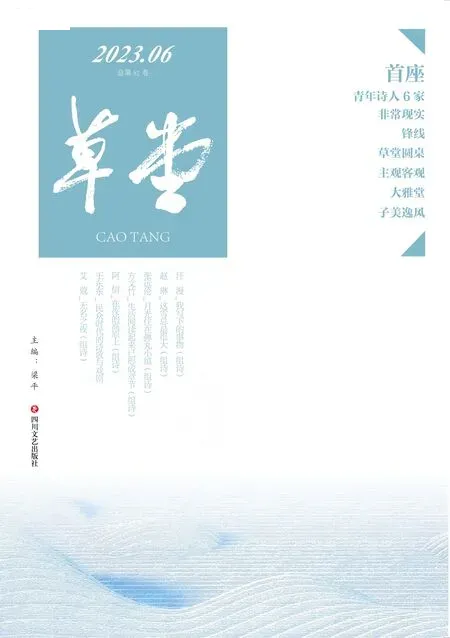開放的語(yǔ)言意識(shí)與智性表達(dá)
隋 倫
本卷六位青年詩(shī)人的作品有著明顯的個(gè)性,他們對(duì)外部世界的觀察和內(nèi)在經(jīng)驗(yàn)的表現(xiàn)充滿審視與思辨,在獨(dú)特的經(jīng)驗(yàn)積累的過程中試圖厘清自我與生活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他們的創(chuàng)作也來源于不同的生活現(xiàn)場(chǎng),有對(duì)生活經(jīng)驗(yàn)與文化經(jīng)驗(yàn)獨(dú)立的姿態(tài)和表達(dá)。開放的詩(shī)歌語(yǔ)言意識(shí)和清醒的智性言說,激發(fā)并浸潤(rùn)著他們的創(chuàng)新性與想象力,使他們的詩(shī)歌在擁有獨(dú)特的個(gè)體語(yǔ)言的同時(shí),也具備了介入和表現(xiàn)復(fù)雜現(xiàn)實(shí)、拓寬寫作視野與空間的能力。
趙琳較早的詩(shī)歌多和大西北有關(guān),獨(dú)特的地域景觀普遍存在于他的詩(shī)歌中,使他的詩(shī)歌在歸屬于大西北的精神原鄉(xiāng)的同時(shí),展現(xiàn)出樸素曠遠(yuǎn)的詩(shī)意與想象。本期所刊發(fā)的趙琳的組詩(shī),在生活經(jīng)驗(yàn)上有所變化,不再是對(duì)過去鄉(xiāng)土生活的簡(jiǎn)單重構(gòu),而是建立起與當(dāng)下城市生活的共生互融,有力地凸顯出趙琳豐富的生活情境與精神向度。《鄉(xiāng)村音樂會(huì)》仍然是對(duì)鄉(xiāng)土生活經(jīng)驗(yàn)的表現(xiàn)和思考,在趙琳的精神世界里,鄉(xiāng)土生活經(jīng)驗(yàn)與內(nèi)在的感覺有著某種共通性,它們?cè)谠?shī)中獲得了一定的平衡,并具備了深沉的情感力量。在《鐘樓廣場(chǎng)》中,趙琳將鄉(xiāng)土生活經(jīng)驗(yàn)同城市經(jīng)驗(yàn)相融合,重新賦予鄉(xiāng)土生活更為開闊的想象空間,從新的感受中理解并認(rèn)識(shí)舊的經(jīng)驗(yàn)。“歸鄉(xiāng)人帶回臺(tái)風(fēng)、數(shù)據(jù)、元宇宙……/那些漲潮的喧嘩與返璞的落寞/像電影一幕幕演繹結(jié)束前/我們坐在鐘樓廣場(chǎng)不談?wù)撓绲穆淙铡保@種帶有新的意象的鮮明語(yǔ)言,更能有效地反應(yīng)當(dāng)下時(shí)代生活的面貌與變化。《博物館》則通過直接的觀照,具體而深刻地表現(xiàn)了他對(duì)時(shí)間與命運(yùn)的理解。“我留意到撒滿顆粒的石壁/一根根線條勾勒著/許多人臉,他們沖破界線/追趕石頭里的大象”,在語(yǔ)言與想象互相糾纏的描述里,塵封的歷史從石壁中復(fù)活并延伸,進(jìn)入到詩(shī)人感性的精神世界,趙琳正是在這感性經(jīng)驗(yàn)與理性認(rèn)知的結(jié)合與表現(xiàn)中,從生活現(xiàn)場(chǎng)出發(fā),不斷開拓與熔煉自己的觀照視域和語(yǔ)言,使詩(shī)歌的表現(xiàn)力與生命力得到強(qiáng)化。
張悅的組詩(shī)中語(yǔ)言與詩(shī)的意義之間形成了某種對(duì)應(yīng),她融合古典意象所創(chuàng)造出的新的表達(dá)形式,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不同層面作出反映,表現(xiàn)出了詩(shī)歌與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的深刻性,當(dāng)詩(shī)歌語(yǔ)言的生成在繼續(xù),詩(shī)歌的意義也在不斷豐富和延伸。《修復(fù)與自愈》中使用了古典與現(xiàn)代詩(shī)歌中不同的意象符號(hào),它們沉淀了厚重的歷史與審美意蘊(yùn),表現(xiàn)出較為豐富的詩(shī)性空間,“被圓月里的強(qiáng)磁吸入山水古意”“被驟雪里的簧片彈向史蒂文斯的二十座雪山”,張悅在虛實(shí)結(jié)合使用上極有想法,通過熟悉的經(jīng)驗(yàn)與想象來感知抽象的觀念,從而獲得對(duì)客觀世界獨(dú)到的理解與表達(dá)。“喜憂參半,是一只斑鳩亮出珍珠/合上扇面的不確定感。/尖塘鱧埋進(jìn)泥沙的白晝/能否逃過夜的砧板?”(《喜憂參半》)不同的事物在張悅筆下,巧妙地與內(nèi)心感受發(fā)生聯(lián)系,抽象的情感以具體的事物來表現(xiàn),在隱喻中透露出深刻的意蘊(yùn)和內(nèi)涵,頗有一種迷幻而生動(dòng)的畫面感。“一支被光、影和空白/漸漸吃掉的鉛筆,/仍可以選擇/被什么樣的手發(fā)現(xiàn)、把握/加入或者背離”(《此生》),沉靜之物如鉛筆,此時(shí)也具備了豐富的生命與哲學(xué)意蘊(yùn),與其說是鉛筆在做選擇,不如說是張悅借助鉛筆宣示了自己的生存選擇,這同樣也是詩(shī)人生活經(jīng)驗(yàn)與智識(shí)表達(dá)的體現(xiàn)。
凌風(fēng)的組詩(shī)里透露著沉靜古典的睿智,豐富的語(yǔ)言素養(yǎng)和靈動(dòng)的想象力,讓他的詩(shī)歌有著歷史的視野,表現(xiàn)出自我對(duì)外在的頓悟與通達(dá)。“野鴨像先知,走在湖面上/仿佛蘇格拉底在林間沉思”(《春日》),湖面的“野鴨”如同“先知”,不由讓人想起“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蘇軾《惠崇春江晚景》),這一象征與“蘇格拉底在林間沉思”形成闡釋上的互文,彼此補(bǔ)充和說明,營(yíng)造出一種辯證而神秘的詩(shī)意氛圍。凌風(fēng)用靈動(dòng)的想象力穿越時(shí)間的表象去體認(rèn)現(xiàn)實(shí)生活,但他的表達(dá)卻不是簡(jiǎn)單的對(duì)歷史的想象和復(fù)制,而是深入到表現(xiàn)自我在現(xiàn)實(shí)中的感受與狀態(tài)中來,或者說凌風(fēng)的大部分詩(shī)歌在完成后,呈現(xiàn)出的除了他本身的生命體驗(yàn)外,還有作為詩(shī)歌本身所擁有的文本的意義與價(jià)值。正如詩(shī)評(píng)家陳超在《詩(shī)藝清話》中提到的“詩(shī)歌不僅僅是傳釋你的情感、經(jīng)驗(yàn)、智識(shí),詩(shī)還有屬于它本身的情感、經(jīng)驗(yàn)、智識(shí)。”也就是說詩(shī)在形成后,便具備了它自己獨(dú)特的意義和價(jià)值,應(yīng)該讓讀者更多體會(huì)到詩(shī)的本身,而不僅僅是創(chuàng)造它的人。“清明過后/雨水像輸不完的點(diǎn)滴,順著屋檐流下來/空曠的堂屋,就像經(jīng)殿/外婆獨(dú)自跟死亡做著辯論”(《一個(gè)人的斷代史》),“雨水”成為“點(diǎn)滴”,“堂屋”變成“經(jīng)殿”,凌風(fēng)將它們聯(lián)系并置在一起,以此達(dá)到對(duì)自我情感經(jīng)驗(yàn)的詩(shī)意傳達(dá)。凌風(fēng)孤獨(dú)的心境與詩(shī)歌的文本情境相融合,在表現(xiàn)了其壓抑而隱忍的憂思后,也建構(gòu)了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表述形式,更為豐富和完整地展現(xiàn)出“一個(gè)人的斷代史”。
在組詩(shī)里表現(xiàn)對(duì)故土自然的精神寄托、實(shí)現(xiàn)自我安置,不斷探索和超越普遍性的寫作經(jīng)驗(yàn),建立起個(gè)體與社會(huì)的共生與連結(jié)關(guān)系,是亮子正在關(guān)注與挖掘的。他認(rèn)識(shí)和理解生活經(jīng)驗(yàn)的方式更為主動(dòng),從小而具體的事物入手,對(duì)自身情感變化進(jìn)行綜合整理,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gè)現(xiàn)實(shí)與理想交織纏繞的感性世界。“我們?cè)谇锾炖镒咧?認(rèn)識(shí)些許草木,辨別其中志趣/胸中自然有一片生長(zhǎng)的天地”(《我們的秋天》),亮子對(duì)自然的態(tài)度是謙遜與溫和的,也正是這種內(nèi)在心境的自由與平和,讓他的詩(shī)歌擁有了曠達(dá)深遠(yuǎn)的思想,而亮子敏感豐富的內(nèi)在世界也得以完整體現(xiàn)。如果說面對(duì)自然,亮子堅(jiān)持的是一種有別于對(duì)抗的共存關(guān)系,能夠在與自然的共生中凝視共同的價(jià)值,那么,詩(shī)的內(nèi)容和意味也在變得豐富與深刻,更加趨向于生命本真的意義與價(jià)值。《又一次哭了》短短幾句呈現(xiàn)出亮子內(nèi)心世界防線的逐漸瓦解,末尾想起稗草般的一生,無助的孤獨(dú)感猶如秤砣,使他感到沉重的壓力。但這種肉身的沉重卻也是精神成長(zhǎng)的基石,在表達(dá)亮子復(fù)雜內(nèi)心世界的同時(shí),也為亮子生存境地提供了選擇的可能。棲遲泉石使人閑適,馳鶩功名讓人淡薄,雖一生如稗草般渺小微弱,卻也可以選擇成為哪一種人,在微光中發(fā)現(xiàn)和捕捉生命的奇跡,或許可以成為稗草豐富的人文意義,成為亮子創(chuàng)作中勇毅而曠達(dá)的追求。
“時(shí)間讓一座沙島沉闊成沃土”,時(shí)間也在這樣的消逝中從虛渺走向清晰,抽象的時(shí)間被指向?yàn)椤吧硩u沉闊成沃土”,生命的感受力自然也就形象和具體化了,這是詩(shī)人葭葦超拔想象力與敏銳洞察力的體現(xiàn)。通觀《沙島》這首詩(shī),可以看出葭葦對(duì)詞語(yǔ)關(guān)聯(lián)性的捕捉能力,紛繁意象與修辭巧妙地呈現(xiàn)出內(nèi)在思想,貼切卻也有些含混的比喻,闡述著她對(duì)愛情的感慨與思考。“我走不出的雨,你有你/澎湃的律令,踽踽,長(zhǎng)鳴。/明天,我會(huì)以哪一種形狀/醒在,你細(xì)細(xì)的水聲里?”(《赤腳醫(yī)生》)在這里葭葦并沒有將兩個(gè)人并立來看,而是運(yùn)用通感把“你”想象成“雨”,走不出的“雨”成為對(duì)走不出“你”的表象,“雨”所帶有的“踽踽,長(zhǎng)鳴”,此刻也指向?qū)Α澳恪钡母惺芘c幻想。當(dāng)事物被賦予新的經(jīng)驗(yàn)和意義后,詩(shī)歌所表現(xiàn)出的思想力度也有所增強(qiáng)。又如《小奏鳴曲》,葭葦豐富的知識(shí)背景與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讓這首詩(shī)歌在形式上富有變化,復(fù)雜的語(yǔ)言創(chuàng)造和意象組合呈現(xiàn)出生動(dòng)的畫面感,而強(qiáng)烈飽滿的寫作激情和主動(dòng)性,也成為葭葦祛除現(xiàn)實(shí)雜質(zhì)、勇面自身問題的深層因子。“無須更多靜思,把你的腳/交給一程一程山。”所表現(xiàn)出的冷靜豁達(dá),更加凸顯了葭葦對(duì)人生命運(yùn)的智性理解,使我們看到了作為年輕詩(shī)人朝向未來的多種可能。傅浩在《葉芝之偉大》中對(duì)葉芝詩(shī)歌的特點(diǎn)理解為激情和智慧,認(rèn)為兩者“彼此交織,互為消長(zhǎng),就像他的哲學(xué)體系中的那一對(duì)螺旋錐體那樣相對(duì)運(yùn)動(dòng)著”,這似乎也成為很多年輕詩(shī)人具備的寫作特點(diǎn)。對(duì)外在世界保有足夠的熱情,對(duì)生命體驗(yàn)具備智性的理解,也正是葭葦組詩(shī)中創(chuàng)作精神自覺的體現(xiàn)。
簡(jiǎn)潔明晰的文字,呈現(xiàn)的是詩(shī)人內(nèi)心面對(duì)日常的獨(dú)特經(jīng)驗(yàn),陳放平的組詩(shī)平靜地講述身邊的人和事,從細(xì)微的生活里發(fā)現(xiàn)隱藏于生活背后的問題。他的詩(shī)歌像一幅幅生動(dòng)形象的生活畫,人物與事件、感覺與經(jīng)驗(yàn)、真實(shí)與頓悟構(gòu)成了生活畫的外在情境與內(nèi)在情感,在啟迪與感動(dòng)人心的輕盈之中,釋放出沉重而震顫的力量。《簡(jiǎn)約》這首詩(shī)和它的標(biāo)題一樣,寥寥幾句微觀經(jīng)驗(yàn)的呈現(xiàn),卻形成了一種豐富的時(shí)空張力。在現(xiàn)代化城市復(fù)雜的背景下,“人力三輪”成為“古老的廣告”,詩(shī)人試圖構(gòu)建起在關(guān)聯(lián)時(shí)間里的詩(shī)歌語(yǔ)境,通過獨(dú)特的生活觀察和體悟,重新理解并賦予生活以現(xiàn)實(shí)的意義。“我們是兩具鋼鐵/在多數(shù)分別的生活里/少數(shù)地團(tuán)聚/我每一次/喊“爸”/都相當(dāng)于表白”(《成年以后》),如果說分別所帶來的感受包含著對(duì)主體更加立體化的表現(xiàn),那么團(tuán)聚所記錄的對(duì)主體思想辯證的挖掘與描繪,則更加凸顯作為主體的父子精神世界的緊張與對(duì)抗。雖然在“鋼鐵”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變得堅(jiān)硬和冷漠,詩(shī)人縈繞著的記憶也不斷桎梏和約束著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但如“喊‘爸’”般的召喚的聲音不斷提示著詩(shī)人,現(xiàn)有的心靈所承載的特殊經(jīng)驗(yàn)與感知,某種程度上推動(dòng)和增加了詩(shī)歌作為表現(xiàn)親情關(guān)系的深度和意義。
讀六位青年詩(shī)人的作品,既是讀文本背后個(gè)體的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也是讀詩(shī)人們?cè)从谌粘S指哂谌粘5闹腔叟c玄思,他們的詩(shī)歌或質(zhì)樸深沉,或隱喻辯駁,或奇詭復(fù)雜,或簡(jiǎn)約細(xì)膩,都是從自身的生命體驗(yàn)出發(fā),用極具特色的語(yǔ)言呈現(xiàn)自我的情感和思考,使詩(shī)歌有力地建塑起時(shí)代背景下的生活圖景,向著多元與深廣處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