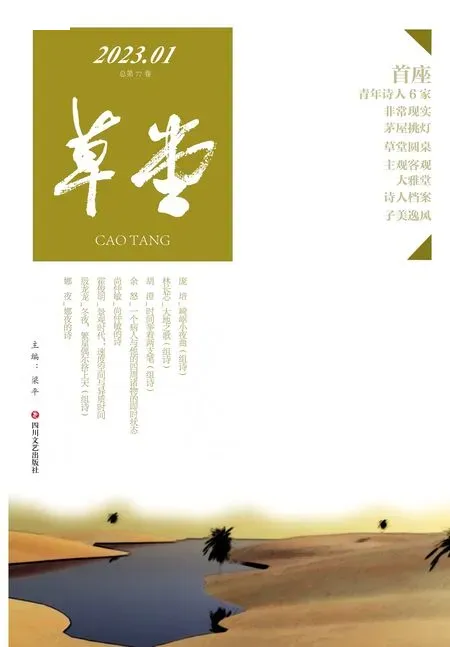小是逃逸的甜(組詩)
◎劉陽鶴
[立冬]
我們耽溺于經驗的水澤,
每回下沉均是輕巧的
淪陷。在晦暗與澄明間,不妨
布防我們細微的裂隙——
一種隱情,隨即浮現無征兆。
來,我們談一談彼此的
關切:死水亦有暗流,這并不
像每副身心的幽結之物
在重中纏繞。至此“世界已經
離去,我承載你。”*
世界看似輕盈,那不過是
我們意識中避重的形態……
瞧瞧這些難挨的日子,你徒有
疊躍的愛欲,而我無畏
無所謂:混淆憐念,怨晚秋。
*注: 策蘭詩句。
[藍頂美術館]——獻給馬雁
在櫻園游走,卻不曾親睹
你生前的喻體:“這迷人之食。”
未能顯現,是否意味著
彼處的痛苦沒有血肉。此刻,
那些個空無的酸澀,大中亦不乏小,
像我腦海里浮泛的紅寶石,
圓滾滾的,翻轉于深灰色的
幕墻之上。而墻上,那被鏤雕的
鍍金字:唯心主義,竟借助無助的
藝術家手筆,不斷迸射出
醒目的造型:橙黃的巨型燈泡、
緋紅的網狀裝置,吞噬著我
身后這幢幽僻的、倒懸的藍頂建筑。
可旁邊不遠處,有些安居者在
心領神會中,揣測某種寓意——
遠離赤貧,即是“保護可能性”的
一種退路?這里的肅殺,不止
安于現狀的沉郁。直到你哀戚地
寫下悼亡詩,把翡翠似的孤島
寫下來,再將玩世之徒寫下,主宰
才可能竭盡全能來,賦予我們
以一場恍如隔世的大合唱。如今,
與你雖遠隔,但蜀地素有的
天府之譽,讓我感到“這些卑微的
造物有力量”。果然,它們意欲
在思想的墓園扎根,待我
暈厥之時,沖抵那未破土的
想象,鮮活而肥美。
注:引號內均摘自馬雁詩句。
[小是逃逸的甜]
不可言說,不是說
我們未曾小過,抑或小是
壓縮的口述史:無字據,故記述
空有褶皺,而我剝不開
鮮橙的缺口,獨在一旁提煉
內在的甜——
這無用的甜,從舌苔
逃逸的甜,或可虛構一場
蜜制的婚姻。一旦苦澀
在啤酒花中漾出你,那些過剩的
情嗜便凝結成核,此中卻有
蜜意流出,裹向永恒……
[棄貓補遺]
好心的姐姐,不顧一切
在半路上撿了只未睜眼的
貍花貓。當時,我們不知道它的
身世、來路,及其眼部疾病的
感染源。看我遠程起疑,
姐姐一面溫習小時候的養貓心得,
一面問我:“你還記得那只小黃貓嗎?”
我來不及回避話中鋒芒,
只好語氣略帶遮掩答復:“記得。”
誰人會忘卻皮毛里涌出的一攤血啊?
至少,心理上會時不時
受記憶色干擾,而我不曾懼怕
紅與黃,即便童年未有像身邊玩伴
那樣歷經頗多歡趣。這些歡趣
換取不了我內心戚戚然的
鳴響,我不知道聲音的外形
碰到跳蕩之物時會不會彎曲,就像她
帶回家的是一門生命拓撲學,
讓一家人得以在繁簡得當的養育中,
重新感念我們來時路的生計——
在可追述的家庭閱歷中,
我們遺棄了諸多物件的心理價值,
滿滿當當,仿佛咖啡盤里的
貓型模具,各有各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