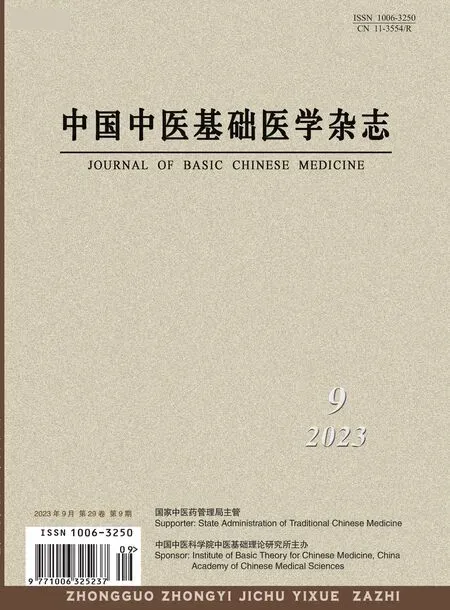基于語料庫的《傷寒論》英譯本翻譯風格比較研究?
蔣繼彪
(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 210023)
《傷寒論》是由東漢“醫圣”張仲景所著,約撰于公元208年前后,為中醫四大經典著作之一。它是傳承和發展中醫學的必讀之作,也是中醫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自1981年美國漢方醫藥研究創始人許鴻源(Hong-Yen Hsu)英譯的首部《傷寒論》譯本問世以來,世界上已有10部英譯本相繼出版[1]。目前,有關《傷寒論》的英譯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5個方面。一是關于《傷寒論》翻譯的理論依據研究,包括功能翻譯理論、生態翻譯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目的論、原型范疇理論、關聯理論、闡釋學、深度翻譯理論、文化翻譯觀、概念隱喻認知等;二是關于《傷寒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研究,包括中醫核心概念、病證名、方劑名,以及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等;三是關于《傷寒論》英譯歷程及其特點研究,包括從節譯到全譯,從初期傳播中醫基礎知識到后期對中醫醫理和文化內涵進行整體詮釋等;四是關于《傷寒論》英譯本的比較研究,包括文本特征、歷史語境、語義辨析、釋義準確性等;五是關于《傷寒論》英譯本的海外譯介和接受研究,包括海外圖書館館藏情況、被引情況、海外暢銷書排名情況、海外讀者評論等級,以及海外受眾評論等。國內學者近年來在《傷寒論》的翻譯理論依據、翻譯方法、翻譯歷程、版本比較、海外譯介與接受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尚未發現基于語料庫對《傷寒論》不同英譯本開展翻譯風格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擬以自建的《傷寒論》語料庫為基礎,運用語料庫檢索軟件,對羅希文和魏迺杰(Nigel Wiseman)的《傷寒論》英譯本的翻譯風格進行考察,并探析兩位譯者翻譯風格差異的原因,以期為《傷寒論》翻譯以及中醫典籍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推動中醫更好地“走出去”。
1 翻譯風格研究
語料庫翻譯學是以語言學和翻譯理論為指導,以雙語真實語料為對象,對翻譯現象進行歷時或共時的描寫和解釋[2]。語料庫翻譯學扭轉了譯學研究的源文本取向模式,譯學界由此開始關注譯者、譯語和翻譯行為的本質問題,使得翻譯研究由質性向量化、由小規模的規定性研究向基于大規模翻譯語料的描寫性研究轉向。
翻譯風格是指譯者在文本選擇、翻譯策略與方法等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個性化特征[3]。翻譯風格研究有利于研究者充分考慮譯者語言習慣和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進而深入地了解譯者行為及其背后的原因[4]。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利用語料庫技術對中華經典文學作品(如《論語》《道德經》《紅樓夢》等)、國外文學經典作品(如《簡·愛》《老人與海》《傲慢與偏見》等)、散文詩詞(如《唐宋散文》《李白詩集》《蘇東坡詩詞》等)、軍事作品(如《海軍戰略》《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等)、政治文獻(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等),以及科幻小說(如《北京折疊》等)的翻譯風格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為開展中醫典籍翻譯風格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2 語料與方法
2.1 語料選取
目前,世界上共有6部《傷寒論》英譯全譯本,分別為羅希文譯本(1986/1993/2007/2016)、魏迺杰譯本(1999)、黃海譯本(2005)、楊潔德譯本(2009)、劉國輝譯本(2015),以及李照國譯本(2017)[5]。本文選取羅希文和魏迺杰的《傷寒論》英譯本為研究對象。之所以選擇以上譯本,主要是因為羅希文《傷寒論》英譯本是世界范圍內首個《傷寒論》英譯全譯本,并于2007年入選《大中華文庫》;魏迺杰《傷寒論》英譯本在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中始終位列《傷寒論》英譯本榜首,在國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兩譯本的相關信息見表1。

表1 《傷寒論》兩譯本的相關信息
基于羅希文和魏迺杰《傷寒論》的兩個英譯本,本研究創建了兩個平行語料庫,分別為LUO PARA和WISEMAN PARA。其中,LUO和WISEMAN分別為羅希文和Nigel Wiseman的姓,PARA則為Parallel Corpus的縮略詞。與此同時,還創建了《傷寒論》的漢語對比語料庫,漢語對比語料庫的命名為SHL COMP。其中,SHL代表《傷寒論》,而COMP則代表Comparable Corpus。
2.2 研究方法
首先,通過語料電子化、語料清洗、人工糾錯、語料對齊等主要步驟構建《傷寒論》原語和多譯本平行語料庫。其中,羅希文譯本共20 358字、魏迺杰譯本共20 526字、原文共16 546字。然后,利用檢索軟件WordSmith 6.0和AntConc 3.5.8分別從詞匯、句子、語篇三個層面考察兩個譯本的翻譯風格。
3 結果與討論
3.1 詞匯層面
兩譯本在類符/形符比、詞匯密度、平均詞長等方面的數據統計如表2。

表2 《傷寒論》兩譯本詞匯層面的統計比較
首先,在標準形符/類符比(STTR)方面。標準形符和類符比(STTR)是文本中每千詞的類符和形符之間的比例,其值越高說明用詞越豐富。表2顯示,羅希文譯本的STTR為29.67%,而魏迺杰譯本的STTR為29.11%,這說明羅希文譯本用詞比魏迺杰譯本更為豐富多樣。例如,對“……主之”中“主之”的翻譯。經統計,《傷寒論》條文中共有109處出現“主之”。羅希文在翻譯時使用了多達18種不同的英譯方式,包括“……can be adopted as a remedy”“……would act as a curative”“……be suited for……”等,見表3,而魏迺杰則均使用“govern”進行英譯。

表3 羅希文譯本中“主之”英譯方式統計
其次,在詞匯密度方面。詞匯密度就是實詞在文本總詞數中所占的百分比。詞匯密度的高低說明文本信息量的大小和難易程度。一個文本的詞匯密度越高,說明實詞與總詞數之間的比值越大,文本所承載的信息量也就越大,文本的閱讀難度也就越高。羅希文譯本共有13 276個實詞,詞匯密度為65.2%。魏迺杰譯本共有14 738個實詞,詞匯密度為 71.8%。數據統計表明,羅希文譯本的詞匯密度比魏迺杰低,說明羅希文譯本的閱讀難度低于魏迺杰譯本。通過譯文可以發現,羅希文傾向于以目的語為導向,更多地使用意譯,而魏迺杰則傾向于以源語為導向,更多地使用直譯。這一點在中醫病證名的翻譯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在“中風”“傷寒”“溫病”等病證名的翻譯上,羅希文將其分別意譯為“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Wind”“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acute febrile disease”,而魏迺杰則分別直譯為“wind strike”“cold damage”“warm disease”。這一結果也印證了盛潔的研究發現,即在《傷寒論》中的61個中醫病證名的翻譯上,羅希文利用意譯對49.2%的病證名進行翻譯,而魏迺杰利用直譯對98.4%的病證名進行翻譯[6],見表4。

表4 《傷寒論》兩譯本病證名翻譯方法統計
最后,在平均詞長方面。平均詞長是指譯文中類符的平均長度。平均詞長較長說明譯文中使用長詞、難詞較多,閱讀難度較大[7]。普通文本由2~5個字母組成的單詞較多,平均詞長大約為4個字母。羅希文和魏迺杰譯本的平均詞長分別為4.91和4.76,平均詞長非常接近。羅希文和魏迺杰譯本中由1~8個字母組成的單詞分別占87.62%和91.26%,這說明兩個譯本對一般讀者而言具有較好的可讀性。
3.2 句子層面
兩譯本以及原文在句子數量、平均句長、句子標準差等方面的統計數據如表5所示。

表5 《傷寒論》兩譯本句子層面的數據統計
首先,在句子數量方面。著名的傷寒大家陳亦人先生指出,《傷寒論》在語言上具有“變、辨、嚴、活、簡”五大特點[8],而“簡”則指的是其語言結構工整、簡潔凝練。統計結果顯示,《傷寒論》原文共591句,而羅希文譯本和魏迺杰譯本中的句子數量均遠遠高于原文文本句子數量。羅希文譯本的句子數量為1 148,幾乎是魏迺杰譯本的句子數量的1.5倍。
其次,在平均句長方面。平均句長就是文本中所有句子的平均長度,即平均每個句子中的單詞個數。Butler曾按長度把句子分為3類,即短句(1~9個單詞)、中等長度句(10~25個單詞)和長句(25個單詞以上)[9]。羅希文和魏迺杰譯本的平均句長分別為17.73和26.25,均較多使用中等及以上長度句子。魏迺杰譯本的平均句長和句子標準差均遠高于羅希文譯本,說明魏迺杰譯本更多使用復雜長句。例如: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魏迺杰:[When there is]clear food diarrhea,[one]cannot attack the exterior[because,if]sweat issues,there will be[abdominal]distention and fullness.
魏迺杰在翻譯此句時,通過增加方括號“[]”,補充原文中省略但卻已經表達了的詞匯以及隱含的邏輯關系,努力追求譯文與原文形式結構和用詞的對等。經統計,類似的方括號“[]”用法在魏迺杰的譯本中出現多達1 489次,這直接導致其譯文平均句長遠遠高于羅希文譯本。
3.3 語篇層面
《傷寒論》全篇以四字駢體連綴成文,語言深奧、言簡意賅、邏輯內隱,形式化程度較低。因此,譯者在翻譯時,需要通過增加連詞彰顯語句內部和語句之間的邏輯關系,使得譯語更加符合目標語的形式和邏輯要求。兩譯本中連詞使用情況統計如下。
通過表6可以發現,兩個譯本的連詞數量分別為2 257個和2 619個,使用頻次分別占總單詞數的11.09%和12.76%,差別不大。兩譯本都能將原文隱藏的各種語義關系,包括并列、因果、時間、轉折、條件等清晰地表示出來,力求向讀者準確地傳遞原文所蘊含的信息。

表6 《傷寒論》兩譯本連詞使用情況統計比較
4 翻譯風格差異之原因分析
通過對羅希文和魏迺杰譯文的數據統計分析,可以發現二人的翻譯風格存在如下差異:前者傾向使用意譯法,用詞更為豐富多樣,句式表達更為靈活,注重譯文的易讀性和可接受性;后者則傾向使用直譯法,句式結構較為復雜,注重譯文與原文語言結構的一致性和準確性。本文認為,翻譯目的、翻譯策略以及知識背景的不同,是造成兩位譯者翻譯風格差異的主要原因。
4.1 翻譯目的不同
羅希文譯本于2007年列入《大中華文庫》,該文庫旨在向世界推介包括中醫在內的中國文化典籍,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該譯本的傳播對象為西方普通民眾,以一種科普讀物的形式進行譯介,需注重讀者的可接受性。為此,他通過簡潔凝練的句式、豐富多樣的用詞表達,來傳遞《傷寒論》所蘊含的醫學內容和文化內涵。魏迺杰于2000年獲得英國埃克塞特大學補充醫學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一直致力于語言學、翻譯學和中醫翻譯研究。鑒于在補充醫學領域的知識背景,他在進行中醫翻譯時,著重保持中醫概念的完整性、異質性和獨立性,努力呈現《傷寒論》的原貌。
4.2 翻譯策略不同
羅希文傾向于以目的語為導向,更多地采用意譯。羅希文《傷寒論》英譯本出版于2007年,而當時中醫在西方國家仍以補充與替代醫學的身份而存在。因此,西方普通民眾對中醫的認識相當陌生,對《傷寒論》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微。為了讓西方普通民眾能夠迅速了解和理解《傷寒論》,他采用意譯法對近一半的中醫病證名進行翻譯。同時,在對句子的處理上,他使用英語語言慣用的習語和表達,靈活處理句式,力求讓西方讀者易于理解。魏迺杰則傾向于以源語為導向,更多地采用直譯法,并認為直譯法最能忠實地反映中醫概念。例如,他將“中風”“傷寒”“溫病”等病證名分別直譯為“wind strike”“cold damage”“warm disease”。他的這一翻譯思想在其《單一漢字的英文對應語》(Single Characters with English Equivalents)一文中進行了詳細闡釋。在他編撰的《英漢·漢英中醫詞典》中,圍繞基本屬性與物質(Basic Categories and Entities)、功能和本質形容詞(Functions and Attributes)、診斷用字(Diagnostics)、疾病用字(Disease)、病機和病證用字(Pathomechisms and Disease Patterns)、治療用字(Treatment)等六個方面,對中醫學中最常用的400多個漢字進行了對應翻譯[10]。在任何一個中醫名詞術語中,按照漢字對英語進行直譯。例如,“斂”譯作“constrain”,“斂肺”則譯作“constrain the lung”;“澀”譯作“astring”,“澀腸”則譯作“astring the intestines”;“平”譯作“calm”,“平肝”則譯作“calm the liver”等。與此同時,在對《傷寒論》條文進行翻譯時,他通過使用大量的方括號“[]”,用以補充《傷寒論》原文中省略但卻已經表達了的詞匯或隱含的邏輯關系,努力追求譯文與原文形式結構和用詞的對等,力求譯文能夠準確地傳遞原文所蘊含的信息。
4.3 知識背景不同
在魏迺杰譯本的主譯團隊成員中,馮曄為臺灣長庚大學附屬醫院主任中醫師,早年畢業于臺灣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專業;魏迺杰為臺灣長庚大學中醫系專任教師,早年獲得過西班牙語、德語學士學位,以及補充醫學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該團隊成員具有漢語、英語兩種語言背景,又擁有《傷寒論》專業知識背景,兩位譯者在語言和專業知識方面能夠形成優勢互補。因此,在譯本內容的安排上,通過總論部分對《傷寒論》的成書背景、作者簡介、學術思想、內容概要、語言特點等的介紹,正文部分對漢語原文、漢語拼音、英譯譯文、文本注釋、歷代醫家評述等的呈現,以及附錄部分對中醫術語、中藥和方劑的拼音和英語的索引等,均全面、準確地展現了《傷寒論》原貌。相比之下,羅希文譯本則由其本人完成。他早年畢業于北京對外經貿大學英語專業。囿于所學專業的限制,他在《傷寒論》專業知識背景方面要稍遜于魏迺杰團隊。因此,他未對《傷寒論》條文的醫理進行深入闡釋,而僅對《傷寒論》的398個條文和112個處方逐一進行翻譯。
5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從詞匯、句子和語篇層面對《傷寒論》兩個英譯本譯者的翻譯風格進行了比較研究。研究發現,羅希文傾向使用意譯法,用詞更為豐富多樣,句式表達更為靈活,注重譯文的易讀性和可接受性;魏迺杰則傾向使用直譯法,句式結構較為復雜,注重譯文與原文語言結構的一致性和準確性。翻譯目的、翻譯策略和知識背景的不同,是造成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差異的主要原因。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本文嘗試利用語料庫對《傷寒論》英譯本進行翻譯風格比較探討,旨在拋磚引玉,引起業內專家學者關注,以期促進中醫典籍翻譯事業的發展,推動中醫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