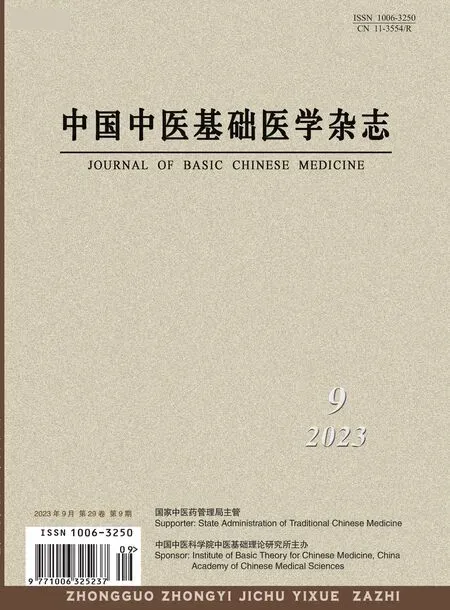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百病問對辨疑》學術思想探析?
施慶武,曾 妮,吳承艷
(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文獻研究所,南京 210023)
《百病問對辨疑》為明代醫家張昶所著,約成書于明萬歷年間。現存明萬歷九年(1581)曲沃張學詩刻本,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孤本。該書對內外科常見疑難病證,設問作答,逐一鑒別,撰集而成。雖已佚一、二卷,但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極具特色。該書不僅反映了明代中期的醫學成就,書中所提倡的鑒別診斷,以及重視脾胃等學術思想,對現代臨床亦頗多裨益。
1 作者與成書
張昶,字甲弘,號海澄,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在《小兒諸證補遺》一書序中有“崇禎九年歲次丙子菊月上浣五日,大梁七十四歲老人張昶序”[1],可知其約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張氏出身于醫學世家,其祖上張銳乃宋代名醫,著有《雞峰普濟方》三十卷,《雞峰備急方》一卷。張昶自幼從學于其伯父張維屏,克紹家傳,又博涉百家,潛心研究五運六氣等內容,頗有心得。除本書外,尚著有《運氣彀》《小兒諸證補遺》等書。
張昶在萬歷六年(1578)染上時疫,病情不斷反復,精神日漸消耗,逐漸出現痰喘、咳血、骨蒸潮熱、遺泄等虛損癆瘵癥狀,先后治療三年,服藥千劑方得痊愈。隨后,“凡醫書有虛損補益者,無不紬繹,潛心日久,頗有一得之愚”[2]25,因此對癆瘵等疾病深入研究,體會深刻。
2 內容與特色
《百病問對辨疑》原書五卷,現存三卷(卷三、卷四、卷五),原書論病或可達百種,現存三卷涉及病證50余種,重點論述了痰證(附五飲)、氣證、郁證、諸血、諸汗、諸痛、泄瀉、痢疾、疝證、淋證、三消證、噎膈、痛風、斑疹、痿痹、眩暈、癲狂等常見病證。后附《癆瘵問對辨疑》一卷,系作者因感染時疫,而潛心研究癆瘵之心得,其體例與《百病問對辨疑》相同。
是書采用問答體形式,全書每篇皆冠以“某病或證問對辨疑”字樣。問答體形式自《黃帝內經》《難經》等中醫早期經典著作創用后,后世如南宋齊仲甫《女科百問》、明代汪機《針灸問對》、清代王子固《眼科百問》、曹仁伯《琉球百問》等亦有沿用,以文風樸實、明白曉暢為特色,與主流寫作形式有所區別。《百病問對辨疑》以內科常見病證為綱,每證之下針對臨床常見疾病的疑難問題,予以答疑解惑,包括疾病的病名、病因、病機、主證、兼證、鑒別、治法、方藥等內容。書中尤其重視對相似癥狀、病機、治則等的細微區別,如在《痛風歷節風問對辨疑》篇中,張昶指出痛風與歷節風都有周身走痛這一癥狀,但是在病因上,痛風是因“血久留熱,復乘涼中風,或涉冷受濕,經絡污濁凝泣,不能運行作痛”[2]44,屬內外合病,而白虎歷節風是因“外感風寒濕邪相搏而成”[2]44,屬外感致病。在癥狀上,白虎歷節風是“氣短,暈眩欲吐,夜日疼痛,走注不定”[2]44,而痛風是“但痛不腫,晝輕夜重”[2]44,可予以鑒別。篇后還列舉了張昶歷履四方時治療的痛風和白虎歷節風驗案各一則,以表明兩病在診斷和治療上的不同,是理論聯系臨床實際的生動表現。
3 學術思想
張昶崇尚醫理,重視鑒別,在雜病辨治上學驗俱豐,特色鮮明。如在虛勞病的辨治上,提出虛勞病機統歸腎經一臟,發前人未盡之說。在痰病辨治上,闡明痰病致病并提出分類辨治。此外,張氏還擅用六經辨證,重視脾胃學說。其反對濫補、重視調攝、清淡飲食等思想實開風氣之先,為后學津梁。
3.1 虛勞理論的闡發
3.1.1 闡發“五勞、六極、七傷”學說 虛勞又稱虛損,是由多種原因所致的臟腑功能衰退、氣血陰陽虧損,日久不復為主要病機,以五臟虛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多種慢性衰弱證候的總稱[3]。早在《黃帝內經》時期,即有“精氣奪則虛”“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的論述,可謂是虛勞病的最早論述。后《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篇》首次提出虛勞病的病名,并提到“五勞、六極、七傷”,但并未具體闡釋其內涵。直到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才詳細論述了“五勞、六極、七傷”,指出五勞有二:一為志勞、思勞、心勞、憂勞、瘦勞,二為肺勞、肝勞、心勞、脾勞、腎勞;六極為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七傷內容亦有二:一指腎氣虧損之七種證候,二指五臟傷及形志傷[4]。張昶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對“五勞、六極、七傷”的內容進行了深入闡發。
他不僅詳細論述了“五勞、六極、七傷”可見的諸般癥狀,還指出了其病機所在,如“或曰:何以致此也?對曰:肝乃足厥陰之經,多血少氣,乙木之臟,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凡謀事不決,拂而數怒,久則肝勞。青則東方正色,病則色見于面,故令面目青色……肝之精華寓之于目,肝和則目睛朗然,肝為勞傷,故令眼目昏暗黑花繞前”[2]10-11。他從本臟的生理、病理、形、竅、志、液、時及五臟間的相互關系入手,病機分析絲絲入扣,病理表現條分縷析。同一種疾病下,張氏還強調知常達變,不可拘泥。如肺勞一證,脈遲緩是其常,主虛寒,用參芪桂附是其正治。而脈數則是肺勞之變癥,此處又有兩種:一是“氣虛而陰湊之,可用溫補”[2]8,即治法同前;二是“金衰火乘”[2]8,則可導致肺痿,這時候要“以苦艱金,以寒勝熱”[2]8,為臨床所少見。此外,根據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根,可用“二冬之清氣,二地之涼補。壯水之主,以制陽火也”[2]8,即從肺腎之間,金水相生的關系進行論治,另辟蹊徑。針對當時濫用溫補治療肺勞的局面,張氏還提出了“豈可一概以溫補而治肺勞乎”[2]8的批判,表明其對肺勞一癥認識之全面,臨床辨治經驗之豐富。
3.1.2 五臟生克,治病求本 在虛勞的辨治上,張昶還強調應分清標本,治病求本。如張氏在心勞辨治時指出心為肝之母,且心主血,肝藏血,肝主疏泄,從肝論治亦是治療心勞吐衄的良法,可謂別具巧思。對于臨床上心勞吐衄而脾胃先傷,飲食不進的情況,張氏認為這是“肝火太旺,克制脾土”[2]9,并批判了不識標本,濫用寒涼藥的醫生,“有庸醫不察標本,止知吐衄之甚,誤用寒涼峻劑。況脾胃喜溫而惡寒,多用則致壞脾胃者有之”[2]9。此時,通過疏肝以緩脾,調中以益胃,則諸癥可解。在“七傷”之“心傷”部分,張氏指出“心傷”可以“溫脾”,他認為根據五行與五臟的生克關系,母病可傳子,子病可及母,通過使用甘味藥補脾,脾氣得以充盈,則不會出現子盜母氣,即脾臟耗心氣,母氣(心氣)得以自養修復。以上皆反映了張氏對五臟關系及治病求本的深刻認識與實踐。
3.1.3 虛勞病機統歸腎經一臟 張昶認為百病皆可導致虛損癆瘵,在治療時應治病求本,究其根源。其中,腎經一臟尤為重要。生理上,腎為水火之臟,內藏相火,水足則制火,共成水火既濟之象。病理上,腎水不足,相火無制,虛熱自生,常出現足心熱、陰股寒、腰脊痛等陰虛火旺之象。陰虛火旺則易導致咯血,虛勞之證也隨之而起。因此,當癆瘵初起之時,腎中元氣未脫,脾胃谷神尚在,調攝合宜,則有挽回之機。如果出現五勞、六極、七傷,疾病不斷發展,纏綿日久,肌肉消耗,相火熾盛,逐漸出現痰喘、吐衄、遺泄、蒸熱等癥,則難以挽救。
3.2 重視痰病辨治
在各種病理產物與致病因素中,張昶尤其重視辨痰,他認為“然痰之為病萬狀,難以枚舉”[2]3“諸病挾痰者甚多,痰病其所由來者此也”[2]8。他對痰的性質、成因、區別、流注形狀、痰之別癥、兼癥、變癥,各類痰證之病狀,以及診治、方藥等均一一辨析,對讀者臨證多有啟發。張昶指出,痰并非外來之物,而是因體內津液流通不順,凝結所成,其根源乃水與濕。對于痰在人體不同部位的流注表現,張氏分為在臟、在腑、上焦、中焦、下焦、皮膚、經絡、空竅等進行了詳細描述,如“流于臟,則病顛癇、中風、癱瘓、勞瘵、吐血、怔忡、驚悸、哮喘、咳嗽。流于腑,在上焦,則噯氣吞酸、嘈雜嘔吐、咳嗽;在中焦,則腹內絞紐、噎塞煩悶、心寒胃痛、發狂;在下焦,則大小便秘結……”[2]1-2,表明痰證致病的廣泛性。在痰的變證上,張氏又細分為驚痰、熱痰、風痰、飲痰、食痰、暑痰、冷痰、酒痰、氣痰等,并列舉了其臨床表現,擴大了臨床上對不同性質痰致病的認識。在痰病的治療上,張氏細分為老痰、郁痰、風痰、痰飲在膈、痰飲在腸胃、痰飲在經絡、痰飲在皮里膜外、痰飲在肋下等,分而論治。或以鹽湯探吐,或用鵝翎挽去痰涎,或以竹瀝、姜汁入痰藥中,或用稀涎散治風痰,治療方法多種多樣,兼取朱丹溪等百家之長。此外,在痰病的治療上,張昶還特別重視脾胃,認為從脾胃論治方是治痰之本,如“古方治痰多用汗吐下三法,是治痰之標也。若吐下過多,脾胃損傷,痰涎易生而轉多,誠非王道之治也”[2]1“順氣消痰祛飲,則脾胃自然調和,飲食易化,痰自不生,此治本也”[2]8。這些認識,是對古人“脾為生痰之源”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3.3 擅用六經辨證
六經辨證源于《傷寒論》,它是以六經所系的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的生理功能與病理變化為基礎,結合人體抗病力的強弱、病因的屬性、病情的進退、緩急等因素,對外感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癥狀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借以判斷病變的部位、證候的性質與特點、邪正消長的局勢,并以此為前提確立治法與處方等的基本原則[5]。在雜病的辨治中,或與外感相關,或由外感引起,張昶十分重視應用六經辨證,采用全身癥狀與局部癥狀結合的方法,分經論治。如頭痛一癥,張氏根據全身癥狀與頭痛部位或性質分而論治,且與現行頭后部屬太陽,前額屬陽明,兩側屬少陽,巔頂屬厥陰的認識略有不同(表1)。

表1 頭痛六經辨證
痢疾作為內科常見病證,現代對痢疾的辨證,主要聚焦于辨痢疾的急慢輕重,辨痢疾的虛實寒熱,以及辨痢疾下利的顏色,主要把痢疾作為內傷病進行辨治。而張昶指出在痢疾的辨治上,如兼有外感,也可根據全身癥狀與便下情況等分經辨治(表2)。這種分經辨治痢疾的模式,不僅定位準確,且補充了現行中醫內科對痢疾兼外感認識的不足。

表2 痢疾六經辨證
在瘧疾的辨治上,張昶繼承了《素問·刺瘧篇》中瘧疾的足六經辨證學說,在足六經瘧的全身癥狀、寒、熱、汗出等表現上與《黃帝內經》一脈相承。但《素問·刺瘧篇》主要偏于針刺治療,而張氏則在瘧疾的內科辨證分型、治法確立及方藥使用上別出機杼,多有發揮,實補前人之不足(表3)。

表3 瘧疾六經辨證
3.4 臨證重視脾胃
張昶受李東垣脾胃學說影響,臨證辨治尤為重視脾胃。如在《腫脹問對辨疑》中指出從肺論治腫脹是治其標,從脾論治方是治其本。他認為腫脹的病因不論是七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太過,總是脾胃受傷,運化失司,導致水濕泛溢。《素問·經脈別論篇》有云,“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闡明了水液代謝的全過程,其中即強調了脾胃在水液精氣運化輸布中的樞紐作用。張氏在此基礎上指出:理脾可以去五臟之水。他認為心肺居上,肝腎居下,脾土居中,轉輸上下,水液方得流通。脾病則津液不得上下,水液泛溢四肢百骸,久病氣滯血瘀,逐漸釀成濕熱,濕熱相搏則成水腫。從脾論治,厚土斂水,水自歸位。即書中所謂“從脾而治,土旺水歸源矣”[2]9。
在《脾胃》篇后,張氏特列《調治老人脾胃》一章,認為老人氣血衰敗,治療上較為特殊,尤應重視脾胃。張氏列舉了不從脾胃論治而易失治誤治的幾種情況:中氣不足之喘,應補中益氣而誤用降氣定喘;土虛不能制水之浮腫,應實上以勝水而誤用逐水利膈;脾虛中空之臌脹,應調中運氣而誤用破氣散藥;脾虛濕郁之寒熱往來,應滲濕疏郁而誤用滋陰降火……皆指明了從脾胃論治雜病的重要性。張氏舉諺語“寧治十男子,不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不治一小兒……寧治十小兒,不治一老兒”[2]16以說明小兒雖然孱弱,但為純陽之體,尤有生意。而老人肌肉消耗,形體枯槁,不耐攻伐,治療上殊為棘手。唯有從后天脾胃入手,方能別開生面,即其所謂“年過八八,卦爻數盡,后天元氣耗凈,精門閉絕,補藥滋腎治非其時,惟賴脾胃腐熟五谷,生長榮衛”[2]16。張昶基于古人“得谷者昌,絕谷者亡”“一無胃氣,危亡立待”的認識,以及脾胃在五臟相互關系中的重要地位,認為“療治老人,先護脾胃。縱有他證,微末治之,即可收功……五臟皆稟氣于中,取之胃氣。心中取,無胃氣,亡血本;肝中取,無胃氣,亡筋本;腎中取,無胃氣,亡骨本;肺中取,無胃氣,亡氣本;脾中取,無胃氣,亡肉本;命門無胃氣,亡髓本……今后但逢諸證,必先調養脾胃,是為治病之本歟”[2]16!他指出治療老人應將顧護脾胃放在首要地位,為我們現代臨床辨治老年性疾病提供了參考。
3.5 反對濫補,重視病后調攝

《素問·熱論篇》有云,“熱病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即指出了病后飲食調攝的重要性。張氏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也強調病人應重視病后調攝,清淡飲食,以免復發。如“染病之人,須薄淡滋味,寧耐調攝,免致勞復,少受痛楚也”[2]45“尤當謹慎脾胃,經年方得無虞”[2]45“然藥雖合病,調攝失宜,神圣莫之為也。天產作陽,厚味發熱,此先哲之格言,若患人不守禁戒,薄淡滋味,吾知終不能安全也”[2]28。此外,張昶還認識到平時注重飲食調攝對預防疾病具有重要作用,如“慎疾者,須戒酒肉炙煿,恐其助火,況厚味過多,下必遺溺,上必痞悶”[2]16“若飲食適宜,寒暑應令,愛護脾胃,受納水谷,充灌臟腑,動作強壯,外邪不能侵……何用調攝之功哉”[2]13?這些認識對現代臨床“治未病”及患者的日常起居調養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4 結語
《百病問對辨疑》一書雖然殘缺不全,且流傳不廣,但是作為一部臨床著作,其寫作形式獨特,涉及病種廣泛。書中論述上至《素問》《靈樞》,下逮金元各家,薈萃歷代名醫之說。書中對于疾病病名、癥狀、病因、病機、治法的鑒別與析疑著墨尤多,與現代臨床重視鑒別診斷亦遙相呼應。誠然,限于時代背景,書中如“傳尸癆蟲有九種而六蟲傳染六代”之說,荒誕奇異,難以取信。但是,瑕不掩瑜,是書所反映的虛勞病機統歸腎經一臟、薄淡滋味、重視調攝、反對濫補等思想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明代醫家張昶醫術精湛、學驗俱豐的特點。該書已入選2018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華醫藏·內科類》編纂項目,表明其具有較高的醫學理論及臨床研究價值,值得進一步整理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