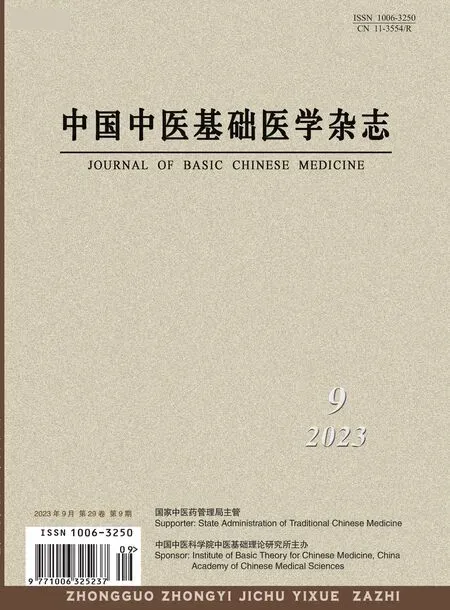王履外感熱病學術思想探析?
王居義,吳文清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北京 100700)
王履,字安道,號畸叟,約生于元至順三年(1332),卒年不詳,昆山(今江蘇太倉)人。元末明初醫學家、詩人、畫家,著有《醫經溯洄集》一卷(1368)、《小易賦》一卷[1]。《醫經溯洄集》雖篇幅短小,但因其能“會通研究,洞見本源……貫徹源流”[2],故在外感熱病、內傷雜病等方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既往很多研究闡發了王履的外感熱病學術思想,但惜未能強調其外感熱病學術思想之源流、創見和影響。故筆者重點比較王履前后醫家的外感熱病學術思想,探究其在外感熱病學術脈絡中的傳承、發展與創新,以期進一步加深對王履學術思想、貢獻和地位的認識,敬請斧正。
1 明辨寒溫名實
漢唐宋元以來,寒溫之名實混亂不清,傷寒、溫病、熱病、寒疫、天行、時行等概念相互錯雜重合。而王履在外感熱病學中最為突出的貢獻就是明晰了傷寒與溫病的不同,從病名、病因、病機、病形、治療方面進行了區分,循名責實,溯本求源,詳細內容見表1。

表1 《醫經溯洄集》傷寒、溫病區分表
1.1 病名——寒溫有別
傷寒、溫病的名實之爭始見于《難經·五十八難》,“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3],這不僅將傷寒、溫病作為兩個獨立疾病,而且賦予了傷寒一詞廣義和狹義的雙層內涵,又遙承《黃帝內經》“今夫熱病皆傷寒之類”的論述,也使得后世醫家在寒、溫之辨中莫衷一是。王叔和《傷寒例》最早開始對傷寒、溫病進行了區分,“冬時嚴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4]。他指出廣義傷寒為冬時感受寒邪,狹義傷寒為冬時感邪即發,邪氣伏藏至春而發者為溫病,從發病角度對外感病的寒溫之別進行了區分。王燾《外臺秘要》收錄了此觀點。王履承叔和之論,但在定義范圍上有所擴大,其言“夫傷于寒,有即病者,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于所感之時;不即病者,過時而發于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溫與暑”[5]13。凡傷于寒邪即發者為傷寒,不必限于冬季即發;過時而發于春、夏者為溫暑,而非單伏發于春季。此外,王履更進一步在《張仲景傷寒立法考》《傷寒溫病熱病說》《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等篇章中屢次強調“仲景《傷寒論》專為中而即病之傷寒作,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作”[5]13,同時對韓祗和、朱肱等不識此意加以批駁。
王氏之說于后世影響有三:其一,吳瑭、周揚俊等醫家沿襲此說,反復強調《傷寒論》專論狹義傷寒,其他五氣,概未提及,但此說遭到陸懋修、雷豐等醫家的批駁[6]。其二,采《傷寒例》《外臺秘要》之說從新感和伏氣的角度區分外感病之寒溫,但范圍限定上較前更為廣闊,為后世葉、吳諸家確立春溫、伏暑病伏邪而發的發病理論打下了基礎。其三,王氏旗幟鮮明地以即病、不即病作為劃分傷寒與溫病的界線,將新感歸為傷寒,伏氣歸為溫病,與后世溫病醫家將溫病分為新感與伏邪兩種類型大不相同。郭雍《傷寒補亡論》首先將新感與伏氣用于溫病的分類,“冬傷于寒至春發者,謂之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寒溫氣而病者,亦謂之溫”[7]。郭雍之后汪機、戴天章、王孟英等逐步確立了溫病新感與伏氣分類的正統地位[8]。王履雖親見郭雍之書但未能承續其說,實為憾事,但其以新感與伏氣理論形成了傷寒與溫病的對峙之勢。
除以即病、不即病來分外感病之寒溫外,王履還討論了伏邪與新感兼感的情況,“春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蓋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不然,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于風寒,或因風寒而動乎久郁之熱,遂發為溫暑也”[5]17,重點描述了新感引動伏邪發為溫暑這一兼感為病的情況。清代溫病醫家多次提及王履之說,對新感伏邪相兼為病大加發揮。如周揚俊《溫熱暑疫全書》伏氣兼外感為病[9],柳寶詒《溫熱逢源》伏溫之病新邪引動伏邪等[10],其淵藪實為王氏之論。
1.2 病因——皆感寒邪
在病因方面王履指出,傷寒、溫、暑的病原皆為寒邪,“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5]13。寒邪致傷寒、溫暑的病因觀與《黃帝內經》《難經》、仲景一脈相承。傷寒溫暑皆寒邪所感,這種觀點顯然具有時代的局限性,后世溫病醫家以“溫邪”作為病原則更為準確。楊璿在《傷寒瘟疫條辨》中肯定了王履在溫病學方面的貢獻,但亦直截了當地指出局限。在自序中稱其“于溫病所以然之故,未能闡發到底”[11]8,在《發表為第一關節辨》中稱其“病源之所以異處,亦未道出汁漿”[11]29,頗有見地。此外,在病因觀上,王履還提及了“感天地惡毒異氣”[5]13。此論上承《肘后備急方》“戾氣”和《諸病源候論》“乖戾之氣”的論述[12]896,逐漸認識到“異氣”在病因學中的獨特性。而后的喻昌、張介賓等醫家繼續發揮,為吳又可《瘟疫論》在真正意義上“戾氣”致病學說的提出打下了基礎。王氏之論有承啟張目之功。
1.3 病機——怫熱內郁
在病機方面,王履獨具慧眼地指出溫病是“怫熱自內達外,熱郁腠理”[5]20,與傷寒由表入里大相徑庭。“陽氣怫郁”理論肇始于韓祗和“伏陽”學說,以闡明傷于寒邪發為熱病之機理,發明于劉完素火熱學說,用于闡發傷寒和內傷熱病之機理[12]903。王履實非首創,但首先將之明確用于溫病之病機,其對溫病病機的準確把握,后世醫家深以為然。方廣《丹溪心法附余》言“溫熱之邪自內出”[13],柳寶詒《溫熱逢源》言溫病熱郁于內、邪伏少陰而發[14],葉天士、吳瑭治春溫直清里熱[15],章虛谷《醫門棒喝》言溫病“郁而成熱”[16]38等,皆與王氏之說相契合,并影響了一大批溫病醫家,在溫病醫家群體內形成廣泛的認同,另有像喻昌、黃元御等傷寒學派醫家也持郁熱之說。故謝誦穆《溫病論衡》曾評價“王安道謂溫病之熱自內達外,只此一語,影響溫病治療思想者,至深且鉅”[17]。
1.4 病形——不惡寒而渴
在癥狀方面,王氏指出“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氣受傷故也;后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5]20。可見,王履承仲景之說,以初起是否惡寒、口渴區別寒溫之癥,還討論了溫病初起惡風寒是由于風寒新中所致。柳寶詒《溫熱逢源》曰“溫邪亦見太陽經證,其頭項強痛等象,亦與傷寒同,但傷寒里無郁熱,故惡寒不渴”[18]。柳氏所論與王履如出一轍,另有吳瑭等醫家諸說皆類。現代《溫病學》教材亦將惡寒口渴與否作為傷寒、溫病初起的鑒別要點。
除癥狀外,王氏還探究了溫病脈象,“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5]20。
1.5 治療——涼解清里
于治療方面,因溫病病機為“怫熱內郁”,故治法上“當治里熱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5]20。治里熱方面,“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而后人所處水解散、大黃湯、千金湯、防風通圣散之類”[5]19,以辛涼、苦寒、酸苦之劑清瀉里熱。經考晉唐宋金元方書,水解散方出《外臺秘要》卷三[19]46,同名方劑有二,分別引自《延年秘錄》和《古今錄驗》,藥物相似,均起解表清里之功,主治天行。大黃湯方出《肘后方·卷二》張文仲引許氏方[20],《外臺秘要·卷三》[19]45收錄,主治六經熱證。千金湯方出《備急千金要方·卷五》[21],但主治小兒暴驚,方證不符,疑為《千金方》中某方之簡寫,王氏從略。防風通圣散方出劉完素《宣明論方》,主治熱病表里俱實。
解表方面,“用辛涼解散,庶為得宜”[5]21。辛涼之劑用于溫病初期,劉完素先發于前,創雙解散、防風通圣散、益元散等治溫新方,王履再發于后,吳瑭、章楠等承續其說。銀翹散、桑菊飲諸方辛涼清解,已成后世治溫初起之主方。此外,王氏還多次強調寒溫治法的差異重在解表之法,“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異……故謂仲景發表藥,今不可用,而攻里之藥,乃可用”[5]21。解表之法寒溫迥異,如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對王氏溫病用辛溫“誤發其表,變不可言”表示贊同[22]。而攻里清熱之法,則差異較小,如吳瑭《溫病條辨》以白虎湯清里熱,化裁傷寒承氣湯而成宣白承氣湯、桃仁承氣湯、導赤承氣湯、新加黃龍湯等諸承氣輩。章虛谷《醫門棒喝》說 “溫病初起治法與傷寒迥異,傷寒傳里變為熱邪,則治法與溫病大同”[16]48,其思想與王氏之說相吻合。
治里而表自解方面,屬王氏創見,與傷寒論先治表后治里,表解里自和不同,王履提出溫病可先治里,辛涼救陰以清里,里和則表自解,于臨床頗有啟發。近現代醫家姜春華“扭轉截斷”之法,溫熱病雖有表證,徑用清熱解毒之法,直搗病巢,截斷傳變,確能熱退表解,邪去正安[23]。可見王氏之說不虛,洵系經驗之談。
溫病初附麗于傷寒之下,有名無實,王履《醫經溯洄集》從病名、病因、病機、病形、治療方面對寒溫進行了明確區分,但其對溫病的認識大體萌出于傷寒之學,如病因仍停留在寒邪致溫,未明溫病傳變轉歸和方藥。錢潢《傷寒溯源集》就指出其“無奈尚隔一層”[24]。但因其能融合折中前代醫家之論而暢發于溫病,形成了對溫病名實證治的簡要概括,使得溫病學真正開始有相對獨立于傷寒之外的理論基石,開啟了后世對溫病學說的進一步深化,影響了包括吳又可、吳瑭、葉天士、章虛谷、周揚俊、柳寶詒等一大批醫家,功不可沒。無怪乎周魁在《溫證指歸》中評價道“《溯洄集》始辨明寒溫,燦若眉目”[25]。
2 首倡傷寒錯簡
王履認為王叔和搜采仲景舊論不至于散佚,功莫大焉,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紜并載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亂”[5]18。于是,他指出“欲編類其書,以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差后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寒有所關者,采以附焉,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5]19,萌生了對《傷寒論》條文混亂編次整理的思想。醫學領域對經典著作刪改增移的實踐始于滑壽《讀素問鈔》,而《傷寒論》“錯簡重訂”思想則肇始于王履。元代學者戴良《九靈山房集·丹溪翁傳》載,“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于殘篇斷簡之余,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無疑”[26]。朱丹溪對《傷寒論》的研究頗具重訂錯簡之意蘊,王履師事丹溪,其錯簡重訂之思想當濫觴于丹溪,而王履有發皇古意之功。王履之后明代醫家汪機著《傷寒選論》,推崇王履重訂思想,在編輯上也仿照王履所定次序[27]。汪機之后,方有執著《傷寒論條辨》形成三綱鼎立學說,而后喻昌、程應旄、周揚俊、吳謙、章虛谷、黃元御等諸名家皆持錯簡重訂之說,成為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傷寒學術流派。面對錯簡重訂派的異軍突起,以張遂成、張志聰、陳修園、高士栻等為代表的維護舊論派與以柯韻伯、尤在涇、徐大椿、錢潢等為代表的辨證論治派形成了明清傷寒學領域廣泛而持久的學術爭鳴。王履錯簡之倡論,使得由唐宋“傷寒八家”為代表形成的注解、歌訣、類編、專題發揮《傷寒論》的“傷寒學”研究,轉變為明清醫家對《傷寒論》篇段、詞句、法方、條文編次排列的“傷寒書”研究,極大促進了仲景傷寒之學“經典化”和“社會化”的腳步[28-29]。這一傷寒學術發展的劇變始于王履,竊以為也是其始料未及的。
3 提倡瀉南補北
“瀉南補北”語出《難經·七十五難》,原是指針對肝實肺虛病證而設的一種特殊針刺補瀉手法[30]。朱丹溪最早將“瀉南補北”之法用于痿證,認為病機為肺熱葉焦,真陰不足,瀉火補水,立虎潛丸以治之[31]。劉完素火熱之論專主瀉火,王氏不贊同“獨瀉火而不補水,瀉火即是補水”[5]42的說法,指出“雖瀉火、補水并言,然其要又在于補水耳”[5]42。瀉火補水當并重,但以補水為主,并進一步解釋,“雖苦寒之藥通為抑陽扶陰,不過瀉火邪而已,終非腎臟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真陰也。欲滋真陰,舍地黃、黃柏之屬不可也”[5]42。可見,王氏充分吸取了劉完素火熱之論與業師朱丹溪“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論,突出強調了滋腎水真陰、瀉南方邪火的觀點。王氏瀉南補北之論雖非專為溫熱而發,但對溫病清熱、養陰兩大主要治法的建立起到了推動作用。后世溫病醫家在醫論、方劑、醫案中多次提及瀉南補北之法。葉天士《溫熱論》言“舌黑而干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32],用于治療溫病邪盛正衰,真陰欲竭之候。吳瑭《溫病條辨》中提出“少陰溫病,真陰欲竭,壯火復熾,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33]107,以苦甘咸寒之法瀉火補陰;治療“暑邪深入少陰,火灼陰傷”[33]118之連梅湯,酸甘以化陰,苦味以堅陰。《張聿青醫案》中薛金楣案,濕熱發斑,神識昏蒙,以瀉南補北法瀉熱透斑醒神[34]。另如蔣寶素《問齋醫案》、王旭高《環溪草堂醫案》等皆有瀉南補北醫案的記載。上皆為瀉南補北在溫熱類疾病中的具體運用,王氏實有倡論之功。
4 溫病慎用麻桂
明代醫家繆希雍于溫病治療主張慎用麻黃、桂枝,汪機《傷寒選錄》亦主張時令暖和不可以麻黃湯發表[35]。明代醫家在治溫實踐中已經認識到溫病當慎用麻桂等峻烈之劑,以防過汗傷陰。此認識是秉王履之說引申而來。王履先駁斥了韓祗和、龐安時、朱肱、劉完素等醫家于麻黃桂枝湯中加入寒涼之藥用于夏季溫熱之病,繼而指出“秋冬之傷寒,真傷寒也”[5]21,真傷寒“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湯之所以必用”[5]19,并反復強調了“仲景立桂枝、麻黃湯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黃湯之有時”[5]16。王履立麻桂為冬月正傷寒而設的觀點,一方面是因為其主張傷寒溫病不同,傷寒為冬月感寒即發,溫病為過時里熱而生,故麻桂辛溫不可與之。另一方面,時醫因名亂實,寒溫不分,濫用麻桂發表而致變癥叢生。陶華《傷寒瑣言》就記載了這一現象,“傷寒之深奧,桂枝麻黃二湯之難用也。服之而愈者才一二,不愈而變重者十常八九……時醫畏而不用”[36]。可見,在寒溫名實不分的情況下,王履主張慎用麻桂之劑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此,王氏進一步勸告“春夏雖有惡風、惡寒表證,其桂枝、麻黃二湯,終難輕用,勿泥于發表不遠熱之語。于是用辛涼解散,庶為得宜”[5]17。啟發了溫病醫家辛涼治溫之法,慎用麻桂發表而改用荊芥、防風之類的藥物。但另一方面,王履近乎教條的論斷也經后世醫家大加發揮,清秦之楨《傷寒大白》作“南北方宜發表不同論”和“南北方宜清里相同論”,認為麻黃湯、桂枝湯二湯專為“冬月正傷寒之方,非治春夏秋三時之熱病……麻桂二湯,乃是北方治方,江浙東南,即冬月亦不宜用”[37]。造成了江浙一帶醫家畏麻桂如虎,南北分治的尷尬局面。南北地域、氣候、地理環境之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理論與治法的創新[38],形成具有差異性的方藥,倘若因地域之別而將學術相互割裂,無疑是不利于學術改良與創新的。
5 結語
王履以嚴謹、求實、批判、繼承的態度探討了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對中醫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39]。第一,王履探討了外感熱病學術史上廣泛爭論的寒溫名實問題,第一次明確指出“溫病不得混稱傷寒”,認為溫病病機為怫熱內郁,癥狀為不惡寒而渴,治療上當辛涼解散或苦寒清里,使得溫病真正開始跳脫出《傷寒論》的藍本之外,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醫學理論。時逸人《中醫傷寒與溫病》評價“至安道才大張旗鼓,將溫病另立門戶”[40]。第二,王履首倡傷寒錯簡,開啟了傷寒學術研究的新局面。因王履、繆希雍、吳又可等醫家的突破,明清以來溫病理論體系不斷深化發展,溫病證治的臨床診療需求與《傷寒論》文本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清代以來復古尊經思想的強化,醫家開始轉變為對《傷寒論》文本的“傷寒書”研究,進一步促進了傷寒學術流派的爭鳴。第三,王履“異氣”致病觀、“瀉南補北”法的論述推動了溫病證治體系的發展。除前所述外,限于篇幅,王履對陰暑、陽暑的辯論,林億校對“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的真偽等方面也都頗具審思。通過繪制王履外感熱病學術傳承圖(圖1),我們可以看到,王履駁斥了朱肱、韓祗和、劉完素等醫家之說,又批判繼承了《千金方》、《外臺秘要》、張仲景、劉完素、韓祗和、朱丹溪等前代醫家的熱病理論,將之發展于溫病理論,并主要影響了葉天士、吳瑭、柳寶詒、章虛谷等一大批醫家,使得溫病學術之發展有源有流,川流不息。謝仲墨《溫病論衡》稱“溫病學說之劇變,王安道啟其端”[41],可謂一語中的。但我們也可以發現,安道雖“脫卻傷寒,辨證溫病”[33]9,但其“論之未詳,立法未備”[33]9,亦是一語成讖,于溫證傳變、方藥創制未見一二。站在歷史后來者的角度,王履對外感熱病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確立了后世溫病學發展之范式,亦開啟了傷寒學術流派之爭。因此,筆者認為,王履詳于論而略于方,不可稱之為溫病學發展之第一人,但其于溫病學術體系承上啟下之功不可磨滅,或可稱之為溫病學理論發展之第一人。

圖1 王履外感熱病學術傳承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