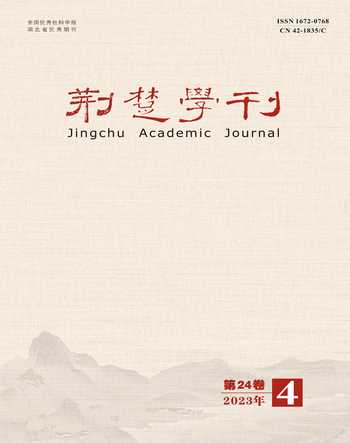“詩性智慧”與自然“附魅”:論古希臘美學思想中的“秘索思”思維模式
孫嵐
摘要: 西方文化中長期以來存在著德里達所謂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特征。西方文化思想最早能夠追溯到“古希臘美學思想”這一源頭,而在古希臘思想的早期階段,其文化基質中帶有較多“秘索思”(Mythos)的成分。“秘索思”是受到原始人類“詩性智慧”思維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對大自然進行想象與“附魅”而逐漸形成的一種思維模式,具有虛構性與想象性的特點。而伴隨著人類理性意識的覺醒,西方思想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出現了“邏各斯”(Logos)的認識方式,對“秘索思”思維模式造成了沖擊。然而,縱觀古希臘早期美學思想誕生以來以及整個西方思想文化世界, 可以發現“秘索思”和“邏各斯”的思維模式始終存在,并彼此相互對立互補,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狀態。
關鍵詞:古希臘美學思想;秘索思;邏各斯;詩性智慧;自然附魅
中圖分類號:I0?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2-0768(2023)04-0028-05
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之中,長期以來都存在著“邏各斯中心主義”這思維結構,認為西方文化之中固有地存在著理性、科學、邏輯的“邏各斯”思維方式傳統。而縱觀整個西方思想文化傳統,尤其是早期的古希臘美學思想世界,我們最初看到的并不是“邏各斯”的思維方式,而是一種想象的、虛構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在古希臘最早被命名為“Mvqοs”。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陳中梅將這種思維方式命名為“秘索思”并介紹到中國,認為“秘索思”與“邏各斯”一樣,是西方思想文化當中重要的思維模式。“秘索思”具有什么樣的含義以及表現形式呢?它在古希臘美學思想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具有什么樣的特點?它與“邏各斯”思維方式的關系是怎樣的?這是本篇文章所重點思考的問題。
一、古希臘美學思想“秘索思”的概念意涵及所指形式
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陳中梅在精研西方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秘索思”這一概念,認為其代表了與西方文化當中的“邏各斯”傳統認知方式相分庭抗禮的另一個支。“秘索思”一詞源于古希臘詞匯“Mvqοs”,其拉丁文形式為“mythos”,意指“虛構以及在此基礎上各種非寫實修辭手段的運用”[ 1 ],同時,“Mvqοs”一詞也有“神話”“故事”等的含義。陳中梅先生認為,古希臘兩千多年來的文化當中,同時存在著“秘索思”(mythos)與“邏各斯”(logos,表示話語、理性、規則等義)兩種文化基質結構。但受限于時代因素以及人們的認識水平,“秘索思”這一元概念往往被人所忽視,有實而無名,以致提到古希臘或西方文化傳統,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以“邏各斯”思維模式為主導的“一元論”。殊不知,“秘索思”是更早于“邏各斯”的、出現于古希臘美學思想早期階段、并長期存在于西方思想傳統中的另一種傳統思維模式,“秘索思”與“邏各斯”一同構成了完整的古希臘美學思想以及西方文化,兩者相互作用,共同給予了古希臘以來西方世界思維與認知方式以重要影響。
“秘索思”一詞所指形式較為寬泛,包含且不僅限于神話、寓言、文學(尤其是詩歌)、宗教祭儀等領域。簡單來看,古希臘美學思想中的“秘索思”的思維方式主要體現在西方文學與宗教兩方面。因西方文學與宗教向來是神秘的、感性的、虛構的、故事般的,常常被冠以“秘索思”的敘述名稱。《伊索寓言》是古希臘公元前四世紀到三世紀之交出現的寓言體裁的文學作品,全書由若干簡短的寓言故事組成,其中故事大部分都是動物寓言,以虛構、想象的方式將動物擬人化,讓動物像人一樣說話和思考,揭示出生活哲理。如《狐貍和葡萄》當中,作者虛構了狐貍看見架上的葡萄,想摘但卻夠不著時所產生的心理,賦予狐貍以人的語言,認為“它們(葡萄)還是酸的”;《烏龜和兔子》虛構了“龜兔賽跑”的故事,將兔子形容為“恃才自負”,將烏龜形容為“奮發進取”[ 2 ],這一與現實相對立的、虛構、想象的故事,是“秘索思”式的。“秘索思”在古希臘《荷馬史詩》中所展現出的是一種“語言(和詩歌)迷人的魅力”[ 3 ] 306,即有“言辭”的意味,《荷馬史詩》當中不僅包含真實的言辭,也包含虛假的言辭。荷馬時期“秘索思”的含義與柏拉圖時期認為的“秘索思”所指稱的“神話”“故事”的專門術語是有所不同的。
二、“秘索思”與古希臘美學思想中的“詩性思維”與“自然觀”之聯系
在對“秘索思”的基本概念義以及表現形式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們不禁要思考,古希臘美學思想早期階段為什么會出現“秘索思”這種思維方式?究其原因,首先,“秘索思”思維模式與人類生活的“詩性傳統”有著同構之處。“秘索思”思維方式形成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種原始的“詩性思維”認知方式的影響。維柯在《新科學》中對原始人類的思維方式進行了考察、分析,提出了一種存在于原始人類思維當中的“詩性思維”也即“詩性智慧”。“詩性智慧”是原始人類整體思維認知方式的統稱,這種思維方式會對人類的行為方式產生相應影響[ 4 ],比如,生活在原始社會時代的人們往往通過“以己度物”的思維方式去認識與把握自然與外在世界,維柯認為,“人在無知中會把他自己當作權衡世間一切事物的標準……人在不理解時卻憑自己來造出事物,而且通過把自己變形成事物,也就變成了那些事物” [ 5 ]。這種“詩性智慧”由此成為處于蒙昧時代的原始人類解釋自然世界的方式,具體到古希臘早期的美學思想中,即相對應地表現為一種“秘索思”的思維模式,人們以神話、文學、故事等形式對事物進行感知與解釋,將自然世界投影到人們的想象與虛構當中,憑借想象進行故事創造,以“詩性思維”認識方式影響下的“秘索思”思維模式對自然現象作出描繪與解釋。正是由于這種從人類原始時期遺留下來的“詩性智慧”,促使了文學與宗教神話等“秘索思”的出現,才有了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伊索寓言》以及后來的《圣經》對古希臘早期思想文化的吸納。
還應看到,“秘索思”思維模式的形成與古希臘早期美學思想之中的“自然觀”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古希臘美學思想在早期就對“自然”十分關注,在古希臘思想形成的早期階段,思想家們普遍認為“自然界不僅是活的和有理智的(intelligent),不僅是一個自身有靈魂或生命的巨大動物,而且是一個有心靈的理性動物”[ 6 ]。在早期的古希臘人眼中,大自然是一個有生命、有靈魂的整體。在古希臘自然哲學形成以前,人們對“自然”的認識與掌握采取的是“宗教神話”的方式,更多的時候是對自然的直接觀察與想象,因而人們認識“自然”總體觀念上秉持著一種“有機自然觀”[ 7 ],認為“萬物皆有靈”,大自然被賦予人類的思想感情,這一時期,“自然”對人們而言是神秘的、難以捉摸的。當時的人們往往采取“秘索思”式的神話宗教與文學想象的方式,去解釋自然現象形成的原因,這實際上是一種對大自然進行“附魅”的過程。因此,在《伊索寓言》中我們能看到動物也會說話,表達所思所想,在《荷馬史詩》里我們能夠看見現實生活中無處可尋的奧林波斯山諸神,以及感受到諸神的喜怒哀樂,在《圣經》當中我們能領略到伊甸園、諾亞方舟、耶穌受難等等奇幻的故事……人們運用虛構、想象的方式去認識自然,以“秘索思”思維模式對自然進行著“附魅”,使得自然界充滿神秘色彩。由此可見,古希臘早期的“有機自然觀”認識方式是“秘索思”思維模式形成的一個動力因。
綜上,原始時期人類的“詩性思維”以及認識外在世界時的“有機自然觀”等觀念促成了古希臘早期“秘索思”思維模式的誕生。而伴隨著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古希臘自然哲學的誕生,人們開始運用理性的、邏輯的思考方式對自然世界進行探索,尋找自然世界與物質世界的本質、真理,逐漸由“有機自然觀”的觀念走向了“自然哲學觀”的科學時代,試圖將此前“附魅”于自然之中的種種神話與想象一一進行剝落。自然哲學家們“開始抱怨和批評荷馬用詩和詩化解釋一切的做法”,并“著意于試圖從神話以外尋找解釋宇宙和自然的途徑”[ 8 ],“邏各斯”的思維認知方式開始萌芽,但“秘索思”思維方式的力量仍然很強大。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的第一個唯物主義學派米利都開始了對世界本源的追問與探討,泰勒斯宣稱“大地浮在水上”,認為萬物的本原是水[ 9 ],可見“邏各斯”的思維模式仍然無法擺脫“秘索思”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兩者在人們認識自然與外在世界的方式上幾乎是共同進行著的,同時“邏各斯”認知方式的發展水平是受到“秘索思”思維方式限制的。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四世紀,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為代表的古希臘美學思想開始以一種理性、分析、邏輯的方式去認識外在世界與自然,“邏各斯”被明確規定為與“秘索思”相對立的思維模式。這一時期,古希臘美學思想當中的“邏各斯”思維模式一經確立,便對虛構的、故事性的、代表著神秘主義的“秘索思”思維模式造成了強烈沖擊。
三、古希臘美學中“秘索思”與“邏各斯”的此消彼長
在赫西俄德、荷馬等古希臘早期文學家的作品當中,“秘索思”代表著與真實、真理、正義相關的事物,有“言辭”“話語”的意思,而邏各斯則意味著謊言、虛構及欺騙[ 10 ]。這與柏拉圖時期所認為的“秘索思”代表神話與虛構,“邏各斯”代表理性與科學是完全相反的。由此可見,其一、看待事物的角度決定了對其性質的判斷。“秘索思”與“邏各斯”在不同的時期其含義甚至可以完全相反。赫西俄德、荷馬從語言敘述的角度,將“秘索思”視為言說、傳達真理的方式,而柏拉圖則出于建設理想城邦的目的,認為“秘索思”是不真實的、虛構的謊言。其二、在古希臘美學思想的早期階段,“秘索思”與“邏各斯”這一對元概念之間的界限并沒有被嚴格的界定,體現出這對元概念在形成以及固定化的過程之中所具有的流動性與生成性。“秘索思”和“邏各斯”在古希臘美學思想以及西方文化當中的相互對立與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者之間深深聯系、此消彼長的密切關系。由此可見,“秘索思”與“邏各斯”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的二元對立,而是于交織對立中不斷演進”[ 11 ]。
大致在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美學思想發展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期,“秘索思”和“邏各斯”才正式開始呈現出涇渭分明的邊界,二者在認知路徑、方法意義上有著很大的區別,并被長期固定下來。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家“試圖通過理性分析( logos) 認知世界的愿望,在認識論領域引發了一場偉大的革命”[ 3 ] 296。以古希臘哲學與歷史學科為代表的西方“邏各斯”(logos)認知傳統,具有一種“‘話語 以及借助話語進行分辨的能力,它代表著‘分析和‘說理時所必須依循的‘規則,顯示出理性的沉穩和科學的規范,象征著‘邏輯的力量”[ 12 ]。而以文學、宗教傳統為主要內容的“秘索思”思維方式,其方法路徑是與“邏各斯”的科學推理、理性分析、邏輯思考截然不同的故事想象、虛構敘述的方式,以此來對自然與外在世界、精神世界進行闡釋。
“秘索思”具有虛構、神秘的特性,而對于以“驚異”的好奇心為本質特征的人類而言,尋找事物背后的真相,消解“秘索思”所造成的神秘感成為他們內在的訴求與向往,因而揭開“秘索思”的“神秘面紗”的過程,也就是人類不斷從孩童時期進行“啟蒙”的全過程。“邏各斯”認識方式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它是人類認知自然世界的必經之路,因為有“秘索思”思維方式的先行出現以及人們理性意識的覺醒,為“邏各斯”的出現提供了必要條件。此外,還應該看到,“秘索思”因其虛構性、神秘性使得其具有欺騙性與迷惑性,對于古希臘時期柏拉圖意欲建立的“理想國”而言,有著不利的地方。首先,“秘索思”中的很多虛假的故事具有蒙蔽性,在柏拉圖看來,它們會對護衛者造成不良影響,使他們動搖甚至喪失理性,墮為欲望的奴隸,不利于發展和形成城邦護衛者在建設理想國中所應具有的高尚品質——智慧、勇敢、節制、正義[ 13 ] 144。其二,柏拉圖拒斥的是“秘索思”中存在著的“壞的假故事”,尤其反對赫西俄德與荷馬在故事中“將最偉大的神描寫的丑陋不堪”[ 13 ] 72,認為神同時降福與禍給人,而極力主張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惡的原因。而對于“秘索思”所傳遞的“好的假故事”,柏拉圖是認可并允許其存在的,例如在《理想國》(卷二)柏拉圖談到對兒童的教育要先從講故事開始,“故事從整體看是假的,但是其中也有真實”[ 13 ] 71。因為柏拉圖認為,兒童在幼年時期最容易受到陶冶,具有很強的可塑性,而“秘索思”當中存在的“好的假故事”對于兒童是能夠起到積極的啟蒙作用的,為了從幼年時期起就培養兒童的美德,應該給他們講高尚、優美的“好的假故事”。《理想國》卷三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到:“我們還必須把真實看的高于一切,如果我們剛才所說不錯,虛假對于神明毫無用處,但對于凡人作為一種藥物,還是有用的,那么顯然,我們應該把這種藥物留給醫生,一般人一概不準碰它”[ 13 ] 88。這也就解釋了柏拉圖為什么在《理想國》的論證當中,采用詩人講故事的方式(即“秘索思”的思維方式)去反對、驅逐詩人。因為,柏拉圖贊許“秘索思”當中“好的假故事”,認為其具有的感染力能夠起到教化民眾的作用,對民眾而言是有幫助的。人類生存的世界是需要“秘索思”的,即使是要將詩人驅逐出“理想國”,柏拉圖仍然保留了“秘索思”當中的贊頌詩和頌神詩部分,而這些被保留的“秘索思”的故事,能夠對人們起到積極的教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也為詩辯護,對詩與哲學的關系問題進行了界說,他認為“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所以,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于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于記載具體事件”[ 14 ]。亞里士多德為詩辯護亦是對“秘索思”的重要作用進行確證。因此,即使是在主張高揚“邏各斯”的理性、科學精神的時期,“秘索思”的思維方式仍潛移默化地發生著重要作用。
公元一世紀以后,伴隨著基督教以及《圣經》的出現,“秘索思”思維方式再一次得到凸顯。《圣經》虛構了神靈創世、伊甸園、諾亞方舟等的故事,無疑是“秘索思”思維方式的表現。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以自然崇拜和神靈崇拜等“秘索思”認知模式為特征的《圣經》,卻成為后世以“人類中心主義”“人類/自然”二元對立等為表現特點的“邏各斯”思維方式的前身。于《圣經》之中“秘索思”與“邏各斯”思想觀念的相互演進,不難發現“秘索思”與“邏各斯”兩種思維模式的確是相互牽扯、如影隨形、彼此勾連的。
中世紀是“秘索思”盛行的時期,神學被提升到至高地位。為分享當時在主流思想中占據主導位置的“邏各斯”的權威光環,神學家們開始用“邏各斯”的外化形式去宣揚具有“秘索思”精神內核的神學思想,如同早期基督教那樣,將“邏各斯”視作神的理性或智慧。“邏各斯”雖然占據著名義上主導地位,但實際上只是潛藏在深層的“秘索思”所披的外衣。直到經過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西方思想變革階段,代表人類理性的“邏各斯”才再次得到確證,并占據主導,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識從以往“附魅”式的解讀走向了“祛魅化”。“不承認自然界、不承認物理科學所研究的世界是一個有機體,并且斷言它既沒有理智,也沒有生命。因而它就沒能力理性地操縱自身運動;更不可能自我運動”[ 15 ]。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后,一方面,隨著自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人們對自然與外在世界的理性認識能力進一步提高,運用“邏各斯”思維方式和理性、科學的手段對世界進行認識與改造,“邏各斯中心主義”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另一方面,“人與自然的對話非但沒有拉近彼此的距離,反而使得人在自然界里更為孤立。這一巨大的吊詭現象使人類理性的勝利蛻變成了一個悲哀的真理,科學似乎貶抑了任何它所觸碰到的東西的價值”[ 16 ]。因此,面對這一現象,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紀開始了一種“向內轉”的傾向,嘗試以“非理性”“反理性”的方式對人類內在精神世界進行觀察與解釋。西方現代非理性思潮往往有著“現代化的宗教神秘主義色彩”[ 16 ],而這正與古希臘早期美學思想之中誕生的“秘索思”的認識傳統不謀而合,可見“秘索思”的思維模式在西方文化的歷史長河中一直存在,并與“邏各斯”思維傳統相互博弈,此消彼長。
“西方文化的發展軌跡并未是一元結構的直線式發展,而是鐘擺式的,是在二元限定的雙軌之間、在不斷的激烈震蕩與自我糾偏中前行”[ 17 ] 66。“秘索思”和“邏各斯”雖然存在認知方式、路徑與意義上的不同,但兩者都是存在于古希臘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世界、人類思維當中的重要模式,是掌握世界、建構人們所謂的真理、價值、理念的重要方式。科學、理性的“邏各斯”需要“秘索思”的調和,感性、玄學、神秘的“秘索思”同樣需要“邏各斯”的糾偏,二者互為補充,此消彼長,彼此糾偏,才共同促進了人類認知方式的不斷更新與生成,帶來整個自然與外在世界在科學與人文精神方面的生長與繁榮。
結語
“秘索思”與“邏各斯”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神話與科學之間簡單的對立,這種“對立”之中亦發生著相互影響、相互吸納并且相互生成的一面。正如學者楊秀敏指出,“秘索思的內核是‘虛構,它并非基于客觀事物本身,而是來自于人類對于某種意義或價值‘真理的主觀建構與追求”[ 17 ] 60,按照福柯的觀點,人類歷史之中的一切學科、知識、理性,都是被建構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已偏離事實或真相本身的。或許,“邏各斯”也只是比“秘索思”更接近真相與本質的“秘索思”而已。從表現感性、虛構、想象的“秘索思”思維模式到反映理性、科學、邏輯的“邏各斯”思維模式,以及“秘索思”與“邏各斯”之間的此消彼長、相互演化與生成、融合,這一變化遵循的正是人類認知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普遍性、客觀性以及自然規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邏各斯”思維模式發展到現代階段,已經呈現出高度理性化、科學性的形態,但人類詩性生存的需要以及生命深處的訴求仍然對“秘索思”念念不忘,呼喚著“秘索思”的回歸。
當代藝術作品當中仍然存在著奇幻的想象與豐富的虛構性,“秘索思”的思維方式承擔著和“邏各斯”同等重要的作用。例如中國當代藝術家徐冰創作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藝術作品《天書》,這一巨幅人人都看不懂的“漢字”印刷藝術作品,卻在當代藝術領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難看到,徐冰的藝術作品《天書》之中既包含了“邏各斯”式的漢字文化的思想觀念,正如徐冰所述他的藝術“總是與文字糾纏不清”;又蘊含了“秘索思”式的創造力與想象力,創作出無人認識的“偽漢字”,為觀賞其藝術作品的人們帶來了藝術的沖擊感與張力。從徐冰的藝術作品中,我們很容易看到當代藝術中“邏各斯”與“秘索思”兩種思維方式的融合趨向。
從古希臘時期“秘索思”與“邏各斯”兩者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纏綿,到現代社會思維認知中兩者和諧共存,這不僅僅反映了“秘索思”與“邏各斯”彼此走向共融的關系,也表征著人類思維方式、認知形式的一次又一次飛躍與圓融。
參考文獻:
[1]陳中梅.Mvqοs詞源考——兼論西方文化基本結構(BSWC)的形成及其展開態勢(上篇)[M].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242.
[2] 伊索.伊索寓言[M].王煥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3]陳中梅.言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06.
[4]劉淵,邱紫華.維柯“詩性思維”的美學啟示[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1):86.
[5]維柯.新科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181.
[6]羅賓·科林伍德.自然的觀念[M].吳國盛,柯迎紅,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6.
[7]王云霞.附魅、祛魅與返魅:人與自然關系之邏輯演進及其生態啟示[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0,42(6):115-119.
[8]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56.
[9]張志偉.西方哲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8.
[10]王倩.真實與虛構——論秘索思與邏各斯[J].外國文學評論,2011(3):64-75.
[11]李麗萍.論柏拉圖《理想國》中的“邏各斯”與“秘索思”[J].文學教育(下),2020(10):7-9.
[12]陳中梅.“投竿也未遲”——論秘索思[J].外國文學評論,1998(2):5-14.
[13]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4]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出版館.1996:65.
[15]羅賓·科林伍德.自然的觀念[M].吳國盛,柯迎紅,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9:6.
[16]李放.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基本特征[J].社會科學輯刊,1995(1):28-31.
[17]楊秀敏. 發現“秘索思”[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4.
[責任編輯:陳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