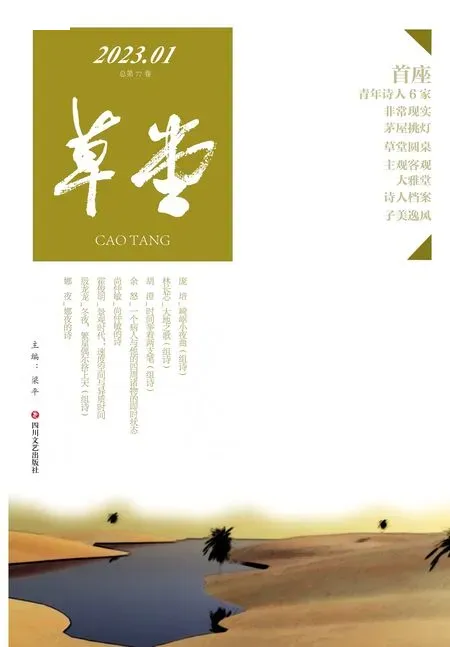【客座】

李亞偉
LI YA WEI
李亞偉
源源不斷地展現出創新精神
尚仲敏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生詩歌最具代表性的詩人,盡管他成名很早,但他獨特、智慧的詩歌作品一直源源不斷地展現出他的創新精神。他的詩歌文本既立足當下,又肩負著先鋒精神,這樣的寫作狀態和文本品質是當代詩歌非常稀缺的樣本。

于堅
YU JIAN
于 堅
“直說”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才能
尚仲敏是口語詩人。口語,就是拒絕隱喻,拒絕言此意彼,直說,信任語言本具的深度。在一個隱喻根深蒂固的傳統里,“直說”需要詩人很大的勇氣和才能。四十年前,尚仲敏還在重慶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通信。他和燕曉東一起辦了《大學生詩報》。許多人都失蹤了,寫不下去。口語不是那么容易寫的,永遠要有激情并樸素自然而不做作。這是對詩的高級要求。造句容易,寫得像是本來就有,自然流露相當難。尚仲敏的口語詩很有感覺。有無感覺是我判斷詩的標準。無論如何解釋,辯護,沒感覺,味同嚼蠟,等于零。我們時代大多數詩人并不自信,尚仲敏從不自吹自擂,也不拉幫結伙,不立旗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是自信的,自在的,理直氣壯的。這部詩集的出版證明了這一點。

楊黎
YANG LI
楊 黎
英雄本色
尚仲敏是漢語詩歌的口語締造者。作為口語的三個特點,尚氏詩歌在開創深入和把握分寸上,均表達出了超乎常人的能力。
首先,作為口語詩歌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有故事性。尚仲敏的詩歌,與真正優秀的口語詩歌一樣,不是以言說和抒情為重點,而是超越簡單的表達,直接深入故事,直接陷在故事里面,成為故事的本身。其次,口語詩歌的特點,在故事之外,更注重語言本身的細節性。細節,使口語生動,同時更使口語真實。比如他非常著名的 《橋牌名將鄧小平》,就是靠語言的細節而打動人。他沉默,只計算著手上的牌。這一細節,簡直就是口語詩歌的靈魂所在。說句實話,一首非口語詩歌,是感覺不到語言在口語和非口語之間的價值差的。除了口語詩歌的故事性和細節這兩點外,其實尚氏口語還有最后一個特點,就是他的人文情懷。建立在個人獨有的語感之上,但又屬于江湖恩怨的語言路徑,實實在在的個性敘述。尚仲敏的語言,有上海灘風味,更近口語,更近人味。
現在,真正的口語寫作正在接近現代漢語寫作的本色。但口語寫作作為純粹的詩歌追求,短說是近四十年的事情,其實卻是從新文化就開始的中國現代化變革。它經歷了黃金十年,隨后漢語的發展幾經沉浮和迷茫。只有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其實就是口語詩歌的出現,才意味著漢語的現代性終于登堂入室。而詩人尚仲敏,是這段歷史成就最為突出的推動者、參與者、評論者和實驗家。
將他同時代的詩人們相比,比如,他比于堅更開門見山。如果說于堅的口語是從非口語開始,甚至在過程中也有反復,那么尚仲敏卻一開始就堅定使用口語寫口語,一直到《只有我一個人在場》。這近四十年的詩集,全部呈現的都是他的口語追求。
與韓東相比,他更自覺和主動。如果說韓東的詩歌是口語寫作的精品,那尚仲敏的卻有去精品的努力,詞語范圍更加廣泛。當然,這樣的比較不是比好壞,而是比差異。
與李亞偉相比,尚詩尖銳但不失精致,沒有莽漢那么多的粗糙和修辭。特別是排比和幽默。他們都幽默,李詩幽默顯而易見,而尚仲敏的幽默卻需要想一想,具有智力要求和社會見識。
尚仲敏是“非非”詩人,是他把口語深入到“非非”里面,使“非非”能夠成為第三代人的詩歌,而不是像“非非”構建時所要做的形而上的語言糾纏。置身當下,渴望生活,是尚仲敏口語寫作的必然性。
一句話,尚仲敏的口語寫作是必然的。他生長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而他的青春期,看的是《上海灘》,追尋的是江湖情仇。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是第一個把偉人平民化寫作的人。著名的橋牌名將、卡夫卡和卡爾·馬克思。而現在,他的人物與他一樣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洗禮,人世間那些內心的淺薄和經歷的復雜,也像他一樣,感嘆和沉默。也就是說他很像不認真,其實不是。
《只有我一個人在場》有尚仲敏熱愛和從小追求的英雄本色。他更為復雜的內心世界,其實也都被他的這些外表深深掩藏。
所以我相信,他還有很大的期待。這個期待,是口語詩歌的本命,更是詩歌口語化所深刻的價值。除了口語,任何寫作,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換句話說,詩歌的口語之爭,實際指向的是才華之爭。

何小竹
HE XIAO ZHU
何小竹
拒絕加入合唱
其實,我也是讀尚仲敏的詩長大的,盡管他比我小一歲。當時在重慶建院(現重慶大學建筑學院)讀書的我的老鄉孔川在暑假帶回一張報紙《大學生詩報》,主編除了阿敏,就是尚仲敏,上面有他本人的詩,以及于堅和韓東的詩。那是1984 年或1985 年,我二十歲剛出頭。后來,1986 年,我們共同成了“非非”的成員,在《非非》創刊號上,讀到了他的《橋牌名將鄧小平》《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卡爾·馬克思》《致卡夫卡》等后來成為名篇的詩作。他是“口語詩”的開創者之一,明確提出否定“朦朧詩”的口號(“打倒北島”),用自己離經叛道的詩和極端尖銳的文章為“第三代”先鋒詩歌搖旗與開路。他在成都送仙橋水電校的單身宿舍是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成都的落腳點之一,我們整夜聊詩,餓了就用電爐子煮面吃。那時的他,意氣風發,目中無人,個子不高,卻長著“一張大師的臉”(引自他自己的詩句)。
現在,他依然意氣風發,目中無人,只是“大師的臉”上多了許多包容與祥和,而把犀利與叛逆保留在詩中。這是一種現場寫作的詩,就好像他隨時盯著這個時代的舞臺,看你們這些演員拙劣和可笑的表演,并適時地予以批評和嘲笑。他知道自己做不了這一臺戲的導演,但搗亂和起哄是能夠的。
拒絕加入合唱,這是我對仲敏詩歌最敬佩之處。

吉木狼格
JI MU LANG GE
吉木狼格
他越任性讀者越喜歡
現實中的尚仲敏和所有的人一樣,都有應酬的時候,只在一個地方他不應酬,從寫第一首詩到現在,他堅持把他的全部真誠用在詩歌上,他以人類社會一分子的身份寫詩,從不把自己拔高、拔出,樂在其中,他的詩就是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寫,讓人倍感親切,溫暖而有力。當然真誠不是他詩歌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一部分,僅僅是出發點。我永遠不會在乎詩人寫什么,只在乎怎么寫,因為“怎么寫”才是詩的全部,至于寫什么,都不會超出人類文化的總和,即不會超出已知。也只有“怎么寫”才可能讓創作成為創作。
尚仲敏的詩,一看就是尚仲敏寫的,他用獨有的情趣和語言方式讓我們看到了他與眾不同的詩歌創作。尚氏幽默在他的詩中隨處可見,他明明在寫自己的詩,說自己的話,借機嘲諷一些人,這些人卻更喜歡他的詩。一句話,他越任性,讀者越喜歡他,也許這正是詩歌的魅力所在。
倡導用口語寫詩,是尚仲敏永不放棄的詩歌理念,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今天,他始終堅持用口語寫詩,鮮活而獨特。在詩歌寫作上,“口語”對應的是“書面語”,也就是用漢語翻譯外國詩形成的傳統,即“翻譯體”。在這個傳統的影響下,許多人堅信詩歌只能用書面語來寫,否則就不是詩。尚仲敏剛好相反,他認為詩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創新,在于創新帶來的獨有。繼承傳統最好的方式恰恰是反叛傳統。書面語是傳統,是過去的語言,它的生命存在于對過去的欣賞中,而不在現實的創作上。口語永遠是最新的,它在每一個當下,因而用口語寫詩,才談得上創作,起碼具備了創作的前提。尚仲敏用他的口語寫出一首首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好詩,但他總說:詩不好寫啊。是的,特別用口語,失之毫厘,謬之千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生詩派的領軍人物尚仲敏九十年代下海,從此離開了詩歌,別人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但我作為他的老朋友,心里滿不是滋味,問他為什么,他總是笑而不答,問急了便說要寫的、要寫的,一看就在敷衍我。除了八十年代那些不算太多的詩篇,難道我再也看不到一個天才的新作了嗎?時間一晃二十年過去了,我都等老了,還是沒有看到他的哪怕一首新作,我決定找他好好談一談。在瑞升步行街的露天茶坊,那天的天氣很好,成都居然出太陽了,我約尚仲敏喝茶,按老規矩先下圍棋,我心里裝著詩,連輸他兩盤,他得意地說,你今天狀態不好啊。滿懷心事的我,狀態能好嗎?我撇開圍棋說,你有二十年沒寫詩了吧,你就跟我透個底,你還寫不寫?他依舊敷衍我:要寫的、要寫的。我問什么時候寫?他說快了、快了。我說這樣吧,你只要寫一首詩,我就殺一頭牛招待你。我一急把一個彝人的本性暴露無遺。也不知是我的話起了作用,還是作為詩人——雖然他已是成功的商人——詩歌又回到他的身體里,沒過多久,他重新開始寫詩了,而且一發不可收,寫了許多首。和八十年代少年人的天馬行空相比,如今的他更關注生活的細節,筆下那些具體的事物,不僅不沉悶,反而令人回味無窮。重新寫詩后,他顯得更加從容,更加游刃有余。我必須向尚仲敏提出,我只欠他一頭牛,而不是一群牛。不管他寫了多少首詩,我的目的達到了,承諾也要兌現。我們共同的朋友、另一位詩人周亞平提議,為尚仲敏的重新寫詩,搞一場一頭牛詩會,我堅決同意,讓我糾結的是,一頭牛詩會是在成都舉辦,還是去涼山舉辦,這是一個問題,我得同尚仲敏商量一下。

柏樺

周東升
BAI HUA ZHOU DONG SHENG
柏 樺、周東升
邊走邊說
尚仲敏揚名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一出現就完全與眾不同,給人印象深刻。尚仲敏有一個很重要的詩觀:“口語詩是一種老實厚道的詩。”他寫的詩不僅僅老實厚道,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品質。前不久我讀到了他剛出版的一本新詩集《只有我一個人在場》,如同看一部緊張的偵探小說。仲敏的生活真是處處都是詩,無時無刻不是詩,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渾身都是詩。即他發現詩意的觸覺、嗅覺,感覺簡直是十分驚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把他每一分鐘的生活都寫成詩。而這樣寫詩的手腕和眼光是罕見的,我在仲敏的身上看到了這一點。他的詩口語,機智,親切,有事實,有來處,有生活,有余味,以小博大,耐人尋思,更耐人驚嘆,說他開一路新詩風,完全實至名歸。
尚仲敏有一首小詩《邊走邊說》,生活日常的邊走邊說,它本來是那樣容易被人忽略,誰會注意呢?如我前面所說,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他都可以用詩意的眼光去打量它、發現它、說出它。而“行走”這個主題也是我一貫偏好的主題,不然,我怎么會寫有一長篇《知青散步記》呢。無獨有偶,我又讀到了他另一首更令我驚艷的行走詩——《雨中的陌生人》。平凡的生活中到底有著怎樣的神秘?那個行走在雨中的人是個什么人?晚歸人,失意人還是特務(聯想到作者幼時的理想是當一個特務)?他為什么深夜獨自在雨中行走?在窗口觀望的人已為我們說出了答案:“星座不合是個大問題”,那似乎又是個戴望舒筆下雨巷般的失戀人?
“邊走邊說”不僅是尚仲敏的詩意發現,也是一種發明,一種機智的即興的詩意發明。發現意味著生活中的詩意被詩人挖掘出來,詩人有他獨特的審美眼光,善于從川流不息的生活中采擷詩的珍珠,像是經驗豐富的果園工人,一眼就能認出成熟的果子,并摘到果籃里。發明意味著無中生有或者有中生有,總之要創造出一種世間原本沒有的東西。尚仲敏的寫作二者兼有,比如《雨中的陌生人》就是發現,它發現了平凡生活的一個神秘裂隙,當“你”用“星座不合”的玄學去解釋、去縫補這個裂隙時,又制造了更多的神秘。正是這波紋般蕩開的神秘,使庸常的生活重新變得豐富、有意味。
也許尚仲敏發明詩意的能力更值得討論。如果說他開了一路新詩風,那么,這個“新”字主要就體現在他的發明上。尚仲敏善于利用稀松平常的細節和語詞,制造一個出人意料的、幽默的又意味深長的判斷,這需要怎樣的機智和即興能力呀!這就是一種詩意發明的能力,生活中原本沒有,詩人憑空制造出來,又把它注入平淡的生活。
很少例外,尚仲敏的詩大都寫得輕松活潑。有時候,他要發明的就是一種快樂。這時,對于他,詩的本質就是快樂,也可以說,詩即語言的快樂。也許有人會質疑,但我們無須引經據典去論證。這世間有苦大仇深的詩,有高深莫測的詩,理應也有專寫快樂的詩。它通過笑聲使生命暫住,使生命在剎那間獲得解脫。
尚仲敏的“邊走邊說”展示了一種即興寫作的機智風格。所謂即興,也就是即景抒情或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寫法。尚仲敏對詩歌抒情向來持有異議,因此他的即興寫作極少抒發胸臆,而多采用敘事的寫法。他所寫之事通常是社會時事或日常生活中的習見之事,諸如抽煙、喝酒、購物、朋友交往……敘述直白,才思機敏,不落刀削斧鑿的痕跡,總是給人一種即興寫作的輕松感(當然,行家里手都清楚,那種看似自然的字句安排和水到渠成的起承轉合,一定來自精心的打磨)。
說尚仲敏的寫作具有即興寫作的風格,主要是想說他的寫作與生活之間的關系。因為即興是一種詩性隨時在線的狀態,它表明詩和生活時刻在關聯著,時刻在發生化合作用,并相互改變著。這正應了張棗后期念茲在茲的一個重要詩歌命題:“如何使生活和藝術重新發生關聯?如何……重返和諧并與世界取得和解?” 也許尚仲敏的詩風不合張棗的口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尚仲敏的寫作一定能提供某種啟迪。
對于尚仲敏,詩不外在于生活,也不大于生活,詩“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寫詩就是一次次緣事而發的即興閃光。同時,正是因為熱愛生活,才熱愛寫詩,又因為熱愛寫詩,更加熱愛生活。這樣的詩歌觀念,決定了尚仲敏的寫作始終有輕松的姿態和無焦慮的心態,也決定了他的詩歌幽默卻絕無尖刻,反諷但帶有善意。
當然,尚仲敏“邊走邊說”的即興風格并不失之于即興寫作的簡單,雖然他總是把詩歌寫出簡單明了的效果,但這樣的寫作絕不簡單。在尚仲敏的寫作過程中,機智主要表現在戲劇性效果的制造上,有時是靠語言的歧義、錯位和跳轉,有時依賴情節的逆轉或戛然而止,有時則憑借一個活靈活現、忍俊不禁的戲劇性情境。這都是尚仲敏的拿手好戲,也是公開的詩藝秘密。比如《明月照大江》,在前文的平鋪直敘后,突然一轉:“我只好回復他/它橫任它橫/明月照大江”,戲劇性出其不意地爆發出來,令人歡樂。《追星》的結尾是一個戲劇性的情節逆轉,“他以為我要找他簽名/我說,把你褲子拉鏈拉一下”。倘若不存偏見,你會發現,這樣寫,并不俗,它善意地打開了生活中有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