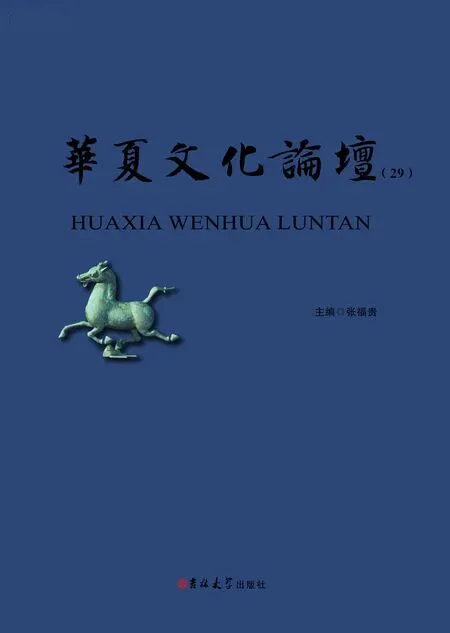超工業化景觀:從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論到東北工業文創建構
鞠惠冰 王麗媛
【內容提要】以東北工業文創為代表的工業文創熱潮重新開發和定義了舊有的工業遺產,并在新時代語境下孕育出了新的社會景觀。本文從貝爾納·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論出發,結合傳播學視角從假象領域和個體感知兩個方面對東北工業文創呈現的動態圖景進行剖析,進一步考察超工業化景觀中技術和美學的共生、整體和個體的同頻、個體和個體的聯結,以及被重新規劃整合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一、問題導入:東北工業文創呈現的社會景觀
21世紀以來,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記憶的形成、傳播和再造等環節正在被全面重塑,工業社會原有的社會系統結構和社會關系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工業文創熱潮重新開發和定義了舊有的工業遺產,并在新時代語境下搭建起具有復雜時間客體的假象領域,展示了工業發展中的新舊技術更迭和過渡,彌合了由工業技術帶來的文化認知分裂,工業歷史記憶被重新書寫。正如斯蒂格勒在《象征的貧困1:超工業時代》的序言中寫道的那樣:“我們時代的特征就是工業技術對象征控制的把持。”超工業時代的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在統一的意志下整合,技術和美學在空間表現的想象張力里共生,整體和個體在時間客體的蒙太奇拼接中同頻,個體和個體在共通的知覺中滋生友愛,新舊技術、新舊城市的分隔線被一種“集體記憶”下的集體計劃替代,社會關系被重新整合,社會秩序被重新規劃。
由于豐富的工業遺產資源和城市發展的迫切需求,我國東北地區工業文創的轉換極為迅速。多種多樣的文創形式將工業制造的具體生產技藝和物質空間進行了藝術化改造,使得工業技藝技術轉化為被用來展示和再開發利用的工業文化符號,并改變了傳統的圍繞著工業生產的人與物的關系,文創空間呈現出來的新的社會景觀將抽離出來的象征符號進行了分離和重組,使之成為被觀覽的“博覽物”,個體也被媒介技術嵌入“博覽物”的展示和傳播中……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能只是忙于欣賞技術所帶來的新的繁榮景象,更要思考的是,新的技術是如何改變了工業文創的媒介屬性和媒介特征,象征表達是如何重塑和定義當下的工業精神和歷史記憶,個體是如何在技術座架下感知社會和認知自我的……這需要一套新的邏輯來重新認識東北工業文創呈現的動態圖景,以及其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所呈現出的超工業化景觀。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以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論開啟對東北工業文創社會景觀的全新解構,通過文獻分析和訪談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握東北工業文創動態圖景這一研究主體,沿著象征信息流動的傳播鏈條捕捉動態圖景中的傳播端“假象領域”和接收端“個體感知”。并以此為切入點,分別對東北工業文創所呈現的假象領域和領域中個體的感知型接收狀況進行深入剖析,探討東北工業文創所呈現的超工業化景觀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并在此基礎上將斯蒂格勒的思考和疑問引入對東北工業文創的考察研究中,延展出一些新的思考:多形態的東北工業文創構建了一個怎樣的假象領域?多形態的記憶工程技術/媒介技術是如何將假象領域構建起來的?在假象領域中,共時記憶、集體記憶是否會將個體意識吞沒,造成個體失去差異性和主動性?東北工業文創是消費主義和技術邏輯下對“文化工業”品的復刻,還是有著旺盛生命力和人文關懷的新型文化形式?
二、理論框架:斯蒂格勒的超工業化景觀
(一)理論基礎:斯蒂格勒的記憶持存與象征理論
斯蒂格勒認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人的歷史性存在是從技術的出現起始的,即人的歷史存在是在工具的制造與使用過程中被發明出來的。工具(技術)既是勞動、計劃和超前的對象,同時也是保留這些經驗和后種系生成結果的記憶載體,是保存出現在人體之外的物性存留。①張一兵:《人的延異:后種系生成中的發明——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解讀》,《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3期。從古至今,記憶持存在不斷存留和傳播人類歷史記憶的同時,也形成了不同的形態變化和豐富的意識層次。隨著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興起和網絡化,原本的工業體系構序結構被改變,技術體系、記憶術體系乃至世界化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融合到了一起,承載著深層次的技術邏輯和復雜的社會關系:記憶工程技術成為技術體系核心,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數字化全球記憶體系,個體通過感知接入持存裝置在集體記憶中被重新發現,人與技術在數字化信息傳播中共生共長……新的社會文化、社會景觀應運而生。
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第三卷中寫道:“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機制的拓展具有前所未有的實效性,并促生了一個新的假象領域,努力為‘大寫的我們’提供了新天地。”在新技術基礎上構建的社會景觀中,斯蒂格勒理論中的三種持存都被多形態的媒介技術納入融合,由此對時空的時序結構進行排列重組,構建起復雜的時間客體:“第一持存是意識留存在時間流的現在之上的東西”①張一兵:《好萊塢文化殖民的隱性邏輯——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構境論解讀》,《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對應著個體的原生記憶,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個體對事物本身的直觀感知;在此基礎上的第二持存是通過個體主動選擇過濾之后保存下來的持存,對應著想象力重塑的“當下”呈現;第三持存則對應著人類物種擁有的第三種記憶——技術的記憶,因此在第三持存的記錄工業中,技術被賦予了超前意識,以“先將來時”的存在狀態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結構進行了分解和重構。由此,過去發生的現實可以轉化為現在的真實發生,過去的不可能可以預言未來的可能。在經歷這一復雜時間客體時,個體感知波動迅速被持存裝置捕捉,生命的流逝和記錄的重放相互融合,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界線在同感中消融,表演與現實邊界消失,生活與蒙太奇虛構同質化,想象和感知換位,原生記憶、第二記憶、第三記憶(持存)相互混合……歷史和現實的橋接中新的假象領域被建立起來,同時感知性的互動中個體在共生網絡中緊密相連。
(二)分析視角:假象領域的建構和個體感知的反饋
斯蒂格勒所說的“新的假象領域”,正是在飛速發展的新技術座架下產生的社會景觀的呈現載體。根據斯蒂格勒的理論,當前時代新的社會景觀正在逐步形成,這種景觀表層是由象征符號搭建的具有復雜時間客體的假象領域,深層結構則是由技術邏輯主導的經濟文化衍變。沿著象征信息流動的傳播鏈條,可以發現媒介技術作為景觀動態發展的核心,一方面占據著敘事主動性,把持著復合型記憶持存建構起具有統一意志的假象領域,另一方面“將不在場的個體即時轉換為在場的狀態”②[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5頁。,使得個體意識暢通無阻地接入媒介技術的敘事邏輯。
在這個假象領域中,媒介技術通過網絡的形式架構起社會的存在情境,肩負著塑造社會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的重任。斯蒂格勒所說的具有實效性的拓展空間是假象領域媒介空間的重要基礎,沿著這一拓展路徑可以還原出世界自我投射的取向選擇和媒介空間的變化過程。同時在多形態媒介構成的假象領域中,媒介技術全面介入時間觀念,將過去的線性時間打碎,轉變為碎片化的、原子式的、分散的、光點式的點狀時間,又使得“物性機械流和時間客體的時間流相互疊合”③張一兵:《好萊塢文化殖民的隱性邏輯——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構境論解讀》,《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沿著復合型的記憶持存對時間的重組和拼接的路徑,可以窺得其背后的深層技術邏輯和發展趨向。社會記憶正是在媒介空間和媒介時間的雙重維度中流動,順著媒介網絡將歷史記憶植入社會場景從而驅動個體行動。對社會集體記憶的流動進行解構,能夠在工業發展中的新舊技術更迭和過渡中找到精神復興的源頭和動力,鼓舞青年重建城市文化。
在假象領域“空間—時間—記憶”的架構下,個體的跨感覺通道(intermodal perception)①Charles Spence,“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A tutorial review,”Atten,Percep Psychophys,Volume 73,Issue 4,2011,PP.971-995.被最大限度地打通,象征性表達“原始地介入他者的感覺性問題中”②[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象征的貧困1:超工業時代》,張新木、龐茂森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頁。,使得個體意識的復雜時間客體性凸顯,更容易接入“大寫的我們”這一集體記憶。斯蒂格勒認為個體之所以對假象領域產生認同,一個深層原因就是在于人類的意識本身的結構具有“由運動構成的時間進行蒙太奇剪輯”的特征,個體意識“會不斷把位于這些客體之前的物體形象投射到這些客體之上”。從個體感知反饋反觀假象領域,能夠對比得出技術記憶的前攝和后攝的變化特點,也能夠更加直觀地比較出社會關系的位移和文化發展方向。
(三)理論適配性:東北工業文創社會景觀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
從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論看東北工業文創,其所呈現出的超工業化景觀具有典型性與特殊性。斯蒂格勒從人與技術的關系出發,對超工業化景觀進行了深層次的考察和剖析,在其理論中超工業化景觀集中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新技術發展驅動復合型記憶持存構建新的假象領域;第二,個體化過程服從于集體性的同感和友愛,集體記憶接入個體意識;第三,強大的技術基礎進一步放大了技術邏輯,技術成為社會座架,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態。受歷史原因和現實需求的影響,我國東北工業文創在物質基礎、動力、文化三個層面均充分展現出了雙重工業技術邏輯和歷史性的優勢,較為完整地呈現出超工業化景觀的全貌。在物質層面,東北工業文創依托于工業遺產原址進行重建,調用大量的工業品和藝術復制品等實物客體配合多形態的媒介進行展演,為假象領域提供了豐富的象征符號資源和記憶工程技術基礎,假象領域的時間和空間得以更好的延展;在動力層面,東北經濟發展和城市復興的迫切需求使得個體以更加積極的心態主動地連接集體記憶,迅速催生出統一的“工業精神”認同;在文化層面,東北曾經輝煌的歷史記憶和振奮人心的工業精神為新的城市文化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使得象征符號的意義歷史真實在場,個體更容易信服和歸屬于集體記憶。
同時,斯蒂格勒也就這樣的社會景觀進行了批判與反思:首先,他認為服從于技術邏輯的超工業化景觀,孕育著新的社會控制形式,被制造出來的共時記憶會使個體意識陷入焦慮與迷失,原始自戀毀滅的盡頭將會是個體化的喪失。其次,技術邏輯下的社會景觀也暗含著新的脆弱性。因為被制造出來的同感和友愛過于依賴媒介技術網絡,不穩定的技術波動很容易激起新的信任危機。最后,他認為在由技術邏輯構建的假象領域中,象征表達被工業生產邏輯裹挾,服務于消費主義,大量象征符號的在場更是暗示著意義的缺場,象征的貧困和文化的虛無將成為新的文化困境。根據斯蒂格勒的批判和反思,對東北工業文創發展歷程與消費主義下的象征表達進行對比,能夠發現其物質文化基礎和動力機制與消費主義下的象征表達均有所不同,所以其所孕育的超工業化景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三、假象領域的建構:時空交錯中的共有記憶重建
(一)空間的交疊重構
在假象領域中,多種的工業實物客體結合媒體影像技術,以“視錯覺”的表現方式被個體感知,將個體拉入東北工業的“場域”中,從而完成媒介空間的交疊重構。作為東北工業文創代表之一的中國工業博物館(即原沈陽鑄造博物館)就是依托于沈陽鑄造廠舊址進行了改造和擴建,成為歷史重演的物理空間。這里的建造者巧妙地將建筑原貌、工業機器、工業產物及其復制品、創意設計品在媒介空間的光影中聚集起來,圍繞著統一的“工業精神”的核心,將實物客體改造成為工業記憶的承載體,從而開辟了工業歷史的藝術空間。在這些被保留和修復的車間梁柱構架下,工業文物和復制品、創意設計被陳列放置,生產場景被通過各種方式局部還原,工業文創利用“視錯覺”最大限度地完成從視覺空間到想象空間的延展。根據被保留下來的不完全的歷史記憶和集體想象,工業文創空間內部又被切割成不同的主題展覽,同一主題展覽中持存裝置聚合為統一的意義指向,使得“錯覺”中的歷史記憶映射到具象的物品上來,讓抽象的工業精神變得真實可感,縱向拓展了主題的歷史空間和藝術空間。而這些相對獨立的媒介空間又由充滿著工業生產影像資料的長廊連接起來,保證了媒介敘事從文創場景展演的工業生產到歷史記憶的工業生產的連續性。在縱深感極強的情境壁畫和實時影像的背景中,感知空間在光影交疊中不斷延展,被延展的空間又相互交疊完成了整個空間的聯結。連續性的保證使得真實空間和虛擬空間的內在距離縮短,個體所能感知到的歷史感和年代感都具化為目之所及的鋼鐵樓梯、鋼鐵欄桿、墻面和齒輪配件等特色工業元素,這使得個體感知變得更加的直接、敏銳,個體身在其中猶如“身臨其境”。“圖像優于存在,所見先于真實”①李簡璦:《后現代電影:后現代消費社會的文化奇觀》,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頁。,觀望即為“眺望”,這種空間奇觀便在感知的“視錯覺”式的整合中形成了。
(二)時間的拼接整合
東北工業文創的數字化媒介形式對應著相對獨立的時間客體,其通過非線性的跳轉和編輯連接起假象領域內不同的時間客體結構,打亂了原本的時間構序,自由地對歷史時間和現實時間、個體時間和集體時間進行“剪輯”,從而完成媒介時間的拼接整合。德波在闡釋景觀的循環時間時寫道:“社會只知道永久性的現存……它不是把時間視作什么東西的流失,而是把時間視為什么東西的返回。”②[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7頁。斯蒂格勒則是更加激進地提出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我稱為工業時間客體的時代”③[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象征的貧困1:超工業時代》,張新木、龐茂森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8頁。。在這樣的模式下,“流動的時間意識被否定”,超工業化景觀組織起符合其需要的循環景觀時間,控制記憶持存技術制造出多層次的時間客體,從而在個體意識中植入總體意識,將個體共時化。在東北工業文創的超工業化景觀中,每一個工業文物和展示品都脫離了其工業價值甚至是物理意義,成為一種歷史記憶的能指,它們配合著影像和媒體的交互技術,被制造為一種工業時間客體,并借助媒介技術的特性在人的感官上延伸,實現工業時間客體和個體意識時間兩者的流動同步,達成“與意識一樣流動順暢”①[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象征的貧困1:超工業時代》,張新木、龐茂森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35頁。。同時,在城市和技術急速發展的時代語境中,出于對流通的急切需要,能指的具象形式被統一地標準化處理。數字化媒介所制造的象征符號使得假象領域和領域中文化傳播的路徑更加靈活、豐富。大量的工業文物及其仿制品作為原生持存的實體性重現則擴充了時間客體帶給個體的感知覺,使得個體的意識時間順著假象領域時間客體的流動而流動。數字化的靈活性和被擴充的感知覺共同塑造了景觀中的“時間積木”②[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象征的貧困1:超工業時代》,張新木、龐茂森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70頁。,并通過對一塊塊“時間積木”的拼接和重組,為假象領域制造感知上的真實性和沉浸感,連接歷史記憶和個體意識,激發個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三)記憶的集體重建
東北工業文創充分調動歷史記憶,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聯結個體感知,使個體深度沉浸在“全息”的場景中,接收時間和空間的記憶傳達,將個人經歷、城市歷史、祖輩記憶重組,從而完成共時記憶的集體重建。媒介技術展現出的空間和時間特性,使個體能全方位感知記憶信息,迅速打通個體跨感覺通道,想象體驗感知的有效性或真實性被最大限度放大,進而個體記憶中的“集體無意識”被激發。卡爾·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深深地隱藏在社會個體的無意識深處,包含了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所積累的先驗產物,并過濾沉淀至基因中。盡管個體記憶存在差異,但存在于基因與意識深處的“集體無意識”會使得個體記憶在總體上具有一般內在相似性。東北工業文創的景觀中,廠房、設備、產品這些以凝固形式被保藏的過去的文化,是被凝視、辨別的物體,也是能夠引起沉思和回憶的記憶對象。它們喚醒了人們意識中對城市的歷史或是個人相似經歷的感知,這種感知圍繞著“工業文化”積聚成一種“集體記憶”,不斷放大個體間的同感,并結合多形態記憶持存制造的共時感,最大限度地在兩者基礎之上建立起友愛。③[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象征的貧困1:超工業時代》,張新木、龐茂森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0頁。而這種友愛影響著人們對東北社會關系變革的重新認知,影響著人們關于東北城市歸屬感、認同感的重新定義。
同時,“集體記憶”和同感之下的友愛經由意識的內化后反過來推動著東北工業文創超工業化景觀中“集體計劃”的達成。正如德波在《景觀社會》中寫道:“借助于‘集體計劃’尋求重建由零碎物和廢棄物等元素構成的復雜的新藝術環境,已在都市生活的整合藝術廢料或美學技術形式的混合物的企圖表達被看到”④[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9頁。——東北工業文創將工業遺產零碎物和廢棄物等元素在新的博物館或創意的美學技術形式下混合,形成一種新的表達,這種表達是一種反思式的表達,一種開放式的過渡和銜接,一種建立在深深沉浸于對東北工業精神的認同感之上的向往和期待。而在這樣的向往和期待中,“東北工業文化復興”的話語設置應運而生,與“東北振興”的城市發展目標一起,向青年人發出召喚。
四、個體感知的反饋:集體感召下的不同感知呈現
(一)歷史的記錄載體
東北工業文創園多依托于工業舊址進行改造,在光影重疊的媒介空間中,歷史記憶與現實空間交錯重合,將東北工業生產場景“還原”。個體置身其中時,感官被全方位調動,舊時的歷史記憶和生活經歷被最大限度地激發,極具標志性的實物客體帶著個體找回真實的生活化回憶,在此基礎上從自身生活出發回溯到更為宏大的歷史圖景。多媒介同屏敘事的工業文創成為個體調取歷史記憶的記錄載體。例如中國工業博物館布景以等比例還原了沈陽鐵西區生產廠房的全貌,真實直觀地展現出工業區的生產生活場景。對于曾經在工業城市中生活、工作的個體而言,置身于這樣的文創空間中,能夠吸引其迅速回憶起曾經鐵西區的生活記憶和社會圖景。行走在鐵軌改造成的小路上,恍然間仿佛回到了東北工業的繁榮時期,歷史記憶在工業文創不間斷的“全息”投放中逐漸清晰。

圖1 中國工業博物館內部場景展示①沈陽工業博物館官方公眾號:《鑄造館》,2017年12月14日,ht t ps://mp.wei x i n.qq.com/s/ab96j8oyifYlfoZOk2CKAA,訪問日期:2021年8月15日。
東北工業文創充分調動多形態的記憶持存裝置。從實物客體形態的小人書到滿是影像記錄的長廊,再到媒體交互的藝術創作……所見所及都成為工業文化傳播的象征符號,同時也成為東北工業記憶的承載體,不斷激活和固化個體意識中舊有的東北記憶和東北印象,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進行重新構序。頻繁來到工業文創園參觀的個體無意識地反復接收了假象領域的象征信息,激活和固化了腦海中舊時的沈陽記憶和沈陽印象,同樣的記憶持存同時承載了個體經歷與城市歷史。個人的記憶與經歷似乎在這里與整座城市的歷史和命運相交融,一本“小人書”便可以串聯出鐵西區整體的歷史面貌,而從一處工業文創園便可以映射出沈陽歷史文化的全貌。同時,東北城市中的個體面對集體記憶時展現出了極強的主動性,這可以從個體對東北輝煌歷史的追憶和對東北城市的眷戀中得到體現。
(二)地方的精神標志
“長期以來,巴洛克藝術在藝術創作的世界丟失的統一性,在某種意義上在今天對過去藝術總體的批發消費中被重新發現……意味著其藝術世界的終結。”①[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8頁。東北工業文化在當下批量加工的文創產品中被重新發現,并在假象領域中達成統一。這種統一一方面呼應了斯蒂格勒所說的持存的“先將來時”——其記錄了東北工業文化輝煌歷史的逝去;另一方面也使得東北工業的輝煌歷史對當下東北工業發展產生正向的互文性影響,東北工業文化的歷史記憶被重新發現,藝術創作被終結,都意味著新的歷史文化正在孕育。在經歷了文化區分之后,被設想的地方主義意識出現,并嘗試“鍛造物理空間上的真實領土形態”②[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8頁。。共時和同感催生出集體計劃,將城市零碎物和廢棄物等元素在新的博物館/創意圖景的美學技術形式下進一步混合,形成一種新的表達,從而鑄造“社會的完整個性”,肯定地方精神標志的價值,推動真正的城市復興。

圖2 中國工業博物館展出的文字影像資料③沈陽工業博物館官方公眾號:《通史館》,2017年12月14日,ht t ps://mp.wei x i n.qq.com/s/esoSlxNCE9S5r2PxfWYTaQ,訪問日期:2021年8月15日。
在東北城市復興的需求驅動下,個體本身帶著強烈的自主意識進入假象領域,也帶著同樣強烈的城市文化自豪感尋找、接入假象領域所呈現出的集體記憶,并企圖將東北輝煌的工業歷史和工業精神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喚醒。東北工業文創在這樣的合力下成為東北地區的精神標志,文創所轉化的象征符號在這種暢通的互動中孕育著同感和友愛,并在同感和友愛之上建立文化認同,在新時代的文化景觀呼喚城市復興。對東北工業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驅動著個體沿著老工業基地遺址的路線對東北工業歷史進行了全面的游覽和考察,借力于技術記憶的“先將來時”的性質,個體在東北工業的輝煌歷史中尋找東北城市發展的資源庫,在對時間的回溯中望見了通向未來的輝煌道路,新的夢想和舊的文化在統一的城市精神下被整合,新的媒介技術和舊的工業精神結合起來集中呈現出地方精神的價值與活力。同時,受訪者對東北工業文創所創造的假象領域中的歷史呈現表達出贊許和認同,積極參與城市集體計劃,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積極地傳播地方歷史精神——向訪者推薦其他工業文創園區、對東北工業歷史進行文化研究,主動融入多層次的時間客體,表達和傳播東北工業文化精神。
(三)城市的新興文化
當下的東北工業文創形式較為多樣,例如某種文化形態的周邊類商品或是文化場景空間的實景式還原……這些不同的文創形式都是東北工業文化衍生出的新興文化,其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影響城市的精神氣質,為城市人群開辟出新的文化生長空間。對東北工業文創產業園進行實地考察,能夠直觀地發現其作為工業遺產的社會功能正在經歷轉換。文創園成為個體娛樂休閑的“棲息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兒童、孩子等成為文創文化的體驗者,新一代的人們在這新舊交疊的空間中經歷著回顧與展望。

圖3 南嶺1932—長春水文化生態園①水石設計官網:《長春水文化生態園》,2019年,https://www.shuishi.com/en/works/1155.html?region=1,訪問日期:2021年8月20日。
在工業遺產的社會功能轉化的同時,舊有的象征符號重組為新的文化形式,其構建的空間成為個體休閑棲息地——這對于年長者來說,是將舊有的工業文化記憶打造為了新型的休閑空間;相反,對于年輕人來說,是在他們司空見慣的休閑空間中填充進了他們并不熟悉的“新內容”。新舊交疊的組合吸引個體聚集,不同個體在這片空間產生不同的文化體驗,城市的新興文化在新舊生活觀念的碰撞中滋長。南嶺1932—長春水文化生態園原址為偽滿時期建造的長春市第一凈水廠,承載著長春市80年間供水文化記憶。生態園在老建筑群落和生態綠地的基礎上,將凈水廠原有的“水管”“水閥”等代表性元素與秋千、滑梯等兒童游樂設施組合起來,滿足了市民休閑娛樂的文化需求;并通過孩子對工業元素組合的好奇和追問,將關于長春凈水廠的歷史記憶注入孩子的城市印象中,從而實現了新舊元素溝通互動。這些組合產生的文化意義賦予了場景特定的美學趣味,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生活的樂趣。生態園在完成物理空間上的“集聚”的同時,也促使個體在關于“凈水廠”的工業象征符號溝通中形成新的社交關系,進而完成文化生活的聚集,城市的新興生活方式和新興文化在記憶持存裝置搭建的“休閑空間”中被構建起來。另外,新型的記憶裝置和歷史呈現形式使得個體以更加積極的態度解讀象征符號,激勵個體擁抱新科技、新生活與新文化。
五、結語
工業時代,城市發展圍繞著工業生產形成了獨特的工業景觀;如今,東北工業文創作為工業時代遺留產物活化后的城市圖景,集中展現了技術與美學、整體與個體的共生關系,其呈現出的超工業化景觀也逐漸趨于成熟:隨著媒介技術的愈發成熟,不同形態的媒介形式之間的特異性被消解,媒介時空的整合更加連續完整;同時,城市對于工業文創的正向反饋也鼓舞了個體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接納共時的集體記憶,“大寫的我們”在假象領域不斷壯大。在此基礎上,個體間的友善被不斷放大、關系更加緊密,“集體記憶”和同感之下的友愛又經由意識內化后反過來推動著東北工業文創超工業化景觀中“集體計劃”的達成,激發個體不斷自發嘗試將工業元素以創意或美學的形式進行重新整合,開辟新的城市成長空間,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表達。
在逐漸成熟的超工業化景觀中,東北人特別是東北青年人也在工業文創塑造的集體記憶中不斷地尋找自我。近年來東北經濟發展的不景氣以及媒體所塑造的東北地域刻板印象使得東北人開始對城市發展道路產生迷茫,特別是東北青年群體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并且企圖“逃離”東北。而東北工業文創所展現出來的工業精神和文化歷史為青年人提供了諸多個體范例,青年人的自我懷疑能夠逐漸在集體文化歷史所提供的個體范例中得到了安放,并在共時和同感的友愛的感召下融入“大寫的我們”。他們逐漸堅信東北工業的輝煌歷史對當下東北發展產生的互文性影響,堅信東北將會在對歷史的回望中找到未來發展的方向,并以強烈的文化自信心和工業奮斗精神對抗現有的社會焦慮和危機,主動承擔起城市復興的重任。
然而,這種新的社會記憶的形成、傳播和再造過程的技術邏輯體現出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路徑值得深究——原因在于假象領域在“塑造自己整個環境的社會”①[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3頁。的過程中,也在不斷“發展出了定形自己真實領土的特殊技術”,也就是說每種意識形態最后都鍛造形成了物理空間上的真實領土形態。麥克盧漢和鮑德里亞預言中的仿真社會正在逐步成型,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之間的界線逐漸消解,人們需要時刻警惕軟性的、無形的社會控制,積極應對斯蒂格勒所指出的超工業化時代所出現的困境。比如要對象征符號的流通過程進行把控,警惕“象征的貧困”困境。要認識到,東北工業文創在呈現上越是聚焦于當代社會需求和消費者喜好,越是依賴對其他城市傳播模式的僵化學習,就越是容易忽略自己文化本身的存在和特點,失去自身獨特的突破出口,最終在文創大潮中 “泯然眾人”。正如《景觀社會》中,居伊·德波寫道:“他越是凝視,他看到的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認自己處于需求的主導圖像中,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再如個體要時刻保持主動性,在真實的歷史記憶和工業精神上營造友愛和同感,與消費主義驅動下的個體化喪失區別開來。最重要的是,要持續對人與技術關系進行深層思考,不斷創新東北工業文創的媒介技術呈現,推動建設新型的社會文化景觀,平衡人與技術的共生關系,在新的技術時代構建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