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聊天惹的禍
陳思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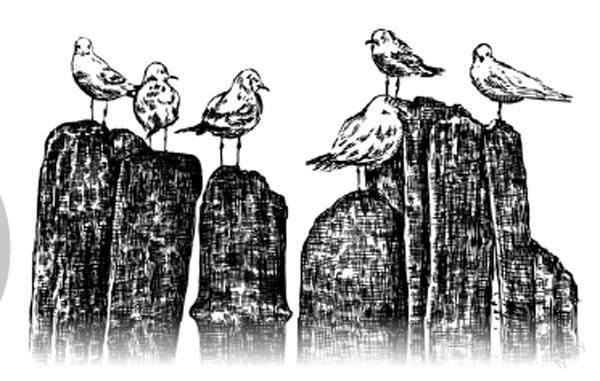
魏晉那些名士那么愛聊天,這事情我一直挺羨慕的。我師兄有文化,他說:政治高壓之下,佛教傳入又激發了許多人的宇宙與生命意識,所以語言覺醒了,名士們用舌尖的快感掩蓋生命的疼痛——他這話太有文化,我也半懂不懂。反正看《世說新語》里一大堆人,都能靠聊天成為偶像、明星,我的感受就是兩個字,羨慕。
比如有個叫支遁的和尚,經常在他寺里坐而論道,每次都能吸引百來個聽眾,個個結舌注目,全聽呆了。支遁談完了,人們就讓他簽名。有人從很遠的地方來,就為了親自看上清談家一眼。注意,愛聊天,也是可以稱之為“家”的:“清談家”。
還有一個叫王平子,聊天聊得好,但人很傲慢,不把別人放在眼里,唯獨看得起另一個人,叫衛玠,因為衛玠更能聊。王平子每次聽衛玠聊玄理,聽到要妙處就要激動得倒在座位上起不來,就像暈死過去那樣。現在我們在網上動不動就說“倒”,大概就是從那里來的。有一次,王平子聽衛玠聊天,倒了三次,就出來了一個成語:衛君論道,平子三倒。
有一個叫許詢(許玄度)的,他自認為“聊遍天下無敵手”,偏偏有人拿他跟另一個清談家王荀子相比,他很不服氣,找了個大家都在場的機會,與王荀子辯論起來。終于王荀子大敗,但許詢又強行掉轉正反雙方,即王荀子用剛才自己的觀點,自己用王荀子的觀點,重新開辯。王荀子再敗,許詢這才罷休。
這個辯論狂許詢,使劉尹說出“清風朗月,輒思玄度”的名言——每當清風朗月好天氣,劉尹就嘴皮子發癢,想和許玄度聊天了。
不過,這些清談家可能有點窮,因為他們有時候要“捫虱而談”。不扯遠了,我只是想說,聊天,也是我們的文化傳統。《西游記》里,有幾個妖怪,因為愛聊天,丟了命。
春天就是一種酶
那幾個是荊棘嶺上的十八公等四人。十八公是松樹,孤直公乃柏樹,凌空子乃檜樹,拂云叟是竹竿。當時,唐僧路過荊棘嶺時,正是春天。
春天是一個特別讓人想聊天和抒情的季節。冰雪初融,泥土芬芳,空氣里有蠢蠢欲動的味道。激動的心情看似不明來由,細細體味,方知季節是一個契機。季節的交替像一個伸展的姿勢,生命里的很多褶皺瞬間展現,讓人想起很多事情。在這樣的時節,因為內心激情鼓漲,所以會特別想和人說話,特別想做一件可以抒發情懷的事。
何況春天的荊棘嶺,又格外生機勃發:“匝地遠天,凝煙帶雨,夾道柔茵亂,漫山翠蓋張,密密搓搓初發葉,攀攀扯扯正芬芳。”大自然的每個物事,都在抒情,十八公他們想找人來談詩說禪,實在是太好理解不過。
也怪唐僧長得太像一個詩人了,正想找人吟詩作對的十八公,便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將長老攝將起去。他這行為有點突兀,其實十八公本人很紳士,完全沒必要搞得像搶人質似的。我的理解是:唐僧三個徒弟,長得呢鬼斧神工,言談呢粗魯火爆,夏蟲不可語冰,十八公實在不想惹他們,只好強搶了。
將唐僧攝到一座煙霞石屋后,十八公盡顯紳士本性,攜手相攙,告明來由:“圣僧莫怕,我等不是歹人……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一向聞知圣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遇。如果不吝珠玉,寬坐敘懷,足見禪機真派。”
唐僧也“定性”了,平靜一看,只覺月明星朗,果然是個談禪論道的好地方。
這是一場清談聚會,與會的還有另外幾位,一個霜姿豐采,號孤直公。一個綠鬢婆裟,稱凌空子。一個虛心黛色,叫拂云叟。
這幾位在禪理上很有悟性!比如拂云叟,就與唐僧擦出了思想火花,聲稱:“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也。……道也者,本安中國,反來求證西方。空費了草鞋,不知尋個什么?石獅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似我荊棘嶺葛藤謎語,蘿蓏渾言。……”
這一段,是《西游記》里頗值得咂摸的一段言論。比之魏晉前輩,拂云叟也是頗得精髓、毫無疑問的一個清談家,不知唐僧以后的取經路上,會不會說出“清風朗月,輒思拂云”的名言。
詩歌沙龍開始了
談完了禪理,又開始吟詩。由唐僧起句:禪心似月迥無塵。這個晚上的唐僧,自我感覺相當良好,“談禪說法,慨然不懼,聯詩起句,情趣盎然”。我們見慣了唐僧的乏味嘴臉,在這一章里,眼見著他從容對答,口吐錦句,倒覺得不認識了。
難怪杏仙姑娘漸有見愛之心!杏仙姑娘也許是在門外悄悄聽了很久了。唐僧顏值高,錦心繡口,所以,這春風沉醉的晚上,四老抒情,杏仙發情,在所難免。抒情和發情,本就是很相近的事物。
如此氛圍,倒與醉酒有點相似。杏仙在酒精作用下,大膽表白:“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耍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等四人,則在酒精的作用下,也開始哄哄抬抬,說杏仙有仰高之情,圣僧不妨就來個俯就之意。
這本是一場心無城府的詩會,一場應景而生的游戲。想想那些聊天盛會,文人雅集,哪一個不是到了后面,總要催生一點不相干的花邊或者樂子來?尤其,又是詩歌,又是酒精,又是春夜,都是一些讓人興奮的“酶”啊。
荊棘嶺上這幾位雅士,也并沒有像蝎子精或者白鼠精那樣把唐僧強行劫入,而是非常斯文地表態:“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茍且行事。……果是杏仙有意,可叫拂云叟與十八公作媒,我與凌空子保親,成此姻眷,何不美哉!”
可惜唐僧實在沒什么風度,適才還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意思,現在突然就勃然變色,翻臉不認人地跳起來高叫道:“汝等皆是一類邪物!這般誘我!當時只以砥礪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么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
禍從中來
看到唐僧這樣反應過度,難免很同情十八公他們了。
本來只是聊聊天,充當月老也是隨興而起的,怎么的,在唐僧眼里,倒成了設的美人局?
果然,他們見三藏發怒,一個個咬指擔驚,再不復言——“咬指擔驚”這四字真是太萌了吧?
唐僧在別的場合遇到妖怪,每每都是“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墜下淚來”,這一次見到十八公、杏仙這幾個妖邪,他卻十分伶牙俐齒。我想這一是因為剛才那一通吟風弄月鍛煉了口舌,二來唐僧是個欺弱怕強的主,他看得出來,十八公這幾位,文弱風雅,沒啥殺傷力的。
所以我若在場,也許是那個赤身鬼使——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這和尚好不識抬舉!我這姐姐,哪兒不好?她人才俊雅,玉質嬌姿,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才,也配得上你。”
到了這時,這幾位風雅的妖精就迎來了他們的悲劇了。
孫悟空幾人喊一聲師父,那諸公與鬼使、女子和女童,消失了個干干凈凈。定睛一看,原地只留下松樹、柏樹、檜樹、竹竿、杏樹、楓樹各一棵。豬八戒一頓釘鈀,連拱帶鋤,將它們全連根揮倒在地,果然根下俱鮮血淋漓。
看到這里,想到剛才笑語陣陣,只覺十分殘忍。
(葡萄摘自上海文藝出版社《一走就是幾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