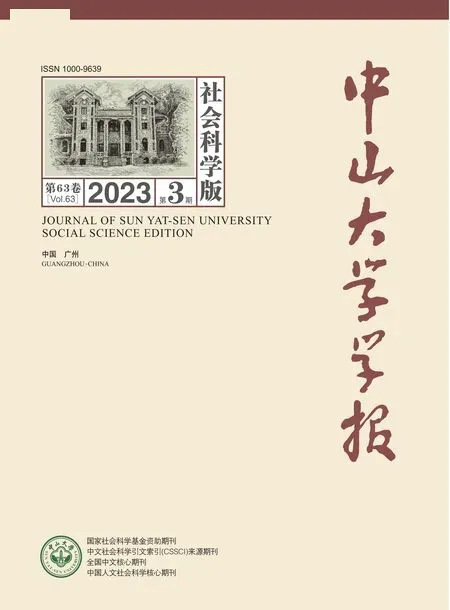互利與共生:北宋時期的杭州佛教與地方社會 *
王菲菲
關于宋代佛教的發展,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學界一般將其視為中國佛教發展的衰落期①Arthur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86-107; 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389-408.。然而進入到本世紀后,這一觀點逐漸受到質疑,有些學者甚至提出,宋代佛教的發展并非處于下降或者衰落階段,相反,其或可稱為整個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期②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Getz ed.,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pp.1-20.。只是其發展形態與前代較為不同,尤其是呈現出了明顯的世俗化傾向③游彪:《宋代寺院經濟史稿》,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1—29 頁。劉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與平民化》,《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2 期;Mark Halperin, Out of the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61-65.。因此,自宋代以后,佛教的發展深刻地融入進了世俗社會,尤其是在地方社會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那么關于宋代佛教的考察,從社會史的視角,有關其與地方社會尤其是與世俗政權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成為對宋代佛教進行全面認識的重要課題④李四龍:《美國的中國佛教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關于杭州佛教的發展,最早要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發展起來。進入北宋以后,由于未受戰爭的侵擾,以及宋初統治者在佛教政策上相對寬容的態度⑤汪圣鐸:《宋代政教關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頁。,杭州佛教事實上呈現出了持續發展的狀態,尤其是吳越時期在地方社會里形成的重要影響力得以延續下來。那么對于新政權而言,如何能夠有效地將其納入到北宋的統治之下,也成為對杭州社會施行有效統治的重要問題,尤其是在各種社會力量對比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其與地方政權之間形成了怎樣的互動關系,對此值得做出細致的探討。
關于宋代杭州佛教的相關討論,在現有的研究中對這一層面問題進行探討的,有《宋代杭州佛教與世俗社會關系研究》一文①張祝平、任偉瑋:《宋代杭州佛教與世俗社會關系研究》,《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該文主要是從世俗化的角度探討了杭州佛教與世俗社會之間尤其是在文化層面上的相互影響。另外的主要研究則是黃啟江關于北宋時期杭州僧人與精英關系的探討,他主要是以北宋時期杭州的幾位重要僧人與部分士人之間的關系展開討論,論述了二者之間由于利益趨同而形成的友好關系②Chi-Chiang Huang, “Elite and Clergy in Northern Sung Hang-chou: A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in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Getz, ed., Buddhism in the Sung, pp.295-339.。因此,學界現有關于北宋杭州佛教與地方社會問題的探討相對有限,已有的研究或從文化融合,或從個別群體關系的視角加以討論。但對于杭州佛教由五代入宋以后,其與地方社會尤其是地方政權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整體互動關系,尚存在一定的討論空間,此即本文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一、北宋杭州佛教與地方政權
自佛教傳入中土以來,隨著其勢力的不斷壯大,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也逐漸形成,僧官制度最早起始于東晉,發展至宋代則進入了一個新時期③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4,4頁。。在制度設置上,宋代的僧官制度大部分因襲唐制,與之前的朝代相比,并未有較大出入。而所謂的“新時期”體現在哪里,這就涉及到至關重要的一點,即關于制度的具體實施狀況。白文固、謝重光在對宋代僧官制度考察后,認為宋代僧官的主要特點是世俗政權更多地插手僧務管理,政府部門兼管僧籍、度牒等眾多佛教事務,僧錄司只管具體的宗教活動④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4,4頁。。游彪也曾論道:“入宋以后,封建政府加強了政府對寺廟的管理,僧侶政治方面的特權受到很大限制……將寺院、僧侶納入世俗化管理的軌道,從而加強了世俗力量對佛教寺院的控制。”⑤游彪:《宋代寺院經濟史稿》,第2頁。可見,宋代的佛教主要是在世俗政權的管理之下,僧官系統事實上并未真正地發揮作用。關于這一點,早在元明時期就有一定的認識:
馬端臨考無所謂僧道官。考《宋史》,僧志言等,道賀蘭棲真等,見方伎傳,非官也。職官志有云:“舊制,五岳、四瀆、東海、南海諸廟各置令、丞。廟之政令多統于本縣。命京朝知縣者稱管勾廟事,或以令、錄老耄不治者為廟令,判、司、簿、尉為廟簿,掌葺治修飾之事。”似近于今神樂觀之提點知觀,然非僧道也。⑥(清)嵇璜、(清)曹仁虎等撰:《續文獻通考》卷61《職官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75頁。
元人在編纂《宋史》時,就未將僧道官視為“官”,相關事宜多劃入方伎之列,在職官志中,也強調廟之政事多由地方世俗官負責。因此,在宋代隨著佛教世俗化的發展,地方世俗政權才是在佛教管理問題上發揮主要作用的力量,然而這種狀態尤其是在宋代建立之初事實上經歷了一定的權力滲入過程,有關于此,在杭州佛教的發展中體現較為明顯。
隨著吳越之地被劃入北宋政權,佛教也自然隨之被納入到北宋統治之下。在朝代變遷之際,北宋政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通過賜額制度將杭州佛教納入到新的行政管理體系中。合法寺院的概念在隋唐時期已經出現,據統計宋代有賜額的合法寺院數量規模較大,比隋唐五代幾乎擴大十倍左右⑦[日]高雄義堅:《宋代仏教史の研究》,京都:百華苑,昭和五十年(1975),第59頁;王仲堯:《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37頁。。鑒于兩朝在賜額制度上的差異,這種數量上的對比,不能作為佛教發展興盛程度的參照。但是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宋代擴大了賜額的范圍,將更多的寺院納入了行政管理體系中,相對之前的朝代,在形式上增強了國家政權對佛教的控制。另外,這種改變也說明了,在佛教的管理問題上開始出現了向微觀領域轉移的趨向,寺院逐漸成為佛教管理的基本單位,這是入宋以后的一個顯著特點。杭州大部分的佛寺,無論是賜額還是改額,確實大都發生在宋代,尤其是北宋①(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76—85,《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4040—4157 頁;王仲堯:《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上,第142頁。。其中真宗大中祥符和英宗治平年間是兩個較為突出的時期,“當是時,吳中浮屠居雖百千數,無是倫者。大中祥符間,例易天下寺名”②(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3《寺觀九》,第4128,4129頁。,“英宗即位,例更天下寺名”③(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3《寺觀九》,第4128,4129頁。。 可見在寺院賜額方面,真宗和英宗時期做過全國性的調整④汪圣鐸:《宋代政教關系研究》,第510—534頁。。杭州寺院在歷經這兩個時期后,基本都獲得了合法的賜額,正式納入到了宋王朝的行政管理體系中,各個寺院成為佛教管理的重點,地方世俗政權也成為關系杭州佛教發展利益最主要的力量。
通過賜額形式將寺院納入行政體系,僅僅是宋廷施行對佛教管理的第一步,有賜額的寺院在形式上受政權的保護,但并不說明國家權力在管理上的完全滲入。對佛教的實際管理,更重要的是對寺院內部的管理,因此關于寺主的任命變得尤為重要。北宋時期,很多寺院在選擇寺主的問題上,主要采取師徒傳承的形式。如在凈慈寺,“圓照禪師住杭之凈慈,招師居上座,別開講席,助誘方來之士,戶外之屨滿矣。圓照退居,師繼之。韓康公絳奏號法涌大師”⑤(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70《人物十一》,第3989頁。。最初由圓照宗本任寺主,在其退居之后,由其門人善本大通繼之,在當時被稱為“大小本也”⑥(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19,《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7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374頁。。再如龍井延恩衍慶院,在辯才法師退居龍井以后,“主者不堪其居,愿人為代以舍去。于是請師徒弟懷益主奉香火,汲巾侍瓶,甲乙相承,以嚴佛事”⑦(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78《寺觀四》,第4067頁。。在寺主的選擇上,也是尊奉甲乙子孫制度。北宋時期諸如此類的現象十分常見,很多寺主的位置均由本支系同門兄弟或弟子繼承,因此甲乙制寺院所占比例較大⑧劉長東:《論宋代的甲乙與十方寺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1 期;汪圣鐸:《宋代政教關系研究》,第482—484頁。。
但與此同時,在北宋時期,杭州也出現了一些十方制寺院。所謂的十方選賢制最起始是一種在禪宗叢林中發展出的民間制度文化,相較師徒傳承制,關于寺主的選舉更加公正,原則上主要通過“期集公舉”的形式公舉選任⑨王仲堯:《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上,第203—216頁。。下竺靈山教寺即為十方寺院,天禧四年(1020),王欽若判杭州,奏請朝廷復天竺寺舊額,在遵式的主持下,天竺寺改制為十方講院。其后遵式在天圣八年(1030)還制定了《天竺寺十方住持儀》的規章,主要是對法主的德學要求、寺院的管理模式等制度性規范⑩(宋)釋遵式撰,(宋)釋慧觀編:《天竺別集》下,《卍續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306—307頁。。遵式的這一規制主要是站在佛教發展的立場,力圖規范寺院的管理,能夠讓德學兼備的人主持寺院,因此提高了對法主在德行上的要求以及僧眾對其的監督,但是在寺主選任上沒有嚴格地限制祖師之約的形式。在天圣九年(1031),遵式:
因與眾訣曰:“我住臺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爐拂,勿為最后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賓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領之草堂。?(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208頁。
遵式在住臺杭兩地時,“長用十方為意”,但是在最終退居后,是將席位傳給弟子祖韶延續護持佛法。因此遵式在天竺寺的十方體制改革,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以至于在其后的寺主選任上還是沒有跳出師徒相傳的模式。祖韶之后,天竺寺傳至海月大師慧辯:
晨起盥潔,謝眾趺坐而寂。杭州通守蘇軾吊以三詩,序而贊之。辯之后慧凈大師思義,義有四弟子:德賢、仲元、永湛、慧日,皆相踵主法。元之弟子曰慈明大師慧觀,又繼日師住持。①(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卷4,《大正藏》,第873頁。
在慧辯之后,由其師弟思義繼承席位,思義之后又由其四弟子相繼主法,慧日之后又傳到仲元的弟子慧觀。可見,改制后的天竺寺在寺主的席位上基本還是沿用法系內師徒傳承的形式。
至此可知,在北宋杭州,部分僧人出于佛教發展的考慮,希望獲得有德行的高僧主持寺院,主動進行了一定的規范,但在具體的實踐中成效有限。但是這種趨向卻受到了官方的關注和支持,因此出現了在官方帶領下進行改革的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蘇軾守杭時在徑山寺的改革: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后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于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眾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②(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72《維琳》,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00頁。
關于徑山寺的住持選任,徑山祖師曾有規定,只遵循甲乙子孫繼承制度。但是蘇軾為了選用有德之人,強行廢除祖師之約,以長老維琳為徑山第一代住持,后來招來很多不滿,但是最終還是改徑山寺為十方住持制。蘇軾在徑山寺的強行改制,相對以上所論的寺院改制情況有所不同,明確提出要廢除甲乙子孫制,改革比較徹底。二者除了在“選用有德”這一改制目的上相同外,在官方推動下的改革,還包含了另外一層考慮。甲乙師徒繼承制下的寺院相對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寺主基本在法系內部傳承,外部勢力難以進入。而對于十方住持制,在新寺主的任命上,官方權力更容易介入,這可能是官方對于十方改制較為支持并且積極推進的主要原因。
因為在北宋時期,通過賜額制度將大小寺院都納入行政體系后,官方已經意識到了加強對各個寺院的管理變得十分重要,就算一些沒有改制的寺院,也受到世俗政權很大的影響。例如關于靈隱寺寺主普慈大師的任命,在《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中記載:
其后,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眾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發鄙悋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李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③(宋)釋契嵩:《鐔津文集》卷15,《四部叢刊》三編第61冊,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葉15b—16a。
在惠照謝世后,曾遺書將寺主傳于普慈,但是官方對此有異議,更命他師主寺。最終普慈法師是在其他知府李兌、孫沔的影響下,相繼主上天竺寺以及靈隱寺的。自此可以明顯看出,部分寺院尤其是影響較大的寺院,雖然秉持法系內部相傳的舊制,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會受到官方介入的影響。這也促使有些僧人會勾結官員搶奪職位,例如《龍井辯才法師塔碑》記載:
(熙寧初)祖公無擇在杭,言者不悅其政,逮制獄。師以鑄鐘事與連,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篦》,撰《圓事理脫》。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于下天竺。
師恬不為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為逐師于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④(宋)蘇轍撰,陳宏天、高秀芳點校:《欒城后集》卷24,《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43頁。
辯才法師主上天竺時,有僧文捷勾結權貴動用轉運使,奪取了辯才的職位,將其遷于下天竺,后又被逐至于潛,最后在文捷敗事以后,才得以又返回上天竺。
通過以上的梳理可知,北宋在杭州寺院的管理上關于寺主的選任,在整體上以甲乙子孫繼承制為主,但是已經開始出現了向十方住持制轉變的趨勢,并且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宋廷對寺院的管理有所加強,在一些未改制的寺院里,官方權力也有明顯的介入。但是這里官方的力量,不是來自僧官而是俗官系統人員。如以上提到的辯才法師,先是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并且為其“請錫紫衣辯才之號”。后翰林沈遘撫杭,“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熙寧六年(1073),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①(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11,第211,210,210頁。。在辯才的歷次遷轉中,均是受杭州地方官之請。關于洪壽禪師對壽寧寺的住持,“御史中丞王公隨,時鎮錢塘,慕師道化,嘗往湖上,去騶從,獨步往詣之。天圣初,以鄰寺壽寧虛席,請師補處”②(清)釋際祥輯:《凈慈寺志》卷8《住持一》,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匯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第519頁。。也是在杭守的作用下補缺。更有甚者,杭州守臣還成為寺院與他州爭奪禪師的主要參與者:
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堅請,欲往而蘇人留之益甚。又以凈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于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剎,請擇居之,迎者千余人,曰:“始借吾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③(宋)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14,《卍續藏經》,第521頁。
神宗年間,杭守陳襄奏請瑞光宗本禪師主凈慈寺,從蘇州寺院借師三年,但是九年之后仍未歸還,在蘇人來杭請師時,杭守動用縣尉加以防護。可見,在北宋大部分參與寺院事務管理的都是杭州世俗地方官。
在佛教的管理上,部分僧官也會發揮一定的作用。如海月法師慧辯,“師既蒞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即捐日會諸剎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設棘圍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后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④(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11,第211,210,210頁。慧辯職為都僧正,其在試經選任寺主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關于都僧正的設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蘇軾對此問題曾作出過相關評論: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于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賬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眾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⑤(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22《海月辯公真贊》,第638頁。
在杭州的地方僧官系統中,除了僧正及副僧正外,又別設都僧正一職,負責“總領要略”,事實上很多人都不屑為之,而僧正副以下也多只負責“簿賬案牒”之事。可見,當時僧官的作用確實較為有限。更重要的是,僧官的任命權也掌握在世俗地方官的手中,“翰林沈遘,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師從容如平生,遘異之,任以都僧正”⑥(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11,第211,210,210頁。,海月之職位是杭守沈遘任命的。因此在杭州寺院的整體管理上,關于官方力量的介入,發揮主要作用的不是僧官系統人員,而是世俗地方官,他們才是掌握主要權力的群體。
綜上所論,在朝代變遷之際,北宋政權通過擴大賜額的方式,首先在形式上將杭州寺院納入到新的行政管理體系中,之后又加強了對各個寺院的管理。在寺主選舉的問題上,杭州寺院大部分采取師徒繼承的形式,但是后來逐漸出現了向十方住持制轉變的趨勢。并且這種方式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借此加強了官方力量在佛教事務管理上的參與。然而這里所謂的官方,主要指代杭州地方世俗政權,相對而言,僧官系統所發揮的作用較小。因此,在北宋時期,在佛教整體世俗化發展的趨勢下,杭州佛教逐漸被納入到了地方世俗政權的管理之下,杭州地方官也成為關涉到佛教發展利益的重要群體。有關于此,還進一步地體現在其與地方公共事務的關系問題上。
二、北宋杭州佛教與地方公共事務
如前所論,關于杭州佛教的發展,在北宋時期基本承繼了吳越階段的狀態,這也促使其在杭州政治地位轉變的情況下,在地方社會里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并且發展為重要的地方勢力。北宋建立以后,杭州地方政權不僅在政策管理上逐漸滲入到對佛教的控制,作為一種重要的地方資源,佛教也成為政權加以利用的主要對象,致使其在地方公共事務中成為發揮主要作用的力量。在此過程中,佛教勢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強化。
北宋時期的杭州佛教,在部分公共事業活動中的參與十分主動,例如在咸平三年(1000)左右,江南之地災荒,知泰州田錫上疏:
今月十二日,有杭州差人赍牒泰州會問公事,臣問彼處米價,每升六十五文足,彼中難得錢。又問疾疫死者多少人,稱餓死者不少,無人收拾,溝渠中皆是死人,卻有一僧收拾埋葬,有一千人作一坑處,有五百人作一窖處。①(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6,咸平三年三月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3頁。
從田錫與杭人的對話中可知,杭州在疾疫中死者無數,無人負責,但卻有一僧人獻身收拾埋葬,為地方公益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另外,在部分公共設施的修建上,也有一些僧人的參與,例如關于北關中興永安橋,就是由“僧舜欽募緣成之”②(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21《疆域六》,第3567頁。。除此之外,地方動亂也是寺僧發揮作用的時期,北宋對杭州影響較大的要屬方臘之亂。“宣和盜起,清溪所至,無噍類犯錢唐[塘],告渠魁曰:‘愿以一身代滿城命’,賊鋒為戢。”③(宋)釋宗鑒:《釋門正統》卷7,《卍續藏經》,第891頁。妙行寺思凈在方臘進入以后,愿以己身代一城之命,賊人受到誠心感動而退,之后他又聚遺骸大作佛事,為死者修建墳塋。藉此可知,杭州很多僧人都曾積極地參與到地方公共事業中,僧人群體在杭州屬于重要的社會力量,為地方公共事務做出過重要貢獻。而他們在這一層面上的潛力,也被地方官充分利用起來,北宋時期很多佛教對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都是在地方官的指導下所進行。
杭州佛教在地方官指導下所參與的公共事業較多,但主要集中于兩類事務中。首先,就是關于河湖治理以及部分公共設施的修建。杭州河湖眾多,江潮問題是一大憂患,早在吳越時期,錢氏就曾利用浮屠進行治理。到了北宋,有些地方官也效仿利用建塔的方式治理河湖,蘇軾守杭,“留意西湖,極力濬復,于湖中立塔以為標表,著令塔以內不許侵為菱灣。舊有石塔三,土人呼為三塔基”,“舊湖心寺外,三塔鼎立。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故建浮屠以鎮之”④(清)釋際祥輯:《凈慈寺志》卷24《外紀二》,第1598頁。。蘇軾在西湖中建塔,一方面是以塔為標,另一方面就是用以鎮三潭。佛塔的建設,有利于佛教的發展,但是更潛在的目的是服務地方社會。
關于西湖的相關治理,歷任地方官都付出過努力,但蘇軾的貢獻最大,并且他十分善于利用佛教資源處理地方事務。除了潭水問題外,西湖還經常淤塞,“宋初,湖漸淤壅”,景德四年(1007),“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規占者,已去其半”⑤(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1《西湖總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頁。。后在天禧三年(1019),“國家每以歲時,祈乃民福。星軺至止,精設于蘭場;羽服陳儀,恭投于龍簡。愿禁采捕,仍以放生池名為請”⑥(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33《山川十二》,第3661頁。。王欽若受杭州僧人的影響,以祝延圣壽之說,奏請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民采捕,自是之后湖葑益塞。元祐五年(1090)蘇軾守郡上言:
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圣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于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⑦(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30《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第865頁。
在此次上書中,蘇軾陳述了五點理由以示西湖不能廢置,并且在哲宗已經特賜度牒的情況下,要求再賜百道才可濟事,以完成對西湖的治理。在此蘇軾利用度牒治理西湖,一方面可以促進佛教的發展,同時也可利用度牒進行募役完成治理。其關于蘇公堤的建設,也是靠度牒募役:
以余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余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①(元)脫脫:《宋史》卷338《蘇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813頁。
在西湖的治理中,除了湖水外,還會涉及到一些附近河水的通暢,以及井、堤的建設問題。蘇公堤的建造,是蘇軾利用救荒余錢以及所請度牒完成。
那么關于六井的重修,在《六井記》中記載,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皆廢壞,熙寧五年(1072)秋:
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于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余人。②(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11,第379頁。
陳公即知州陳襄,在重修六井時,其選差僧人董治其事,共有二十多人出力,可見關于六井的修建都是在僧人的支持下完成。當時蘇軾為通判,“親見其事”。后經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在《乞子珪師號狀》中記載:
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于六井中控引余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③(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31,第902頁。
在陳襄修井之后,歷經十八年蘇軾知杭州,沈公井枯涸,于是蘇軾尋訪熙寧中修井四僧,但是三人已亡,只有子珪師健在。其在六井上新創二井,最終在子珪的二次修復下,“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若非子珪心力才干,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④(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31,第902頁。。因此,蘇軾基于子珪在兩次修井中的重要貢獻,向朝廷為其申請師號以作嘉獎。在此過程中,地方官與僧人之間,事實上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合作,僧人在地方事業上的貢獻也使佛教獲得了一定的利益。
在利用佛教資源處理地方事務時,除了河湖治理方面,蘇軾在廨宇的修建中也曾借用佛教資源,例如《乞賜度牒修廨宇狀》載:
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復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余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后百余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系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余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刬刷兵匠應副去訖。⑤(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29,第842—843頁。
在元祐四年(1089),蘇軾上書,錢氏當國,官屋皆珍材巨木,入宋之后,官司無力修換,日就頹毀。其在熙寧通判杭州時,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力圖在此次守杭中加以修復。因此向朝廷奏請,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公使錢五百貫。在此廨宇的修建中,同樣也是利用度牒解決問題。可見,蘇軾確實比較善于利用佛教資源治理地方事務,杭州佛教在北宋取得的發展,應該有他一定的功勞。
其次,杭州佛教在地方官指導下對地方事務的參與,在公益賑災、救荒、救濟事業方面也有很多貢獻。最明顯的一個例子發生在范仲淹領浙西時,皇祐二年(1050),“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乃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⑥(宋)沈括撰,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卷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9頁。。在吳中出現饑荒時,范仲淹利用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的特點,鼓勵民眾宴游。
同時:
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以發有余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①(宋)沈括撰,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卷11,第419頁。
他還召諸寺主,鼓勵他們大興土木建設,于是很多佛寺在此時得以重修。范仲淹的這一舉措受到監司的彈劾,認為其“不恤荒政”。但事實上他是利用大興建設的方法,帶動經濟發展,即用以工代賑的方式治理荒政,最終使得兩浙中唯杭州災情得以緩解。在此過程中,關于佛寺的修建,地方官事實上并未直接從人力或物力上予以支持,很多寺院的興修都是靠僧人的力量。地方政權主要站在解決地方事務的角度,以兩全的方式對佛寺建設予以支持,二者之間形成的亦是合作與互利的關系。
相對而言,蘇軾在救荒的政策上,同樣是利用佛教資源,但慣用度牒解決問題,“杭州適值歲旱,公請于朝,免上供米三之一,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明年,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厄。又為湯劑治病,活者甚眾”②(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25,《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8冊,第630頁。。在蘇軾知杭時,遇到杭州大旱,他一方面通過奏請免上供米和糶常平米的方式救災,同時還以度牒易米的善策解決災荒。除此之外,他還創設養濟院、漏澤園,用以賑濟災貧,“先是,守蘇文忠公嘗于城中創置病坊,名曰安樂,以僧主之。仍請于朝,三年醫愈千人,乞賜紫衣并度牒一道。詔從之”。在元祐年間,蘇軾創設病坊,以僧人負責,同時替僧人向朝廷奏請賜封。關于漏澤園,崇寧三年(1104)二月,“詔諸州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槥櫝之無主者,若暴露遺骸,悉瘞其中”③(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8《恤民祥異》,第4174—4175頁。。在漏澤園設立以前,很多暴露遺骸也均由寺院處理。可見,佛教在北宋賑災、救濟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在旱澇災荒年間,佛寺還擔任著祈晴、祈雨的責任,很多都是在地方官的帶動下進行。如無相寺,熙寧七年(1074),“久旱,郡守沈起禱之,至晚大雨”④(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77《寺觀三》,第4052頁。。蘇軾在杭時,也曾多次到寺院祈雨、祈晴,“立秋日禱雨,宿靈隱”⑤(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0《寺觀六》,第4087,4093,4094,4094頁。,其曾與周、徐二縣令一起祈雨,并宿于靈隱寺。由于觀音大士在祈雨方面的靈驗,上天竺是進行祈雨活動最多的寺院。最早的即郡守張去華所進行的祈雨活動,“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禱,即日雨,自是遇水旱必謁焉”⑥(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0《寺觀六》,第4087,4093,4094,4094頁。。在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便率僚屬將大士迎至城內寺院進行祈禱,自是有禱輒應。另外,《靈感觀音碑記》記載:
(紹圣二年)臣自去秋視事,民方薦饑,今年春、夏,雨彌月不止,吳興苦卑,連歲水災,父老日夜憂懼。臣即率官屬躬禱像下,沖雨入山,衣帽沾濕,渠決壞道,從者皆涉。比臣之還,天宇開霽,纖云不興,白日正中,清風穆然,邦人合爪嘆息。既又輿致城中作佛事,與民祈禳。已而雨旸有時,農不告病,稼穡旆旆,遂為豐年。實茲像之庇此土也,所不可忘。⑦(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0《寺觀六》,第4087,4093,4094,4094頁。
陳軒守錢塘時,吳興遭受重大水災,于是其也率領眾官在上天竺觀音大士像下祈禱,靈驗之后,又迎至城中作佛事,最終“雨旸有時,農不告病”。因此陳軒據此向朝廷奏請:
“臣不勝大愿,愿給祠部空名度僧牒數十道,貨緡錢,市材僦工,撤而新之,不唯俾東南之人永有瞻式,儻遇水旱禍災,吏不能力者,亦庶幾有所控告。臣皇恐以聞。”奏下尚書禮部,禮部則以敕令從事,許裒一路祠廟施利以充其費。于是毗陵胡公宗哲、番陽張公綬,偕為轉運副使,特主其事,乃得錢五百萬,民樂施者,又若千萬。⑧(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0《寺觀六》,第4087,4093,4094,4094頁。
陳軒奏請希望朝廷能夠給度牒數十道以及部分支持,用以重修上天竺。獲得準許后,禮部使胡宗哲、張綬為轉運副使,“特主其事”,經始幾年后,上天竺的重修之役得以告成。在上天竺的修建過程中,地方官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其之所以向朝廷奏請支持,是基于上天竺在祈雨祈晴造福杭州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范仲淹以工代賑事宜一樣,地方官對佛教的支持是站在服務地方社會的角度,與佛教建立起一種合作關系,此可謂杭州地方政權在佛教相關事務參與上的一個顯著特點。
綜上所論,杭州佛教在地方公共事務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關于河湖治理、公共設施的修建,還是救濟賑災,他們都是杭州地方公共事業建設中一個主要的群體。地方官們以直接請寺僧參與,或者間接奏請度牒等方式,利用佛教資源大力發展地方公共事業。在北宋的杭州,能否與僧人群體建立起良好的關系,基本上決定了地方官們是否能夠在地方社會有效地施行管理職責①Chi-Chiang Huang, “Elite and Clergy in Northern Sung Hang-chou: A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pp. 325-327,p.321.。在此過程中,地方政權通過對佛教資源的利用,一方面實現了對社會的治理,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佛教帶來了一定的利益。杭州佛教延續五代的發展,在北宋時期成為重要的地方勢力,因此其與官方之間基本形成了合作互利的關系。
結 語
自錢氏納土之后,杭州自吳越國國都轉為北宋兩浙西路之路治,成為州縣級的地方行政區域,這種政治地位上的轉換,給杭州社會帶來了一些深刻的改變。關于佛教的整體發展,在北宋時杭州基本延續了吳越國的繁榮狀態,并未受到嚴重破壞,甚至名僧輩出,成為11 世紀朝廷征僧入京最多的地區②Chi-Chiang Huang, “Elite and Clergy in Northern Sung Hang-chou: A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pp. 325-327,p.321.。因此,在吳越國發展的基礎上,北宋時期的杭州佛教在全國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在地方社會本身,隨著杭州政治地位的降低,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對比也隨之發生改變,佛教團體成為重要的地方勢力。
北宋政權建立以后,面對杭州社會的特殊發展狀態,其一方面通過賜額制度將大部分寺院納入宋廷的管理之下,同時加強對住持選任的干預,以及增強對僧官的管理等方式,加強了世俗政權對佛教的控制;另一方面,佛教勢力和資源也成為地方政權在地方社會發展中加以利用的主要對象。在北宋時期,僧人群體基本成為杭州公共事業的主要參與者,除了一小部分是佛教群體的主動行為外,大部分的參與都是在地方官的引領下所進行,其中包括河湖治理、廨宇修建,以及賑災、救濟等公共事務。同時,在此過程中,佛教也會獲得一定的田產、資金、度牒,或者師號的賜封等利益。因此,杭州地方政權一方面利用佛教資源和力量對地方社會進行治理、另一方面又通過給予佛教一定的利益與其建立起良好的關系,達到對地方勢力的控制。二者之間在北宋時期呈現出了特殊的互動關系,在合作互利的基礎上形成了共生。這一關系的形成,主要是受杭州佛教自吳越以來的發展地位,以及杭州特殊政治地位轉變的深刻影響。進入南宋以后,隨著高宗的南渡,杭州再次歷經了政治地位上的重大轉變,因此各方勢力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一定的變遷,佛教在都城政權的環境下,所譜寫的則是另外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