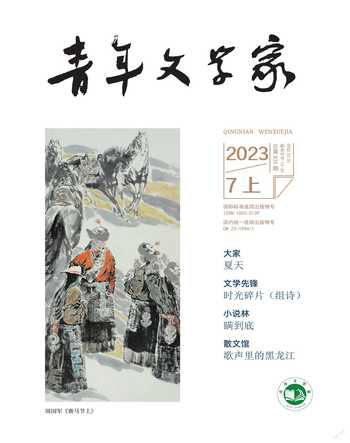父親治水
趙宏宇

父親病了,我與愛人匆匆趕回老家看望。曾經那么高大、偉岸的父親,如今卻病得臥床不起。我從小就怕父親,每次他回家,我都想藏起來,不敢見他。五十多年過去了,父親老了,病了,糊涂了。蜷曲著身體躺在床上的父親吃力地辨認著我,我的心里五味雜陳,不由得潸然淚下,一幕幕往事不斷地浮現在眼前……
1933年,父親出生于中條山東北麓絳縣的槐泉村。因家境貧寒、兄妹多,父親又排行老大,剛強的他,16歲便外出謀生。父親以工代干,因表現突出,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父親又先后任衛莊鄉團委書記,小河口水庫工程南樊團團長,紫家峪水庫、陳村峪水庫、里冊峪水庫工程總指揮,磨里公社黨委書記,絳縣水利局局長等職。
從不向困難低頭的父親,無論遇到什么困難,都會勇敢地面對。水庫工地上的民工都佩服地說:“趙團長是個正派、有能力、敢擔當的好領導!”1970年的春天,紫家峪水庫攔洪蓄水,水閘合不嚴,潛水工一次次地入水,又一次次地無功而返。眼見天色已晚,在場的父親心急如焚,猶豫片刻后竟脫掉棉衣,沿著水閘側壁下水。人們都清楚地知道,水閘下面暗流涌動,隨時都有被水沖走的危險,不要說一般的人,就是專業的潛水員也難免遭難。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大家焦急地望著水面,拼命地喊著“趙團長”……好一會兒,父親才艱難地從水里冒了出來。大家擁上去把他扶出水面,只見他嘴唇憋得紫青,哆哆嗦嗦地說:“落—閘!”多年后,父親談及此事時,我疑惑地問父親:“爸,當時您會水?”父親淡淡地說:“會狗刨。”“萬一被水流吸住,上不來咋辦?”我擔心地問道。“當時沒想那么多。”父親像個做了錯事的孩子,低著頭說。我又問:“閘門為啥合不嚴?”父親嘆了口氣說:“閘槽內有石頭,我把它清理了。”
以身作則、當機立斷的父親為絳縣的水利事業贏得了時間。1972年秋天,絳縣最大的里冊峪水庫工程開工建設,首先要將大壩的基礎挖至基巖層。當挖深接近十米時,基坑滲水不斷涌出,且水量隨著挖深還在增加,嚴重地影響了工程進度,傳統的長白班及手提肩背的運石方式已不適用。時至初冬,時間緊、任務重,且施工難度大,怎么辦?緊急關頭,父親立馬召開了現場班子會,果斷采取了措施,決定由長白班改為三班倒。大家邊挖掘邊抽水,將基坑內的碎石采用人傳人的運輸方式,各鄉鎮以兵團編制,兵團間開展施工進度打擂奪旗競賽。一時間,工地上晝夜通明、機聲隆隆、人頭攢動……在挖掘最難的時刻,父親常常站在冰冷的水里,帶著民工一起勞動,為民工鼓勁兒加油。清理壩基后,其最深處竟達三十二米,堪稱天坑。
做事認真負責、極富同情心的父親,在處理工地死傷事故時,費盡心思,一切從群眾利益出發,無論工地距傷者家有多遠,都親自登門撫慰,并從經濟上最大限度地給予補償。老百姓感慨地說:“還是趙團長算話!”
一心撲到工作上的父親很少回家,有時幾個月見不到一次,侍奉公婆、撫養孩子、務農養家的重擔就全部落在了母親的身上。兒時,我對父親的印象是模糊的、陌生的。當看到玩伴都有各自的父親陪伴時,總是跟奶奶討要父親。奶奶說:“你爸爸是吃公家飯的人,等你長高些他就回來了。”
大禹治水名垂千古,父親治水名揚古絳。父親治水十五年,親自指揮建設了三個水庫,真正實現了下游旱地變水田的愿景。“致廷俊同志:鑿山筑壩千秋業,造福于民水利人。”這是當時的縣長專門為父親題的詞。1974年,運城地委組織部還以《艱苦治水15年》為題撰寫文章,記載了父親興修水利、造福人民的事跡。
2021年秋,我陪同父親前往闊別四十多年的里冊峪水庫。父親先是沿大壩走了一圈兒,接著站在大壩中央,心情顯得很凝重,望著水源方向,久久不愿離去……
晚年的父親身體一天天地消瘦。住院期間,請的護工竟然認出了父親,激動地說:“趙團長還認識我嗎?我是水庫連部的,我的弟弟當過你的勤務員……”過后,護工告訴我,父親在水庫可有威望了,是響當當的一位人物,領導著來自全縣的兩千多人,在安全、衛生等方面都像軍營一樣井然有序。
幼年時,父親就是我仰慕的高山,至今我依然崇拜他。但是,我至今也未弄明白,為啥有那么多人愛戴父親,為啥調皮搗蛋的人都順從父親?也許是所謂的人格魅力,抑或其他原因吧。
我們常常為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驕傲和自豪,父親就是我們的福報,衷心地期盼父親早日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