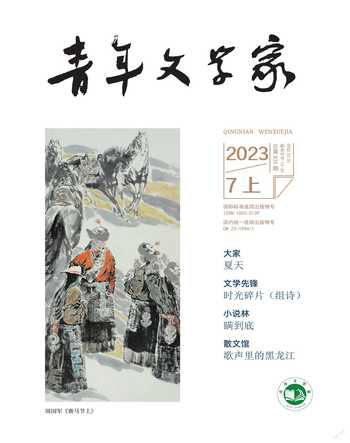瞞到底
麻靜雯
江上的小船悄然駛過,枯黃的盧葦凹陷成一個記憶的窩,像有人來過。邱伯尋著船的方向沿岸邊緩緩行走,他想象自己是一匹脫韁的野馬,可是那細碎倉促的步履,始終追不上破浪前行的船,漣漪朝他沖過來,泛起的浪花,白不過邱伯的頭發,只好緩緩退去。
邱伯睜開眼,原來是一場夢。他的右手被眼前的男人緊緊握著,男人的臉憋得通紅,雙眉擰成疙瘩,眼里泛著淚光,焦急而用力地喊道:“爸,爸,您醒了,您看看我……”
空氣凝成緊張的一團。邱伯呆望著他,沉浸在不知是夢里還是現實的記憶中。那江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等船駛遠了,江面才恢復平靜。邱伯停下來,就停在凹陷的盧葦旁邊,那里的空間似乎要大一些,正準備坐下,身后熟悉的聲音竟把他喊住了。
邱伯沒有轉過頭去看,離開太久,一定會有人找過來。他們小心翼翼地托舉著邱伯的手臂,輕聲說:“您猜誰來看您了?”
是男人來了,邱伯知道。每逢周末,便有人來看望他,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五六個年頭。
邱伯笑,念叨:“趕快回去。”
從岸邊往回走,踏上長長的臺階,靠江的漂亮房子是邱伯的居所。居所一邊望江,一邊望山,靠山的窗戶外面,景色常年沉浸在深邃的清幽里。邱伯說,山上連飛鳥的影子也看不見半只。山景看得久了,仿佛草木都已凝固,心跳也漸漸地沉寂下去,他才想到要去江邊聽一聽風聲。
“阿爸,下次出門讓他們陪著,您一個人我不放心。”男人放下手里的果籃,接過邱伯的手臂仔細挽著,嘴里絮絮叨叨地叮囑著,如同很久以前,邱伯一遍又一遍地叮囑兒子那般,顯得細心又貼心。邱伯自然很滿意。
那些身穿同樣制服的人,讓邱伯覺得無趣。他們總是在一旁忙忙碌碌,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吃穿用度不用邱伯自己操心,只要開口,就有人為他安排妥當。盡管如此,邱伯還是想往外走,他們便認為是否服務得不夠好。
“您在江邊看見什么有趣的事嗎?”他們同情而又關懷地看著患了健忘癥的邱伯,為他遞去一杯溫度剛好的茶水。
邱伯說:“江面上能看見鳥呢,比在房間里看見得多。”
窗外,空曠的天空里,只是些灰白迷蒙的云,云層缺處看得見半角藍天,光芒欲藏還露。這些年,邱伯多半是在等待中度過的,仿佛多看幾眼,太陽就能出來,也許再過幾年他真的會忘記發生過的事。但至少,邱伯此時清醒地記得,兒子在很遠的地方工作,邱伯沒有去過也去不了,忙碌的節奏使得兒子不能時刻陪伴,瞞著兒子安然無恙,一切才會叫人稱心如意。
男人察覺出邱伯有心事,小心翼翼地關懷著,要替老板盡全力哄邱伯開心。有人則在一旁附和著:“您兒子真是孝順,您老有福。”
邱伯對男人點點頭,嘴角擠出一抹淡淡的笑,緩緩地喝完手中的茶水。雖然男人很努力,但一點兒也不像兒子,邱伯心里明白,這個男人只是在演戲。邱伯極力配合著,生怕男人看穿自己假裝出來的健忘,只敢表現得愚鈍些。
天空越來越暗,暗得能望到漆黑的盡頭,窗外樹影的模樣也變得很奇怪。
當邱伯再次醒來,看見雙眼含淚的男人站在跟前。邱伯右手冰涼,不管男人怎么捂都溫暖不起來,身上插滿管子,竟說不出話。呼吸機一刻也不能停,否則會令邱伯窒息。
過了一會兒,邱伯察覺到疼痛,他卻逼迫自己朝男人擠出一個笑,極力用咽喉發出類似于“好”的聲音。邱伯心想,這個男人一定會向兒子匯報自己的情況,他要盡量裝得淡然一些。邱伯眼前的男人再也忍不住,心疼如刀絞,眼淚“唰”地一下掉了出來,沉重地砸在慘白的床單上。
邱伯感到身上一陣痛苦,于是,他緊閉雙眼盡量不想被看出來,再次陷入糊糊涂涂的狀態里去了。原來,邱伯已經不記得,眼前緊握他右手的可憐男人,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