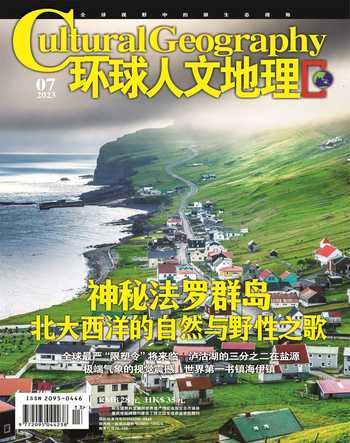蘇州評彈都市文化圈的形成
唐力行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建城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明清時期就已成為了稱雄天下的商業大都會,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評彈就是其中之一。
蘇州評彈由評話與彈詞兩個曲種組成,淵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義的蘇州評彈興起于明末清初,與蘇州市民社會的繁興同步。天下人無不樂居蘇州,致使這里人地矛盾日益尖銳,歷代統治者視蘇州為取之不竭的聚寶盆。這里的稅糧總數、田畝平均賦稅、人口平均賦稅不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十倍,也高出江南地區其他府縣。在重賦與人口雙重壓力下,蘇州人并不采取極端的行動,而是重理性、求變通,善于在夾縫中找到舒展自己才能的天地。為保障財賦收入,統治者對蘇州的控制十分嚴密,鄉紳、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隱心態濃重,轉而構筑私家園林,寄情于詩書歌吟之間。
清朝時期,蘇州狀元達26人,占全國的22.8%。經濟與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評彈與昆曲這對姐妹花。評彈有著雅俗共賞的特點,受眾遍及士農工商乃至販夫走卒。相應于蘇州人的性格,評彈弦索叮咚如江南之水。如果說評話像太湖般開闊澎湃,彈詞則似穿街越巷的小橋流水。水是最柔和的,也是最堅韌的。似水長流的評彈深藏著蘇州人的心態,流淌著蘇州人的心曲,敘說著蘇州人的機敏、睿智、沉穩和變通。進茶館品茗聽書成為蘇州市民的生活方式,而紳商官宦則把評彈藝人請進家門舉辦堂會。蘇州的大街小巷到處可以聽到悠悠的評彈音樂和聲如金石的評話,與小橋流水枕河粉墻融合成一幅有聲有色的蘇州圖景。
評彈從形成之初便走出蘇州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吳語地區擴散,這是由評彈的藝術形式和內涵所決定的。評彈藝人在一個地方演出,根據書目,演出周期少則十余天,多則數月。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口流動小,演畢就要變換場地,數年內不會再重復蒞臨——這就是評彈的走碼頭。“不過說書的走碼頭,僅是南抵嘉興,北達武進。以此一小小地域為限,因過遠之處聽不懂蘇白,去亦徒然。”蘇白就是蘇州話,也稱為吳語,主要通行于江蘇南部、上海、浙江,是除北方官話以外的第二大漢語方言。雖同處江南,但各地語言實際上仍有較大差別。傳統的吳語以蘇州話為代表方言,所以“南抵嘉興,北達武進”劃出了蘇州評彈都市文化圈的邊界。
江南水網密布,評彈藝人行裝簡單。評話藝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彈詞藝人則背一琵琶或弦子,就可以搭船成行。評彈的演出場地也極簡單,村落集市的茶館設一桌一椅(或二椅)即可開講。評彈碼頭有大中小之分,藝人也相應分為蘇州響檔、碼頭響檔和普通說書人。從小碼頭走進大碼頭,從普通說書人成為蘇州響檔,這里充滿了競爭、才能和機遇,能成為蘇州響檔的是極少數。
實際上,說書人并不只是從小碼頭向大碼頭進軍,即使身為蘇州響檔的說書人也是要到中小碼頭去的。評彈藝術借著走碼頭深入到江南的每一個細胞中,都市文化圈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發展,到乾隆年間,評彈已趨成熟,如乾隆時期的彈詞抄本《雷峰古本新編白蛇傳》《新編重輯曲調三笑姻緣》等一直流傳至今;也有了一批知名的評彈藝人,如演說評話《隋唐》的季武功、彈詞《落金扇》的王周士等;還有了評彈藝術的經驗總結,如王周士的《書品·書忌》。至此,蘇州評彈都市文化圈形成。
據統計,在評彈最興盛時期,江浙滬評彈書場有1000多家。僅蘇州城區表演評彈的書場就有120多家,常熟地區有103家;評彈從業人員有2000余人;上演的各類長篇評彈書目有150多部;評彈觀眾數量僅次于電影,位居第二。評彈在“南抵嘉興,北達武進”的評彈都市文化圈內,已成為地域性的文化記憶和認同的符號,聽書已是這里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