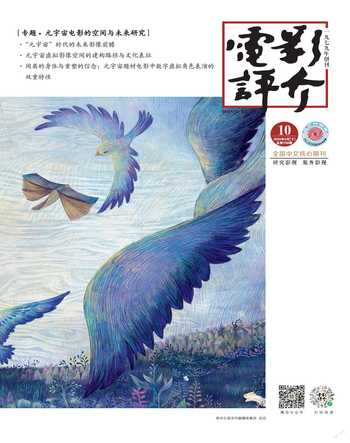實驗電影中的線條美學:空間創造、超驗理念與美學形式
孫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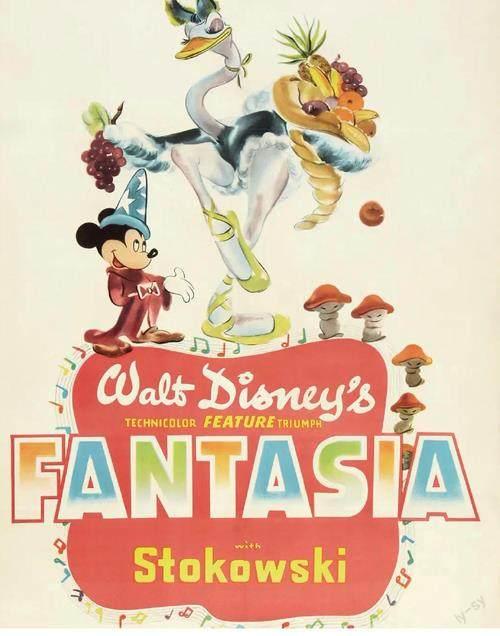
實驗電影指那些在視覺建構與信息傳達形式上與主流的敘事電影相異甚至對立的探索性影片,其始終以先鋒性的拍攝風格、制作方式等走在電影語言探索的前列。實驗電影中非常規的敘事順序、無次序的電影空間、使觀眾注意力分散的拍攝剪輯技巧、有意為之的畫面鏡頭失焦、通過不均衡的曝光在膠片上弄上亮點或暗點、快速凌亂的剪輯等技巧,都呼喚著一種新的視聽語法的出現。從19世紀20年代用16毫米膠片拍攝的表現主義影片,到戰后先鋒電影時期的地下電影創作、結構唯物主義電影等,在所有實驗電影中,基礎的抽象圖形總是畫面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實驗電影都會特別注重線條的形式,如用線條分割圖像或其本身也可構成圖像。無論是沿著線條前進的鏡頭,還是不斷交叉重疊的線條本身,抑或在線條的抖動中展現出的圖形——線條總能在實驗電影中釋放出強大的視覺張力。
一、純粹運動中的空間創造與創造性空間
電影,尤其是實驗電影中的線條首先在創造空間方面肩負著重要的作用。實驗電影中的線條保留了它最開始的狀態與生成時的原初目標,它在自身力量的展現中表達自身與其他視覺要素之間的關系,從而創造出一個神奇的影像空間。在速寫、草圖或兒童畫般的抽象圖形中,線條傳遞出純粹圖像的創造性力量,并借助蒙太奇將這種力量釋放在影像空間中。即使現實主義者往往認為“自然中不存在什么線條”,而將兒童畫或實驗電影中的抽象線條視為“抽象的結果”,但實際上“藝術創造的是一種與現實事物在結構上等同的事物,而不是對它的復制時,當我們記住,線條是由運動通過一定的媒介產生出來的事實時,我們就會發現,這種一度的軌跡(線條)本身,實際上是對于人們所知覺到的形狀的最直接和最具體的再現”[1]。在敘事電影中,構成復雜圖形與現實事物的線條勾勒著既定的目標和對象,它們將自身的存在隱沒在看似自然的事物中;而實驗電影中的線條更多的僅僅是以純粹的形式釋放自己,在整體性畫面中畫出自身的軌跡,展現自身的節奏、速度與未定型的模糊現象,并反身性地勾勒出空間的存在。
從某種程度上講,實驗電影就是利用線條將未畫出的圖像符號轉化成純粹的、只為自身而存在的圖像,讓它在釋放的輕盈中被快速顯現出的一種電影。在《別煩我》(曼·雷,1926)中,達達藝術的代表人物曼·雷利用實物投影技術將圖釘、線圈和其他物體直接放在感光紙上,將其暴露在光線下。這種獨有的拍攝方式,讓圖像處于抽象符號和具象物品之間,也為影片提供了新的空間創造方式。雷通過照相機的移動、側向、倒置等技巧將實物中的線條凸顯出來,將碎裂、解構、分離的局部鏡頭重新組裝拼接成扭曲、毫無規律的片段,從而打破了原有的空間性;繼而在立體主義方法中,讓穿插在畫面中的幾何物體呈現出流暢的運動狀態,從而營造出動態的活動空間。在成片中,燈光、花朵、指甲、廣告牌、漿過的衣領、濃妝的少女眼瞼等一長串不相關的圖像在畫面中扭曲、旋轉,處于介乎實物與符號之間的中間狀態。這些對抽象元素、超現實主義動機和定格動畫的實驗在當時較為前衛。影片中的線條營造了一個圍蔽的空間,在形式上包圍作為視覺中心的人物,并分割空間,以一種強大的表述欲望打破了電影本身景框的穩定性。《別煩我》中的影像空間創造與一條代表膠片的領帶緊密相關:它在旋轉和舞蹈中漸漸變成了圖像,這是對膠片在放映中形成連續畫面的隱喻;男人選擇領結可以看作導演進行剪輯的過程,最后男人丟掉了領結,說明對全部素材不滿意,要推翻重拍。這部影片深受立體主義的影響,片中的線條先從實物狀態中剝離自身,繼而在純粹的線條運動中營造了一個純粹的圖像空間,達到自然隨性、毫無意義的反藝術性境界。同時,原初的線條也并沒有在整體電影中消失;相反,將線條的形式明確地保留下來,并包含在電影中,實驗電影才能存在。這樣的影片通常是一次釋放,它能夠描繪并給出現實生活中難以察覺的強烈沖動。
實驗電影中的線條經常被用來考察自然知覺的斷裂與生活變化中那種難以捕捉的空間,這并不是鏡頭塑造、記錄或尺度的問題,而是事物的本源性問題。一些實驗電影會以與人類感知迥然不同的形式,探索并發現新的空間形式。在《電影眼》(吉加·維爾托夫,1924)中,攝影機鏡頭長時間沿著地面上的車道線和人行道前進行拍攝,人行道與車道之間的阻隔線條、車道之間的虛線在影片中是有形的、可以直觀辨別的線條;但這并不是攝影機要直接指向的具體目標。與其說這段鏡頭拍攝的是有形線條,毋寧說攝影機專注于表示線條本身的運動與速度,因此在有形的線條上,攝影機鏡頭劃過的軌跡構成了無形的動線。除此以外,攝影機沒有關注任何行人或景物,更沒有發生戲劇化的事件。整部影片給觀眾的便是一場無窮無盡的旅程,旅程的起點也是旅程的終點,線條與自身相連。這樣,它的軌跡便是無窮無盡、無法界定的無限軌跡,這個起點看似擁有時間意義上的固定起點,但實際上卻是一個無法定位的空間。
“從現在起,我將把自己從人類的禁止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將處于永恒的運動之中,我接近,然后又離開物體,我在物體下爬行,又攀登到物體之上。我和奔馬的馬頭一起奔馳,全速沖入人群,我越過奔跑的士兵,我仰面躍下,又和飛機一起上升,我隨著飛翔的物體一起奔馳和飛翔。現在,我,這架攝影機,撲進了它們的合力的流向,在運動的混沌之中左右逢源,記錄運動,從最復雜的組合所構成的運動開始。”[2]蘇聯電影導演維爾托夫認為,電影眼睛的本質是基于“電影視覺”的“電影寫作”與“電影組織”,其方法論建構在對生活事實系統記錄和對影片紀實素材之上。線條的運動軌跡顯現了這個空間在攝影范圍中暫時可見的一部分,但更大程度上顯現的是空間的無限性本身。與敘事電影相比,這樣的電影鏡頭傳達了事物的原初狀態,描畫了一種釋放純粹力量的創造性空間。這一空間本身不僅是在純粹的線條等圖形運動中被發現的,也是富于創造性的場域,可以揭示影像比其表面形式具有更深目標也更隱秘的東西。
二、不可還原的超驗理念與“無身體器官”
正如實驗電影存在的意義是探索電影本身未經開發的部分一樣,實驗電影中的線條不是以某些社會意義或真理為導向被創造的,而是影像在對自身創造的過程中呈現出來,而自行舒展和運動的。例如在時長8小時的《帝國大廈》(1964)中,導演安迪·沃霍爾任使用一臺裝有足夠膠片的攝影機架拍攝帝國大廈,以不剪接、不設置片名和演職員表的方式,展現帝國大廈在8小時內的狀態。這部紀錄性的實驗電影沒有任何電影語言或電影技法上的實驗、革新,它只是在電影中展現運動性和靜止性,追隨銀幕空間的線條構成畫框,與引起主體行動與情感的敘事電影全然不同。在普通的敘事電影中,所有劇情結構、人物情感與利益總以預設性的道德目標顯現出一個穩固的立場;在明確的結構與計劃中,電影如同紙和筆一般,按照畫面的既定布局前進。而在實驗電影中,一切并非經驗的,而是亟待創造的超驗與空白。此時,運動或靜止的線條突然在空白的空間中劃出了一道軌跡,一種“帶有不可還原的線條的欲望的,姿態性的印記”[3];“對于其而言,手與線,由于彼此關系,而一同出現——從沖動角度而言,這是一個自律的主體”[4]。在實驗電影中,線條并非是以隱喻的經驗的方式表達的,而是以超驗方式展示自身的,非源于藝術家的主觀布局。
在一般電影利用線條進行的創作中,無數人可能會感慨創作者在線條的大膽使用中顯示出“運動的趨勢”“天才的想象力”“驚人的天賦”或“優雅的法國南部風情”等。在一種符號學的想象中,這些對人類經驗之物的描述,最后取代了線條本身,在陳詞濫調的評論中徹底喪失價值。這是由于人們在一開始就被告知電影符號的層級和規則,例如曾經的“八大段”理論中,整體性的敘事組合段落統御著零散的敘事段落,零散的敘事段落又統御著其中的單個鏡頭,單個鏡頭又可以細分到幀與畫面等。線條則是單幀畫面中最基本的單位之一,導致其習慣性地在一種層級化的秩序中進行價值判斷。“符號只是一個標記,它具有隨意性,無法完全展現和表達生命。所以藝術不是符號,符號無法表現藝術。理論原點中的缺陷最終使得電影符號學在闡述電影中的磕磕碰碰。”[5]實驗電影中的線條絕非被繪制或制造出來后,死氣沉沉不再變化的東西,而是擁有沖動和目的性的事物。在實驗電影中,它仿佛是未完成的一部分,在超驗的形式中不斷釋放或者發散著自身的能量。
事實上,作為“基礎單位”的線條擁有與整體電影不相上下的力量,這恰恰是因為實驗電影剝離了戲劇化的風格與具體的故事情景,令線條的力量不在整體的故事中表現,而是從它自身的痕跡與運動中顯現。以動畫大師諾曼·麥克拉倫的一組實驗動畫為例;《幻想曲》(1952)以意識流的動畫風格創作,畫面從片名文字漸變至天地混沌,畫面中的元素構成了自主變化的連貫線索,展現了純粹的圖形變化;《線與色》(1955)的畫面中同樣充滿跳來跳去、不停閃回的線條;《彩條》(1971)亦然,不斷變幻的線條仿佛自在自為般運動舞蹈……在麥克拉倫的實驗短片中,線條本身構成了運動的主體。在墨水筆、鉛筆、圓珠筆或者膠片刮寫的隨意勾勒上,可以辨認出線條本身的沖動。線條既是形式,也是表達著自身的內容和欲望的表述主體;它不是創作者展現自身意識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種誕生于世界本源、對真理獨特的共鳴。這種充滿活力的圖像沖動不涉及電影符號學或敘事組合中的層級,而是直接從藝術家的手上繪出并轉化為膠片上遺留的痕跡,并從痕跡再回返到手的運動中。
“在所有這些當中,一種沖動的輕聲慢舞,一種能量中整個文化和歷史匯聚起來的思想或對世界的體驗都在痕跡的震動中匯聚在一起。”[6]藝術家在其中被稱為導演、畫家、繪制者等,這些創作者的身份僅僅是評論者,在一般意義上對這個位置上的創作主體的稱呼,將他繪出或制作的繪畫或影片、他的風格、他的思考方式等作為繪制過程的主體。但在實驗電影中,唯一掌握畫面主導權力的只是躍動的、富有活力與張力的線條本身。盡管庸俗或大眾文化的影響力可能會再次將線條吸收回到上述那些含混的符號性描述中,但線條并不會增強這些描述的可信度,而是再一次讓它們無法命名。與其說線條是被漫畫家的手所繪制的,不如說它以自身的運動讓“手”成為一個獨立于人體,或者說創作者主觀意識的“無身體的器官”。畫手之手以類似“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形式,以一種非有機的方式體驗他們的器官。器官作為元素或奇點,在“機械組合”的復雜功能中與其他元素相連,創造出一種比經驗更加強烈的感覺,促使我們發生轉變。“器官的重要非器官功能和它們凍結的緊張癥停滯,以及它們之間存在的所有吸引和排斥的變化——可以說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全部痛苦的轉化……在感官的幻覺和思想的譫妄之下,有一種更深刻的、強烈的感覺,即一種轉變。”[7]
三、純粹美學形式中的真理與力量
在刨除人類經驗性的審美需求與標準之后,是否存在一種關于線條的美學形式?這種形式是依賴任何標準存在的純粹之美,是真理突然出現時綻放的光芒,是對真理的勾畫并渴望的進發。在德國美學家黑格爾看來,美是對真的突然的澄明,它也是“真”最會被視為欲望的特征,是理性在自然中的感性顯現。美的終極是自由的體現,“是一種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認識,一種對感性客觀事物本身的形式和形態的認識,在這種認識里絕對理念成為觀照與感覺的對象”[8]。如果說存在一種線條的美學形式,那么它與一切美學形式一樣,同真理相互溝通。實驗電影創造了一個令線條欲望迸發并成為其自身的場域,在圖形的輪廓、運動的旋律與演奏、無體積的紋理框架中,顯現出線條自身抑揚頓挫的節奏感。由于線條本身是存在的,因此線條的美學形式也是存在的。關鍵在于,這種美學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的能量傳遞,一種“永不知足”的,將真理與視覺形式關聯起來的行動。線條的形式和它的內容緊密聯系且不可分割,它本身的存在就彰顯著一種欲望或意義。在分割空間、分割圖像,通過布局和構圖來改變畫面的過程中,它將自我的根源隱匿在整體圖像中,從而為其它圖像和空間開啟了新的可能性,最后消失在自身的運動中。
實驗電影在察覺到線條這種運動趨勢的同時,也在心理層面或視知覺層面上,以觸覺和感覺的方式重新感知和呈現線條的運動。《貧血的電影》(馬塞爾·杜尚,1926)中,不斷旋轉的原型轉盤上的螺旋線條不斷旋轉,交替出現旋轉的螺旋和題字創造出錯綜復雜的圖文戲,令人眩暈。當電影中的線條突破了二維平面,在運動中擁有了創造性的空間后,實驗電影就成為超越人造物的藝術。欲望過程中的線條總是在其自身的真理中,將自身顯現為任何世俗事物都無法企及的、純粹的美的形式,并讓自己感到快樂。它讓觀眾癡迷地凝視著銀幕,被來自另一個世界絢爛的、純粹形式的美所俘虜。《貧血的電影》顯示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純粹形式,令人眼花繚亂的線條在永不止息的運動中顯現出自身的身體與觀念,一種源自世界本源的真理在這樣的形式、身體與觀念中澄明了自身。實驗電影中的線條結合了形式與力量,并最終與世界的真理彼此結合在一起,成為純粹的美本身。
結語
世界從來不會向預先給出的計劃妥協,但人類會永恒地追求著世界的真理。世界的真理永遠擺脫不了人類對它的構型與勾勒。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創作者刻意去強調自我話語的表達,強調自身的主體化特性,那么他對世界的表現將限于自身經驗的矛盾之中。只有以一種更原初、更先驗的形式,在作畫的過程中探索這一過程本身可能為創作者帶來的感受,作品才能更加接近于世界的本源與意義。從這一角度而言,電影中的運動線條等圖形才是電影的本體,而創作者只不過是借助這一行為探索自身的客體罷了。在所有迷人的形式中,在所有勾畫世界真理的方式中,實驗電影中的線條首先勾勒出這種構思,它本身對愉悅的追尋開啟了電影探求意義的無限性。
參考文獻:
[1][美]魯道夫·艾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1.
[2]李恒基,楊遠嬰.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修訂本) [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129.
[3][4][6]朱其.當代藝術理論前沿[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5:146,147,151.
[5][法]讓·米特里.電影符號學質疑[M].方爾平,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31.
[7][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無身體的器官 論德勒茲及其推論[M].吳靜,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15.
[8][德]黑格爾.美學[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07.
【作者簡介】? 孫 峰,男,江蘇常州人,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