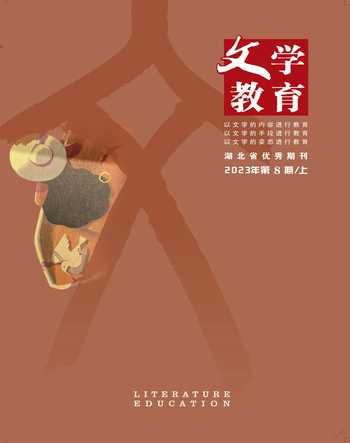后現代主義影響下余華長篇小說的中國意識
馬迎春
內容摘要: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后現代主義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創作,但隨之而來的是文學活力與民族精神的缺失。許多作家認識到了西方后現代主義給文學創作帶來的局限,開始摒棄西方后現代主義注重解構與非理性的創作,轉而將創作基點聚焦于中國,余華作為轉型的代表作家受到關注。論者將余華20世紀90年代以來創作的六部長篇小說與之前的作品對照可以發現,余華在轉型后更加有意識地展現中國面貌,書寫“中國意識”,更新“中國形象”,以求在世界性中彰顯民族特性。余華不僅將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具體化,展現了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回歸,還深入中國民間社會,探尋真實的中國民間生活,挖掘中國民間底層人民堅韌、樂觀的民族性格。同時,余華也開始吸收家鄉的地域文化資源,在標準的漢語中融入海鹽方言和越劇腔調。
關鍵詞:余華 “中國意識” 長篇小說
“中國意識”是中國歷史、中國社會風貌、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集中表達,本文談論的“中國意識”是文化審美意義上的“中國意識”。“中國意識”在中國文學創作中有跡可循。新中國成立前,《阿Q正傳》、“激情三部曲”、《子夜》、《四世同堂》等都包含著作家對中國社會的思索。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作家的創作轉向“工農兵方向”,構建了一個有別于西方“公民”社會的“人民”社會。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后現代主義盛行。西方后現代主義以其在內容上消解文本意義,在敘述上表現解構、顛覆與非理性,在結構上呈現出一種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影響各國的文學創作。當時中國正值文化轉型時期,且20世紀80年代的趨勢就是“全球化”“一體化”,西方后現代主義也就順勢進入中國,直接促進了先鋒文學的誕生。由于許多作家對西方后現代主義的過度模仿與跟隨,“中國意識”被剔除在文學創作之外,只關注內容的解構和形式的實驗。之后,雖然西方后現代主義仍在盛行,但中國的先鋒文學并沒有持續很久,中國的學者與作家認識到跟隨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創作失卻了文學的活力和獨特的民族精神,敘事內容與敘事形式的重復也引起了審美疲勞。許多作家開始將創作基點聚焦于中國,創作出了一批有民族特性的作品。
余華深受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早期創作了許多內容上展現非理性、解構與顛覆,語言上使用陌生化手法冷漠敘事的文學作品,如《十八歲出門遠行》(1987)、《現實一種》(1988)、《世事如煙》(1988)。正因為余華對西方后現代主義了解深刻,他認識到了西方后現代主義給文學創作帶來的局限性,開始將書寫對象和寫作資源指向中國。余華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陸續續創作了一批展現中國風貌的長篇小說,包括《在細雨中呼喊》(1990)、《活著》(1992)、《許三觀賣血記》(1995)、《兄弟》(2005至2006)、《第七天》(2013)、《文城》(2021)。余華的長篇小說中浸潤著余華對中國人民的人性關懷、對樂觀與堅韌的生活態度的贊揚和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的深刻認識,敘述風格也由冷漠、荒誕轉向溫情、樂觀。余華在《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2008)中也說“我相信文學也是一樣,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了解自己民族傳統中特別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這里“民族”的指向對象就是中國。
由此,論者認為余華是在受到西方后現代主義影響且認識到其局限之后,有意識地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書寫自己筆下的中國,探尋其中包含的“民族性格”與“中國意識”,尋求民族性建設以求在世界彰顯獨特的“中國意識”,更新“中國形象”。本文以余華創作的六部長篇小說為研究文本,從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回歸、中國民間社會的溫情思索和中國地域文化資源的吸收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回歸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在《文化轉向》(1998)中指出后現代主義是有關經濟、消費的,歷史感已經消失殆盡。歷史與現實不再是敘述的重點也并不具備內涵指向,只是功能性的符號。《十八歲出門遠行》敘述了一個剛成年的男孩獨自出門遠行的故事。在這一路上,主人公受到的攻擊可以是發生在任何時間段的,時間也就失去了意義。余華早期創作中的歷史與現實是缺席的、符號化的,或者說是無時間性的。20世紀90年代開始,余華創作的長篇小說中,中國歷史與現實開始回歸。正如洪治綱所主張的,余華也“試圖在重建一種具有中國經驗的、比自己以前小說更具歷史豐富性的‘大敘事”。[1]這時,余華筆下的歷史與現實是能夠影響人物和情節的存在。
(一)中國歷史的回歸
《活著》以福貴的經歷為線索,講述了20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歷史變遷,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歷史與人物命運的交織與同敘。余華書寫的是個人記憶中的歷史,也是被歷史影響下的個人命運,歷史成為余華小說創作中的重要情節結點。《活著》敘述了福貴的一生,歷史與福貴的命運息息相關。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福貴敗光了家產、田地,福貴認清事實決定重新做人開始租地種田,開啟了他的農民生涯。之后,歷史的偶然使福貴跟隨軍隊過了兩年,福貴的命運被改變了,也正是因為戰爭福貴明白了生命的可貴。再后,福貴又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運動、三年饑荒等歷史事件,在這其中歷史和偶然一次又一次改變著福貴的命運,也加強了福貴對生命的堅守。福貴就如歷史長河上的浮萍無法控制地被帶往別處,在漂浮中不僅見證了中國的歷史,也堅定了福貴活著的信念,福貴的命運與歷史同構。
不僅福貴的命運與中國歷史聯系密切,許三觀的命運與中國歷史也有著關聯,陳思和指出“許三觀一生多次賣血,有幾次與重大的歷史時間有關,如三年自然災害和上山下鄉運動”。[2]在大饑荒時,許三觀因為家里糧食短缺而賣血。二樂參加了“上山下鄉”運動,許三觀為了招待二樂所在的生產隊隊長又一次賣血。從這兩次賣血中可以看出,許三觀是受到歷史影響的被動賣血。歷史不僅影響著許三觀的命運,也影響著賣血情節的構造。
《文城》中小美的生命歷程也與歷史交織在一起,“小美入土為安,她生前經歷了清朝滅亡,民國初立,死后避開了軍閥混戰,匪禍泛濫”。《文城》不僅勾勒了清末民初的歷史,也補全了余華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書寫。
自余華創作長篇小說始,余華以小人物的命運為表征,敘述人物背后中國歷史的變遷。余華筆下的歷史開始具體化,歷史開始與人物的命運和情節的構造相勾連,歷史也成為余華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國現實的回歸
新世紀以來,余華愈來愈關注中國當下的現實面貌,《兄弟》和《第七天》就是典型代表。
余華在《兄弟》的后記中表明《兄弟》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說”。《兄弟》是余華對現實發起了“正面強攻”。《兄弟》以兩個人物四十多年的經歷敘寫了中國20世紀60年代至改革開放的“中國記憶”,也書寫了余華對改革開放后中國道路的思索以及經濟繁榮背后的憂思,有著現實警惕性。李光頭去福利廠當工人搭上了改革的熱潮,成為劉鎮最富有的人,也帶領劉鎮成為新的經濟中心。劉鎮可以說是中國的縮影,由李光頭、宋鋼帶來的劉鎮的變化也是中國現實的變遷。《第七天》是對《兄弟》的接續,以亡靈的見聞敘述中國的現實。余華將許多新聞事件引入創作,許多學者也將《第七天》看作是“非虛構”作品,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第七天》的現實指向性。
余華在20世紀90年代主要通過書寫中國歷史對中國底層人民的命運進行思索,在新世紀主要對現實“正面強攻”。由此,論者認為余華早期受后現代主義影響,其創作的歷史與現實是符號性的,中國歷史與現實是失卻的。之后,余華開始有意識地書寫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探索“中國意識”,從中展現對中國本民族歷史與現實的思索。
二.中國民間社會的溫情思索
陳思和主張“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有融入民間才有力量。余華“從八十年代的‘極端先鋒寫作,轉向了新的敘事空間——民間的立場,知識分子把自身隱蔽到民眾中間”開始講述老百姓的故事。[3]余華找到了“民間化”的道路,余華雖然深知民間是藏污納垢的地方,但民間也是至真至情的地方。余華拋棄早期創作中人物書寫的符號化、小人物的“非理性”體驗和敘述風格的冷漠,轉而書寫中國民間的日常生活,挖掘中國民間底層人民樂觀、堅韌的民族性格,對中國民間底層人民寄予溫情的思索。這不僅更新了中國民間形象,還進一步構建了具有民間性的“中國意識”。
(一)中國民間的日常生活
余華與老百姓共同經歷民間生活,著重描摹老百姓的生活細節。就像余華在《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5)中說“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然后再回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余華從《活著》到《許三觀買血記》再到《兄弟》描摹了一幅幅老百姓平凡的日常民間圖景。
《活著》細致地描寫了福貴的農耕生活,福貴在家道中落后深刻思索蛻變為農民,每日勞作、種田。田地不僅是生活的希望,也是生命的象征。福貴對田地有著深沉的熱愛,小時候,福貴的娘告訴他泥巴能治百病,福貴的爹跟福貴訴說著田地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時,最開心的就是家里獲得了五畝地,這代表生活的安康。《活著》中還有著民間歌謠的傳唱,如福貴會唱“皇帝叫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少年去游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等民謠。因此,陳思和、逸菁在《逼近世紀末的回顧和思考——90年代中國小說的變化》(1995)中認為《活著》是中國民間性與民族性的代表,“這個故事的敘事含有強烈的民間色彩”。
《許三觀賣血記》細致地書寫許三觀因為生存和家庭十二次賣血的經歷。《兄弟》則細致地描寫了宋凡平和李蘭相愛的細節,宋凡平和李蘭這一二婚家庭組建的過程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如宋凡平細細呵護李蘭、幽默地陪孩子玩耍;李蘭和宋凡平耐心教導宋鋼和李光頭;宋鋼和李光頭又吵鬧又溫馨的童年生活。此外,文中還寫了劉作家童鐵匠、蘇媽、余拔牙等居住在劉鎮的老百姓的喜怒哀樂。
余華不僅書寫中國底層人民的生活細節,還有著中國民間道德倫理的敘述。如《兄弟》中對“你會有善報的”這句話重復了7次,始終縈繞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民間倫理觀念。
余華筆下的福貴、許三觀、宋凡平等老百姓都身處于中國民間的底層,他們日常生活的描寫不僅展現了中國民間底層人民真實的生活狀態,還是民間社會經驗、民間倫理的結合。論者認為,余華正是站在民間立場上書寫中國民間底層人民的衣食住行、愛恨情仇。民間的一切在余華的手中鮮活起來,余華也在其中試圖尋找獨屬于中國民間的智慧,探索“中國意識”的民間性。
(二)中國民間底層人物的溫情思索
在王安憶、余華對談暨余華作品研討會(2023)上,王安憶指出:“過去的‘人以符號的方式存在,現在的‘人以‘人的形象出現。”余華于90年代發現了“別人”的存在,開始注重“別人”的聲音,他筆下的“人”更鮮活了。余華筆下的“人”都是中國民間底層人物,有著樂觀、堅韌的民族性格。正如洪治綱在《悲憫的力量——論余華的三部長篇小說及其精神走向》(2004)中所言,余華“回到現實的底層,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悲憫的情懷”,對世間抱有著善意的憐憫。
雖然福貴一家與許三觀一家的生活多是無奈的與悲苦的,但他們仍能樂觀面對命運的撥弄,坦然堅守自己的真情。福貴早年紈绔不顧家庭且輸掉了家產,他的母親說出“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的樂觀之語。妻子家珍在被父親接走后仍帶著兒子回到富貴身邊不離不棄、共渡難關。鳳霞的丈夫二喜不管每天干完活多累,都要走十多里路到鄉下看兒子苦根。許三觀即使知道一樂不是自己的孩子,仍然真情相待。
《兄弟》則更側重書寫人性的美好。宋凡平是人性美的代表,他身上仿佛集中著世間所有優秀的品質,他正直善良、同情弱小。宋凡平面對妻子時,處處體貼照顧,兩人雖然相處時間不久,但仍能不離不棄、忠貞不渝。宋凡平永遠是李蘭心中最愛慕和最驕傲的丈夫。宋凡平面對孩子時,細心愛護孩子,與孩子一起玩鬧。宋凡平獨自承擔著悲痛給孩子帶去的永遠是笑臉、樂觀與堅韌,盡管他的胳膊被打的脫臼仍然沒有抱怨,而是幽默地對孩子說“它累了”,熱情地教孩子如何讓胳膊“休息”。宋凡平以其樂觀、堅韌、微笑以及人性中閃光的溫情與命運抗爭,成為了偉大的丈夫、偉大的父親,始終“有尊嚴的活著”。
當然,《兄弟》中最值得思考的還是宋鋼與李光頭這兩個毫無血緣關系的兩兄弟至真的手足情。在童年時,兩人的家庭是樂觀的、溫暖的,他們一起品嘗綠豆湯、一起吃糖、一起玩耍,兩人也慢慢懂得了愛。長大之后,李光頭發工資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給宋鋼買那副最貴的眼鏡,宋鋼始終記得他在母親臨終時說的話“媽媽,你放心,我會一輩子照顧李光頭的。只剩下最后一碗飯了,我會讓給李光頭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會讓給李光頭穿”,并以之為行為準則。兩人一直樂觀、堅韌的生活,盡管兩人經歷了斷交,但兩人心里放不下的始終是對方。
在以上這些血肉豐滿的中國民間底層人物形象中,余華秉持著悲憫的情懷,用孕于中國民間底層人物樂觀、堅韌的民族性格,探索“中國意識”的溫情特性。
三.中國地域文化資源的吸收
余華早期的創作有選擇性地吸收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如《古典愛情》中對才子佳人形象的借鑒、《鮮血梅花》中對江湖復仇情節的書寫、《河邊的錯誤》中對俠義公案小說的模仿,但其中敘述多是無地區性的。論者發現,20世紀90年代之后,余華也從中國地域文化資源中汲取創作靈感,探尋他故鄉中特有的“中國意識”。
(一)海鹽方言的吸收
余華出生于浙江杭州,三歲時隨父舉家搬遷至浙江海鹽。余華曾在《我能否相信自己》(1998)中說“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這里的家就是海鹽。余華曾寫到“雖然我人離開了海鹽,但我的寫作不會離開那里。我在海鹽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長的時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長,河流的成長。那里的每個角落我都能在腦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語時會脫口而出”。[4]可見,海鹽作為余華的故鄉,對余華的創作影響頗深。
余華在《許三觀賣血記》的意大利文版自序中指出“我就是在方言里成長起來的”。《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中就有著海鹽方言的留存。《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中近二十次使用“眼淚汪汪”這一海鹽方言,敘述許三觀、許玉蘭、李蘭、李光頭、林紅等人回憶的悲傷或感動的喜悅。“擱”、“淘”等海鹽方言也展現了中國民間底層人民真實的生活細節。此外,“熟了”(過世)等方言俗語也經常運用。但余華曾針對方言的使用做出思索“十五年的寫作,使我滅絕了幾乎所有來自故鄉的錯別字,我學會了如何尋找有力的詞匯……我學會了在標準的漢語里如何左右逢源”。[5]
因此論者認為,余華雖然竭力避免著“故鄉的錯別字”轉而在“標準的漢語”中左右逢源,但他始終無法擺脫海鹽方言對其創作的影響,其語言是具有民族特性的。
(二)嵊縣越劇的吸收
余華于海鹽縣文化館中接觸到了越劇,越劇(中國第二大劇種)發源于浙江嵊縣,影響了余華的創作。余華意識到越劇唱詞和臺詞是相似的,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2018)中說“臺詞是往唱詞那邊靠的,唱詞是往臺詞那邊靠的”,于是余華開始將越劇唱詞與敘述語言結合,讓說話呈現出“節奏和旋律”。
《許三觀賣血記》中的對話有著明顯的越劇腔調。如許玉蘭問許三觀,在她生產時許三觀是不是在外面哈哈大笑。許三觀說:“我沒有哈哈大笑……我只是嘿嘿的笑,沒有笑出聲音”。許玉蘭回道:“所以你讓三個兒子叫一樂,二樂,三樂,我在產房里疼了一次,兩次,三次;你在外面樂了一次,兩次,三次,是不是?”許三觀與許玉蘭的對話宛如越劇唱詞中的一唱三嘆,敘述節奏輕快,有著明顯的韻律節奏。余華在一次訪談中也指出“那個許玉蘭,她每次坐在門檻上哭的時候,那全是唱腔的,我全部用的那種唱腔”,這里的唱腔就是越劇唱腔。[6]
由此,論者認為余華的長篇創作中有意識地吸收海鹽方言和越劇資源,在標準的漢語中融入浙江的氣息,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話語”,尋求“中國意識”的地域性。
綜上,論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許多作家跟隨并模仿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創作,中國先鋒文學的誕生就是“他塑”的結果,注重解構、非理性與語言實驗,“中國意識”被剔除在文學創作之外,失卻了中國的民族特性。余華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積極地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書寫自己筆下的“中國意識”,展現中國面貌,更新“中國形象”,在世界性中凸顯民族特性。當下文壇也亟需創作具有“中國意識”的內容,構建具有中國民族特性的“中國形象”和“中國話語”,增強文化自信力,有意識地在世界文學中“自塑”。
參考文獻
[1]余華.在細雨中呼喊(第3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余華.許三觀賣血記(第3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余華.兄弟(第3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余華.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6]余華.文城[M].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
[7]余華,楊紹斌.“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J].當代作家評論,1999(01):4-13.
[8]洪治綱,余華.回到現實,回到存在——關于長篇小說《兄弟》的對話[J].南方文壇,2006(03):30-35.
注 釋
[1]洪治綱:《在裂變中裂變——論余華的長篇小說<兄弟>》,《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4期,第96-104頁。
[2]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23頁。
[3]陳思和,張新穎,王光東:《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之后》,《文藝爭鳴》,2000年,第68-70頁。
[4]余華:《余華自傳》,見《余華作品集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381頁。
[5]余華:《在細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5頁。
[6]余華、陳韌:《余華訪談錄》,《牡丹》,1996年第8期。
基金項目:2022年度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資助:《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中國意識”——以余華的〈兄弟〉和黃碧云的〈烈女圖〉為例》(項目編號:2022SKY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