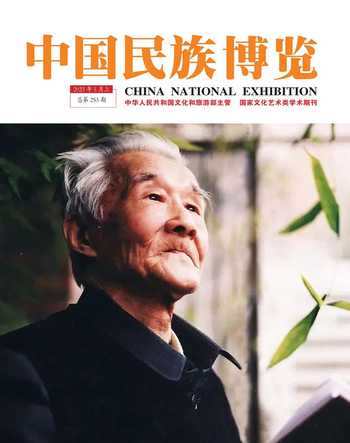譯者主體性在翻譯中的體現
【摘 要】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重要參與者,一直以來其地位和作用得不到重視。隨著“文化轉向”的興起,譯者的主體作用逐漸凸顯。本文試從譯者主體性的理論層面出發,通過對翻譯主體的界定,揭示出譯者作為翻譯活動主體的內涵及表現,并選取不同題材的文學作品,分析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表現,進一步肯定翻譯過程中適當發揮譯者主體性的必要性。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文學翻譯;良心;風格;反思
【中圖分類號】I046;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09—227—03
引言
翻譯,作為一項跨越文化障礙、促進世界各民族之間相互交流溝通的重要活動,由來已久。傳統譯論長期以來,一直忽視了譯者的貢獻,甚至否認了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譯者從古至今的一些形象化稱謂“舌人”“媒婆”“擺渡者”“傳聲筒”“帶著鐐銬的舞者”等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譯者的尷尬地位[1]。更有學者直接指出“譯者永遠是文壇上的冷門人物”,“書譯好了,大家就稱贊原作者;譯壞了,就回頭罵原作者”[2]。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哲學語言論轉向和翻譯理論界的文化轉向,為我們開辟了譯學研究的新視角”[3],譯者的作用和地位研究逐漸受到西方學界的關注。
21世紀頭十年,有關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在我國學界引發了熱烈討論,直到今天,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或從新的理論視角出發,或依托全新語料,討論之聲依然不絕于耳。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主體、主力軍,譯者發揮的作用對翻譯結果有重要影響。我們將譯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及其他影響翻譯過程和結果的個人因素稱為“譯者的主體性”。
譯者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始終,不僅體現在譯前的準備環節,還表現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延續在譯后的整理環節里。本文選取文學作品翻譯中最能體現譯者主體性的特征及行為,通過具體分析,透視其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表現。
一、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體現
面對同一文本,不同譯者有著不同的理解。這種理解差異在文學文本的翻譯處理中最為常見。一方面,作者在作品創作中注入情感,但是譯者無法百分之百感同身受,故產生理解偏差,甚至出現誤譯。另一方面,譯者會不由自主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自己既有知識背景去理解和感悟原文精神。這種主觀能動性不僅體現在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也表現在譯者采取何種策略、如何組織譯語文本上。文學翻譯是一項極其復雜、十分細致的活動,對譯者的水平要求極高,同時也十分彰顯譯者的主體性特點。
(一)譯者的“良心”——譯者主體性的基本前提
對文學翻譯而言,在譯前準備階段,譯者主體性主要表現為對文學作品的甄別和遴選。譯者的社會責任感、社會參與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選擇。我們稱之為譯者的“良心”。
茅盾曾指出,文學翻譯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人民通過翻譯能夠認識世界,了解其他民族的優秀精神文化,還可以增進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4]。五四運動期間,涌現出大量優秀的西方文學作品譯作,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風氣的要求,以及譯者自覺的社會責任感。
魯迅作為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在翻譯領域里的貢獻同樣舉足輕重。有學者統計,魯迅共計翻譯過14個國家90多位作家逾200多種作品,翻譯成果豐厚,涉及面廣,其中數量最多的譯作當屬俄蘇文學[5]。魯迅的翻譯經歷,按照時間順序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6]。他本人的翻譯觀在每個時期表現出相應的時代特征。縱觀魯迅的翻譯經歷,唯一不變的是他的本心,即譯者的“良心”。
魯迅的翻譯活動主要以個人興趣愛好為主,翻譯文本集中于科學小說領域[7]。隨著國內形勢加緊,魯迅意識到“行醫救國”是行不通的,轉而“棄醫從文”魯迅的譯者主體性體現在他個人思想的轉變以及對翻譯文學文本的選擇上。從一開始進行科學小說的翻譯,到之后進行藝術性、思想性作品的轉播與譯介,無一不體現著魯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作為一名譯者,魯迅是有良知的,在意識到國內外政治形勢猛烈變化之時,他毅然在翻譯中加入政治因素,希望通過文字上的“政治革命”起到振聾發聵的效果。在翻譯活動的后期,由于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震撼,魯迅認識到只有通過“政治先行”的方式,才能令國民清醒,于是后期翻譯了大量俄蘇文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促進了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的建立[8]。
譯者主體性在魯迅翻譯實踐中的另一顯著表現為翻譯觀的變化。最初魯迅的翻譯觀只限于個人興趣愛好,在國家危難之際,他意識到“啟民智”的重要性,隨后總結提出自己的翻譯觀,即為:“①進化觀念;②尚武精神和復興中國;③改良群治或者革新民智;④傳播科學”[9]。魯迅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感知國民的要求,通過自發的翻譯活動,自覺加入社會改良運動中。正是魯迅本人的“良心”,使他產生“翻譯革新民智”的愿望。因此,譯者的“良心”、社會責任感在一定程度上是譯者主體性得以發揮的重要前提。
(二)譯者的“風格”——譯者主體性的重要體現
譯者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具體表現為譯者對于翻譯風格的把握,即譯者采取何種策略、善用何種角度切入翻譯過程。
文學作品的翻譯“風格”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指原作寄寓著作家本人的創作風格;二指譯者根據自己對原文的理解,結合個人翻譯經驗、知識背景、善用的策略技巧等,逐漸形成彰顯個性的翻譯風格。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譯者的翻譯風格與原作的寫作風格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貫通。文學作品中作家的風格依托文字而呈現,故而風格的基礎是語言。
以小說翻譯為例,作家擁有自己特定的創作風格,譯者由于知識背景、翻譯技巧存在差異,呈現出對原作不同的理解與處理,不同譯本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立足契訶夫的創作特點,具體分析不同譯者的翻譯風格,例:“Рассказывали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и”。曾婷將其譯為“兩人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汝龍將其譯為“他們講起各式各樣的事”[10]。這句話中汝龍的譯本更好地貼近了原文風格,更加簡練。曾婷的翻譯更加歸化,譯文更多表現出譯者的風格,反而淡化了原作的風格。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必須掌握“適度”原則,要以忠實原文為前提,而不是譯者個人的主觀臆斷。風格的發揮必須建立在原文基礎之上。原作風格與譯作風格并非完全對立,譯者應根據實際,選擇最合適的翻譯策略,不拘泥于直譯或意譯,也不局限于歸化或是異化,努力尋求原作風格與譯作風格的有機統一。
以詩歌翻譯為例,把握詩人的創作風格依然是前提。以曼德爾施塔姆創作風格為例,胡學星指出,曼德爾施塔姆詩歌風格最突出的一點在于“充分利用性質不同、跨度很大的意象,讓讀者靠自己的意識活動將詩行間不同意向的相互聯系揭示出來,詩歌因此變得內涵豐富、韻味無窮”[11]。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意識到詩人的創作特點后,需要充分磨練自己的語言能力,盡最大努力再現詩人的風格。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切忌在詩歌翻譯中過分歸化,否則詩歌本身的意境美、詩人蘊含的情感無法被譯出,譯作將毫無價值。
文學作品的翻譯,講究原作風格與譯作風格的有機統一,譯者應在原作風格基礎上,發揮譯者主體性。因此,譯者的風格不是無源之水,也不是無本之木,而是以再現原作風格為目標、個人主體性的有機體現。二者關系是相輔相成的,絕不能拋棄一方空談另一方的發揮。
(三)譯者的“反思”——譯者主體性的自我完善
譯者主體性貫穿整個翻譯過程,無論譯前、譯中,還是譯后階段,都伴隨著譯者主體作用的發揮。翻譯活動的結束,并不以簡單的譯本呈現為目標,其中還包括譯者后續的修改與不斷完善。
在譯后階段,譯者對譯本的修訂與完善,我們可以將其視為譯者的“反思”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譯者精益求精態度的體現,譯者通過自我反思,逐步達到自我完善的境界,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促進翻譯事業的向前發展。在這之中,傅雷的翻譯實踐給了我們很多啟示與思考。
傅雷的譯作甚豐,包括《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約翰·克里斯托夫》等世界名著[12]。對傅雷而言,翻譯是一種工具,是達成個人精神追求的工具。因而,在翻譯過程中,傅雷十分重視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主要表現在他對自己的約束和譯后階段的自我反思中。
以傅譯《都爾的本堂神甫》手稿為例,通過對比發現傅雷針對同一作品,甚至是同一句話的翻譯,不同版本均有一定不同。例如,法文原文中有這樣一句話“—Je vous en avais assez dit, vous ne me compreniez point, et je ne voulais pas me compromettre”,傅雷在前后三次翻譯中均進行了一定的修改與完善。初譯稿為“過去我話說得夠了,你們就是不了解;我可不愿意惹是生非”,修改稿為“過去我話說得不算少,你們就是沒聽懂;我又不愿意把自己牽進去”,最后的謄正稿為“過去我話說得不少,你們就是沒聽懂;我又不愿意把事情弄到自己頭上”[13]。許鈞認為,初譯稿較之后來的譯稿顯得更加直譯,例如“話說得夠了”中的“夠了”顯然在漢語中帶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因此傅雷在后來的譯稿中將其改為“話說得不少”,并且此舉更顯說話力度;將初譯稿中的“就是不了解”改為“就是沒聽懂”更顯準確性[14]。最后的譯稿與前幾稿相比,更加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
由此看出,傅雷十分重視譯后的反思過程。他首先努力傳遞出原文意思,緊接著在后續完善中不斷修改語言措辭,使之更加符合漢語表達習慣。這一反思性還體現在傅雷翻譯《高老頭》時,1944年傅雷翻譯《高老頭》大獲成功,前后出版過四次,但建國以后出于精益求精的態度,傅雷仍于1951年完成了對《高老頭》的重譯,并于1963年又在重譯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譯[15]。
二、結語
譯者主體性作為譯者主觀作用的能動性體現,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始終。譯前階段,譯者受良心驅使、本心指導,抑或是社會責任感的激發,進行翻譯文本的抉擇,并為后續翻譯活動開展做鋪墊。翻譯過程中,譯者對于翻譯風格的把握,必須建立在原作風格基礎之上,在傳遞原作風格與彰顯個人特色之間達到平衡。譯者在譯后階段需要具備自我反思與臻于完善的自覺性,才能在翻譯道路上越走越遠。合理掌握翻譯技巧,不斷擴充知識儲備,合理、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作用,逐步提高翻譯水平,提升個人的翻譯境界。
參考文獻:
[1]仲偉合,周靜.譯者的極限與底線——試論譯者主體性與譯者的天職[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7).
[2]余光中.余光中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
[3]屠國元,朱獻瓏.譯者主體性:闡釋學的闡釋[J].中國翻譯,2003(6).
[4]茅盾.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斗——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在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的報告[A].翻譯研究論文集(1949—1983)[C].1984.
[5][6][9]彭建華,邢莉君.魯迅的翻譯觀念、翻譯反思與翻譯論爭[J].外語教育,2011(0).
[7]于潔.從意識形態操縱角度看魯迅之文學翻譯論[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7(2).
[8]雷亞平,張福貴.文化轉型:魯迅的翻譯活動在中國社會進程中的意義與價值[J].魯迅研究月刊,2000(12).
[10]閆怡紅.契訶夫小說譯本風格翻譯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4.
[11]胡學星.巧用詩歌意象之間的間隔——曼德爾施塔姆詩歌奧秘簡析[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6).
[12]金瑞,邵華.譯者主體性在傅雷翻譯實踐中的體現[J].海外英語,2019(23).
[13]傅雷.傅雷全集(第三卷)[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14]許鈞,宋學智.傅雷文學翻譯的精神與藝術追求——以《都爾的本堂神甫》翻譯手稿為例[J].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2013(5).
[15]馬曉冬.外來啟迪與本土創造:傅雷的翻譯思想研究[J].中國翻譯,2019(2).
作者簡介:秦萌遙(1996—),女,漢族,山東濰坊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俄語語言與文化、翻譯理論與實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