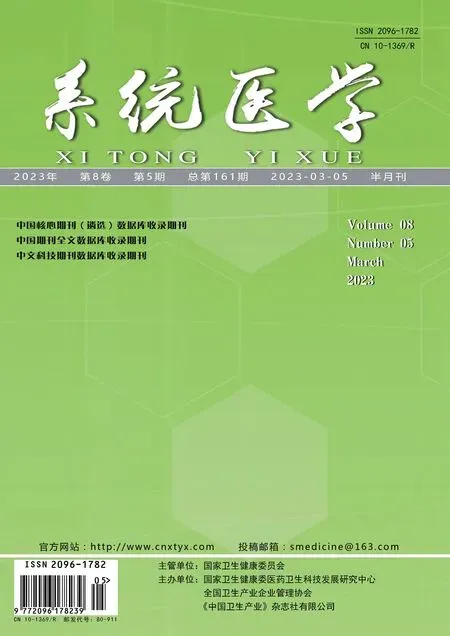潰瘍性結腸炎上皮內瘤的進展研究
李瑩,楊蔚峰
1.廣西欽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病理科,廣西 欽州 535000;2.廣西欽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廣西 欽州 535000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為腸道炎性病變,病變位處在大腸黏膜及其下層,范圍多累及遠端結腸,可逆行發展到近端,甚至全結腸[1]。UC 上皮內瘤具備癌變概率,而結腸炎相關結腸癌(colitis-associated cancer, CAC)發生風險要比散發性大腸癌高4~10 倍[2]。CAC 屬于歐美等多個發達國家中常見惡性腫瘤,位居第3 名,位于病死原因中第2 名[3]。CAC 治療方式主要為手術,輔以放化療、靶向治療等,但五年生存率仍約50%[4]。以往CAC 等的研究點是腫瘤細胞、組織,對于UC 及其發病因素、預防檢測、癌變機制等有局限性[5]。近十年,隨著對炎性反應、腫瘤免疫反應的認知深入,結腸癌發病機制同樣開展深入研究,逐漸明確發生機制,另發現其確認潛在干預靶點[6]。筆者就UC 上皮內瘤轉變至相關性結直腸癌中相關機制研究進展予以綜述。
1 UC 流行病特點
UC 者已處于患結直腸癌的高危人群。炎癥環境在慢性UC 癌變機制中有重要作用。UC 發病10年CAC 發生率1.6%,20年發生率8.3%,30年發生率1.4%,UC 癌變發生率總體可達3.7%,尤其是美國與英國發病率較其他歐美國家明顯[7]。有文獻指出,UC 或結腸癌發生率僅為1.4%[8];但有研究顯示,近10年UC 或者結腸癌發生率達3.3%[9]。目前,關于UC 結腸癌發生率仍存在較大爭議。
2 UC 上皮內瘤癌變的基本進程
UC 上皮內瘤始于炎癥,涉及多階段、系統、信號傳導通路等復雜網絡,而網絡內任意節點若有改變,均具有干擾UC 癌變發展速率作用,甚至干擾疾病預后與轉歸[10]。
UC 上皮內瘤多伴有異型增生。UC 上皮內瘤、異型增生關系為異型增生陰性、異型增生不確定型、異型增生陽性型。UC 癌變期間各類基因變化和散發性結直腸癌(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SCC)之間具有一定差異性,基于基因表達頻度差異與時間順序方面。SCC 發病期,多因為是APC基因突變于癌變早期,從而啟動癌變,中期k-ras基因突變,晚期p53 基因發生突變可促進病情發展。UC-CAC 發病期間,P53 發生突變可能屬于早期事件,APC 突變于UC-CAC 晚期,k-ras 基因突變率于UC-CAC 中比較低,作用較小。Wnt 信號通路的激活為疾病發展的早期事件,和β-連環蛋白(β-Catenin)具有緊密的關聯性。APC 基因在UCCAC 中呈低突變率與晚期突變的現象一般出現于平坦型的UC-CAC 病變,SCC 常見腺瘤息肉狀的病變有差異。
UC 上皮內瘤癌變分子事件中,P-連環蛋白(PCatenin)、P53 表達升高,提示P-Catenin 激活對UC上皮內瘤癌變具有積極作用,P53 過度表達更加和病程存在密切聯系,提示P53 可能早期參加癌變過程,且持續積累突變效應。
UC 上皮內瘤癌變期間各類癌變基因相關蛋白發揮效果存在差異性,與UC 相關性結腸癌、結腸腺瘤之間的E-連環蛋白(E-Catenin)表達量有差異,APC、Wnt 表達量無差異,預示在癌變機制中,于Wnt 途徑中激活E-Catenin 重要性高于Wnt-1、APC。P53 蛋白在UC 上皮內瘤病變不同病程的組織內表達不同,病程越長,則陽性率越高。
UC 上皮內瘤病情進展中,是由多個炎癥介質(氮簇、活性氧簇、環氧酶、細胞因子)構成腫瘤微觀環境,經過對于腫瘤因子(例如P53)、各種信號通路、表觀遺傳學(例如CpG 島甲基化)干擾,在加快腸上皮細胞炎性反應時,使上皮細胞發生異型增生的風險升高。
3 UC 上皮內瘤癌變的研究進展
3.1 染色體不穩定
宮頸上皮內瘤樣病變(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是UC-CAC 的早期事件,具有較高發生率。脫氧核糖核酸(deoxyribo nucleic acid, DNA)異倍體屬于CIN 表型之一,CIN 可使其他染色體水平發生變化,例如染色體易位、擴增以及缺失等,進而與鱗狀細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特征差異性較大,例如在染色體臂增減方面,5p 增加、17q 或者5q 缺失比SCC 中更為常見,反而14q 缺失更為少見。SCC 內異倍體出現于癌前病變的腺瘤期,SCC 發生風險54%~80%[11]。UC-CAC 更早的產生異倍體、分布更廣,可產生于組織學無異型的增生黏膜。CIN 在瘤癌變中重要機制可能與結腸炎癥內高含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縮短端粒有關。
3.2 免疫細胞、炎癥因子在潰瘍性結腸癌變中作用
肥大細胞(mast cell, MC)在CAC 進展中起到推動作用,為重要的免疫調節細胞。目前未明確自上皮內瘤-癌變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的MC 亞型,黏膜肥大細胞(mucosal mast cell, MMC)、結締組織肥大細胞(connective tissue mast cell, CTMC)有不同,穩態、炎癥下可保護腸屏障。誘導型結直腸癌中MMC 數量、特異蛋白酶呈高表達狀態[12]。肥大細胞蛋白酶(mast cell protease-1, MCP-1)可引發CD11b+Grl+炎癥細胞于癌組織中積累,調CD11b+Grl+的活動,提高細胞的成長速度,同時阻滯T 細胞的活化[13-14]。故MMC 調節、招募以及激活CD11+Grl+,繼而促進CAC 進展,還可為預防CAC 進展的潛在靶點。
巨噬細胞分泌與釋放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屬于多功能細胞因子,利用NK-κB 信號轉導通路、信號轉導抑制因子3(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3, SOCS3)參與上皮內瘤癌變。腸道中巨噬細胞釋放的IL-6 能激活癌變細胞避免凋亡途徑;IL-6 持續高表達,增強癌變細胞的增殖、存活;巨噬細胞源性的IL-6 調節癌細胞黏蛋白的表達,創造癌細胞擴散與轉移環境。
中性粒細胞可分泌、釋放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 IL-1β),而IL-1β 加快單核-巨噬細胞分泌、釋放IL-6,具有促瘤效果[14]。補體系統為固有免疫組成部分之一,在UC 上皮內瘤癌變中有促進功能,經過調節IL-1β 水平來促進CAC發生[15]。
單核-巨噬細胞釋放的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激活,能夠干擾腫瘤的生長,積聚中性粒細胞于腸黏膜的炎癥處。于UC 上皮內瘤癌變期間,TNF-α 含量下降能夠減輕腸黏膜損傷、阻滯巨噬細胞浸潤,從而下調腫瘤數量、體積[16]。微生態調節劑減緩巨噬細胞分泌IL-6、TNF-α,改善炎性反應,下調癌變率[17]。提示TNFα、IL-6 表達水平升高和巨噬細胞浸潤存在密切聯系,可一定程度加快癌變進程。
IL-17A、維甲酸相關孤兒核受體γT 細胞(retinoic acid receptor related orphan receptor T cell,RORγT cell)參與炎性腸病的發病機制,氧化偶氮甲烷(azoxymethane, AOM)∕葡聚糖硫酸鈉(dextran sulfact sodium, DSS)報道中表明,RORγT 細胞在結腸腫瘤進展中發揮重要作用[18]。RORγTh17 細胞缺失時,結腸炎癥狀顯著,且腫瘤結節少。RORγT 細胞缺失者發生腫瘤生長減緩狀況并非為結腸腫瘤發生風險低引起的,也就是說明這類于RORγ 缺失Th17 細胞下調腫瘤細胞的增殖,RORγT 細胞參與腫瘤細胞增殖。
IL-10 可減緩胃腸道腫瘤的產生,IL-10 缺乏能加快結腸炎癥的進展,引起結腸炎上皮內瘤與癌癥[19]。CD4+、CD4+、Foxp3+T 細胞均為IL-10 來源,經移植釋放IL-10 到息肉中,預防疾病,T 細胞中消融IL-10,加快遲發性息肉的生長,繼而使息肉喪失了細胞的毒活性,變成癌癥,因干擾素γ 喪失免疫監視能力所致。
3.3 其他細胞因子在潰瘍性結腸癌變中作用
CD166 為間充質肝細胞的一種表面標記物,于結直腸癌為一類存在機體各個組織器官糖蛋白,其通過異嗜性、同嗜性黏附作用來介導細胞和細胞互相作用,其參與到機體的多個病理生理過程,于多個腫瘤細胞中呈高表達,于腫瘤的轉移浸潤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ALCAM 能可以促進新生血管形成,從而促進腫瘤細胞轉移。
趨化性細胞因子(chemokine)為具備趨化功能細胞因子,其對單核細胞、淋巴細胞以及粒細胞等發揮趨化吸引與激活功能,可使肝細胞與免疫前提細胞遷移至不同組織與器官,于器官形成與血細胞發生和炎癥中發揮“歸巢”信號的功能,而這種信號機制于惡性腫瘤的轉移過程中起著重要功能,靶器官產生與釋放特殊趨化因子經對應特殊的受體吸引附近與遠處腫瘤細胞,從而促進腫瘤細胞的浸潤、遷移。
4 小結與展望
UC 上皮內瘤屬于癌前病變,具有較高癌變風險,且隨病程遷延逐漸升高。臨床圍繞UC 上皮內瘤癌變相關研究的出發點與結局各有不同,到目前為止,對于UC、UC 上皮內瘤參與免疫調節與反應等多個機制,而關于和結腸癌發生的關聯性未闡述明確,希望能更深入地闡明相關機制、發現高敏感、特異癌前病變的指標,且可應用到臨床中提高監測篩查方式與治療藥物研發,進而抑制結腸癌相關癌癥發生,延長生存期,優化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