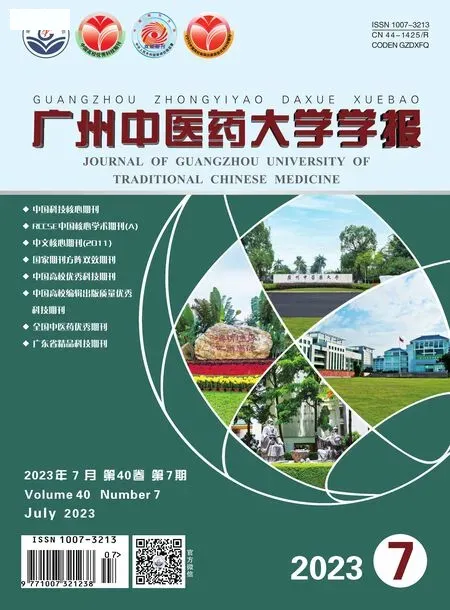劉茂才治療登革熱后繼發痙證的經驗
張佛明
(廣東省中醫院腦病三科,廣東廣州 510120)
痙證是以項背強直、四肢抽搐,甚至口噤、角弓反張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病證。痙證俗稱動風,為溫病常見的臨床表現之一。登革熱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其典型的臨床表現與中醫學的溫熱病相似。溫病可致痙,早期多數因溫邪熾盛致實風內動,后期則可因陰津虧耗、筋脈失養,引起虛風內動,表現為陰津虧虛兼痰瘀阻絡的虛實兼夾之證。
劉茂才教授為全國名中醫及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素有“腦病圣手”之美譽,善于運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診治中風、癡呆、癲癇、痙證、失眠、頭痛、眩暈等疾病。筆者有幸成為劉茂才教授的學術繼承人,侍診左右,真切感受其辨病必求其本、治病務求實效的臨證態度。以下總結劉茂才教授運用養陰熄風法治療登革熱后繼發痙證的經驗,以期為其臨床診治提供參考。
1 “陰虛風動”為登革熱后繼發痙證的病機之本
溫病是感受溫邪引起的急性外感熱病。在溫病早期邪盛階段,容易引發實風內動,多表現為高熱,頸項強直,牙關緊閉,四肢抽搐,甚至角弓反張,兩目上視,舌紅絳而干,苔燥,脈弦數有力;其病勢急驟,抽搐頻繁有力。到了溫病后期,溫邪傷陰耗氣,氣陰虧虛,筋脈失養,也可導致虛風內動,表現為形體消瘦,午后或夜間低熱,兩顴潮紅,手足心熱,口干咽燥,手足徐動,肢體不自主顫抖,或口角抽動,舌絳枯萎,牙齒枯燥,脈細數無力或結代,病勢徐緩,抽搐無力。遷延日久,則可致氣陰兩虛兼見痰濕、瘀血等留滯絡脈,演變成虛實夾雜之證。
劉茂才教授認為,痙證的病因病機主要分為外感與內傷兩個方面,其中內傷以肝腎虧虛和陰虛血少最為常見。先天稟賦不足,或久病臟腑功能失調,或情志不暢,肝火灼傷津液,日久均可致肝腎陰虛。陰虛血少多由誤治或他病所致。誤治者,即汗、吐、下太過,陰精耗散;他病所致者,即產后失血或汗證、血證、體虛等,傷精損液,導致津傷液脫,亡血失精。《靈樞·百病始生》云:“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眾人肉堅,其中于虛邪也,因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1]。劉茂才教授認為,溫病致痙是內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患登革熱后,溫邪傷氣陰,筋脈失養,若未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延至疾病后期,氣陰虧虛則引動虛風,導致溫病后期出現虛風內動。《臨證指南醫案》提出“熱盛傷津,肝風內動”的觀點,認為“五液劫盡,陽氣與內風鴟張,遂變為痙”,“津液受劫,肝風內鼓,是發痙之源”[2]。《溫熱經緯》則認為:“木旺由于水虧,故得引火生風,反焚其木,以致痙厥”[3]。
2 滋水涵木、養陰熄風為登革熱后繼發痙證之治則
因“陰虛風動”貫穿了登革熱后繼發痙證的全過程,故在治法上,劉茂才教授認為應始終不離滋水涵木、養陰熄風的原則。臨證用藥時,一方面以鉤藤、羚羊角骨(或羚羊角膠囊)、水牛角平肝清肝,或加白蒺藜、天麻增強熄風之效;另一方面,重用龜板滋補腎陰,加白芍、玄參、生地黃、麥冬、沙參、山茱萸肉等以加強養陰清熱。
溫病致痙,“陰虛”是“風動”之因,“陰虛”先于“風動”出現,而且是遏制“風動”的治療切入點。故滋陰養陰之法,適用于溫病各個階段邪熱傷陰的多種病證。津血受傷,正氣已虛,此時需用甘寒或咸寒之品,直接滋陰養陰,才能達到扶正祛邪的目的。用藥當選用滋陰柔肝之品,使真陰得復,肝木得養,虛風自熄。劉茂才教授常用龜板、枸杞子、黃精、山茱萸肉、肉蓯蓉等滋補肝腎之陰與精血;兼有陰血虧虛者,加當歸、白芍、何首烏、熟地黃以滋陰養血。在使用補益藥時,劉茂才教授始終遵循從小劑量遞增、循序漸進的原則。以北芪-黨參補氣藥對為例,針對某些患者,北芪的劑量可達100 g 以上,但剛開始的劑量多為30 g,待患者適應后才逐漸加量,黨參則多從15~20 g 開始酌加。臨證運用龜板、鱉甲、熟地黃、當歸等滋陰養血之品亦遵此理。
在痙證的不同階段,患者可兼有痰熱內擾、氣虛血瘀等證候。劉茂才教授在養陰熄風的基礎上隨證加減、靈活處方,常以雞血藤、丹參、益母草等活血補血,以茯苓、白術、陳皮、法半夏等健脾化痰,使正虛得補、邪實得瀉,共奏止痙之效。嶺南地區氣候多潮濕、溫熱,患者常兼夾濕熱,此時需因地、因時治宜,酌用茵陳、布渣葉、救必應等輕清透邪、清熱祛濕之品。
溫病常合并陽明腑實證,緣于溫熱之邪易于內傳,與腸中糟粕搏結,燥結成實。溫病所致之痙證,若合并陽明腑實證,此時應速用瀉下通閉之法,通腑法在治療中占重要地位[4]。誠如《溫病條辨》所謂:“有邪搏陽明,陽明太實,上沖心包,神迷肢厥,甚至通體皆厥,當從下法”[5]。針對溫病所致之痙證合并陽明腑實證者,劉茂才教授臨床上多辨證配合選用諸承氣湯,或者使用通腑醒神膠囊(院內制劑),根據患者病情,靈活運用口服、鼻飼、灌腸、穴位貼敷等多種方法給藥。通腑法以祛邪為務,中病即止,運用過程中需謹防過下傷正,切不可用于脫證。
劉茂才教授在其長期的臨證中,堅持用藥平和、穩中求效的基本原則[6]。注重培植人體正氣,主張治病求本、不囿表象,從病因病機及發病規律把握“虛證”。在處理扶正與祛邪的關系時,力求揆度虛實,進退有度,即祛邪時,衰其大半,注重護本;扶正時,以平為期,穩中求效[7]。虛實夾雜之痙證在臨床上是難治之證,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可見效。臨證時須細察患者的體質和既往病史,綜合考慮后方可立法處方用藥,需緩緩圖之,不可急于求成,頻繁調整治療方向,致使病情愈加復雜。
3 病案舉例
患者麥某,男,35 歲。2014 年10 月20 日初診。患者自訴于2014 年9 月22 日開始出現高熱,最高體溫達39 ℃,自服中藥湯劑(具體不詳)后于9 月26 日開始熱退,后出現惡心欲嘔、泄瀉,腹瀉約每天4 次,無肌肉酸痛,未見皮疹;10 月5 日傍晚患者開始出現神志模糊,表情淡漠,時有自言自語,無法正常對答,無肢體抽搐,無煩躁不安,急送廣東省中醫院急診科就診,查頭顱CT未見出血。登革熱抗體檢查結果示:登革病毒抗體IgM 陽性;登革病毒抗體IgG 陰性。登革熱病毒核酸檢測陽性。腦脊液壓力140 mmH2O,腦脊液常規檢測未見異常,腦脊液墨汁染色未發現新型隱球菌。腦脊液生化檢查結果示:氯化物水平為106.8 mmol/L,余項正常。血常規檢查結果示:白細胞計數為5.32×109個/L,中性粒細胞比例為72.2%,淋巴細胞比例為13.4%,血小板計數為213×109個/L。肝功能檢查結果示:谷丙轉氨酶為65 U/L; 谷草轉氨酶為41 U/L。輸血4 項均陰性。既往史:5 年前發現鼻咽癌,于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行放療及化療治療。
刻下癥見:神清,精神可,表情淡漠,反應遲鈍,言語含糊不清,頭頸部持續后仰,不能低頭,四肢拘攣,四肢間斷出現抽搐發作,發作時伴有大汗出,口張不能合,口氣臭穢,無發熱惡寒,無頭暈頭痛,無咳嗽咳痰,停留胃管,納差,夜眠可,小便調,大便不通。舌淡,苔黃,脈弦數。
西醫診斷:登革熱;腦橋中央和腦橋外髓鞘溶解癥。中醫診斷:痙證(陰虛夾熱,風痰內擾)。治法:養陰清熱,滌痰熄風,通腑醒神。處方用藥:羚羊角骨30 g(先煎),鉤藤20 g,生地黃30 g,白芍20 g,地龍10 g,醋龜甲30 g(先煎),葛根30 g,天竺黃15 g,虎杖20 g,石菖蒲15 g,重樓20 g,甘草10 g。每日1 劑,水煎取汁約300 mL,分兩次于早晚采用鼻飼服藥,連服7 劑。并鼻飼通腑醒神膠囊(廣東省中醫院院內制劑),每次3粒,每天1次。
2014 年10 月27 日二診。患者神清,精神好轉,表情較前豐富,反應較前靈敏,有自發言語,言語含糊不清,頭頸部持續后仰,可稍自行低頭,四肢拘攣,無四肢抽搐發作,口能稍微閉合,口氣臭穢較前明顯減輕,無發熱惡寒,無頭暈頭痛,少許咳嗽咳痰,停留胃管,納眠一般,小便調,大便已解。舌淡暗,苔黃,脈弦緊。辨證:氣陰兩虛,風痰內擾。治法:益氣養陰,理氣通絡,熄風開竅。處方用藥:羚羊角骨30 g(先煎),鉤藤20 g,生地黃30 g,白芍20 g,醋龜甲30 g(先煎),天竺黃15 g,虎杖20 g,甘草10 g,太子參30 g,黃芪45 g,山茱萸肉20 g,郁金15 g。每日1 劑,煎服法同前,連服7 劑。停服通腑醒神膠囊,改用鼻飼羚羊角口服液,每次10 mL,每天3次。
2014 年11 月3 日三診。患者神清,精神可,反應靈敏,對答合理,言語較前清晰,頭頸部后仰,可稍低頭,自訴頸部酸痛感,四肢拘攣,無四肢抽搐發作,口能閉合,無口氣臭穢,無發熱惡寒,無頭暈頭痛,無咳嗽咳痰,留置胃管予全流飲食,夜眠可,小便調,大便不暢。舌淡暗,苔膩微黃,脈滑。辨證:氣陰兩虛,痰熱內擾。治法:益氣養陰,清熱化痰,通腑開竅。處方:生地黃30 g,白芍20 g,醋龜甲30 g(先煎),天竺黃15 g,虎杖20 g,甘草10 g,太子參30 g,黃芪45 g,山茱萸肉20 g,枳實15 g,夏枯草15 g,黃芩15 g。每日1 劑,煎服法同前,連服7 劑。停服羚羊角口服液。
2014 年11 月18 日四診。患者神清,精神可,反應靈敏,頭頸部僵硬感較前明顯減輕,可自行低頭,對答合理,言語明顯較前清晰,口能閉合,雙上肢伸直度較前增加,可在攙扶下緩慢行走,雙下肢可自主活動,無四肢抽搐,無口氣臭穢,無發熱惡寒,無頭暈頭痛,無咳嗽咯痰,留置胃管予全流飲食,夜眠可,二便調。舌淡暗,苔膩微黃,脈滑。患者要求出院,囑患者出院后于門診調理善后。
按:本病案患者是在溫病后期熱勢已退、邪去正衰的階段發作的痙證。劉茂才教授認為,患者5年前因鼻咽癌行放化療治療,此類患者素體氣陰虧虛;本次發病以高熱起病,熱盛傷氣陰,加重了氣陰兩傷,筋脈失養,因而在溫病后期出現虛風內動。
初診時,患者以表情淡漠、言語含糊不清、全身肌肉強直為主要表現。《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暴強直,皆屬于風”[8]。此風非外風,結合患者氣陰兩虛之本,乃陰虛、血虛生風,發為本病。《金匱要略》云:“夫痙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9]。患者脈弦,符合此病癥。又《景岳全書·痙癥》云:“凡屬陰虛血少之輩,不能養營筋脈,以致搐攣僵仆者,皆是此證”[10]。患者曾有發熱,兼有放化療等傷陰耗血之舉,故類似痙證。治當養陰清熱、滌痰熄風、通腑醒神,標本兼治,虛實兼顧。
二診時,患者經過前一階段治療后,熱象明顯減輕,表現為大便已通,口氣臭穢較前明顯減輕,且全身肌張力較前下降。患者陰虛之本同前,風痰阻絡之標未去,加之患者久病臥床,正氣虧損,氣不足而經脈不通,血氣不從,往復循環,其氣日衰,故風痰內擾為之實,氣陰兩虛為之虛,仍為本虛標實之象。中藥湯劑在原方基礎上去清熱之品如葛根、重樓,增加黃芪、太子參等藥以加強益氣養陰、理氣通絡之力。
三診時,患者肌張力較前進一步降低,無肢體抽搐發作,內風已平息,但仍有苔黃、大便不暢,提示熱象仍明顯,故在前方基礎上去鉤藤等熄風之品,加入枳實等清熱行氣通腑之藥。
四診時,患者肌張力繼續下降,雙上肢伸直度較前增加,可在攙扶下緩慢行走,雙下肢可自主活動,大便已通,苔黃減輕,熱象較前減輕,病情已逐漸向愈,故囑其出院后門診調理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