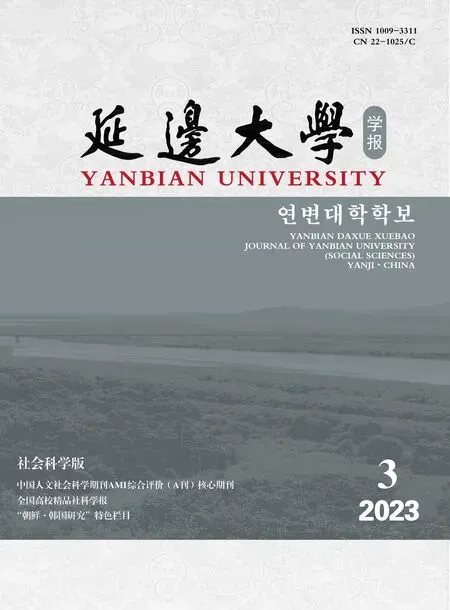新舊之間的外交轉變:從《中日修好條規》看近代早期中國對日外交
王新瑋 郭婷婷
對于《中日修好條規》的相關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30年來成果豐碩。劉世華先生提出,“《中日修好條規》基本上是相互平等的條約,表達了中國人民友好往來、和平相處的良好愿望……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第一個不要人刀壓脖子簽訂的帶有積極性的條約,從而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1)劉世華:《李鴻章與〈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第220頁。近年來,多位學者對其簽約過程、性質和影響進行重新討論。劉袁認為,《中日修好條規》“最直接的影響是重新調整了東北亞地區各國之間的關系,即打破了原有的長期存在的華夷朝貢體系,使該體系從此以后有兩個所謂的‘上國’并存”。(2)劉袁:《〈日清修好通商條規〉與東北亞地區國際關系》,碩士學位論文,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08年。廖敏淑提出,“通過梳理日本與中國的修約交涉過程,可以從修約層面來探討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因。”(3)廖敏淑:《〈中日修好條規〉與甲午戰爭——以修約交涉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6期,第85頁。韓東育指出,“條規的簽署,不但讓中方喪失了東亞的傳統核心地位,還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惡用下無法不棄琉保臺、棄韓自保直至割臺茍安。近代以降東亞世界的整體變局和日本對鄰國的侵越與壓迫,亦始自條規,成于條規。”(4)韓東育:《日本拆解“宗藩體系”的整體設計與虛實進路——對〈中日修好條規〉的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70頁。對于《中日修好條規》與其他外交條約的對比,前輩學者也進行了較為翔實的論述。(5)趙李博望:《〈中日修好條規〉與〈朝日修好條規〉簽訂之比較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延邊大學,2018年;王家耀:《從〈中德通商條約〉到〈中日修好條規〉——淺析清末外交近代化過程中爭奪話語權的實踐》,碩士學位論文,中國政法大學,2014年。本文擬通過對中日兩國在《中日修好條規》談判、議定、換約過程中關于“一體均沾”條款的爭論,探究清政府由傳統“朝貢體制”向近代外交體制轉變的歷史進程。
一、《中日修好條規》訂立過程中的爭與讓
對于建立近代意義上的正式外交關系,中日兩國均有自己的外交考量。
1868年,日本開啟明治維新的歷史進程,同年明治政府發布《外交布告》,提出日本在對外關系中面臨三方面的主要議題:第一,廢除同歐美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第二,侵占朝鮮;第三,同中國簽訂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從當時日本的國力來看,短期內同歐美列強完成修約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明治維新后,日本曾派使臣給朝鮮送去措辭強硬的外交照會,但是,由于日本照會中存在“皇帝”等名詞,被朝鮮當局退回。這一事件使日本更清楚地認識到,在中朝宗藩關系體制之下,霸占朝鮮必須取得同中國相同的地位。1870年5月,日本外務省在《對朝政策三條》中列舉了三種對朝鮮方案,明確提出“向中國方面尋求舊盟如獲成功,則朝鮮問題當無棘手可言”。(6)[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31頁。同年7月,柳原前光提出“朝鮮之事,仍北連滿洲,西接韃清之地,若綏服之,實乃皇國保全之基礎,將來萬國經略進取之基本”。(7)張景全:《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對日本外交的影響》,《日本研究》2003年第1期,第76頁。9月,日本政府以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為代表,率領使團出訪中國,向清政府提出訂約通商的訴求。
對于日本方面主動提出的修約請求,總理衙門進行了委婉的拒絕,在給日本的外交照會中,清政府認為“貴國既常來上海通商,嗣后仍照前辦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條約。古所謂大信不約也”。(8)《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133頁。在總理衙門看來,中日之間應該繼續堅持只通商不立約的傳統。但是,這一答復顯然不能讓柳原前光滿意,為完成立約通商的任務,柳原前光到訪天津,拜會初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并對李鴻章表示:“英、法、美諸國,強迫日本通商,伊國君民受其欺負,心懷不服,力難獨抗。唯思該國與中國最為近鄰,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9)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第四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頁。柳原前光的游說打動了李鴻章,李鴻章上書總理衙門稱:“若拒之太甚,勢必因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彼時再準立約,使彼永結黨援,在我更為失計。自不如就其求好之時,推誠相待,俯允立約,以示羈縻”。(10)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35頁。李鴻章希望同日本訂立條約,正式建立近代體制下的外交關系。曾國藩也認為“日本國二百年來,與我中國無纖芥之嫌……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勢難終卻”。(11)《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234頁。
經過總理衙門與地方大員的會商,清政府逐漸確定“(日本)精通中華文字,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連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輔”(12)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3頁。的總體對日外交策略。一方面,聯合日本可以打破中國的外交孤立,維持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大國地位,并防止日本同中國為敵。最先接待日本使團的署三口通商大臣成林認為,“(日本)雖難遂為我用,第恐拒之已甚,致彼舍而之他,將來愈難收拾。”(13)《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169頁。李鴻章在奏折中寫道:“日本自元代,與中國不通朝貢,今彼見泰西各國業與中國立約通商,該國亦與泰西各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似系情理所有之事。……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14)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53頁。在李鴻章看來,聯合日本可以防止歐美各國利用中日議約損害中國利益,削弱日本與歐美諸國聯合所帶來的巨大風險,為中國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順利推動內部洋務運動的發展。另一方面,聯合日本也是清政府外交的無奈之舉。柳原前光來華時恰逢天津教案爆發,在天津教案的處理過程中,法國強勢的作風給清政府各級官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俄國趁火打劫,覬覦中國新疆和東北地區,清政府短期內很難求助歐美各國。此時日本主動提出修好建交,也使清政府認為可以試圖通過日本維持中國的和平局面。
1871年,日本外交使團在伊達宗城的帶領下來到天津。伊達宗城來華后,提出了日方所擬定的條約底稿,在這一底稿中“臚列各款,其條約則抄襲布國(普魯士)稅則,章程則抄襲美國。又將去秋柳原前光等在津所呈議約底稿作為廢紙,惟事事援照泰西,未免諸多流弊”。(15)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第四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5頁。實際上這是一份不平等的條約文本,這是清政府難以接受的。
在同日本正式進行談判之前,清政府對于條約的主要內容征詢過曾國藩的意見,曾國藩認為,“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等語。尤不可載后有恩渥利益施與各國一體均沾等語”。(16)《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235頁。李鴻章也覺得“一體均沾”的條款使西方國家可以“一國所得,諸國坐而享之”,使清政府難以利用諸國矛盾謀求國家利益。曾國藩、李鴻章的建議被清政府所采納,1871年2月,清朝發布上諭,要求在對日立約談判時“體制與稅務兩端,仿照泰西之例固無不可,但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及后恩沃利益施于各國者一體均沾,以免含混……應因時制宜,不至再蹈從前隔閡覆轍,是為至要”。(17)《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二十一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24頁。在清政府看來,“一體均沾”條款比“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等各項條款危害更大,不能按照與歐美各國議約的先例與日本訂約,反映出清政府經歷鴉片戰爭打開國門后,對30年來外交政策的總結與反思。
在正式談判時,李鴻章拒絕了伊達宗城提出的條約底稿,而另行擬定了新的條約章程。在中方的條約初稿中,刪去了所有帶有“一體均沾”性質的條款。對日本來說,清政府提出的文本同樣難以接受。為此柳原前光曾致函清政府談判代表,堅決要求以中國同西方簽訂的各條約為藍本,并威脅“交際之道,只可劃一,不可特異開例,自破條規,以招彼之覬覦也。今兩國欲于天下人中特立好看字面之約,何益于事……不若姑從西人跟跡,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以穩其心之為俞也”。(18)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第四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6-367頁。
對于柳原前光的威脅,清政府也給予強硬的回擊,稱“中國非有所希冀同貴國立約,特因去歲情詞懇切……是以我中堂奏準派使前來會議……茲本幫辦等會商,擬將前送條規章程彼此再行酌商刪并,以便早日議定,如尊意必不謂然……只好仍照總理衙門去歲初議,照舊通商和好,毋庸立約”。(19)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第四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7頁。
在談判過程中,柳原前光要求“于章程內請添凡兩國準與別國優恩及有裁革事件無不酌照施準一條”。(20)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第四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5頁。對此李鴻章認為,“雖與本年曾國藩折內所指不可載明一體均沾等語措辭稍變,而命意仍同,終屬含混”。(21)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第四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5-366頁。從這一點來看,日本在“一體均沾”待遇的內容上作出讓步,至少從條約文本表面來看,已屬雙向“最惠國”的內容,但仍被清政府拒絕。
中日雙方經過兩個多月的激烈談判,反復爭論,終于在1871年9月13日正式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中日修好條規》作為近代中國和日本第一個正式的建交條約,共有18條。條約中規定了中日雙邊關系的各類要求。其主要內容大致有:第一,雙方互派使臣進駐京師;第二,兩國官員在外交關系中對等;第三,兩國互相開放口岸同對方進行通商貿易;第四,雙方在通商口岸具有領事裁判權;第五,兩國人民在對方國內禁止攜帶刀具;第六,兩國軍艦可以進入通商口岸;第七,理事官不得由商人擔任;第八,雙方應互相引渡本國罪犯。條約中規定了中日雙方應該遵守的權利和義務,也規定了中日雙方應該承擔的外交責任。《中日修好條規》是一個略帶同盟性質的條約,條約第二條規定:“兩國即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蔑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22)王鐵崖:《中外舊約章類編》,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第317頁。這一條款雖然讓日本難以接受,但是在中國方面的堅持下,仍然保留了下來。
總的來說,《中日修好條規》基本上是按照清政府的意愿進行談判修訂的,在大的原則性問題上,例如“一體均沾”待遇,在中國的堅決反對之下,沒有寫入條約。至于領事裁判權,雖然日本在中國具有領事裁判權,但由于相應的中國也擁有在日本的領事裁判權,即條約雙方互相擁有領事裁判權,雖然不符合國際法的內容,卻是相互對等的,對中日兩國之間很難說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1873年,中日雙方完成換約,《中日修好條規》正式生效,中國與日本正式建立了近代的外交關系。雙方在條約簽訂后大致實現了簽約的目的:日本在東亞“朝貢體系”中取得了同中國對等的地位,為進一步擴張掃除了障礙;清政府通過這一條約,開始了向近代外交體制的轉變,同時為自己在東亞贏得了十多年的平穩發展時期,有效地推遲了日本向朝鮮的擴張,保證了洋務運動的順利開展和深入。
二、近代外交體制下的“以夷治夷”
同治年間,清政府的實權派大都實際參與過對太平天國的軍事鎮壓,他們更早地接觸歐美各國,接觸歐美軍隊,并且曾經在實戰中配合歐美軍隊作戰。因此,對清政府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十分清楚,這就形成了他們在對外交往中力圖維持和平局面,不輕言戰事的基本主張。也正是基于這種思想,在處理同歐美的外交事宜時,清政府更希望通過利用歐美各國的矛盾,取得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這也就是傳統上所說的“以夷治夷”。
19世紀中葉之前,宗藩體制是中國社會乃至東亞地區外交關系的重要形式,“直至晚清時期,通行于東亞區域內部顯在關系原則,依然是中華中心的宗藩體制”。(23)韓東育:《日本拆解“宗藩體系”的整體設計與虛實進路——對〈中日修好條規〉的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70頁。統治者希望通過朝貢關系達成萬國來朝的景象,以彰顯國力的強大。自明清以來,中國一直是東亞政治外交活動中唯一的中心。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后,中國作為東亞單一政治核心的地位開始發生動搖。
日本來華立約恰逢天津教案,這時的中國在外交上面臨許多新的問題。李鴻章曾在奏折中寫道:“強臨四逼,蠶食鯨吞,外國強兵利器百倍中國,實開辟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24)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14頁。而積極推動同日本修約建交,則反映出清政府在應對新的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中的具體辦法。在洋務派官員看來,與日本正式建立對等的外交關系,是傳統“和戎”政策的基本表現形式和“以夷治夷”思想在近代東亞外交中的一次嘗試。
在清政府看來,國家已經到了危機存亡的關鍵時刻,必須進行改革。他們在中國內部掀起洋務運動,從西方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希望通過技術革新帶動清王朝國力的增長,挽救民族危機。這種策略與同時期的日本相比,是一種短期見效的自強方式,能夠幫助國家通過快速提高軍隊戰斗力增強國家的總體實力。而與內部政策相對應的,是在對外政策中的“和戎”方針。所謂“和戎”,就是在對外交往中采取守勢,不輕言開戰,維持和平的外交局面。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和戎”兩個政策互相支援,互相補充。
而“以夷治夷”則是“和戎”的具體手段和措施。清王朝積極響應日本的訂約請求,正是其“以夷治夷”政策的具體表現。李鴻章對于日本很早就開始留心關注,這其中既有對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習俗的認識,也有對于日本自立自強手段和方法的認識。李鴻章雖然在洋務運動中采取了一條先軍事后經濟的自強方法,但是,他仍然十分欣賞日本相比于中國更為全面的改革。他在給曾國藩的信函中曾經提道:“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2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214頁。
然而,此時的日本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國力雖然有所增強,但其軍事實力相對于清王朝并不具有優勢,如果貿然同中國開戰,很難取得勝利。這一情況在1874年日軍入侵臺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臺灣一戰,日軍死傷500多人,花費軍費700多萬兩白銀,卻沒有占到任何便宜。中日兩國的國力差距十分明顯,這也使清朝代表在談判過程中可以堅持強硬的態度,同日本進行周旋,在涉及核心利益的條款上毫不退讓,也才能最終促使日本方面接受以清政府提供的條約文稿為底本進行談判。
清政府通過與日本訂立條約建立外交關系,既顯示出了對外“和戎”的主張,也體現了“以夷治夷”的思想主張,同時,也體現了洋務派追求平等外交機會的決心。在《中日修好條規》談判進行到僵局的時候,日本曾經希望借助英國的力量逼迫中國應允涉及“一體均沾”內容的條款。1871年7月,日本通過外交照會的形式希望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出面,對李鴻章施加壓力。威妥瑪也確實致函李鴻章要求見面,但被其委婉地拒絕了。隨后,威妥瑪直接致函總理衙門表明意圖,對此,李鴻章態度依然強硬,他上書總理衙門希望總理衙門拒絕威妥瑪的提議,稱“東約鐵案已定,縱欲倚西人為聲援,斷不能轉白為黑。若果威使真于事后饒舌,應請尊處囑其徑向弊處辯論,鴻章當有以折之”。(26)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3頁。此時的清王朝,國力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得到極大的發展,也使清政府敢于拒絕英國公使的威脅,在《中日修好條規》談判商定的過程中保持自身的原則,維護自身的利益,捍衛了主權。
同時,《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也表明,清王朝并不愿主動放棄東亞各國宗主國的地位。清朝自從1644年入關以來,逐漸繼承了漢族政權建立的以“朝貢體制”為核心的宗藩外交體系,在二百多年間,清王朝屬國眾多,在東亞宗藩外交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成為東亞外交體系中的中心。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向中國朝貢,清朝作為宗主國給予屬國相應的保護。日本希望同中國簽訂條約建立外交關系,很大程度上是為侵略朝鮮半島,對此,清政府也在條約談判中進行了預防,《中日修好條規》明確規定“嗣后,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27)王鐵崖:《中外舊約章類編》,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第317頁。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希望通過條約的形式保障朝鮮的安全,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同時也再次明確了中國在東亞宗藩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但是,這一條款也在事實上表明中國承認了日本在東亞與自己對等的地位,為日后日本侵略琉球群島、朝鮮半島提供了口實。
《中日修好條規》的準備、談判、商定、簽約過程,無不體現了洋務派“以夷治夷”為核心方式的“和戎”政策。通過這一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表達了自身希望通過建立新的對外交往體系來改變外交政策,建立平等的外交關系,創造穩定和平的外交環境,為國內洋務運動的發展爭取時間,增強國力,進而建立同西方平等的外交體系,實現中國的自強。
三、議約后“和戎”與“洋務”的統一發展
《中日修好條規》于1871年正式簽訂,1873年清政府與日本政府進行換約,條約正式生效,這也標志著中國與日本正式建立近代外交關系,兩國關系進入新時期。
在清政府看來,日本是清王朝在當時國際關系之下實施“和戎”政策的唯一選擇。第一,聯合日本,可以避免日本成為歐美諸國在東方的盟友,避免日本加入侵略中國的統一戰線,在東亞形成相對穩定和平的外交環境;第二,從當時中日實力對比來看,中國選擇同日本訂立條約,建立外交關系,可以避免同歐美強國的直接對抗,增加訂立平等條約的可能性,減少中國外交上的損失,同時也能夠更好地顯示清政府希望追求平等外交的思想;第三,從當時東亞的國際關系來看,日本如果想要在東亞有所作為,仍然必須要取得中國的支持。
通過訂約談判,清政府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日本很難作為一個可靠的盟友與中國進行聯合,共同對抗歐美列強。早在《中日修好條規》簽訂之前,李鴻章就曾在同恭親王奕的信中對中日兩國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雖對日本的發展充滿贊賞之情,但也對日本快速發展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于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數”。(28)《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169頁。可見,在清政府看來,中國與日本能否在東亞的外交關系中保持和平友好,主要在于中國是否能夠自立自強。
中日雙方在建交談判時,日本代表的表現給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朝官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這次談判,他們更加感覺到應對日本的緊迫感。李鴻章在《中日修好條規》簽訂后,多次上書清政府和總理衙門,希望能夠增強對日本的重視,表示“日本自與西人訂約,廣購機器兵船,仿制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色技術,其志固欲自強以御辱”。(29)《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329頁。在給友人的信中,李鴻章也曾提到“日本頗為西人引重。其制造鐵廠鐵路練兵設關,一仿西人所為。志不在小”。(30)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6頁。這么做,也是為了提醒清政府,能夠正確地認識周邊國際關系和國際形勢,增強清王朝自強御辱的決心。
《中日修好條規》簽訂后,清政府同樣對洋務運動進行反思改進。洋務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興起,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王朝戰敗為止,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在19世紀70年代之前,洋務運動以“自強”為口號,主要發展與國家機器相關的軍火、造船等工業項目,禁止民間創辦工廠,很少發展民用設施。正是在這種單一的軍事工業的發展帶動下,清王朝的軍事實力顯著提升,但同時,單一的軍事發展路線也使洋務運動的發展顯得后勁不足。
為了在同日本的談判中不處于弱勢地位,李鴻章等人對日本進行了深入研究,也對日本的變法圖強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在《中日修好條規》換約的當年,洋務運動的重點開始發生轉變。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政府先后創辦一系列民用工業,使洋務運動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也更加系統。
《中日修好條規》換約后,清政府在軍事布局上也相應地進行了調整。作為談判代表,李鴻章對于日本侵略朝鮮的設想是比較清楚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只有強大的國力才可以震懾日本。雖然他極力主張聯合日本抗衡歐美,但他并沒有在軍事上放松對日本的警惕,在談到聯合日本對抗歐美的計劃時,李鴻章很冷靜的表示“以東制西之說本不足恃,中土不能自強處處皆我敵國,又何東西之分”。(31)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6頁。1874年,清政府正式啟動了新式海軍的創建工作,1888年,北洋艦隊正式組建完成,對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震懾日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上可知,條約簽訂后,清政府官員很清楚地認識到,僅靠《中日修好條規》一紙條約,并不能真正地建立起中國與日本的牢固同盟,這種同盟關系在實際的外交事務中能產生多大的作用,更多地仍是看中國的發展。在條約簽訂后,李鴻章曾感慨道“愿從此各自強兵固本。不獨東人無慮,即西人亦不多覬覦。若仍因循虛飾,本自先拔,內患已增,又何論東西洋之分乘哉。數千年之大變局,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爾”。(32)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27頁。
四、結語
《中日修好條規》是中日兩國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反映了清王朝開始反思宗藩體制的弊端,同時這也是清政府在國際交往中逐漸放棄宗藩體制下朝貢形式轉向近代外交體制的一次嘗試。自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至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簽訂,清政府先后同英國、美國、法國等13個歐美國家簽訂《通商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經過30年近代外交的洗禮,清政府逐漸認識到“一體均沾”條款的危害,但歐洲各國間利益交織,清政府難以實現“以夷制夷”的外交目的。
清政府在同日本商定建交條約時,極力避免出現“一體均沾”等字樣,這固然保證了中國的利益不被日本損害,但同時也喪失了通商時在日本獲得更大權益的機會。由于清政府認識到“片面最惠國”待遇對中國的危害過大,清政府大員對“最惠國”待遇產生誤解,在對日議約時沒有任何回旋余地。隨著清政府對外交流的增多,對近代外交關系逐漸明確,對“最惠國”待遇的理解有所變化,因此在1873年中秘建交時明確“今后中國如有恩施利益之處,凡通商事務,別國一經獲其美善,秘國官民亦無一不一體均沾實惠;中國官民在秘國,亦應與秘國最為優待之國官民一律”。(33)王鐵崖:《中外舊約章類編》,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第341頁。1880年,中巴建交時同樣約定“嗣后兩國如有優待他國利益之處,系出于甘讓,立有專條互相酬報者,彼此需將互相酬報之專條或互訂之章程一體遵守,方準同沾優待他國之利益”。(34)王鐵崖:《中外舊約章類編》,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第395-396頁。即使在甲午戰爭后,清政府依然堅持將雙向“最惠國”待遇寫入條約,1898年清政府同剛果建立外交關系,雙方約定“行船、經商、工藝各事,其(剛果)待華民與待最優國之民人相同”。(3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類編》,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第785頁。1899年,在與墨西哥議約時也規定兩國“永敦友誼,與相待最優之國人民同獲恩施權利”。(36)王鐵崖:《中外舊約章類編》,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第934頁。
清政府改變對最惠國待遇的認識,一方面是由于隨著對外交流的增多,對近代外交關系有了更深的理解,逐步放棄天朝上國的觀念,追求平等的外交利益,建立平等的外交關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王朝自洋務運動開始后國力逐漸提升,在對外關系上有能力爭取自身的利益。這反映出清政府對“一體均沾”條款和對最惠國待遇由最初的反感到逐步接受,并為自己爭取外交權益,體現了清政府近代外交關系的逐步成熟。
總之,《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在晚清是一件大事,它標志著清政府在東亞地區的外交觀念由“萬國來朝”的宗藩體制向近代外交制度轉變,基本實現了將洋務運動與對外“和戎”相結合,爭取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促進綜合國力發展,內外相結合的總體外交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