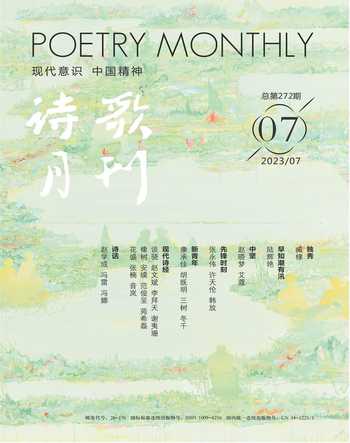巫山來信(組詩)
冬千
火山石
歷史是多么有限的空間,而一次爆發
握緊雙拳的巨石將膨脹,出口變得狹隘
作為一種孤獨的存在,絕對地成為
倒影的面具,火塘假裝是鏡光,使牛羊
和牧歌的方言由此清亮,偶爾我也
坐在石上,不停更換坐姿,找到最痛的
那種,像鸛鳥啄住了一只木籠,兩塊
蟲蛀的拼圖,裂紋在吻合的須臾
就造成了我們和余光仍有一道背影的
距離,為此我總往這座火山的一小
部分灌水,熄滅無意中復燃的舊情
甚至植入水藻,放進魚缸
我越來越討厭做一個舊派的人
除了自己的所有事物,仿佛都在趨于
那個隱遁的極端,我早已習慣像潛浪
暗礁,獨立而內斂著生命的激情
“牛蒡和貓頭鷹外,別無其他珍物”
夏霽書
云朵撒下那些珠子,如此清澄又易碎
擁向土壤,以維持水的完整
牛肝菌從濕透的木樁隙間
撐開了身體
像折疊的紙張起翅膀
“讓它自由,變成蝴蝶”
蟲類世界的箴言,不止一次
被我們用來安慰。菌群在低處
那些傘篷覆蓋的,又是一個微茫
的世界,野蘑菇護佑著
螞蟻,它們身懷知足的心情
遷徙繁衍,憑雨止渴
手持電筒的少年,出沒在凌晨
謹慎地刨出菌菇,再把土填回去
并不是葬下什么,我們感恩
所有失去的殖土,轉晴之后
山地松軟,是凈土放下了戒備
少年游
騎行途經這段路,每次我都小心翼翼。
道旁側柏長著蜂巢,和雛鳥
在疾馳的貨車盲區里
啄食面包糠,一旦有羽毛凋零了,
我就仿佛看到滿地刺透我的箭鏃。
受過多年時間的蜂蜇,騎行的
我,穿過這棵行道樹時,仍
不自覺地減速,仿佛不遠處
夢中的孔雀,在朝我開屏,
每根羽毛,都有感泣和自尊的形態。
巫山來信
掠過他頭頂的,幾對飛燕,還有火燒云
“它們一直燃燒,就好了。燒到天邊
至少要,你所及之處。”如果一直這樣
浮云比櫻花永恒。從中他得到
愛的啟示。他跑進澗底,讀寫給她的信
向瀑布后的聽眾。仿佛如此,回信
才足夠及時。流水反復地念
幻聽成雨聲亂作一群細蟻,排好隊搬家
在土地沾濕之前,他夢見它們的秩序
竟然情話般完整。生活將在新的穴道開啟
霧起山中,空蒙如檸檬水
塊壘凹陷,僵涸的心事被澆釋
相愛的過程,一個燈謎的小曖昧
認出會更艱難。水汽懷疑我們
是否僅是露水的關系。退去的時候
我們呆在原地。云的余燼被吹散
是花神降臨,他的手心被誤認為雄蕊
“我知道如何愛了,就這樣,一瓣一瓣的
沒有放棄,那意味著枯萎。”
分水嶺
爬上絕頂,面前是陽宗海
身后是松茂水庫,曾經
欺負我的那些烏云也經過這里
雨滴在兩條歧途上無法三思
曾經我們的郊游隊伍也經過這里
我們分頭去拾柴禾,我們一直
沿著泥流,邊哭邊奔跑,邊猶疑
在距離不明的兩片水域之間
架火取暖,柴焰像沉默中
掙扎的信號,直到今天
也沒有滅,畢業后每當我登上
一座分水嶺,似乎就聽到
有人呼救,我躺在嶺中的空地
想象大霧里一朵芳華不再的花
隨風吹熄了淡水湖上的煙火
幾縷煙乘風而起,在嶺頭見面
動物園
后來我越來越討厭,用嗜好和審美
去成立一種規矩,尤其在柵欄里
那些鐵籠鉗制了犄角和根須
蔓延整個森林內部,就像那些年
要講的每句情話,都要悄悄地說,以致于
你每個富于觀賞性的動作
都被我看作手語,一句口齒不清的話
在長頸鹿的胃中反芻著
我趕了夜路來這里,把月光烙在
我的鏡框、臂章以及一切反光
的事物上,劣跡斑斑
最憂慮的是禽類
我都在靠近,逼它們撲騰起來
而另一個受驚者,時而
是如虎添翼的我,時而
是插翅難飛的我
不出意外的話,我一直以
后者的身份,混在人群里,一聲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