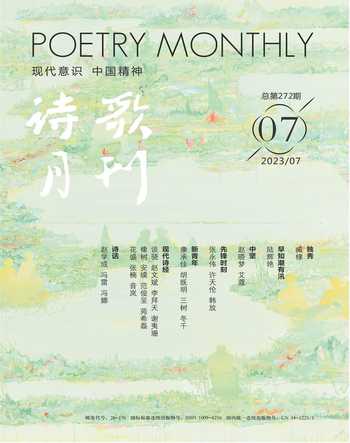花燈觀止(組詩)
臧棣,1964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研究員。曾獲昌耀詩歌獎、屈原詩歌獎、魯迅文學獎。著有詩集《燕園紀事》《騎手和豆?jié){》《情感教育入門》《沸騰協(xié)會》《詩歌植物學》《精靈學簡史》等。
稻草
風中的顫栗。如果不借助
最后一根稻草,時間的面龐
凸起過多少命運的弧度,
幾乎無法辨認。
風中的顫栗也包括
伸長的過程中,激烈的抖動
并不僅限于你的手;
但愿內(nèi)心的掙扎也阻止過一種塌陷。
黃昏的時候,你看到的
每一朵云,都是一桿膨脹的秤。
猶疑之際,心中的幾樣東西
已被輕輕稱量過。
譬如,金黃的背影早已被飛鳥縮小成
無數(shù)的小麻點。論清晰的程度,
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最后的稻草;
一旦松開,鳥屎就會假冒運氣。
兩斷
鋒利地解決。仿佛有
一種粉碎性代替你抓住了
晦暗的宇宙中一個可疑的重點。
十年后,時間的幽靈
已是上好的涂料,效率很高,
駭人的疤痕會自行拼湊
美麗的圖案,痛苦蛻變成故事。
如果只是一把刀,那些聲音
包含的絕望,會持續(xù)反彈
生活的諷刺對你的特別眷顧。
激烈的動靜呢?如果只是
脆斷了兩次,偉大的遺忘
會以你為新的療效,去展示
影子的秘密。但事實上,
那斷裂的物,幾乎無法命名,
典型于無形對有形的糾纏,
不只是制造了容易混淆的眾多碎塊,
不只是結(jié)局已經(jīng)消腫;
依然活躍的,也不只是忽明
忽暗的,一個消息對你的過濾,
而是堆積中的積木,
甚至擺脫了看不見的手,
開始向你頻繁取經(jīng)如取景。
良夜
心潮漫卷,一個感嘆
從坎坷的糾纏中脫口而出。
比我們更早成熟的有些果實
像極了夜晚的星星。
命運的黑暗被重重樹影
分散在前方,野鳥和夜鳥
仿佛在共有同一個化身;
或者僅僅因為你,鳴囀比婉轉(zhuǎn)更傾心。
良人難遇。但其實不如借水月
看清自己。換一個角度,黝黑的淺浪
已抹平了很多事情。能認出良夜,
也算沒看錯一個出發(fā)點。
迷途
霧已經(jīng)散去,但后遺癥還在。
絮狀情緒里有太多的繩子,
卻找不到適合的對象。
說是徘徊,卻怎么也湊不齊
幾個回合。紅墻固然醒目,
藍瓦卻少見。只剩下
偏綠的時間還算色差穩(wěn)定。
冷風斜吹,方才注意到
墻頭草不一定都長在斷墻上;
石縫里既然能蹦出
故事的主角,環(huán)境應該
也很營養(yǎng)。是的。目送你的時間
被拖得太久了,已出現(xiàn)銹斑。
一開始,迷途非常確定;
影子的告別,時而輕飄,時而焦灼。
一旦消失得太徹底,
誰更有資格判斷迷途,
誰比誰更迷途,都還不一定呢。
如此,幸福的曖昧
有點像非要從道德的狹隘
擠出新鮮的羊奶。
芬芳
矯健屬于你,但不論如何飛奔,
你都不能把它帶走。
赤誠屬于你,巖石的靜寂屬于你,
灌木背后,你脫光衣服,
裸體僅次于天體,
但它不是水,它的浮動
不同于波浪對人的暗示,
你無法浸潤于它的濃烈。
漫溢在自然的喜悅中,
散發(fā)出的氣息,超越你的世界觀里
有一個始終新穎的痛苦。
琴弦準備好了,但任何彈奏,
任何共鳴,都無法取代它的緘默。
刀光錚亮,無論從哪個角度,
無論多么用力,猛砍或斜刺,
你都不能把它一分為二;
那樣的裂縫,對你而言,是創(chuàng)口,
對它來說,從來就不存在。
鮮明的肉感已經(jīng)被轉(zhuǎn)化,
你不能用叉子插住它,
也不能用繩子將它捆緊。
即使給你一個密不透風的口袋,
你也不能將它封閉在其中。
甚至非凡的記憶,也不一定可靠,
你的淡漠不會對它構成恥辱。
現(xiàn)在,你知道,我所說的魂魄
大致是什么意思了吧。
我的針眼
從灰燼中抽出手心,
夜晚的孤獨像安靜的鞭子,
垂掛在你的無知中。
如此置身即如此幽深,
像神秘的愛已經(jīng)漸漸冷卻。
上升時,星光很新鮮,
黏黏的,像是從夢的縫隙里
分泌出了大量的防腐液。
下沉時,傷痛中的刺痛,
尖銳于每個人都有一個無法逃掉的
無形;唯一的安慰來自
朋友口中,還有很多地方,
天涯比起芳草,一點也不虛無。
失敗的愛,也很講究口吻,
時常會突起一種陡峭,
深邃得像綴滿白霜的懸崖。
兩種可能性,都將你視為
必須的對象。痛苦比沙子積極,
因而從告別的深淵中
得到一個熟悉的解釋,離不開
丹麥人索倫·克爾凱郭爾。
秋天的氣息浸透在月光中,
可以這么認為嗎?有的時候,
人的恐懼會完美于
你的顫栗;正如此刻,
巨大的夜晚不過是我的針眼。
騎桶人協(xié)會
冬日收緊了北方,
但你看不見那些網(wǎng)眼;
隱秘的情緒被光禿禿的樹梢
挑進鉛灰的記憶。而悲觀
也可以是去年揪下的
已經(jīng)干透了的一撮棕熊胸毛,
標志就是,即便是多云天氣,
房間里的光線也很好。
經(jīng)過了你的稀釋,永恒才靠譜;
鐘聲源于內(nèi)心的回音——
怎么聽,都像是“很抱歉,我暫時
還無法告訴你,騎桶的理由”。
我不缺煤,我的身體里
有的是烏黑的石頭。
任何時候,和愛有關的寒冷
都是一場誤會。沒有蝴蝶,
就像椅子摸上去有點冰涼,
但你依然可以問:你想跳舞嗎?
舞會開始后,我會騎著桶
來收拾我的誤會。裝沒裝過百合花,
就是不一樣。忘掉那些道具吧。
畢竟,百合花是用來分神的。
迷航
比起迷途,它過濾了
更多的生與死;更成熟的困惑,
以及更無用的安慰;
也包括拔去那些毛刺后,
更純粹的回憶;甚至
從未涉足過的小鎮(zhèn)
也回蕩著你的口哨。
哪怕只有片刻很生動,
也意味著神秘的值得。
再往后,更多的經(jīng)歷
只意味著,每個角落,
從未有過的飄墜感,
都像無形的火焰,串連起
意識的旋渦。黑暗中的尖叫
仿佛也加入過一陣清洗;
效果接近底片還在滴水——
盡管年輕,男人和女人
彼此摟緊,狠狠地模糊在
同一個漂亮的側(cè)影中。
邊界已經(jīng)消失,生命的黑暗
突然回歸原始;接著,
被擴大成無時間的懸念。
每個可見的星辰都在暗示
你身體里的器官
都已在更陌生的黑暗中
被一一對應過。更突兀的感嘆,
人,怎么可能沒有翅膀呢?
那不過是世界的偏見
一直在嫉妒人的永生,
誤導了你我的《變形記》。
天鵝不需要被純潔
到碧波為止。憑借
一個獲得了廣泛認可的影子,
雪白將寧靜擴散;
雪白來自它的奉獻,不摻雜
純潔是否過度,也不焦慮
純潔的神話是否道德;
效果很明顯,高貴的寧靜來自
另一個世界已被悄悄激活。
你好像也奉獻了心中的蕩漾,
卻無法融入它的節(jié)日。
還有什么需要顛覆嗎——
假如你已懂得:每次見到它,
真身也好,影子也罷,
那一天,都會成為雪白的儀式。
優(yōu)雅的警惕,自始至終
都以你為側(cè)影。神秘的距離
保持得很好;不減弱,
也不見怪,尤其不反射
你的渴求對它的純潔的投影。
第一件事情,如果真的你學會了,
它就不再是純潔的化身。
感謝空氣。感謝美好的走神。
幻覺消失后,它會領你去參觀
世界究竟美在何處。
花燈觀止
燦爛的燈火確實刷新了
什么叫很外向。荷花燈勾魂
冬天里的夏日印象,
龍燈看上去有點草率,
但閃爍中,也有彩虹的影子,
且氣勢已貫穿了氣質(zhì);
甚至人都做不到這一點。
光線飄忽的蝴蝶燈里
并不確定多少人已經(jīng)化蝶。
一旦被觸動,冰也很微妙。
兔子燈最精通此刻的時間倫理;
不像兔子,不假裝栩栩如生,
兔子的秘密才有機會悟到
有一種精神果然很有趣,
一直渴望將你滲透到夢的底部。
從不同的側(cè)面,肆虐的寒冷
不得不委屈于燈下黑;
雖不透明,卻被欣賞到
有不止一個偉大的漏洞。
按比例,人也是我的漏洞,
如此,滲出的光叫停了
騙人的魔術,將節(jié)日的道具
還原為線索,很晶瑩。
有不有心,就看誰在你身邊了。
愛者入門
每一次,剝離都很洶涌,
近乎噴薄的黎明,將黑暗和光明
在我們的身體里分開。
她即他,雌雄同體
即便很激烈,也不過是
太偶然的借用。神借用過天鵝,
你借用過仙鶴。兩只箭,
沿著同一個洞孔,穿過靶心,
將無限的愛欲縮短在
有限的表情中。雕鑿之后,
光滑的大理石,試圖將他永遠
定格在一個堅實的形象里;
抑或,從更多的側(cè)面看,
她的凝固,復活了更光滑的
石頭的呼吸。這之后,還需要
一次更幽深的剝離,才會醒悟到
那些出色的雕像,實際上
并未捕捉到它的真相。
它更信任無形,尤其是
你的無形最好多于你的真容。
最近即最遠,顛覆多么溫柔;
它深藏在你的身體,構成了
一次神圣的埋伏。僭越已不太可能。
不必幻想可以取代它;
即使你穿戴更多的華麗,
將自己的外形擴充到非常完美,
你也無法冒充它。甚至
時間的神話也不能令它上當。
記住,最好的結(jié)果,你即我,
已經(jīng)是一次很好的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