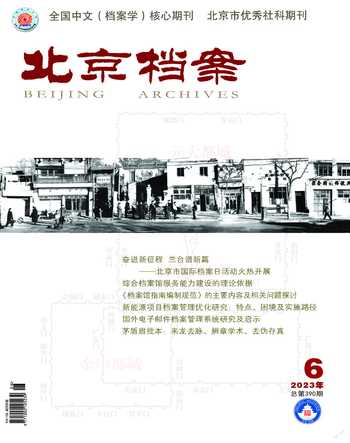梁啟超與晚清西學(xué)翻譯
伍媛媛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思想家、翻譯家、史學(xué)家,是“戊戌變法”的領(lǐng)袖之一。作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領(lǐng)域開啟新風(fēng)氣的一代大師,面對(duì)中華民族未有之變局,梁啟超提倡西學(xué),極力推動(dòng)外國著作的翻譯,以期“興民權(quán)”“開民智”。值此梁啟超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特根據(jù)晚清檔案記載,追記梁啟超致力西學(xué)翻譯的歷史片段。
一、譯印書報(bào)的倡議宣傳
梁啟超的譯書思想,源于強(qiáng)學(xué)會(huì)對(duì)譯書的重視與提倡。1895年前,我國翻譯的西學(xué)主要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的著作。甲午一役失敗,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jī)。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認(rèn)為,中國戰(zhàn)敗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軍事技術(shù)的落后,而是政治體制落后所致。于是,他們主張學(xué)習(xí)宣傳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的進(jìn)步思想,進(jìn)行政治改良。為了號(hào)召更多有識(shí)之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于1895年11月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強(qiáng)學(xué)會(huì)。強(qiáng)學(xué)會(huì)倡導(dǎo)西學(xué),主張譯印圖書,傳布要聞;出版報(bào)紙,刊布新聞;購置圖書,設(shè)圖書室。在這期間,梁啟超“居會(huì)所數(shù)月,會(huì)中于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余日盡瀏覽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1],從而引發(fā)了對(duì)譯書的關(guān)注。
強(qiáng)學(xué)會(huì)在遭到清廷的封禁后,梁啟超深感時(shí)局維艱,風(fēng)氣未開,于是將注意力轉(zhuǎn)向辦報(bào),以開民智。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等共同創(chuàng)辦《時(shí)務(wù)報(bào)》,汪康年和梁啟超分任經(jīng)理和主筆。梁啟超在《時(shí)務(wù)報(bào)》發(fā)表了60篇慷慨激昂的文字,“他利用這一宣傳陣地,較全面而系統(tǒng)地宣傳了他的變法主張、文化追求、改革內(nèi)容和具體思路”[2]。該報(bào)為旬刊,每期3萬余字,設(shè)有“西文報(bào)譯”“域外報(bào)譯”“英文報(bào)譯”專欄,廣譯五洲近事。梁啟超在其中多次呼吁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如刊登于《時(shí)務(wù)報(bào)》第8期的《西學(xué)書目表序例》一文,對(duì)中國近代譯書史做了系統(tǒng)梳理和研究,指出“國家欲自強(qiáng),以多譯西書為本;學(xué)習(xí)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3]。在《時(shí)務(wù)報(bào)》第45期中,梁啟超撰寫了《讀〈日本書目志〉書后》,再次提到“今日中國欲為自強(qiáng)第一策,當(dāng)以譯書為第一義矣”[4]。他將興西學(xué)與譯西書作為維新變法之重、救國之道,認(rèn)為此舉必將影響深遠(yuǎn)。
二、大同譯書局的實(shí)踐嘗試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清廷掀起了“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其主張之一就是創(chuàng)辦西式學(xué)堂,培養(yǎng)外語人才。最初,清廷僅有同文館及江南制造局等幾處譯印西學(xué)之書,所譯之書僅數(shù)十種,“且皆二十年前之陳編”[5],不敷使用。1897年9、10月間,梁啟超在多方努力下,于上海南京路創(chuàng)設(shè)了大同譯書局,康廣仁任經(jīng)理。梁啟超在《大同譯書局?jǐn)⒗分蟹Q,此舉是促成維新變法的關(guān)鍵一步,“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
由于日本明治維新時(shí)期曾翻譯了大量資產(chǎn)階級(jí)思想啟蒙著作,加之清政府于1896年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xué)生,梁啟超認(rèn)為,譯介西方社會(huì)科學(xué)名著,從日文間接翻譯是一條捷徑,他提出“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xué)為先,而次以藝學(xué)”的翻譯宗旨,具體方法為“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來變法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xué)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wù)書,以興中國商學(xué),挽回利權(quán)。大約所譯先此數(shù)類,自余各門,隨時(shí)間譯一二,種部繁多,無事枚舉。”[6]
大同譯書局在開辦第二年奉諭改為官書局,后因戊戌政變失敗而被迫停辦,但在這一年中陸續(xù)出版了《俄皇大彼得變政考》《意大利俠士傳》《日本書目志》等書,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huì)學(xué)說、政治制度,為中國人了解世界、認(rèn)識(shí)時(shí)局提供了精神食糧。
三、變革中擬定《譯書局章程》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光緒帝詔書里強(qiáng)調(diào),“嗣后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fā)憤為雄,以圣賢義理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xué)之切,于時(shí)務(wù)者實(shí)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jīng)濟(jì)變之才。”[7]
6月13日,翰林院侍讀徐致靖上奏,向光緒帝舉薦“維新救時(shí)之才”,他提到梁啟超“英才亮拔,志慮忠純,學(xué)貫天人,識(shí)周中外,其所著《變法議》及《時(shí)務(wù)報(bào)》諸論說風(fēng)行海內(nèi)外,如日本、南洋島及泰西各國并皆推服。湖南撫臣陳寶箴聘請(qǐng)主講時(shí)務(wù)學(xué)堂,訂立學(xué)規(guī),切實(shí)有用,該省風(fēng)氣為之大開”,建議“或置諸大學(xué)堂令之課士,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施裕如,著效甚速。”[8]當(dāng)日,光緒帝諭令“著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察看”[9]。總理衙門察看后,認(rèn)為梁啟超“平昔所著述貫通中西之學(xué),禮用兼?zhèn)洌瓰橛杏弥拧!盵10]
與此同時(shí),設(shè)立譯書館以開風(fēng)氣啟民智已然成為一些朝中大臣的共識(shí),如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楊深秀認(rèn)為,“言學(xué)堂而不言譯書亦無從收變法之效也”,他提出,將泰西、日本各學(xué)精要之書可盡譯之,“而天下人士及任官者咸大通其故,以之措政,皆有條不紊”。[11]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李盛鐸也請(qǐng)旨“開館專辦譯書事務(wù),遴調(diào)精通西文之翻譯數(shù)員廣購西書,分別門類,甄擇精要,譯出印行,以宏智學(xué)”。[12]對(duì)此,總理衙門議奏,肯定了譯書的必要性,“今當(dāng)更新百度之始,必以周知博采為先”,同時(shí)也提出,如另設(shè)譯書局,“易致復(fù)出,徒費(fèi)無益”,建議北京的譯書局“可與上海聯(lián)為一氣”,由梁啟超辦理,“所有細(xì)章皆令該舉人妥議”。[13]
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梁啟超向光緒帝提出了開啟民智的方案,光緒帝賞予其六品官銜,并令其辦理譯書局事務(wù)。8月16日,梁啟超擬定《譯書局章程并瀝陳開辦情形折》[14],由吏部尚書孫家鼐代奏。在這份奏折里,梁啟超對(duì)譯書的原則、譯書局的設(shè)置及經(jīng)費(fèi)來源都做了規(guī)劃。
一是譯書原則,梁啟超認(rèn)為以往所譯之書,多為兵制、醫(yī)學(xué)類的圖書,學(xué)者并不能真正悟出西方富強(qiáng)之本,他提出譯書應(yīng)“先政而后藝,先總義而后專門,庶幾條例本末粲然具見。”梁啟超將翻譯圖書種類按輕重緩急的次第順序做了規(guī)劃:第一,“西國富強(qiáng)由于內(nèi)政修明,今當(dāng)首譯其政治學(xué)、憲法學(xué)、行政學(xué)、律例學(xué)各書”;第二,“西國富強(qiáng)由于變通盡利,今當(dāng)多譯其史志,以觀其沿革得失之跡,其各國名人傳亦當(dāng)搜譯”;第三,“西國各省各部之章程皆屢經(jīng)損益,密之又密,今當(dāng)廣搜多譯,俾他日欲辦某事,即可酌照某事之章程施行”;第四,“富國之學(xué)全恃開源,今當(dāng)廣譯農(nóng)政、礦政、工政、商政之書,以資取法”;第五,“各種藝術(shù)皆以格致為根本,天文、地質(zhì)、聲光化電各書,舊有譯本,今專采其新出者譯之”;第六,“各國蓄志積慮窺伺東方,今當(dāng)取其論中國情形各書盡譯之,悉其陰謀,借以自警”。因日本已譯出西書六十余種,他建議“先由東文轉(zhuǎn)譯,其事更捷,至一年以后然后譯英法各文”。
二是設(shè)立譯書局的內(nèi)部機(jī)構(gòu),包括“總辦一人,坐辦二人,總翻譯一人,東文翻譯四人,英文翻譯四人,法文翻譯二人”。在譯書局之外,另設(shè)翻譯學(xué)堂,培養(yǎng)翻譯人才,學(xué)堂“設(shè)總教習(xí)一人,其分教習(xí)即以各翻譯兼充,校勘六人,鈔寫十人,司事四人”。學(xué)堂設(shè)東文、英文、法文三館,其學(xué)生分為兩種。對(duì)“中學(xué)頗深,曾多閱譯出各西書,而未通東西各文者”,則教授東西文。對(duì)“已通東文、西文,中學(xué)尚淺者”,則教授中學(xué),梁啟超認(rèn)為,“兩途并進(jìn),則成就譯才自易”。
三是譯成圖書的使用,梁啟超提出,譯出各書擬寫書目提要,加以裝潢。圖書分為三類,首先“進(jìn)呈御覽”,其次“呈送軍機(jī)處、總理衙門、大學(xué)堂各一份”,最后送各省督撫、學(xué)政各一份,“以備考試調(diào)閱之用”。對(duì)于各省新設(shè)有藏書樓的學(xué)堂,也加送一份,“其余則減價(jià)出售”。梁啟超同時(shí)提出,譯出各書當(dāng)仿照東西各國之例,不準(zhǔn)坊間翻刻,以杜偽誤。
四是譯書局的費(fèi)用。梁啟超提出,每年年終,要將一年譯印書數(shù)量、所需費(fèi)用開列清單,呈報(bào)總理衙門備查。因譯書局為官商合辦,如遇經(jīng)費(fèi)不足的情況,“即依原奏招集股份,以竟其成”。
光緒帝充分肯定梁啟超對(duì)譯書局的構(gòu)想,親筆御批“尚切實(shí),即著依議行”。光緒帝認(rèn)為,梁啟超提出此事,應(yīng)為“經(jīng)久之計(jì)”,而不是草率遷就。為確保譯書局的經(jīng)費(fèi),光緒帝還大大增加撥款,特批:所請(qǐng)開辦經(jīng)費(fèi)銀一萬兩尚恐不足,著再加給銀一萬兩;常年用項(xiàng),原定每月經(jīng)費(fèi)一千兩外,再行增給二千兩。自七月初一日起,“各款均由戶部即行籌撥”。[15]
然而,1898年發(fā)生的“百日維新”不久就以“戊戌政變”的失敗而告終,康有為、梁啟超不得不亡命日本。梁啟超早期的翻譯事業(yè)至此暫告一段落。
維新變法推動(dòng)了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蓬勃興起,促進(jìn)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醒。“在此影響下,中國近代翻譯也實(shí)現(xiàn)了由單一器物翻譯向自然科學(xué)翻譯與社會(huì)科學(xué)并重轉(zhuǎn)變,開啟了中國近代翻譯的新境界”,梁啟超則“在思想上為這次轉(zhuǎn)向發(fā)揮了領(lǐng)導(dǎo)作用”[16]。他提出譯當(dāng)譯之本,盡譯西國章程之書等觀點(diǎn),打破中國封閉保守的文化狀態(tài)。正是他的大力倡導(dǎo)和宣傳,使得中國的翻譯事業(yè)迎來了清末民初的學(xué)術(shù)重心轉(zhuǎn)變。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大量日文書籍得到翻譯出版,其中以商務(wù)印書館、譯書匯編社、廣智書局、教育世界出版社最為有名,“對(duì)時(shí)人曾發(fā)生極大之影響,受其啟發(fā)而研究西學(xué)者接踵而起”[17],推動(dòng)了近代中國人文社科領(lǐng)域翻譯的潮流。
注釋及參考文獻(xiàn):
[1][6]湯志鈞,湯仁澤.梁啟超全集:第4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8:109,271.
[2]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4.
[3]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9:123.
[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9:52.
[5]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李盛鐸為開館譯書事奏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檔號(hào):03-5615-0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
[7]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諭檔第1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翰林院侍讀徐致靖為密保梁啟超等維新救時(shí)之才請(qǐng)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事奏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檔號(hào):03-9446-03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
[9]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諭檔第2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0]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為遵查廣東舉人梁啟超學(xué)問淹通究心時(shí)務(wù)詢?yōu)橛杏弥耪?qǐng)酌予京秩并特賜召對(duì)事奏片,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檔號(hào):03-9446-03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
[11]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楊深秀為譯書智民其功至大請(qǐng)總署議行事奏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檔號(hào):03-9446-03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
[12]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李盛鐸為開館譯書事奏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檔號(hào):03-5615-0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
[13]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為遵旨議復(fù)責(zé)成梁啟超辦理京師編譯局事奏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檔號(hào):03-9447-02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
[14]呈舉人梁啟超所擬譯書詳細(xì)章程清單,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檔號(hào):04-01-38-0029-04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
[15]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上諭檔第1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6]馮志杰.中國近代翻譯史·晚清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4.
[17]姚明達(dá).中國目錄學(xué)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75.
作者單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