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歷程與學術選擇
閻浩崗

我的童年記憶都與毛主席有關,與“革命”有關。
我出生在河北省吳橋縣一個離縣城40 華里、只有三百多人口的小村莊里。最初的記憶,是被大姐抱著在村里大街上走,街上烏壓壓一片人,紛紛過來對我說:“你唱‘嘎拉呀兮咯若’!”我一看人太多,就扭頭趴在大姐的肩上,予以拒絕。其實,我只會這首歌的開頭兩句:“毛主席的光輝,嘎拉呀兮咯若……”既然是被抱著,現在推想那時不會超過三四歲,應該是在1966 年或1967 年間。接下來印象深的記憶,是街上扎起彩色牌樓,上面紅綠彩紙寫著“滿懷激情慶九大”——那時應該是在1969 年。我雖然還沒上學,但聽別人念,這幾個字就記住了。
1970 年,我開始上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的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這年盛夏時節,老師讓全校五個年級的學生學習并背誦毛主席新發表的“五·二〇聲明”,記得是一個64 開的小紅本本,最先、最熟練地背下來的同學,將到全村社員大會上展示。我雖然是最低年級,竟然被選中了。那天中午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如在目前:烈日炎炎,社員們午休剛過,準備下地之前,都聚集在大街上,各自找個有陰影的墻根或樹蔭下蹲了、坐了。村支書先說了幾句什么,然后教我們語文的齊萬興老師就讓我出來背誦全文。我小跑過去,站到街心,一口氣背誦下去,機關槍一樣很少停頓,此間偶用眼睛余光看向蹲在墻根陰涼處的齊老師,他手中拿著原本在核對呢。背誦完了,我又小跑到他跟前,似乎這時有一片掌聲。齊老師拍著我的后背說:“讓你娘給你買個新背心!”當時我穿的是一個帶破洞的小背心,原先是白色的,母親用顏料給染成了綠色,齊老師不說的話,我還自以為很漂亮呢。
多年之后,我一直感激這位齊老師。當年父親在外地教書,母親一人帶五個孩子過日子。我們家在村里并不吃香,什么好事也不會輪到我。但在學校,齊老師對我特別重視:小學五年,隔三差五要開各種會,常常是幾個村子的小學聯合召開。齊老師總是指定我為閻莊小學的“發言人”。雖然這種發言稿多靠抄報紙拼湊,但也給了我看報的機會,鍛煉得當眾發言不怯場。齊老師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曾用自行車馱著我,騎行十幾里地去后郭村看階級教育展覽。齊老師本人文化水平并不高,現在回想他教我們語文也有教錯的地方,但他給了我機會,給了我自信,這對我早年成長是最重要的!
1975 年至1978 年讀中學的四年,正是中國政治風云激蕩之時。我對那一時期的時事特別熟悉:能記得國內每個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能熟練地按順序背誦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單,知道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知道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前面的名字叫列昂尼德……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有特殊機緣。從讀初中開始,我享受了“教師子女”待遇:住在父親的宿舍兼辦公室里。父親擔任高中班的班主任,班主任有學校公費訂閱的報紙《光明日報》和《參考消息》,這使我每天都能讀到新報。我獲取外部信息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是收音機,家里那臺木殼收音機豐富了我的精神生活,打開了封閉小村莊通向外面世界的空中通道。
那時,我們家的書都放在一個黑色的大柜子里,數量并不多,卻已是全村藏書之冠。這些書有的是父親讀中學和師范時的課本,有的是他省吃儉用購買的,還有一些則是學校圖書資料室“破四舊”時他“搶救”回家的,上面還印著學校的紅章。對我影響最大的有《自然地理》《中國近代歷史故事》《世界近代現代史》《史記故事選譯》,以及中國地理和世界地理的課本。對書里的插圖或照片,我印象最深:《自然地理》中地球與太陽及其他行星的對比,讓我知道了宇宙之浩茫、人類之渺小;《史記故事選譯》雖無插圖,但它有大字文言原文、小字注釋和白話譯文,讓我有了讀文言文的初步感受。那時候最喜歡讀的當然是小說,但家里藏書中小說僅有三種:《播火記》、《葉圣陶短篇小說選集》和《高爾基選集·短篇小說集》。現在回看,這三本恰好分別代表了當代文學、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大概是我十歲的時候,有一天,父親去縣城,捎回來兩本白色封面上印有魯迅灰色側面浮雕像的新書《吶喊》與《彷徨》,我如獲至寶:這是小說,又是新書啊!由于可讀的書少,上述幾本書我讀了一遍又一遍,以至于感興趣的段落都能夠背誦。回頭來看,我在《文學評論》發表的論文《重新認識葉紹鈞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和《論〈紅旗譜〉的日常生活描寫》,與早年的閱讀體驗不無關系。
連環畫是我童年、少年時期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我生平做過的唯一一次“生意”,就與連環畫有關。記得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春節前,母親讓我到集上去賣一只公雞,事先告訴我底價不得少于六毛錢。一大早起來,吃過飯后,母親將公雞的腿綁好,放在一個竹籃子里,上面蓋上一條毛巾,讓我攜著去賣。走到半路,雞在籃子里叫了幾聲,后面跟上來一個老頭,他問:“小孩,這雞是賣的?”我說:“是。”他問:“你賣多少錢?”我按母親的囑咐回答:“你給多少錢?”他說:“我給你七毛,賣吧?”我二話不說,掀開毛巾,舉起籃子說:“你拿走吧!”老頭給我點出七毛錢,我拿在手里,攜著空籃子一溜小跑,直奔街上唯一一家小書店。由于時間太早,書店還沒開門,我就坐在門前等。等開了門,我進去后就直奔連環畫玻璃柜,看中一本《沙家浜》,一問,一毛七分錢。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也不進街里趕集,仍是一溜小跑趕回家去,將剩余的五毛三分錢如數交給母親。本以為母親會責怪我花這么多錢買小人書,但母親只是說:“傻行子不知道跟那老頭再講一下價錢!”我答:“我比你說的多賣了一毛呢!”后來,母親對別人說:“俺小華不饞,趕了回集連塊糖都沒買。”
這些連環畫的作用,一是拓展了我的空間想象,二是彌補了可閱讀的“字書”資源的不足。這些連環畫大多以英雄主義為主題,它們與當時的電影、樣板戲、語文課本一起,塑造了我的英雄主義價值觀。
童年和少年時期,“樣板戲”也是我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樣板戲風行的1970 年至1976 年間,正是我七歲到十三歲之間。我敢說,在同年齡段中,我對樣板戲是最熟悉的:我基本可以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從頭唱到尾,包括對白、音樂前奏和過門,都能說下來或哼下來。許多年以后,曾和有樣板戲記憶的同行比賽對臺詞,偶有輸給比我大三四歲以上者,但從未輸給同齡者。這大概與我家里有那臺收音機有關,更重要的還是出于強烈的興趣。
有一件關于唱《龍江頌》的趣事:上小學時,三伏天老師要求學生們午飯后在學校午休。有一天午后,我在教室里睡不著,就跑到了院子里,坐在窗臺底下陰涼處,不覺間唱起《龍江頌》中盼水媽的大段唱腔“舊社會,咱后山十年九旱”。唱得情感有起有伏,聲音有高有低,節奏有快有慢,唱到動情處,竟熱淚盈眶。正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忽聽窗內一聲大喊:“好!”原來窗內正是齊老師的臥室,把他吵醒了!我以為肯定要挨訓了,不料窗內他接著說:“唱得好!唱得好!”并無責備的意思。
1975 年1 月,我升入初中。在班上,我擔任板報小組組長,負責選稿、設計版面,畫報頭、標題和花邊。這算是掌握全班“輿論陣地”的位置。我因此每天讀報,了解重大新聞。“評《水滸》,批宋江”時,得以首次通讀綠色封面的《水滸全傳》。那時父親枕頭底下還壓著一本《紅樓夢》,我也偷偷挑著讀。父親發現我讀“閑書”,把書鎖進了抽屜,我又想辦法找到鑰匙,打開了繼續讀。不過那時感覺《紅樓夢》遠不及《水滸》吸引人,說的盡是些雞零狗碎,令人不耐煩。后來,我又從父親枕頭底下發現了沒有封面封底的豎排版《三國演義》,雖然文字半文半白,比《水滸》又深奧些,但由于以前讀過相關連環畫,特別是覺得《三國》里的英雄比《水滸》里的更厲害、更讓人有想象空間,也特別迷戀。由于讀的課外讀物比別的同學多些,平時和同學說話時不覺加進一些書面語,有同學就戲稱我為“閻教授”。
初中時,我的語文成績雖然在班上領先,但沒有什么相關的特殊記憶。進入高中后,教我們班語文的洪中星老師是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性格豪放,在當時的鄉村教師中視野很不一般:就在教我們語文期間,他曾親赴京城,參加教育革命大辯論。學校文藝匯演時,他朗誦自己創作的詩,或表演單口相聲。他上課時說過的一句話我一直記得:“阿爾巴尼亞有個諺語——母雞的理想只是一把糠!”意在教育我們要有遠大的理想。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他給我們描繪考入大學后的情景:教室里是毛玻璃的黑板,地面光可照人;給你們上課的,將是全國知名的教授……聽得我對“大學”無比神往,將其想象為天堂。洪老師對我個人成長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作文課上特許我不按老師命題,自擬題目。我的作文常常被他當作范文在課堂上朗讀;二是學校舉行作文比賽時,他力保我為第一名。當時獲得第二名的,正是我父親的得意弟子,他的文章詞匯更豐富、辭藻更華麗,但洪老師更贊賞我于樸實中透出的真情實感與自然化文采。這使我加強了自信。
1978 年的夏天,我尚未升入高二。這是因為,此前農村的學制都是小學五年、初中和高中各兩年,每年年底畢業,年初升級,而1978 年開始由冬季升級向夏季升級轉軌,所以本年度的高一都延遲半年升級。那年有高一跳級參加高考的名額,跳級者可以與高二畢業的考生一起參加高考。大概這是為滿足農村里的優秀生想早上大學、早畢業、早掙工資的需求吧。跳級名額只有一個,需要高一四個班三百多名學生競爭。父親希望我早掙工資、早給家庭經濟作貢獻,讓我參加跳級競爭。我的語文、歷史、地理、政治成績占優,數學尚可,理化成績差。所幸學校決定考的是語文、數學和政治三門文理必考科目。三門中我兩門有把握,數學相對也不太落后,最后總分第一,爭取到了跳級名額,參加了1978 年夏季的高考。高考的結果,我的語文、歷史、地理、政治成績較好,數學卻只考了百分制的22.5 分。原因是其他幾科沒學過的課程我可以自學,數學卻不可以。這樣,高考數學試卷中高二以后的內容我只能眼巴巴放棄。大概一個月后,縣里有線廣播公布本縣高考成績,我的總分位列全縣文科考生第八名。
這個成績,肯定不能被前幾個批次錄取。等待的時間是漫長的,也是有些尷尬的。秋季到來,我只好回到學校接著讀高中。此時原先的高一已升為高二,重新分班。學校沒有按文理分班,而是按“快慢”(即優秀和一般)分。我被分在快班,這個班選擇學文科的只有五六人。于是,每次上物理或化學課時,我們這幾個“異類”就被“驅逐”出去,到學校剛建的閱覽室里自習。這雖有點被歧視的感覺,但我們終于可以自由閱讀,合法地看“閑書”了!在這期間,我通讀了浩然的《艷陽天》,厚厚的三大本,用三四天時間夜以繼日地讀完。之所以夜以繼日,不是因為勤奮,實在是被情節吸引,拿起就放不下,記得讀完之后還累病了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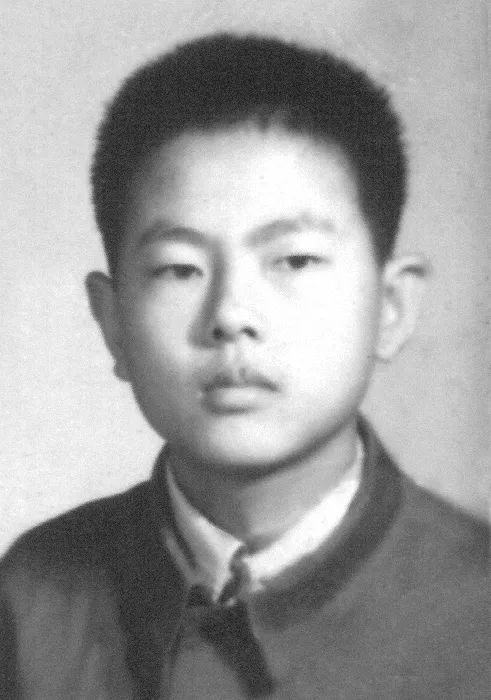
1979 年,本文作者攝于滄州師專
入冬后一個周末的傍晚,天已擦黑,我在父親的辦公室里,尚未回家。這時,教導處主任徐老師敲開房門,遞給我一封信,信封上印有“河北師范大學”的字樣,里面是我的錄取通知書。我馬上一路小跑著往家里趕,還記得腳下灰蒙蒙的鄉間土路起伏著往身后飛的情景。到家時,全家正在準備吃晚飯。我帶來的“新聞”,總的來說令全家高興,但我和父親二人還是有些遺憾和猶豫:雖然錄取通知書上的紅章是“河北師范大學”,但正文中“河北師范大學”后面又有“滄州地區師資專科班”的“后綴”,性質就不同了:是專科,不是本科,而且報到地點是滄州,不是石家莊。如果不服從分配、拒絕報到,明年跟著高二班按正常程序再考一次,即使考中也有可能被取消資格,而且萬一考得還不及今年呢?最后決定還是去報到。
1978 年12 月,我進入河北師范大學滄州地區師資專科班中文專業學習。后來知道,這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
所謂“河北師范大學滄州地區師資專科班”,實際就是當時的滄州師范學校,是中師的升格。我們入學時學校仍保留有中師班。同學們原本期待河北師大的老師來給上課,后來得知學校只是借了河北師大的牌子和紅章。后來,學校改稱“滄州師專”,正式升格為大專,如今則叫“滄州師范學院”,是二本院校。2010 年我們老同學聚會,查學籍檔案,在滄州師院查不到,后來在河北師范大學查到了:看來名義上我們一直算河北師大的學生。我們1978 年12 月入學,1980 年12月畢業,但1980 年的6 月就離校去實習了,所以在校時間僅一年半。課程表上的課程與本科的中文系所設基本一致,但開課時間短,老師講得匆忙,而且老師多是從原中師或高中調上來的,學術視野有限。不過,老師們畢竟都是“文革”前畢業的正規大學生,還是引領我們初步進入了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學術天地,起碼我們都知道了本學科每門課程的概貌。我們那屆學生年齡差異很大,最小的我入學時十五歲,而班上最大的“老三屆”畢業生三十多歲,有的同學已是兩三個孩子的父親或母親了。我童心未泯,上課時常走神,例如古代文學老師講唐詩時,我不記筆記,在本子上畫了一幅幅詩意畫。
在滄州期間,正是新時期初期乍暖還寒的“早春季節”。關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各路大員的紛紛表態,我們都是通過高音喇叭聽到的。得知第四次文代會的盛況,除了通過報紙和廣播,還因在北京親自參會的詩人雷霆到滄州探親時,給我們作了一場專題報告。記得雷霆作完報告離開后,主持會議的李校長馬上“消毒”,說:“雷霆到這里放毒來了……”我那時聽得懵懵懂懂,不知“毒”在何處。畢業離開滄州后,我回到本縣在鄉村中學教書,又重歸“前現代”環境。雖然每天讀報、聽廣播,知道城市里有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知道“清除精神污染”、知道有“潘曉之問”的討論,也有共鳴,在自己訂閱的《作品與爭鳴》上讀到了《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等作品,但是我的思想觀念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可以說,1978 年至1986 年這八年,是我思想觀念的漸變或過渡期。除了不曾近距離接觸思想前沿人物,主要還是個人經歷與生命體驗及地理環境與社會環境使然。這八年是我大量閱讀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原著的時期,由于上述原因,我該時期的閱讀還是以古典的、傳統的和革命的作品類型為主。那時,滄州師專的圖書館雖然只是幾間大平房,我從這里借閱了《紅旗譜》《創業史》《林海雪原》《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悲慘世界》《魯濱遜漂流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名著,畢業后故鄉任教六年間,又按照古今中外文學史的線索閱讀了大量作品。外國長篇中最震撼我的是《悲慘世界》,幾年間陸續讀完先后出版的全部五冊。不過,我這一階段所讀作品仍以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作品為主,比較“正統”。1984 年,我被評為吳橋縣優秀教師,在表彰大會上發言,談到對我人生觀影響最大的幾部書時,我列舉的是《浮士德》《悲慘世界》《怎么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此前,袁可嘉等選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在《光明日報》刊登書訊,我郵購了其中的第二冊,從中讀到了意識流作品,對現代主義有了大致了解。

1987 年,本文作者攝于南開大學
有一件事能夠說明我當時閱讀的廣度與缺失:1985 年冬,我應考南開大學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其中有一門大綜合,百分制,每題一分,共100 個小題。我考了97 分,沒有答出的三個題,一個是《精忠旗》的作者,一個是格里高利·麥列霍夫是哪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個是《尤利西斯》的作者。這三題中《靜靜的頓河》雖也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屬于其中的“異端”,肖洛霍夫在中國還曾被當作修正主義批判過;我雖讀了現代派作品選,但當時對《尤利西斯》這個書名幾乎沒有印象。
還有一件事能夠說明我當時價值觀念的“前現代”性質:1985 年,我在縣文教局電視室里看了電視劇《新星》,很有共鳴,很欽佩“青天”李向南大刀闊斧的精神。后來在《作品與爭鳴》上讀到批評該作“清官意識”的文章,很是不解,心想:難道清官還不好?也在《文學評論》《當代文藝思潮》《文藝研究》上知道有“85 新潮”,但沒有和自己的感受與思考共振,沒能真正理解。
回顧來路,思考今朝,我發現:如果超出人文知識分子的小圈子,我們很多普通國民的觀念和意識,仍然基本停留在我在80 年代初期時的那個階段,也就是說,他們不曾經受“啟蒙現代性”的洗禮,生命體驗不到位,即使接觸到相關信息也會無感或不見,何況相當多的人無緣接受相關信息。但我以為所接受信息是主要因素,因為單從生命體驗來說,啟蒙現代性觀念與人的天性更為貼近。
我的觀念發生實質性變化,是1986 年至1989 年在南開大學讀碩士研究生的三年。雖然我的導師張懷瑾先生是典型的思想比較保守的人物,在我入學之前的那個學期他剛剛在南開大學主樓小禮堂作了題為《現實主義路漫漫》的報告,但我在校內接受的信息不僅僅來自導師。各種信息的強烈沖擊,使我自幼形成的價值觀念受到質疑和撼動。我開始對人道主義思想產生強烈共鳴,同情“純文學”觀念。其思想結晶,就是我的碩士畢業論文《論藝術目的》和后來發表在《理論與現代化》上的論文《文學與人道主義:不解之緣》,后者在新世紀以后被收入了《河北新文學大系》。
然而,我在逐步接受啟蒙現代性價值觀的同時,并未徹底否定自己原先的價值系統,只是對其偏頗和缺失予以反思。我仍然對自己過去曾經激賞的革命文學作品抱有敬意。應該說,最初的強烈閱讀體驗具有決定性。如前所述,我寫出關于《紅旗譜》和葉圣陶小說的研究論文,與童年少年時的閱讀體驗分不開。在此,要特別提到姚雪垠的《李自成》。我最初接觸這部小說,是通過收音機里的“小說連續廣播”,那應該是1977 年的事。在故鄉教中學時期,我又騎車二十里,到縣文化館借閱了該作第二卷三冊,又購買了第三卷三冊。從1981 年第三卷出版,到1999 年姚雪垠先生去世,十八年間我一直關注著小說最后兩卷出版的消息。當初的閱讀令我如癡如醉、神往無比,所以后來學界即使有多少對它的質疑乃至否定,也不能撼動我對它的欣賞;文學史對它的輕視或無視,我更不能認同。需要強調:我后來對它的評價,是以專業研究的、文學史的眼光予以審視的結晶。對《艷陽天》的評價,同樣離不開早年的沉浸式閱讀:一部長達一百二十余萬言而能使我三四天一口氣讀完、最后累病了的作品,肯定不會是單憑概念虛構空想之作。

2003 年,本文作者在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畢業時留影
啟蒙現代性話語與革命話語在我精神深處的對話,決定了我學術研究的個人角度。我主持的第二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 世紀中國土地革命敘事研究”,體現的正是兩種話語之間的對話、沖撞與融合。為此,我特意在結項成果名稱里加上了“多面之詞”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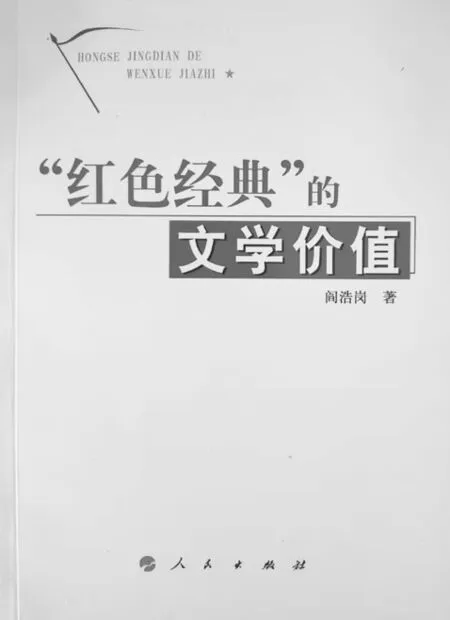
閻浩崗:《“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
從1989 年碩士畢業,到2000年考博,十一年間我一直是高校文藝理論教師。我從文藝理論研究轉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出于對個人具體情況的考慮,也有特殊機緣。在90 年代,我雖然發表過幾篇文藝理論論文,但總體感覺發理論文章很難。1991 年,我偶爾寫的一篇當代小說研究論文《也論新寫實小說作家的心態》,投給《藝術廣角》后卻很快得以發表,而且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到1996 年,天津首位現代文學專業教授邱文治先生一語點醒夢中人。他問我:“在文藝理論界,你覺得你算老幾?”我眨眼一想,前衛的文藝理論批評家都在北京或上海,整個天津都沒幾人!邱先生接著說:“跟著我搞現代文學吧!”他正承擔了天津市“九五”重點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流派藝術研究”,我于是欣然參加,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雙重職業生活”:課堂上我是教文藝理論的,發表的文章卻大多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方向的。
2000 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博之后,我終于正式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隊伍中的一員。這首先要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李岫教授,還要感謝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曾給我學術上以啟發導引和直接幫助過我的各位老師!感謝讀博三年間各領域眾多前沿專家的講座給我的學術啟迪!感謝給我發表文章和出版專著的各位責編或主編!
我在“前線”親歷了新潮理論與概念術語“大轟炸”、以“新”為最高價值的80 年代,又在90 年代中期開始逐步由文藝理論轉向文學史研究。雖然“背叛”了文藝理論隊伍,但從宏觀考慮問題、量化分析時不忘基本性質判斷,這是原有學歷導致的思維習慣。我堅決反對從理論出發、演繹概念的思維與行文方式,始終將文學文本閱讀置于首位,堅持從閱讀中發現的實在“問題”出發。近年也越來越感到一手資料、獨家資料占有的重要性,這又是向各位現當代文學研究前輩、同輩和晚輩同行學習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