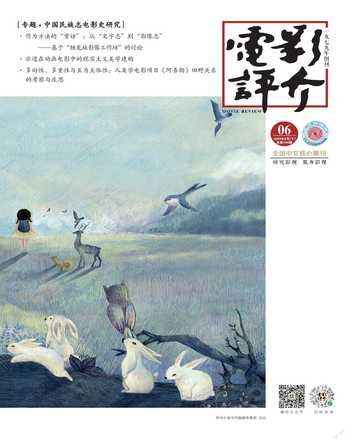非遺在動畫電影中的現實主義美學建構
張珊珊

非遺是一個國家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下動畫電影要表達“中國風格”的豐沛寶庫。中國動畫電影對非遺的關涉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以大眾化的非遺技法為電影藝術手法,例如剪紙動畫片《金色的海螺》(1963)、《一條絲腰帶》(1961)、《江海漁童之巨龜奇緣》(2019),折紙動畫片《聰明的鴨子》(1960)、《三只狼》(1980)、《湖上歌舞》(1964)等,其將非遺剪紙、折紙作為電影藝術風格手法,是傳統美術和電影藝術結合的產物,兼具兩者的美學特點;第二類是將非遺元素作為電影的重要視聽符號,例如《驕傲的將軍》(1956)中的京劇,《大魚海棠》(2016)中的客家土樓,《小門神》(2016)中的年畫等,重在形象塑造和感官效果,是提取非遺中能夠妥帖表達影片視聽意義的符號;第三類是以非遺為題材進行電影創作,又分為民間文學改編和非遺題材原創兩個方向。前者為主要陣地,早期的有《大鬧天宮》(1961)、《鐵扇公主》(1941)、《哪吒鬧海》(1979)、《女媧補天》(1985),近年來的有《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白蛇:緣起》(2019)、《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等,都是對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和神話進行再創作,其擁有較廣的受眾基礎和流暢的意義交互空間;后者如《雄獅少年》(2021)以廣東醒獅為題材,《星際小螞蟻之英雄蔡李佛》(2015)以蔡李佛拳為題材,這類電影面向非遺真實生境,從中提煉能跨越時空、民族和文化的對話性事實,以現實主義關懷為主旨訴求。
以上三種類型既有時間上的次第,也有共存的交融,呈現出多元化的審美意義。但是,在近些年“國漫崛起”的語境中,對動畫電影東方美學、魔幻奇觀、技術美學的探討卻遠超對其現實主義的關注:一方面,與動畫電影虛擬視聽符號和數字媒體技術的基本構成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現實主義在動畫電影藝術性和市場性的“夾層”中經常是含混的。因此,有必要厘清非遺在動畫電影中的現實主義內涵,進而闡揚現實主義美學在當前中國動畫電影事業中的重要意義。
一、從“異質”到“并軌”:非遺影像的現實主義轉向
盡管“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整套理論和實踐體系被國人所熟知,是從2004年中國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才開始的,但動畫電影與傳統美術、民間文學等非遺的“聯姻”歷史卻由來已久。新中國動畫電影以“美術片”為獨特開篇,“將具有濃郁東方傳統意味的圖樣、造型、色彩、構圖等搬入動畫創作”[1],從中國傳統美術風格與技法中汲取靈感,與折紙、剪紙等美術類非遺項目可謂“異質同源”。從兩者的“異質性”來看,動畫電影偏向于媒體技術表達而逐漸走向仿真,這是其現實主義美學的基本要義;美術類非遺是民間智慧和文化的濃縮,能夠反映地區特性、民族特色和群體特征。因此,兩者結合不僅具有先天優勢,而且還形成了具有東方神韻的“中國動畫”美術風格。這種美學建構是通過物質性手段將兩類藝術形式進行糅合,是用新的影像技術“改造”傳統民間美術和“改編”民間傳說和神話。所以,非遺在動畫電影中的現實主義創構主要體現在技術美學層面。
隨著非遺保護與傳承的議題日趨顯豁,動畫電影與非遺的關系也逐漸突破“技術線”而深入“內容線”。非遺事象具有深厚多維的價值,其體系枝葉繁茂,內容龐雜,可以從國家、歷史、民族、地域、人文、藝術、心理等多個維度切入,動畫電影可嘗試多樣態的創作實踐。例如影片《大魚海棠》借鑒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莊子傳說》及多個民間神話,將“天人合一”的中國古典哲學與現下年輕群體對于“愛情”“生活”等問題的思考并線,完成一次“古今對話”;影片《雄獅少年》將非遺價值的挖掘作為影片主旨,根據嶺南醒獅在現實情境中的生存狀態來提取影像表達要素,完成對非遺的活態性呈演,是動畫電影嘗試與非遺深度融合的一次現實主義突破。借助非遺事象,動畫電影可以開拓東方主義中華之美的現實主義表達路徑,建構國產動漫的新理念、新風格;以電影為傳導,非遺事象能夠在“保護搶救”和“傳承新生”的交織地域探索新的文化實踐,兩者在內容生產上逐漸走向“并軌”,這是當前動畫電影中非遺影像現實主義的重要表征。
學者沈義貞認為,現實主義美學“包含創作原則與創作方法兩個層面”。[2]在動畫電影創作中,前者決定影片的邏輯理路,后者左右影片的意義生產。從創作原則來看,關涉非遺的動畫影片既要考慮數字技術與藝術的綜合表達,也要與時代語境、主流思潮等現實議題形成映照,基本思路是“將動畫片的藝術性放在主體地位,將可借鑒的民族文化符號放在從屬地位”。[3]就創作方法而言,通過3D動畫、VR、CG技術等數字仿真工具,可以將傳統非遺技法和非遺特色元素變成現代的、新潮的符號。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推出的哪吒、敖丙、李靖、太乙真人等官方手辦僅上線7天,預售額累計超過550萬元。[4]但是,僅憑奇幻絢麗的仿真技術和符號改造,還是無法全面搭建動畫電影回應現代社會心理需求的敘事體系。因此,在上述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兩個層面之前,還應有一層“創作構想”,這是指在動畫與非遺創作“并軌”的過程中,要提前對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如何交匯、歷史經驗與社會心理如何呼應等框架性問題進行抽繹,進而確立影片的命意與主旨,以指導創作原則和方法。
從國內當下動畫電影的生存境遇來看,對非遺現實主義美學的認識才剛剛起步,對非遺題材的現實主義創作還存在畏怯。因此,建立“創作構想——創作原則——創作方法”的現實主義美學框架,對開掘影片文化深度、豐富“中國風格”動畫電影話語體系十分必要。
二、意象美與現實美:構想闡釋
意象是中華美學的一個基本命題,葉朗稱美“是一個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5]電影的意象是指通過對“象”(以聲畫為載體)進行表征而產生多重意境,以“象”生“意”、以“意”悟“象”、“意”“象”合一是電影中意象美的基本釋義。從創作的規律看,電影意象的生成要依賴主旨,沒有創作構想的挈領,其意象仍是拼貼式的虛空之景,很難與受眾達成情感融通和共鳴。動畫電影的本質就是虛擬的藝術形式,是離想象更近的隱喻王國,但這并不意味著現實性不重要;相反,影片要想通過意象傳遞更深層的價值理念和美學意蘊,在創作構想層面就要從現實的現代語境和文化局面出發,建構一個能夠通古達今的意象世界。
(一)意象中的現實情境
非遺題材改編類電影《濟公之降龍降世》(2021)是對國家級非遺《濟公傳說》的翻新與再造。影片通過對少年濟公李修緣成長經歷的刻畫,呈現了一個更細膩、全新的濟公形象。為了更貼近傳說中濟公生活的原貌,影片創作團隊在濟公出生地浙江省臺州市天臺縣多個景區實地取景,高度還原了臺州天臺山大瀑布、華頂云錦杜鵑、國清寺等景點,并且植入了傳說中濟公發明的非遺美食——餃餅筒,以虛擬視聽符號復現現實情境,縮短了想象與生活的距離,這種超真實環境能夠更加立體化地表現濟公是如何從一個少不更事的孩子蛻變為舍身取義的英雄。
模擬現實情境所產生的意象與受眾心理有天然的貼近性。影片《大魚海棠》借鑒了國家級非遺客家土樓的原型,這類圓合的土樓建筑歷史悠久,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民間智慧和人文理念,土樓中常有燈籠、楹聯、題刻等文化符號,是宗族內文化傳承的重要體現,這些場景在影片中被高度還原,在寄托神秘與奇幻想象的同時,也承托起一系列現實社會的價值追問。土樓中少女椿的族群既有嚴格而仁愛的宗族禮法,也有順應天道的處事之理,少女椿在“規制”和“自由”中選擇了后者,隨心而動、隨意而行,這正與現代年輕觀眾群體的普遍性心理相吻合。
非遺題材電影《雄獅少年》用帶有典型嶺南鄉土特色的自然景觀、建筑、市井生活等符號構筑了“小城意象”,并在小鎮鄉土空間與城市工業空間環境中進行切換和對比。醒獅之所以能在嶺南地區長盛不衰,離不開小城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傳統,在“年例”(當地傳統的賀歲方式)、婚娶、慶祝等民俗活動中都有舞獅之習,是當地文化空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影片中的小城環境是溫暖、活潑、明快的,而城市環境是逼仄、冰冷、壓抑的,隱去的工業化社會機器,淹沒于靜默空洞人海中的瘦小身軀,影片通過意象組合和現實情感共同傳達了醒獅于個體和社會的重要意義。
(二)意象中的現實問題
出于對現實主義題材的考慮,《雄獅少年》將嶺南醒獅在當前面臨的傳承困難作為影片的基本戲劇沖突,將醒獅文化和個體成長一并放置到“磨礪”的主旨下。基于這個創作構想,影片既要通過醒獅故事來提出非遺存續的核心問題,又要兼具中華美學神韻與意境,用靈動的意象傳達時代心聲。
動畫電影中現實主義構想需要將意象美與現實美交融合一,而不是生硬組合,要實現這種“水乳交融”的效果,一般采用“立沖突、促轉化”的思路。醒獅炫目、夸張、風趣的表演方式是《雄獅少年》的影像風格和意象特色,與少年阿娟酸澀而坎坷的成長經歷構成對照性框架,還多次使用具有戲劇性、沖突性甚至荒誕性的像、形、景、聲、字等虛構符號來反襯情感的真實。影片中使用了逼真的醒獅道具(獅頭、獅身)、表演程式(采高青、過橋、擂鼓等)和競技規則來呈現舞獅活動的精彩場面,在展示“喜慶”“吉祥”意象的同時,將人物的沖突性心理植入其中,產生深層次的觀影意義——越是精彩的舞獅傳統和動人故事,越能夠引人思考它當下的生存和傳承空間。但是,影片并不刻意強調這類醒獅的現實生存困境,而是將受眾的觀察視角放在阿娟的最后一次舞獅競技活動的圓滿完成,可未來阿娟的人生路仍舊會通往大城市,醒獅也會隨著傳承人的流動而繼續傳播。在這里,影片完成了對沖突性心理的轉化與和解。
三、“祛魅”原則與隱喻敘事
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將兼具意象美與現實美的創作構想進行分解、增殖和重構。為了保證影片對非遺的裁剪、借用不偏離主旨,讓非遺的真實之美、生活之美、情韻之美成為影片現實主義的“點睛之筆”,就需要在創作中重點考量“祛魅”原則和隱喻敘事方法。
(一)“祛魅”之魅
電影中的“祛魅”與紀實性和生活化有緊密聯系,但也不能如此簡單地理解。它與現存的遮蔽現實意義的話語體系相反,其主張祛除虛假和神秘。近些年,魔幻類型動畫電影的數量具有絕對性優勢,荒誕、浮巧的風格與宏大、空洞的敘事擠占了現實主義美學的空間,缺乏對現代社會實際和個體文化心理的觀照。2015年,《西游記之大圣歸來》開啟了國漫“祛魅”之路,影片對婦孺皆知的孫悟空進行重塑,顛覆了這一傳統形象的大眾化認知,將一個苦悶、迷茫的“臭猴子”是如何進行自我救贖的心理變化過程進行放大,契合現代人對自我和生活等問題的思考。自此之后,無論是非遺題材改編類還是原創類,“祛魅”成為連結想象世界和現代命題之間的一個現實性原則,或主張寫實手法,或追逐時代洪流,主要目的是拆解奇幻巨制的虛擬表象,植入現實性思考。
影片《雄獅少年》在阿娟的成長中設計了一條“蘇醒—驚醒—覺醒—清醒”的隱伏線,將非遺傳承人的時代群像化簡為個人肖像,著力建構“醒獅在舞臺,也在人海”的層次化圖景,以期形成沉浸式共鳴體驗。少年阿娟一開始出于對醒獅純粹的熱愛而獲得了一種堅定的力量,但迫于生存壓力不得不放下獅頭進入城市成為流動性勞工。盡管他與小城故事割舍,但最終卻在醒獅比賽中頓悟夢想對于平凡人的重要性。師傅咸魚強可以從一個舞獅高手歸隱市井,也可以端起獅頭重回舞臺,這些身份的切換與合并都是在對宏大的、復雜的、傳統的非遺事象進行祛魅,目的是為了讓社會重新認識非遺價值以及在非遺傳承中努力的“阿娟們”。
(二)微觀敘事中的隱喻
關注現實并不等于必然選擇宏大敘事,動畫電影的現實主義美學往往會通過解蔽性的微觀敘事表現出來,將宏大敘事進行祛魅和轉化。好的電影需要創造“敘事與隱喻相融會的美學意境”[6],非遺可以作為影片的點綴性視覺元素,也可以作為主旨性理念,以語言、圖像、色彩、聲音、構圖等多模態隱喻完成對現實性的指涉。
1.物象隱喻
物象隱喻通常借助物體的外形、色彩與動態特征等綜合要素進行表征。影片《雄獅少年》中最核心的物象是獅頭,多處特寫鏡頭也映射凝視之人的心境,是醒獅之人的自我心理審視,是虛實呼應的用法。當最后殘缺的獅頭掛在擎天柱上時,一只雄獅已然成形,象征阿娟不懼表象殘敗,內心已然懂得舞獅真諦。擎天柱是影片為實現完成敘事閉環而虛構的物象,盡管現實中嶺南醒獅并無這一設置和規則,但它是醒獅文化地位的代表,同時也是傳承人少年阿娟心理成長的驅動性符號。木棉花是嶺南地區常見的植物,是富有傳奇文化色彩的“男性之花”,影片中少年阿娟在迷茫之際出現過數次木棉花,這是其內心逐漸向“雄獅覺醒”接近和靠攏的隱喻。
影片《大魚海棠》中,土樓里先后出現過兩塊匾額——“天行有常”和“慧納萬川”,第一塊匾額掛在少女椿與掌握生死薄的靈婆對話時的如升樓里,“天行有常”意指天之道不可違,這與椿企求靈婆讓鯤復活的做法是沖突的,暗喻違反自然規律做事要付出沉重代價;第二塊匾額出現在靈婆施法將椿和鯤的靈魂合二為一的房間里,椿面臨深不可知的未來命運,她決意付出自己一半的壽命救活鯤。如果說“海納百川”,那人的情慧比大海更深闊、更恒久。這種創作手法借鑒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里以匾額傳達義理情感的做法,這使影片敘事層次更豐盈,更具感染力。
2.人物隱喻
人物隱喻的意圖是借助人物外貌、行為及其他鮮明特征來塑造更易被受眾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影片《大魚海棠》中人物的名字“椿”“鯤”取自莊子《逍遙游》中“上古有大椿者”以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椿”是上古大樹,指少女椿有掌握海棠等植物生長的神力。同時,也用“春去秋來”暗喻椿與湫之間不可能相愛的故事情節。“鯤”可以化鵬而飛,自由是其天性,也喻指椿與鯤的情感是自發的、率真的,這也遵循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莊子傳說》中所傳達的順應自然、性情處世的基本哲理。此外,“祝融”“赤松子”“嫘祖”“句芒”等均取自中國民間神話,利用這些廣為人知的人物名字,影片可以快速拉近與受眾的心理距離。
影片《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中,孫悟空打斗動作的設計靈感來自京劇的身段表演,與京劇鼓點形成呼應,具有雙重戲劇效果,增加了孫悟空形象的多面性。影片《雄獅少年》中,舞獅少年阿貓阿狗的名字看似隨意普通,卻暗示著平凡之人也有大夢想,現實生活中的非遺傳承人都是在平淡的生活中做著文化傳承這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膽怯、卑弱的阿貓阿狗與阿娟一起成長為勇敢、自信的少年,這種人物性格的轉變也與當下青年的生活經歷相吻合,更容易使觀眾產生“共同成長”的觀影感受。
3.空間隱喻
空間隱喻通過影片意象環境中人物、畫面、聲音和文字之間的多模態結構產生意義。影片《大魚海棠》中的土樓有大量的非遺元素:燈籠、油紙傘、對聯、牌匾等,營造了一個虛實難辨的影像空間。從現實意義來說,圓形閉合的土樓代表著權威性的宗法族規,少女椿沒有聽從母親的告誡,離開土樓來到人間,享受到自由的椿是歡騰的,這種空間情境的對比能更好地應和現代社會中的家庭教育環境。
影片《雄獅少年》中出現了三次“月光佛影”的情景,一方面真實地反映出醒獅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傳統;另一方面,月光下人與佛的“對話”,也是對影片中少年阿娟心理微妙變化的隱喻。第一次出現的佛像是巨大的虛影,其與懷抱獅頭的阿娟的瘦小身體形成鮮明對照,這種朦朧是對阿娟內心并不明白舞獅真正意義的暗指;第二次的佛影仍然是背影和側影,以近距離俯視視角呈現佛像暗淡的面部,這與阿娟內心逐漸接近生活真相但仍未懂得如何抉擇的狀態相映;第三次是阿娟將獅頭掛在擎天柱之后,一只獅子渾雄低吼著從佛像前走過,這次的佛像是正面平視角度,光線明亮溫和,而雄獅卻以暗影輔之,這是阿娟解開心結、堅定信念的寫照。
當阿娟一行三人第一次來到小鎮街口找到咸魚強的店鋪時,收音機里響起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名句:“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這種情景狀態和人物關系的反差隱喻了個體與社會的關系。阿娟背上行囊去廣州打工,鋼筋水泥的城市是灰暗色調,逼仄的生活空間和看不到天空的窒息感,象征阿娟眼中的城市生活意象。直到他凌晨到頂樓舞獅,黎明的第一束陽光從密集的高樓縫隙中透射,照亮了紅獅頭和阿娟的身體,此時城市中才有了光亮和色彩。這種城市空間的色調、音樂和敘事轉換喻示著個體對社會境遇的認知更新。
以上幾種隱喻都不是單獨完成的,而是要靠形式與內容、敘事與主旨的合一,將傳統文化元素、流行音樂、后現代戲擬等方法糅合并置,從“意象—現實—個體”的復合式關系中另辟新徑,用心打磨影片的共情點與共鳴點。
結語
非遺的歷史性和人文性可為動畫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提供更宏闊、更立體的場域。這種現實主義并非機械性復制真實生活,而是在藝術想象與社會實際兩種生境中建構一整套可以互譯的美學系統,深融社會文化肌理,對跨越時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理念進行縫合。以藝術闡發現實,以現實映照藝術,這是中國動畫在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語境下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張承志.中國動畫“美術片”的特點及其價值分析[ 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9(03):61-64.
[2]沈義貞.“現實主義電影美學”再認識[ 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03):10-15.
[3]蔣瑩瑩,黃心淵.動畫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啟用與傳播[ J ].電影評介,2018 (02):89-91.
[4]摩點網.《哪吒之魔童降世》官方授權手辦:做自己的英雄![EB/OL].(2019-08-12)[2023-02-17]https://zhongchou.modian.com/item/73989.html.
[5]葉朗.美是什么[ J ].社會科學戰線,2008(10):225-236.
[6]賈磊磊.什么是好電影——從語言形式到文化價值的多元闡釋[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