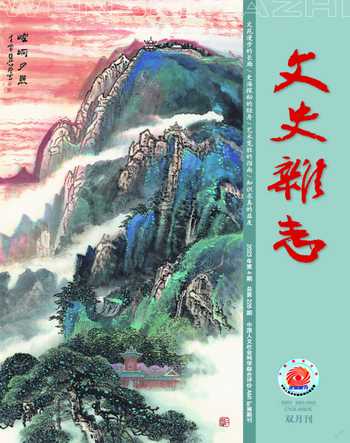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賢相完人”張鵬翮《忠武志》的特點及影響
梁中效
摘 要:被雍正皇帝贊譽為“一代完人”的張鵬翮,其所編的《忠武志》乃開一代風氣,成為清朝武侯墓志、祠志編寫的先導。張鵬翮不僅以諸葛亮為楷模,而且欲將諸葛武侯的“忠義之經”與“醇儒之學”傳承下去。張鵬翮的《忠武志》承前啟后,古今結合,縱橫交錯,貫通文史,成為三國文化的經典文獻,諸葛亮志書的典范之作,扭轉了重文輕史的三國研究學風,開啟了諸葛亮文化的“志書時代”,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張鵬翮;諸葛武侯;《忠武志》;影響深遠
明清時期,隨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橫空出世,諸葛亮形象更加偉岸高大,官方與民間對諸葛亮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蔚然成風。被雍正皇帝贊譽為“一代完人”的張鵬翮,其所編的《忠武志》則開一代風氣,成為清朝武侯墓志、祠志編寫的先導。
一、張鵬翮編寫《忠武志》的背景
張鵬翮(1649—1725),字運青,清代四川潼川府遂寧縣黑柏溝(今四川遂寧市蓬溪縣任隆鎮黑柏溝村)人,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歷官刑部主事、禮部郎中、江南蘇州知府、山東兗州知府、浙江巡撫、江南學政、兩江總督、河道總督、刑部尚書、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壬子(公歷3月8日),拜文華殿大學士,成為宰輔;雍正二月十九日(1725年4月1日)病逝,享年77歲。[1]張鵬翮編寫《忠武志》,與其書香門第、世代忠貞有密切關系。
張鵬翮一生體現出來的公忠體國、勤政愛民、清正廉潔、擔當奉獻的高貴品質與完美人格,都是以諸葛亮為榜樣。張鵬翮作為遂寧張氏家族家規的集大成者,其為人為仕無不彰顯張氏“忠孝為本”和“清儉傳家”家規家風的清正影響。張鵬翮出身于四川蓬溪一個書香世家。在良好的家教影響下,他從小就“自行修潔”“端靜如成人”。有一次,他在讀《陸宣公奏議》時,感嘆道:“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可見,一個人要成功,從小就必須有明確的奮斗目標。張鵬翮以伊尹、諸葛孔明為目標,以“一介不取”“淡泊明志”作為自己人生的行為準則。事實上,張鵬翮終其一生,都在踐行著自己兒時的諾言。他決心向諸葛孔明學習,潔身自好,為國家建功立業。他在《信陽子卓錄》中說,“凡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奸臣必貪而貪者必奸,而孔明生于季漢而成都至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奸于唐,而胡椒至八百石,由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奸臣之分矣。”[3]少年張鵬翮出賢入圣的志向,在《遂寧張氏家乘》也有明確體現:“存孝悌之心,行仁義之事,出為忠臣,處為端士,為士者詩書,為農者勤儉,使稱為清白吏,子孫不亦美乎”。[4]如果說“忠臣端士”是張鵬翮的人生定位,那么“忠勤廉能”的諸葛亮便是他人生的榜樣。因此,編寫《忠武志》正是他敬仰圣賢、激勵后人的實際行動。
張鵬翮編寫的《忠武志》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冰雪堂刊行。他在序言中說:“或問于予曰,《忠武志》何為而述也?予應之曰:‘為臣而忠,天之性也。三代而下,人多溺于利欲之習,而不知忠義之經,獨有武侯毅然純忠,立元臣之極則。故予表其風徽,使天下后世知武侯醇儒之學,王佐之才,有所感發興起,而忠愛之心油然生焉。”[5]由此可知,張鵬翮不僅以諸葛亮為楷模,而且欲將諸葛武侯的“忠義之經”與“醇儒之學”傳承下去。
二、張鵬翮所編《忠武志》的特點
忠武侯氣貫長虹,激勵后世忠貞報國。明清時期編寫“武侯全書”蔚然成風。
明代萬歷年間輯諸葛亮文者,除王士騏、張燮外,尚有郭惟賢、楊時偉諸人。郭惟賢本刻于福建,存佚不詳;王士騏、楊時偉所輯《諸葛忠武書》流傳至今。
明崇禎間,諸葛亮三十六代孫諸葛羲、諸葛倬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18卷,遺文單編,同時收錄歷代評論、詩文及遺跡、遺事等。只收諸葛亮文而不涉及其他內容的,只有明天啟間張溥輯《漢諸葛亮集》。清代輯諸葛亮文者最早為朱璘。其字青巖,江蘇常熟人,官至南陽知府。他在任內編輯《諸葛丞相集》四卷,成書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與上述諸葛亮文集相比,張鵬翮編寫《忠武志》目的明確,特點突出。
(一)崇敬孔明,薈萃嘉言懿行
張鵬翮編寫《忠武志》時約在50歲左右,刊印面世時56歲,正是他生命歷程中的爐火純青階段。將心比心,他對54歲就離世的諸葛亮更加崇敬。因而,他不僅以諸葛亮為楷模,更以薈萃他人生的嘉言懿行為己任,編寫《忠武志》的目的非常明確。其序言說:“武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清心之學也;高臥隆中,三顧而起,出處之正也;受遺托孤,之死靡他,忠貞之至也;道不拾遺,野無醉人,治國之善也;師出以律,百姓安堵,將兵之長也;用人盡其器能,誅伐使人不怨,刑賞之平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休休之量也;其言親賢臣、遠小人則興隆,遠賢臣、親小人則傾頹,開國承家之龜鑒也。”[6]這既是對諸葛亮人生事業的高度肯定,又是他自己踐行孔明足跡的體驗感悟。他的朋友們與他一樣也崇敬孔明,著名文人劉廷璣在其書的跋語中說:“真儒之間出,王佐之挺生,既秉非常之質,必遂非常之志,然有命焉以限之,未能大展其內圣外王之學,千百世而下,未嘗不為之咨嗟太息,敬慕不忘,如諸葛武侯之出處是也。”[7]諸葛亮不僅幫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而且以其文治武功為蜀漢贏得了“正統”地位。而張鵬翮“學探淵源,才宏經濟,游藝所臻,尤耽尚論,念侯之至德豐功,昭垂今古,不有全書,曷以傳后?于是博搜廣采,因侯之年表,考其始終,以按其生平之經歷,刪浮存要,匯為一編,名之曰《忠武志》。”[8]由此可見,張鵬翮編寫《忠武志》的目的,就是要將諸葛亮的“至德豐功”記錄下來,以便“昭垂今古”,成為炎黃子孫學習的楷模。
(二)承前啟后,成為志書典范
張鵬翮的《忠武志》完成之前,有關諸葛亮的文獻稱為《武侯全書》《諸葛忠武書》,或名之為《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諸葛丞相集》等,都是以“書”或“集”命名,而第一次以“志”命名諸葛亮的文獻,始自《忠武志》。正如曾任沔縣(今勉縣)知縣的馬允剛在《忠武侯祠墓志》序文中所說:“天下事之可傳者必有志,志者志之使不忘也。然志其地,志其事,志其山川草木,要皆以其人之不可忘而志之也。”[9]諸葛亮正是三代而下不可忘之人。“循名而責實”,《忠武志》開啟了以諸葛亮為傳主的志書典范,在其影響下,產生了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羅景修撰的南陽《臥龍崗志》、道光年間李復心編纂的《忠武侯祠墓志》、道光年間潘時彤編纂的《昭烈忠武陵廟志》,可謂導夫先路,后繼袞袞。
清康熙年間南陽知府羅景的《臥龍崗志》深受張鵬翮《忠武志》的影響。羅景在《重修臥龍崗忠武祠紀》中說:“適造袁江拜辭大司農遂寧張夫子,夫子出所纂《忠武志》示余,且諄諄以師表忠武為訓,及抵任即刻詣臥龍岡仰瞻遺像,肅致拜跪。”[10]此可證羅景修葺南陽武侯祠并纂修《臥龍崗志》,這兩大工程皆受到張鵬翮及其《忠武志》的直接影響。更值得稱道的是,張鵬翮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題寫了南陽武侯祠“寧遠樓”匾額,落款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河道總督書”。寧遠樓是南陽武侯祠后部的主體建筑,也是祠內最高建筑物,為重檐廡殿式建筑,流角飛檐,氣勢軒昂;“寧遠”即寧靜致遠之意,語出諸葛亮《戒子書》。寧遠樓又名“清風樓”,傳為諸葛亮藏書、彈琴及憑欄遠眺之所。羅景在修繕一新的三顧堂內,“供文昌帝君寶座,內貯《臥龍崗志》板及《忠武志》板。”[11]另外,南陽武侯祠還有張鵬翮詩碑,其云:“宗臣俎豆有余香,想象當年道德光。澹遠心傳洙泗訣,千秋生氣尚堂堂。”這一切皆可證明,張鵬翮不僅在南陽武侯祠有墨寶余香,而且直接促成了南陽知府羅景修繕武侯祠和編纂《臥龍崗志》。
清道光三年(1823年)羽客李復心編纂的《忠武侯祠墓志》也深受張鵬翮《忠武志》的影響。陜西沔縣是諸葛亮北伐時期的大本營所在地,這里的定軍山下又是諸葛亮長眠之地和全國最早的武侯祠創建地。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曹魏時,因積勞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軍中,臨終遺命歸葬定軍山。蜀漢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劉禪下詔在沔縣為諸葛亮修建了第一座祠廟(今武侯墓廟宇)。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都御史蘭璋建議在漢江北岸昔日諸葛亮的行營相府陽平另建一處新祠,與漢江南岸定軍山下的武侯墓廟宇,共同構成祭祀諸葛忠武侯的祠墓體系。李復心,號虛白道人,出生于乾隆年間的蜀之錦官里(今四川成都),早年操習儒業,中年歸寄道觀。他接任武侯祠住持后,于嘉慶十九年(1814年)始編《祠墓志》,歷經十載,于道光三年(1823年)完成初稿。林則徐于道光七年(1827年)拜謁武侯祠時,有詩《虛白道人住持武侯祠三十年,編〈祠墓圖志〉裒然成帙,喜其用心之勤,詩以贈之》:“比擬南陽結草廬,道人有道此中居。二千尺愛祠堂柏,三十年通宰相書。欲附大名垂宇宙,善推奇陣護儲胥。請看黃石仙蹤跡,同是功臣命不如。”[12]《忠武侯祠墓志》之所以得到名臣林則徐的嘉許,原因之一就是李復心以《忠武志》為主要參考書。他在《祠墓志·凡例》中說:諸葛亮文章及仕漢各事,“遂寧張文端尚書(張鵬翮謚號文端)、古虞朱青巖太守志之甚詳,近時武威張介侯太史刻諸葛故事五卷、文集四卷、附錄二卷,載在張氏叢書。”[13]由此可知,李復心首選《忠武志》為其編纂《祠墓志》的參照,甚至在“凡例”之后的“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公像贊”,一字不差地照錄《忠武志》張鵬翮所書的贊辭:“儒者之氣象,王佐之經綸……”,仍署名“小溪張鵬翮”,[14]如此作為全書開篇的“導語”。今勉縣武侯祠也有張鵬翮詩碑,內容與南陽武侯祠相同。這一切皆說明張鵬翮的《忠武志》對李復心的《忠武侯祠墓志》影響深刻。
清道光九年(1829年)潘時彤修纂并雕版成書的《昭烈忠武陵廟志》,是第一部詳細記載成都武侯祠歷史的專志,也是武侯祠歷史上唯一志書,成為記錄武侯祠發展沿革及傳承發揚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潘時彤熱愛三國文化,常與文友相偕同游武侯祠。他不僅對祠內景物十分熟悉,更格外關心祠中文物保護和建筑維修。他留下了許多有關三國及武侯祠的詩詞歌賦,表達對武侯祠一草一木由衷的珍愛之情。當時,張合桂主持祠中事務日久,有感于南陽武侯祠、沔縣武侯祠都有自己的志書,提出成都武侯祠也應修撰志書。該提議立即得到四川總督戴三錫、布政使董淳等官員的支持。因潘時彤十分熟悉武侯祠,又是當時成都著名學者,“著述宏富,向曾延修邑乘,稱博雅焉”,遂得張合桂邀請修撰廟志。道光七年(1827年),潘時彤開始修纂廟志。他日以繼夜,以一人之力,用21個月時間完成了《昭烈忠武陵廟志》30萬字文稿的撰寫。脫稿后,經陸文杰、道士黃合初等人校對,再由戴三錫等十人鑒定,成都縣知縣王升元等四人參閱后,于道光九年初雕版成書。這部志書也以張鵬翮的《忠武志》為主要參考書。《昭烈忠武陵廟志·凡例》云:“斯地陵廟,舊無專志,茲歷稽正史,旁及叢書,并取資升庵《全蜀藝文志》《四川通志》,遂寧張相國《忠武志》,古虞朱太守《丞相集》,武威張介侯明府《諸葛武侯故事》諸書。”[15]此說明張鵬翮的《忠武志》對潘時彤的《昭烈忠武陵廟志》也產生了直接影響。張鵬翮、李復心、潘時彤都是四川人,雖然也屬明清移民的后代,但他們具有濃郁的蜀漢文化情結。三人都是諸葛亮的忠實粉絲,三部著作都寄托著他們的思想情感和對家鄉的熾熱感情。
(三)諸葛文化,成為扛鼎之作
張鵬翮的《忠武志》承前啟后,古今結合,縱橫交錯,貫通文史,成為諸葛亮文化的扛鼎之作,三國文化的經典文獻,諸葛亮志書的典范之作。
首先,內容宏富,是研究諸葛亮的百科全書。張鵬翮文友兼幕府知己的劉廷璣為《忠武志》所寫的“跋語”說:“舉凡侯出處之正,抱負之宏,得君之專,托孤之誠,知人之明,刑賞之公,制度之巧,用兵之神,薦賢之忠,聲教之廣,將略之深沉,相業之彪炳,與夫帝統正閏之辨,一展卷間,了如指掌。”“后之人展讀是編,慨然敬慕侯之為人,則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16]這是說有《忠武志》一卷在手,即可以全方位領略諸葛亮文化與三國文化的豐富多彩。
其次,體例創新,是忠武侯志書的典范之作。《忠武志》繼往開來,在體例上有諸多創新。全書由八卷構成,篇目是:卷一本傳、年表、世系,卷二心書、新書,卷三遺文,卷四遺制,卷五遺事、用人、勝跡,卷六表、碑記、銘贊,卷七評、論、辯,卷八序文、詩賦。其與明代王士騏的《武侯全書》、楊時偉的《諸葛忠武書》、諸葛羲的《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相比,突出了諸葛亮的主體地位。它將本傳、年表、世系放在卷一,給讀者以立體化的、全方位的諸葛亮及其家族的文化印象,然后是諸葛亮的文章和事功,最后是有關贊頌諸葛亮的詩文。這種體例被后世繼承和發展。
再次,思想領航,是儒家重名教的經典文獻。張鵬翮是理學名臣。他崇尚程朱理學,主張以蜀漢為正統。他在《忠武志》序言中說:“文中子云:‘武侯無死,禮樂可興。朱子稱之曰:‘武侯智慮日益精明,威望日益隆重,俱從寡欲養心中得來,良有以也。程子曰:‘大臣功蓋天下,必誠積于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然后無專權之過,斯可得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嗚呼!周公圣人也,程子以周公孔明并稱,其推許武侯至矣。”[17]從中可知,宋代理學大師對孔明的推崇,對張鵬翮產生了較大影響。他以諸葛亮為理學的道德偶像。因而劉廷璣在《忠武志》“跋語”中說:“是編之有關于名教,豈淺鮮哉!”[18]
總之,張鵬翮的《忠武志》在明清諸葛亮文化及三國文化書寫蔚然成風的時代潮流中,繼往開來,影響深遠。
三、張鵬翮所編《忠武志》的影響
張鵬翮的《忠武志》誕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既是盛世思想文化的一大碩果,又是崇尚諸葛亮、追求大統一的時代潮流的一朵浪花。它扭轉了重文輕史的三國研究學風,開啟了諸葛亮文化的“志書時代”,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它將諸葛亮推上了與周公、孔子等量齊觀的崇高地位。張鵬翮贊頌諸葛亮是“儒者之氣象,王佐之經綸。去利以懷義,純忠而得仁。”[19]
其次,它開啟了諸葛亮文化遺存的志書時代。在其影響下,《臥龍崗志》《忠武侯祠墓志》《昭烈忠武陵廟志》等相繼產生。
再次,它成為諸葛亮與三國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雖然張鵬翮的《忠武志》主要是薈萃有關諸葛亮的文獻,但這種系統化的整理,給我們提供了研究的便利。
總之,張鵬翮的《忠武志》是盛世的杰作。其以編輯思想的深刻、體例的科學與內容的廣泛、文字的謹嚴等,彪炳當世,澤被來者,值得今人高度重視。
注釋:
[1][2]胡傳淮主編《張鵬翮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第153頁。
[3]張鵬翮:《信陽子卓錄》卷四,《四川文脈從書》,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版。
[4]張知雄:《遂寧張氏家乘》,清光緒刻本。
[5][6][7][8][16][17][18][19]張鵬翮:《忠武志》,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版,第1頁,第1頁,第2頁,第3頁,第3頁,第1頁,第3頁,第4頁。
[9][13][14]李復心:《忠武侯祠墓志》序及卷一,清同治六年刻本。
[10][11]羅景:《臥龍崗志》卷二,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2]林則徐著、鄭麗生校箋《林則徐詩集》,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頁。
[15]潘時彤纂輯、吳洪澤校點《昭烈忠武陵廟志》,成都時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作者:陜西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