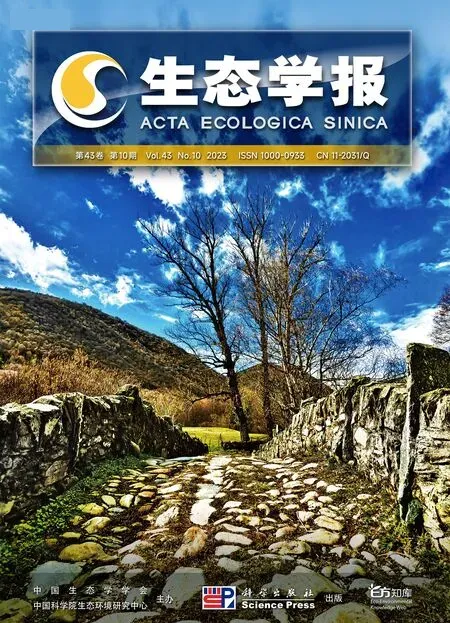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及應對路徑
——以青海省為例
張 健,周 侃,*,陳妤凡,3
1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可持續發展分析與模擬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01
2 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049
3 寧波大學地理與空間信息技術系,寧波 315211
隨著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牧業現代化不斷推進,城鄉聚落經濟規模擴大、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城鄉居民生活垃圾產生量和組分特征發生根本性變化[1],由生活垃圾治理不當導致的面源污染問題日益突出[2]。尤其在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由于當地氣候高寒性、城鄉居民點分布零散性以及建設資金長期短缺,生活垃圾治理面臨處理設施配置滯后、集中治理服務覆蓋范圍不足等失效挑戰[3],逐漸成為損害青藏高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潛在風險。一方面,城鄉居民點生活垃圾的無序堆放和隨意處理,已造成局部地區水環境、土壤、大氣環境污染[4],破壞居民生活環境質量。另一方面,高原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難度大、運維成本高[5],現行垃圾治理體系難以在青藏高原長效運營。因此,探究生活垃圾治理失效背景下生態環境風險及應對路徑,是提升青藏高原地區生活垃圾治理能力的關鍵環節,對改善人居環境、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從垃圾末端處理不當導致的地下水污染[6]、土壤污染[7]、空氣污染[8]等環境問題出發,研究生活垃圾治理污染風險,并從污染擴散[9]、治理服務供給能力[10]、設施選址[11]等方面探討潛在風險。研究涉及小城鎮[12]、城市[13]、國家[14]、洲際[15]尺度等,并從設施布局調整、技術改進、體系建設等方面提出相應的優化措施[16—18]。其中,國內多從社會學[19]、管理學[20]、農學[12]、環境科學[7]等學科視角,運用問卷調查[14,21]、實地調研[22]、樣品測量[23—24]等方式,從居民感受反饋[2]、環境污染負荷現狀[6]、垃圾處理設施配置數量[14]等主客觀角度揭示不同地區城鄉居民生活垃圾的治理效果及其生態環境影響,研究范圍多集中在中部、東部經濟發達省份的平原區[25]以及西部中心城市[26]等。由于統計數據獲取困難,針對青藏高原地區的相關研究較少,少數已有研究通過統計分析等方式揭示青藏高原垃圾收運處置設施建設落后[3]、垃圾集中收集難度大[23]、垃圾無害化處理程度低[27]等實際問題,并初步提出增強居民環境保護意識、加大垃圾處理設施配套資金力度、完善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制度等改進措施[28—29]。然而,現有研究多以垃圾處理設施單要素配置為判斷指標,間接評估由垃圾處理設施配置不足導致的生態環境風險,較少從體系視角結合垃圾治理實際過程系統評估,未考慮一般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在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失效問題。因此,亟待綜合收集、轉運、處理三個垃圾治理關鍵環節,從微觀尺度定量揭示垃圾治理失效引發的生態環境風險,為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因地制宜優化生活垃圾治理體系提供科學依據。
針對相關研究在生態屏障區的研究不足以及不同尺度風險定量分析的空缺,本研究以綜合評估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態環境風險為科學問題,以青海省4306個城鄉居民點為研究對象,選取垃圾集中治理率作為特征指標,在測度青海省城鄉聚落生活垃圾產生及治理水平基礎上,基于生活垃圾治理體系的收集、轉運與處理全過程視角構建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框架,采用主客觀綜合賦權的TOPSIS方法和障礙度模型,多尺度評估城鄉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并識別風險管控阻滯因子,探討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優化對策及差異化垃圾治理模式。
1 材料與方法
1.1 基本概念與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生活垃圾治理作為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重要內容,是針對城鄉居民日常生活消費中產生的固體廢棄物管理活動的總和[30—31],生活垃圾治理一般包括收集、轉運與處理三個基本環節。生態環境風險則是在一定地域和時間范圍內,由環境變化、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等不確定性事件引發生態環境組分、結構及功能損失等不利影響的可能性[32],指示生態環境安全與健康水平。基于此,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態環境風險特指由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失效導致生活垃圾未合理處置而使生態環境受損害概率,其本質是生活垃圾治理效能穩定性、生活垃圾污染危害性共同作用表征的當地生態環境脅迫程度。
生活垃圾治理通常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按“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模式將城鄉居民點產生的生活垃圾經由收集轉運網絡匯集至垃圾填埋場等末端處置設施集中處理。在青藏高原特殊自然與人文特性影響下,現有生活垃圾治理體系面臨收集不便、轉運困難、處理低效、設施滯后等現實問題,導致垃圾過度堆放、遺撒滴漏、不當填埋焚燒等污染脅迫,使大氣、水、土壤、生物環境暴露于生活垃圾治理失效風險之中。據此,借鑒已有生態環境風險研究[33—34],以生活垃圾治理失效原因和風險生成機制為評價基礎,考慮評價尺度轉換和風險疊加遞進關系,構建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概念框架(圖1),通過“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治理體系具體環節表征風險強度。進一步地,基于改進的災害風險評價范式[32,35],將治理環節與危險度、暴露度、脆弱度三類風險構成要素匹配融合,刻畫村、鎮(鄉)、縣(區)不同尺度風險過程。

圖1 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概念框架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co-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barrier zone
在評價概念框架基礎上,結合已有青藏高原生態風險評價研究和垃圾治理研究[3,36—44],遴選適宜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自然環境與垃圾治理體系不同層級尺度的核心指標,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表1),共包括9個評價要素和12個評價指標。其中,準則層中的垃圾收集、轉運、處理環節分別從村域尺度、鎮域尺度和縣域尺度,以危險度、暴露度、脆弱度為基本要素評價生活垃圾治理失效風險。因而,該指標體系可對不同垃圾治理環節與不同行政層級進行分解評價,提升垃圾治理體系優化策略針對性與實操性。

表1 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co-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barrier zone
1.2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青海省位于北緯31°39′—39°11′,東經89°25′—103°04′,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部,土地總面積約為72.23×104km2。青海省地勢高聳,地貌類型復雜多樣,平均海拔約4171.27m,屬高原山地氣候,其范圍和高程分布如圖2所示。青海省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大江河發源地,是維系我國乃至亞洲水資源安全的戰略要地和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45],兼具生態脆弱性和敏感性強、生態保護重要性突出的特征。2021年,青海省常住人口達592.4×104人,人口密度僅為8.2人/km2,城鄉居民點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聚”特征。在我國現行“村收集、鎮(鄉)轉運、縣(區)處理”生活垃圾治理體系[30]下,青海省是生活垃圾治理的弱勢區域,以青海省為例探究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態環境風險和應對路徑具有一定代表性,對維護青藏高原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安全屏障功能具有現實意義。

圖2 青海省高程與各類居民點分布Fig.2 Elev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Qinghai Province
本研究數據主要包括地理信息數據和社會經濟與垃圾治理調查數據。①地理信息數據:行政區邊界數據來自中國1:400萬基礎地理要素數據集;數字高程模型數據(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來自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生態脆弱性評價數據集等來自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②社會經濟與垃圾治理調查數據:以青海省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2016年)為主,缺失的部分數據依據省級、州市級統計資料進行補充收集與校對。
1.3 研究方法
1.3.1生活垃圾產生與治理水平測度
目前,青藏高原生活垃圾產生量的數據來源較少,且存在不完善、不準確等問題,需要以居民點為單元,估算青海省城鄉生活垃圾產生量。針對生活垃圾產生量的估算,一般從人均生活垃圾日產生量入手,采用抽樣實測、文獻研究、問卷調查、數學預測模型等方法得到產量參數[46](表2),但由于針對農牧區居民人均生活垃圾日產生量測算較少,且生活垃圾產生量具有地域差異特征,故需修正參數以滿足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研究需要。基于青海省經濟發展水平和能源結構特點[27],本研究將人均生活垃圾日產量參數范圍設置于0.16—0.80 kg 人-1d-1之間。

表2 生活垃圾人均日產生量研究結果Table 2 Research on daily generation of domestic waste per capita
根據居民主要從業類型與居民點地理位置,將城鄉居民點劃分為牧民定居點、鄉村居民點和城鎮居民點3種類型[50],并結合青海省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中“月均生活垃圾清運量”這一普查項進行判別[51],在參數范圍內將估算結果與普查數據進行比對,將總相對誤差[|普查數據-估算結果|/普查數據*100%]控制在5%以內,最終設置各類居民點人均生活垃圾日產生量參數:牧民定居點0.25 kg 人-1d-1,鄉村居民點0.40 kg 人-1d-1,城鎮居民點0.60 kg 人-1d-1。
在估算生活垃圾產生量基礎上,通過垃圾集中治理率指標刻畫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內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垃圾集中治理率為實現垃圾集中治理居民點的生活垃圾產生量占垃圾總產生量的比重。居民點內生活垃圾是否集中治理根據青海省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生活垃圾是否集中處理”這一普查項對居民點進行判別[51]。通過測算轄區內居民點生活垃圾集中治理率向上匯總得到鄉鎮、縣區、州市尺度垃圾集中治理率。
1.3.2基于TOPSIS模型的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方法
TOPSIS模型是基于理想解排序的多指標決策方法,已廣泛應用于生態風險評價領域[52]。本研究進一步采用主客觀綜合賦權的方式改進TOPSIS模型中理想解的計算過程,避免單一賦權方法的偏差。主觀賦權法使用層次分析法[53](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客觀賦權法使用熵權法[54](Entropy Weight Method,EWM)。將兩種賦權法得到的權重通過線性組合的方式進行疊合[55](式1),得到層次分析法和熵權法的組合權重W:
W=αWAHP+(1-α)WEWM
(1)
式中,WAHP表示層次分析法計算出的權重,WEWM表示熵權法計算出的權重,α為權重偏好系數,本研究中取α=0.5。最終,分別應用層次分析法和熵權法計算得到的組合權重如表3所示,其中,層次分析法計算中各判斷矩陣均通過一致性檢驗(CR≤0.1)。

表3 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指標權重Table 3 Weight value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本研究將組合權重代入TOPSIS評價模型,計算得到4306個居民點的風險評價指數R,并將風險評價指數歸一化至[0,5]范圍內。根據相關研究[56],將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劃分為5個等級,依次為低風險(0≤R<1)、中低風險(1≤R<2)、中風險(2≤R<3)、中高風險(3≤R<4)、高風險(4≤R≤5)。在此基礎上,通過各級行政區劃范圍內匯總統計,即可得到鄉鎮、區縣、州市尺度的風險指數(轄區內所有居民點風險指數平均值)。
1.3.3基于障礙度模型的生態環境風險管控阻滯因子識別方法
采用障礙度模型[57]定量識別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管控的各類阻滯因子及阻滯程度。評價方法如下:用因子貢獻度表示單個評價指標對總目標貢獻大小,一般用指標i的權重Wi表示;指標偏離度Ii為指標實際值與風險管控目標值的距離之差,在本研究中Ii等價于各指標經過標準化后的值;障礙度Oi表示各評價指標對風險管控的阻滯程度大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式2):
(2)
式中,n代表單項指標個數。在要素層內對障礙度Oi求和得到不同要素障礙度Tj(式3):
(3)
式中,j表示第j個評價要素,m代表評價要素中的單項指標個數。
2 結果與分析
2.1 生活垃圾產生量與治理水平
2.1.1生活垃圾產生量總體特征及空間分布
青海省城鄉生活垃圾產生量總體較低。2016年,城鄉居民點生活垃圾年產生量約為60.17萬噸,人均生活垃圾日產生量為392.12 g人-1d-1,低于青藏高原城市居民平均水平1370.00 g人-1d-1[58],也低于全國農村居民平均水平790.00—860.00 g人-1d-1[14,21]。不同類型居民點產生量差異顯著,城鎮居民點、鄉村居民點、牧民定居點生活垃圾年總產量分別為24.82、19.26、16.08萬噸,城鎮居民點產生量顯著高于其他類型居民點。州市尺度青海省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如圖3所示,河湟谷地區的海東、西寧2地市內多城鎮居民點和鄉村居民點,垃圾產量最高,分別為20.67萬噸和18.48萬噸;青南高原地區玉樹、海北、黃南、果洛4地州內以農牧民散居為主,垃圾產生量分別為3.73、2.68、2.48、1.84萬噸。

圖3 青海省州市尺度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對比 Fig.3 Annual generation of domestic waste in Qinghai Province at the prefecture scale
青海省城鄉生活垃圾產生呈整體分散、局部組團式集中空間分布(圖4)。以西寧、海東為主的河湟谷地區居民點分布密集,產生量呈組團分布并顯著高于其他地區。以格爾木、大柴旦、德令哈、茫崖為主的柴達木盆地區內垃圾產生量主要來自縣級政府駐地鎮及其周邊地區城鄉聚落。青南高原地區生活垃圾以分散分布為主,年產生量明顯低于其他地區,尤其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居民點年產生量基本在300噸以下。不難發現,不同區域內垃圾產生量和垃圾分布特征的異質性顯著,導致不同地區生活垃圾治理體系配置成本差異。經濟相對發達的人口密集區應是生活垃圾治理體系的配置主體;相反,由于地理環境原因,散居的牧民定居點經濟條件相對落后,垃圾治理體系運維成本高、經濟負擔重。

圖4 青海省城鄉居民點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分布Fig.4 Distribution of annual domestic waste gene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Qinghai Province
2.1.2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及地域分異
青海省城鄉居民點生活垃圾集中治理率為62.33%,2016年中約有22.66萬噸生活垃圾未得到集中治理,尚有183.36萬居民和2246個居民點未納入生活垃圾集中治理服務范圍。河湟谷地區的海東、西寧兩地市生活垃圾治理水平較高,垃圾集中治理率均超過60%(圖5)。但仍需關注的是,由于該地區人口規模基數大、居民點分布密集,兩地市尚有95.60萬居民未納入生活垃圾集中治理服務,涉及未集中治理生活垃圾12.87萬噸,分別占全省27.39%和29.42%,垃圾治理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在青南高原地區內,垃圾產生量分散、垃圾處理設施配套滯后等問題嚴重制約垃圾處置效果。果洛州垃圾集中治理率僅為6.79%,州內約有14.66萬居民的生活垃圾未得到集中治理,尤其是大量未實現垃圾集中治理的居民點位于黃河源腹地,對生態屏障區生態安全格局構成直接威脅。

圖5 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多尺度分布Fig.5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Qinghai Province at multi-scale
鎮域尺度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對比發現,生活垃圾治理服務未能有效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盤。非縣級政府駐地及其連片區域的一般鄉鎮平均垃圾集中治理率僅為42.84%,覆蓋全省人口74.62%,集中治理率為0的鄉鎮占比更是高達26.72%。作為“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生活垃圾治理體系中的關鍵節點,鄉鎮層面垃圾處置的失位將使得垃圾收運處理各環節難以發揮應有的治理效果。由于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資金缺乏與地區間設施配置成本差異,青海省各縣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西寧市各縣平均垃圾集中治理率達82.04%,其中,城中區所轄范圍內居民點垃圾集中治理率達100%,而果洛州各縣平均集中治理率僅為7.62%,遠低于青海省各縣平均水平56.34%,達日縣和久治縣更是2016年全省僅有的垃圾集中治理率為0的縣區。綜合上述分析發現,目前生活垃圾治理在青海省同時面臨人口密集區垃圾治理壓力大、生態環境脆弱區垃圾處理設施供給不足等挑戰,垃圾治理體系配置的非均衡性突出,生態屏障區面臨生活垃圾治理失效的直接威脅。
2.2 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等級
2.2.1生態環境風險等級總體特征
整體上,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較高,各地市間生態環境風險差異顯著(表4)。從全省尺度看,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指數達2.42,生態環境處于中風險等級水平,其中,中高風險及以上居民點占比達36.90%,表明生態屏障區生態環境面臨普遍垃圾治理壓力。地市尺度上,除西寧市屬于中低風險等級以外,所有地市均處于中風險或中高風險等級,進一步反映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整體較高的現狀,亟待強化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防范意識,健全垃圾治理體系以降低風險等級。此外,三江源地區內的海南、黃南、玉樹、果洛四地市低風險等級居民點僅分別占比6.36%、11.65%、0.00%和0.00%。其中,果洛州由于高寒性氣候特征,供氧條件差、地形起伏大,垃圾收集轉運困難,垃圾處理設施配置嚴重缺位,其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最高,風險指數達3.79,全州92.59%居民點處于中高風險或高風險等級,降低三江源地區等重點生態功能區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的必要性、緊迫性突出。

表4 青海省及各地市居民點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等級Table 4 Eco-environmental risk level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of settlements in Qinghai Province
2.2.2生態環境風險等級地域分異
空間上,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呈現“南高北低”的地域差異(圖6),并呈河湟谷地區向柴達木盆地區、環青海湖及祁連山地區和青南高原地區風險遞增態勢。位于河湟谷地區和柴達木盆地區的居民點,由于垃圾集中治理率相對較高,即使生活垃圾產量水平高,其生態環境風險等級也顯著低于青南高原地區,強化青南高原地區全域生活垃圾治理是生態屏障區生態環境風險防范的重中之重。但也要看到,河湟谷地區內部仍然有892個居民點處于中高風險或高風險等級,占同等級居民點的56.14%。因此,在防范重點生態功能區垃圾治理風險同時,應當警惕居民點分布密集、人類開發活動強度較大的河湟谷地區居民點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等級提升。

圖6 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多尺度分布Fig.6 Eco-environmental risk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Qinghai Province at multi-scale
結合鎮域尺度和縣域尺度結果進一步發現,生活垃圾治理風險總體呈河湟谷地區“低值集聚”、青南高原地區“高值集聚”的空間格局。在地區內部,風險值表現為以縣級政府駐地鎮為中心向外圍梯度遞增的態勢,縣級政府駐地及其連片鄉鎮垃圾治理風險平均值為1.84,而一般鄉鎮則高達2.70,充分說明由垃圾治理服務供給不均導致的生態環境風險等級差異。此外,環青海湖與祁連山地區、三江源地區等重點生態功能區范圍內鄉鎮生態環境風險等級以中風險和中高風險為主,進一步表明當地生活垃圾治理體系難以適配生態安全屏障建設要求,易對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構成威脅。
2.2.3生活垃圾治理環節生態環境風險等級差異
生活垃圾治理各環節風險差異顯著(圖7),收集、轉運、處理三個環節的風險評價值分別為2.24、2.43、2.33。“鎮轉運”環節在現行生活垃圾治理體系的生態環境風險最高,祁連山脈、昆侖山脈東段以及青南高原峽谷地帶由于地形起伏大、地表生態環境脆弱敏感,轉運環節風險突出。一方面,垃圾轉運環節失效將直接擴大垃圾清運處理的暴露風險,破壞當地的生態屏障功能,另一方面,垃圾轉運環節的缺位造成垃圾收集環節與處理環節難以有效銜接,不利于現行生活垃圾治理服務的長效運營。此外,垃圾“縣處理”環節方面,26.09%的縣區處于中高風險和高風險等級,生態環境風險仍相對較高。需注意的是,縣城處理環節作為垃圾治理的末端環節,其垃圾處理水平高低基本塑造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格局。因此,提升縣城垃圾無害化處理技術和消納能力仍是降低垃圾治理總體生態環境風險的根本基礎。垃圾“村收集”環節方面,雖風險指數較低,但僅有4.76%的村收集點處于低風險狀態,體現出青海省山地地貌和垃圾產生量分散分布對村內垃圾收集的普遍約束作用。

圖7 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各環節生態環境風險Fig.7 Eco-environmental risk of each aspect of the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Qinghai Province
2.3 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管控阻滯因子
垃圾轉運危險度和垃圾處理危險度為青海省大部分縣區風險管控主要阻滯因子(圖8),管控障礙度分別為18.14%和22.72%。在青藏高原,高寒氣候和山地地貌是限制垃圾轉運的根本原因,垃圾處理技術適用性低和資金投入不足導致垃圾處理技術滯后性突出,研究適用于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復雜地理環境的垃圾轉運方式和分散式垃圾無害化處理技術對降低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態環境風險至關重要。從所有縣區障礙度來看,可根據不同阻滯因子的作用大小,將各州市內部縣區劃分成不同風險管控阻滯類型。西寧市各縣區內居民點分布密集、人均垃圾產生量高,導致垃圾收集因子成為垃圾治理風險管控的單一阻滯因子。海西州各縣區呈“轉運—處理”因子的雙重阻滯,該地區內生態環境脆弱惡劣、居民點分布分散,垃圾集中收運成本和垃圾處理設施的配置難度均較高。海東、海北、海南、玉樹四地市各縣區主要受“收集—處理”因子雙重阻滯,這些地區山地峽谷地貌廣布,居民生活垃圾投放較為困難,同時,高海拔造成的低氧條件也阻礙一般垃圾處理技術的有效應用。黃南、果洛兩地市則屬于“收集—轉運—處理”因子的綜合阻滯,當地高寒氣候條件以及高生態保護重要性使垃圾收集脆弱度及暴露度、垃圾轉運危險度和垃圾處理危險度等因子均構成顯著的阻滯作用。生活垃圾治理風險的疊加效應,使管控阻滯因子作用隨風險值上升而復雜化,存在多重短板的垃圾治理弱勢地區是垃圾治理體系優化配置的關鍵地帶。

圖8 青海省各縣區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管控障礙度Fig.8 Proportion of obstacle to eco-environment risk control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Qinghai Province at the county scale
3 討論
3.1 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優化建議
根據不同區域風險管控阻滯因子差異,從設施配套、政策支持、基層引導三個層面出發,結合垃圾治理體系中的收集、轉運、處理環節針對施策,以生活垃圾全處置和生態環境零脅迫為導向,綜合提升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效能:①設施配套層面,對照風險管控主導阻滯因子,補強生活垃圾治理的軟硬件弱項。在有條件農牧區逐步推行簡單易用的垃圾分類收集設施,推動居民點生活垃圾干濕分離和分類回收;在交通區位偏遠的農牧民定居點,以固定和彈性轉運相結合的方式靈活配置垃圾轉運站點和轉運車輛,形成垃圾跨區轉運與就地消納并舉的收轉運體系;加快推進高溫熱解處理技術、閃蒸礦化垃圾處理技術等適用于青藏高原低溫低氧條件的環境友好型垃圾處理技術裝備配置。②政策支持層面,應完善高效收集與處理的獎補政策機制,強化生活垃圾多元共治。一方面,通過稅收減免、資金補貼等方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農牧區生活垃圾治理體系,減輕政府垃圾收運與處置職能負擔;另一方面,可根據農牧區實際需要設置專項清潔員、生態環境管護員等專職崗位,激發原住居民參與垃圾治理積極性,對表現突出的村集體及個人,給予治理工作補貼、農牧產品收購補貼、垃圾治理積分兌換等多項獎勵措施;③基層引導層面,加強城鎮與農牧居民環境倫理教育,規范垃圾治理行為。以當地居委會、村委會、牧委會為組織單位,借助學校、寺廟、農牧民集市等場所,通過廣播、公示欄公告、橫幅標語、入戶宣傳等多元方式宣傳垃圾治理成果與效益,營造全民參與垃圾治理良好氛圍;在生態敏感區、牧民定居點、高山峽谷等生活垃圾治理薄弱區域,適度引導農牧民通過回肥、回填等方式就地消納處置,推進生活垃圾源頭減排。
3.2 生態屏障區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空間配置
目前,“村收集、鎮(鄉)轉運、縣(區)處理”的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已在平原地區村鎮得到廣泛應用[30]。然而,上述實證分析表明,由于生態環境的敏感性和居民點“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差異性,現行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在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難以普適應用。因此,應基于城鄉聚落與生活垃圾產污分散性,充分考慮垃圾治理全過程的生態環境風險,將生活垃圾治理體系配置的基本單元由縣域下沉至鎮域尺度,綜合研判城鄉居民點適宜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
根據生態環境風險評價結果在收集風險、轉運風險、處理風險不同維度上的耦合性,從居民點層級識別不同區域垃圾治理的薄弱環節與優勢環節,從而針對性地提出垃圾治理模式優化方案:①在垃圾處理環節風險較低的縣級政府駐地村、鄉鎮政府駐地村等人口相對密集的城鎮居民點,應發揮垃圾收運優勢區位條件,融入縣城垃圾收運處置體系,實施“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城鄉一體化生活垃圾治理模式;②在生活垃圾轉運環節風險相對較低、生活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的農牧民居民點,可以借助垃圾轉運便利條件,在村鎮居民點聚集區域增設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吸納周邊居民點生活垃圾集中治理,實施“村收集、鎮處理”的鄉鎮集中治理模式;③在生活垃圾收集風險較低,但是不具備生活垃圾轉運條件、且人口規模相對較小的偏遠農牧民定居點,宜通過小型、分散、環保的終端處理工藝,以無害化填埋、焚燒、堆肥、沼氣池處理等方式實現垃圾在地化處理,實施“村收集、村處理”的村分散治理模式。根據城鄉居民點垃圾治理模式空間配置特征,以鄉鎮為單元實施鎮域片區治理如圖9所示。其中,在以西寧、海東為主的河湟谷地區,以城鄉一體化治理片區為主、鄉鎮集中治理片區為輔;在柴達木盆地區、祁連山地區、環青海湖地區,以城鄉一體化治理片區為主、村分散治理片區為輔;在青南高原地區,以村分散治理片區為主、鄉鎮集中治理片區為輔。

圖9 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空間配置Fig.9 Spacial configuration of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model in Qinghai Province
4 結論
本研究以青海省4306個城鄉居民點為例,多尺度評價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生態環境風險,為系統優化現有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及治理模式空間配置提供科學依據。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 青海省城鄉生活垃圾產量及治理水平均較低。2016年,生活垃圾年產生量約為60.17萬噸,人均生活垃圾日產生量為392.12 g人-1d-1。城鄉生活垃圾產生呈整體分散、局部組團式集中空間分布。全省垃圾集中治理率為62.33%,尚有183.36萬居民和2246個居民點未納入生活垃圾集中治理體系。
(2) 青海省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態環境風險指數達2.42,總體處于中風險等級水平,中高風險以上居民點占比超過三成。生態環境風險呈現“南高北低”的地域差異,且河湟谷地區向柴達木盆地區、環青海湖及祁連山地區和青南高原地區呈風險遞增。現行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在鎮級轉運環節的生態環境風險最高,祁連山脈、昆侖山脈東段以及青南高原峽谷地帶轉運風險突出。
(3) 以生活垃圾全處置和生態環境零脅迫為導向,提出生活垃圾治理風險應對路徑:補齊生活垃圾治理的軟硬件短板;完善高效收集與處理的獎補政策機制;加強城鎮與農牧居民環境倫理教育。同時,優化居民點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空間配置,將生活垃圾治理體系配置的基本單元由縣域下沉至鎮域,因地制宜實施城鄉一體化治理、鄉鎮集中治理、村分散治理三類鎮域片區治理模式。
未來值得繼續研究的方向:鑒于生態屏障區現有垃圾收運處理設施承載能力短板,應結合外來游憩活動、節日集會等垃圾產生峰值情景,探索生活垃圾彈性收轉運周期和路徑優化模擬方案;針對城鄉一體化治理、鄉鎮集中治理、村分散治理等不同模式可行性實證不足,需從投入成本、處置效果、環境脅迫等維度構建多目標優化模型,探究經濟成本與生態效益權衡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考慮不同主體參與垃圾治理活動的利益沖突,后續研究應在演化博弈等視角下,深化討論政府、居民、企業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