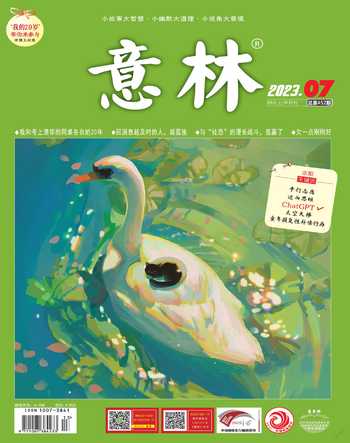與“社恐”的漫長戰斗,我贏了
夏溦

一直替我買飯的同學拜托我給她帶倆包子,為了不讓她失望,我咬牙答應下來。于是,在包子鋪前徘徊半小時后,我終于下定決心走上前去,悶頭說:“買兩個包子。”
熱騰騰的包子拿在手里,我心想:好順利啊。但走到教室門口,聽到同學們人聲喧嚷,我又忍不住身體發抖,一下子癱倒在墻角,無聲地痛哭起來。
自7歲起,我一直抗拒同別人講話,盡可能回避社交。讀大學后,也總是獨來獨往,連去買早餐,也要拜托同學。或許在同學眼中,我冷漠懶惰。但他們不會想到,我是怎樣絕望地隱瞞自己嚴重的社交恐懼癥,極力偽裝成一個“正常人”。
在買包子事件后,我意識到:即便痛苦,但如果逼自己一把,或許會有意料之外的收獲。
我根據由易到難的原則,制訂了一套游戲升級似的自救計劃。首先是生存必備項目:一個人坐公交車。上公交車并不困難,難的是下車。很多時候,司機都會在快到站時,大喊一句:“有下的嗎?”假如無人回應,就會飛馳而過。
中學時代,我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在車廂內大聲回應,能到站下車全憑運氣。為了喊出那句“下車”,我采取的策略是:離司機近一點。成功回答幾次后,我漸漸移動到車廂中部,提升完成的難度。每個周末,我會隨便上一輛公交車,練習開口回應的能力。漸漸地,我能自由下公交車了。
接下來,我開始挑戰去麥當勞點餐。最初我只敢在餐廳門口徘徊,兩個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終于推開那扇幾乎要被我的目光盯穿的玻璃門。
“歡迎光臨麥當勞,請問您要點什么?”漂亮的紅衣女孩看著我,我的心跳猛然加快,抬起顫抖的手指,指向桌面上最顯眼的套餐:“就這個。”
這樣的周末行程持續了大半年,購物和點單依然使我痛苦,但對人的畏懼心理像一塊被細流沖洗的寒冰,正在慢慢地消融。
畢業前,我參加了學校的一場招聘會。我們在夏季悶熱的教室里等待招聘人員。漫長的兩個小時后,招聘方終于來了。他們走進教室,輕描淡寫地說:“都排隊吧。哦,對了,你們沒什么問題吧?”
我“噌”一下舉起手,站起來說:“我有問題。我就想知道,今天的面試時間到底是幾點?”場面陷入尷尬。輔導員出來打圓場:“路上堵車,所以來得晚了一點兒。”
“所謂晚了一點兒,是指兩個小時嗎?這么熱的天,讓我們汗流浹背地傻等,卻等不來一句道歉,我們難道不值得被尊重嗎?”蟬鳴聒噪,教室里卻越發靜謐。我在無聲的人群里,像個熱血主角般慷慨陳詞。
至今我仍不明白,一向逆來順受的自己何以在當時突然爆發,仿佛那個為買包子嚇哭了的社恐患者已消失無蹤。但我清楚地知道,那個社恐患者灰暗的影子一直蟄伏在我的身體里,但我不會再為此自卑和痛苦,我選擇接受“她”也是“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