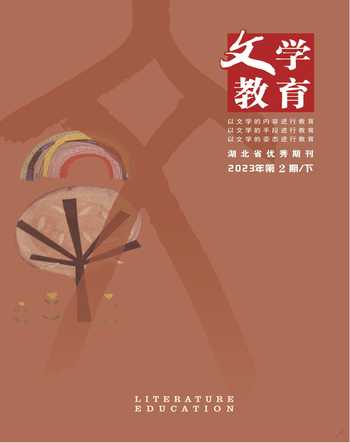“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媒人形象初探
凃皓文
內容摘要:“三言”“二拍”的文本,敘述了婚戀故事中的女性媒人角色群體,透過女性媒人的特點行為展示出其貪圖利益、卑劣巧言的形象,體現出女性媒人在社會地位上的低微。但女性媒人在內容和結構上起到連接男女主人公空間、推動情節衍生的功能性作用。同時其中還暗含著深刻的觀念表達,即女性即使有了打破傳統規范的意識和行為,但最終仍然要回歸封建父權夫權,即男性占話語主導權的儒家秩序之中,若偏離了這一方向,則只能遭受殘酷的壓制。
關鍵詞:“三言”“二拍” 女性媒人 儒家秩序 女性地位
在儒家學者看來,夫妻關系是一切傳統人倫道德的根基所在。婚姻大事自然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里極其重要的一環。在古代中國,很早就有了基本的婚姻制度框架,并在后世逐步形成了以“三書六禮”為主的成熟婚姻制度。而在婚姻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媒妁”同“父母”一道,長期共享著決定青年男女婚事的權力。《孟子·滕文公下》中也有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可見媒人在中國古代婚姻制度里地位崇高。直至明清時期,媒妁制度仍存不廢,風行于民間。媒人說媒是處處可見的尋常景象,儼然為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市民階層在這一時期逐漸發展壯大。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通過其擴大的影響力,沖擊著傳統“士農工商”界限分明的社會結構,以及包含了婚姻制度在內的舊制度。既然對于市民階層而言婚制已然過時,那么媒人的權威也自然跌落千丈。在明代白話小說里,媒人不再是曾經備受重視與尊敬的群體,其自上古時代便具有的“掌萬民之判”的神圣色彩逐步被明代商品經濟中的商業因素和拜金逐利的思想所取代,變成了謀生的普通職業。這種祛魅化加以新興市民階層對傳統婚姻制度一定程度上的背離與不滿,使得媒人在這一時期里的文學形象多以負面為主,少有光彩形象。譬如在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中,替西門慶和潘金蓮通奸牽頭的,正是開茶鋪的兼職媒人王婆。以王婆為代表的媒人,正是明代白話文學里時常出現的女性媒人形象。
通過觀察這一時期里的媒人形象,當可窺見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中晚明社會中所出現的種種新的習俗風尚和價值判斷。
一.“三言”“二拍”中女性媒人的社會地位分析
婚戀故事在“三言”“二拍”中占有較大篇幅,女性媒人在其中起著牽線搭橋的重要作用。文中對女性媒人形象的描寫能夠反映出作者對于這一角色的態度好惡。女性媒人這一角色在男女雙方締結婚姻關系中的社會互動方面起到連接的作用,其社會地位由先天的性別因素和后天的媒妁職業因素影響構成。
基于“三言”“二拍”的文本,我們發現作者在文本中對這些女性媒人的個性和行為進行描寫時,蘊含著對這類角色的態度傾向。故事情節中,她們在促成男女相會的過程中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以及為達到的目的和結果,大都是令人不齒的。作者在文中偶爾對其有著直接的批判,例如“富貴隨口定,美丑由心生,再無一句實話的”以及“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都可以反映出作者對于這類群體的貶低。由此可見,作者在對媒人角色的態度上厭惡明顯多于喜好。
故事中作者貶低的這一部分媒人角色,主要由婆子老媽等群體承擔,這類人的稱呼大多采用“媒”“婆”“嬤嬤”等稱謂,甚至有的被省去了姓氏,對其描寫也往往較為簡略;也有部分年齡較為年輕的丫鬟在故事中充當了女性媒人的角色,她們的名字也并非自己的本來姓名。文中的女性媒人有些是職業媒人,也有兼職媒人——有的甚至將其他職業作為說媒的幌子。“三言”“二拍”的故事中,大部分女性媒人貪財好利,為了一己私欲常采用設計誘騙等手段,通過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夸大其詞、弄虛作假,來促成婚姻。她們作為男女締結婚姻關系的重要角色,往往沒有盡到媒人應有的責任,其盡職業義務的前提是利益的驅使,在其與社會的互動中違背了角色的行為規范,在市井百姓心中的形象也就較為卑劣。
二.“三言”“二拍”中媒人形象及其功能
在作者對女性媒人的敘述中,負面印象成為這一類社會群體在“三言”“二拍”中帶給讀者的第一直觀感受和閱讀體驗。作者對女性媒人群體的貶斥,不僅在文本中以說書人的角度直截了當地評論;同時,在對這些媒人的形象塑造上也多貶抑諷刺。
其一是缺乏豐滿形象,在文本中難以真切的看到此類角色的真實形象,即使她們職業各異,可以以“三姑六婆”籠統呼之,但形象豐滿者甚少,最大的特點便是缺少姓名。例如,“二拍”中的半數以“婚姻”“牽頭”為主題的故事中,出現的媒人幾乎只有姓沒有名,被作者不甚在乎地冠以“媒”“嫗”“婆”等稱呼:“無非姓張、姓李”。她們在故事中也多只有對白,而無外貌服飾等細節描寫。姓名和細節的缺失導致讀者無法從腦海里準確回憶起她們的形象和故事。
其次,則是前文中提及的女性媒人所處階層與自身職業的低賤,在“三言”“二拍”中出場的媒人角色,多是屬于“三姑六婆”之列。馮夢龍《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里提到“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1]其中就包括了牙婆,作者還特意提到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
身為“三姑六婆”的這些女性往往出身不佳,常常在市井中走街串巷,又被時人目之為有悖女德。這些女性媒人往往不僅替人做媒或是“牽頭”,也從事一些商業活動或是其他職業,如《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里的薛婆,便是“賣珠子”的小販。年齡的設置也是作者用以反諷女性媒人的手段,“三言”“二拍”中如薛婆等人皆是老年女性,然而卻替男女青年“做馬泊六”,行事甚不檢點,言語下流粗俗。如薛婆這樣年過五旬的婦人,卻毫無顧忌地向王三巧吐露自己年輕時的各種淫穢丑事,使得三巧“欲心”膨脹。作者通過塑造她們粗俗不堪的言行,對這些壞人清白的婆子進行了尖銳的反諷。
然而,即便是作者對這些女性媒人大多給予鄙夷不屑的態度,或是在文本中極力淡化她們的存在與形象,也無法改變她們在故事情節中起到的功能性的橋梁作用——溝通男女主人公,將兩人的空間連接在一起的作用,同時也能夠對小說情節的縱橫開闔、跌宕起伏、回旋反復起到了很好的推進作用[2]。
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男女主角開始時所處的空間是界限分明的。這也對應著中國傳統社會中男女有別,授受不親的社會意識。這兩者之間如何出現交集?往往是需要女性媒人打破這一界限的阻礙。這些媒人往往能輕而易舉地穿越封建社會的普通青年男女難以跨越的“大防”界線。例如《閑云庵阮三償冤債》中的王守長尼姑,替阮三和陳小姐“牽頭”,二人才得以突破家庭內外的隔絕;那些在肉欲驅使下做出丑事的男女也需要暗中謀劃,例如《陸五漢硬留合色鞋》中的陸婆,就替陸五漢蒙騙了潘壽兒。女性媒人們在情節中功能性極強,是男女主角交流溝通為數不多的途徑,也是從屬于促成男女婚姻這一情節的。媒人在發揮其功能性人物作用的同時,也蘊含了深刻的觀念表達。
三.女性媒人背后隱含的觀念表達
如前文所說,女性媒人事實上起到了連接男女空間的橋梁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也意味著這些女性媒人憑借自身的能力得到了跨越儒家曾經劃定的男女空間界限的機會。高彥頤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認為:明末的大家才女甚至是部分煙花女子,往往通過提高文化修養,構建沒有男性參與的關系網,秘密進入從前只有男性才能踏足的領域。不過,高彥頤的觀點是比較片面的——它的擴展雖然沒有遭到來自男性的過大阻力,甚至得到了男性的支持。但這只是因為她們躲藏在儒家的性別話語體系下,仍然依附著男性而得到的極為有限的妥協。相反,在“三言”“二拍”中,這些女性媒人擴展女性空間的行動,毫無疑問地動搖了儒家的規范。薛婆之流,都不是傳統道德中認可的賢良淑德的女性。同時,她們的社會性別也出現了偏差——她們在文本中幾乎都無法找到所屬的家庭,也沒有其他直系的親屬出現,以一種“無根無葉”的狀態出現在各個文本的情節中——這種狀態在重視血緣宗法關系的中國封建社會是十分特別的。她們在文本中沒有了父、夫、子的束縛和壓制,從事著一些手工業或是小本買賣,做媒也是以金錢作為報酬而進行的,體現著商業交易的性質。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即使是替才子佳人說合姻緣的女性媒人,也是受到“重金相謝”的利益驅使而四處走動——這種完全商業化的行為在當時受到了道德上的譴責。而作者則站在儒家道德的高地,對這一類社會性別偏移的群體進行壓制。
“三言”“二拍”中亦有其他動搖儒家規范的女性,即那些私會傳情的大家小姐。但在文本中,作者幾乎都對此持支持態度,如馮夢龍即以這些突破傳統規范的愛情故事來鞏固支撐自己“情教”的合理性。許多“佳人”的結局最后多為大團圓式的收梢。緣何這類佳人多能得到馮夢龍、凌濛初的寬容?與故事中的女性媒人群體不同,佳人們雖然在其中跨出了簾幕重重的閨閣的束縛,但最后依然選擇了屈服于儒家的“秩序”,如同《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中所提及的:
"進入秩序"是古代愛情小說中最不可少的結局,是不論怎樣千攔萬阻,最終都必定要達到的一種敘事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完滿和完整。[3]
“三言”“二拍”中的閨秀王三巧、劉素香乃至名妓王美娘等“佳人”,都在不同程度以滿足自己的肉欲為標志背離儒家道德,然而最終她們又尋獲了“才子”達成婚姻,以此再次進入儒家秩序,安分地待在“某某之妻”的符號限制里,她們曾經對秩序的“背叛”就這樣被“原諒”了,因此她們重新回到傳統女性的范疇中。馮夢龍、凌濛初對佳人故事的認可,也不過是《浮出歷史地表》所提到的一種隱蔽的“性別整合”——將女子進入封建男性話語統治下的秩序粉飾為唯一的完滿。
既然如此,女性媒人這一始終沒有回到儒家秩序,對社會準則進行沖擊的群體自然會遭到男性的敵對與排斥。在文本中,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這一群體得不到完整的自我,得不到完整的身份以至于“莫名所生所死之義”。[4]通過女性媒人的功能以及形象,實際上仍然只能看到男性作者對封建父權夫權的維護,只不過披上了一層虛幻的愛情的面紗而已。同時在女性這一性別角色的社會關系上,雖然有試圖打破封建傳統束縛,以實現男女在社會關系上的平等的趨勢,但是最終通過媒人受到道德譴責、女性重回封建婚姻體系的結果,男女性別角色仍然回歸了不平等的社會關系,這也是媒人角色側面反映出的觀念表達。
在明代中后期,傳統嚴密的兩性二元對立的空間界限在晚明這一末世變得模糊,不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但根據筆者在本文中的論述,這也不過是一種“性別整合”而已。而女性媒人就是這種性別整合的漏網之魚。
在本文提及的“三言”“二拍”的婚戀故事中,女性媒人這一形象大多由女性承擔,并且多為貪圖利益、行為卑劣之輩,從文本中我們能夠分析出作者對這一群體的厭惡明顯多于喜好,并且在社會地位上也處于較為低微的層次,雖然形象不甚豐滿,但是在文中卻起到了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一方面連接男女主人公,促成婚姻,另一方面對小說情節起到推動作用。除此之外,女性媒人這一角色形象也暗含了深刻的觀念表達。她們追逐利益,像男性一樣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雖然在道德上或許會被譴責,但不可否認她們的確屬于早期的一批類似于“獨立女性”的群體——因為她們擁有工作,不依附于男性,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的自主。但正因如此,她們無法回到儒家的秩序下,并遭到了男性文人的排斥和厭惡。
總體上,“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的確有試圖擺脫儒家體系的束縛,打破傳統的規范的行為,但本質上來看,最終她們還是回到了維護男性話語權占主導,封建父權夫權統治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固化。當時的時代即使存在部分女性意識的覺醒,但依舊缺乏改變這種封建體系的力量,僅僅通過逃避媒妁婚姻的部分覺醒是完全不足以撼動的,這也是馮夢龍和凌濛初思想的局限和他們筆下人物的結局還是被封鎖在傳統規范中的原因,女性仍然沒有突破男女性別空間的約束,在社會地位上處于較低的不平等之位,屈服在了儒家的秩序之下。
參考文獻
[1]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2]程建忠,曾玉梅.論“二拍”婚戀故事中的“牽頭”[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6):54-60.
[3]朱全福.論“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J].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0(06):30-34.
[4](德)奧古斯特·倍倍爾著;沈端先譯.婦女與社會主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
[5]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 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7](元)陶宗儀著;武克忠,尹貴友校點.南村輟耕錄[M].濟南:齊魯書社, 2007.
[8]魏同賢,安平秋主編.凌濛初全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9]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0]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標點本1周易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注 釋
[1]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古今小說[M].鳳凰出版社,2007.15頁.
[2]朱全福.論“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J].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0(06):30-34.
[3]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 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3頁.
[4]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 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