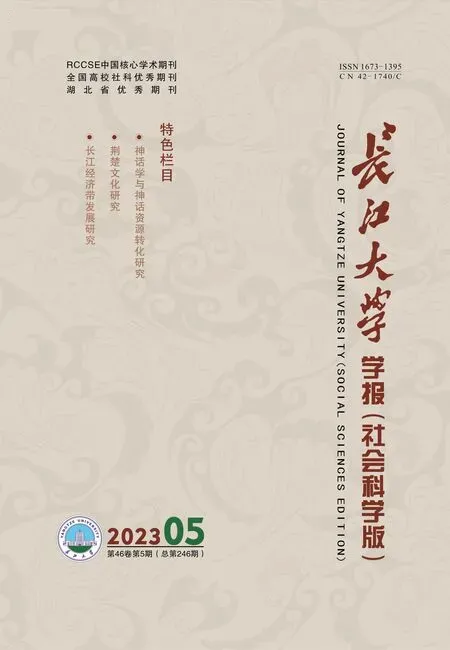神話元宇宙的現代書寫:動畫電影《心靈奇旅》的創意編碼解析
張洪友 蔡嵩霖
(北方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寧夏 銀川 750030)
《心靈奇旅》(Soul)是皮克斯出品的第23部動畫片,該片于2020年12月25日上映,并獲得第78屆金球獎最佳動畫長片獎和第93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通過擬構傳統神話和重塑個人神話,《心靈奇旅》取得了巨大成功。該片不拘泥于單一故事文本,而是模仿神話在傳統社會中所具有的整體性功能。它在模仿傳統神話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可以回答世界的本源、死亡和人的內在本質等問題的幻想世界,并通過主人公在死生之間的探險,重塑有關生命意義的現代神話。
一、神話元宇宙
神話是傳統世界的元宇宙。“元宇宙”由英文Metaverse翻譯而來,該詞源自科幻小說家尼爾·斯蒂芬森1992年出版的小說《雪崩》。在漢語語境中,“元”為本源、源頭的含義。《說文解字》云:“元, 始也, 從一從兀。”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元者為萬物之本。”也就是說,在漢語語境中,“元宇宙”是人類所建立的能夠回答世界終極問題的文化宇宙和意義宇宙。神話與人類相伴而生。“人類對自身必死性的認識以及超越死亡的愿望是神話產生的原動力。”[1](P20)神話必須回答宇宙奧義、死亡和人的內在本質等三大問題。[2](P96)神話給予人類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回答了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等終極問題。神話是對人類的重要價值及終極問題的回答,因此,神話是傳統世界的元宇宙。而《心靈奇旅》則以當下文化視野為基礎,建構了一個力圖繼承傳統神話功能的現代神話元宇宙。
《心靈奇旅》在現代背景下建構了一個模擬傳統神話功能的幻想世界,這個世界融合科學視域與神話思維,雜湊多元神話傳統,并回答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人的個性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
現代社會背景中的神話王國。在人們所生活的日常世界之外,還存在一個神秘世界,這個神秘世界包括人出生之前的世界和人死后的世界。人出生前的世界為生之來處(The Great Before),而人死后的世界稱為生之彼岸(The Great Beyond)。在這個世界,負責計算死亡靈魂數量的特里,更像人類世界中的會計,錙銖必較;而負責教育、看護尚未出生的靈魂的杰瑞們,更像人類世界的老師,他們對待靈魂非常寬容。這個世界現代化設施隨處可見。通向生之彼岸的通道類似大商場的自動電梯,而塑造靈魂生前性格的靈魂學院更像孩子們學習生活的幼兒園和游樂園。學院邀請生前做出杰出貢獻的靈魂擔任尚未出生的靈魂的導師。這些尚未出生的靈魂需要接受導師的指引,激發出火花(spark),才能獲得地球通行證,有資格去地球生活。這種安排更像學生的畢業考試。激發火花的萬物宮殿更類似于地球上的大型購物商場,里面展示了地球上所有事物的模型,用來培養未出生的靈魂對地球生活的興趣。
神話想象與科學視域融合而成的奇妙世界。影片首先運用神話創建形象。杰瑞既是同一個,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名字;卻又不是同一個,因為他們具有不同的形態,并且他們還擁有變化為不同形象的能力。22號和特里也擁有這種能力。與此同時,這種形象又融合了現代科學觀念。比如,杰瑞曾經這樣介紹自己,“我與宇宙的所有量子場同在,以弱小的人腦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現。”神秘世界的形象竟然用“量子場”這種現代物理學術語來介紹自己,讓人嘆服。通過神話與科學共生的方式建構幻想世界,是《星球大戰》以來美國電影的創意傳統。在《星球大戰》系列中,原力是現代科學觀念與神話觀念融合的產物。牛頓力學是現代科學的重要貢獻,《星球大戰》中的原力借用了這個概念,卻賦予其神話內核。漫威公司的《復仇者聯盟》則讓具有魔法、超能力的神話世界的人物形象(雷神托爾、洛基、女武神、古一法師、奇異博士等)與現代科技塑造的超級英雄(美國隊長、鋼鐵俠、綠巨人等)出現在同一個故事宇宙中。這些電影在迎合受眾生活語境的同時,又希望借用神話的力量拓展幻想世界。它們融合科學與神話的力量,創造了現代影像奇觀。
多元傳統雜湊而成的奇幻景觀。“雜湊”(bricolage)是神話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LaPenseeSauvage)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神話書寫基本上是運用現成的神話,拼湊出一個新的神話。[3](P22~23)《心靈奇旅》運用英雄之旅模式展開敘述,在離開、探險、歸來的基本框架上,雜湊了多元傳統,塑造了一個與當下多元傳統融合共生的文化觀念相對應的幻想世界。影片講述了一個不想死的靈魂(喬)和一個不想活的靈魂(22號)的英雄之旅。喬和22號的英雄旅程交疊進行,相互補充。電影中存在著神秘世界與日常世界,而喬和22號都想永遠滯留在各自的世界。喬沉迷在日常世界不想死,因為他還沒有實現自己的音樂夢;22號卻不想活,她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火花,沒能產生活的愿望,是神秘世界的千年釘子戶。但是,喬卻陰差陽錯地成了22號的導師,他對生命的熱情引發了22號的好奇心。喬的靈魂在返回地球的過程中出現了失誤,22號被迫離開靈魂學院,投身到喬的身體中,在自己討厭的地球上探險。通過喬的身體,她品嘗到美味的食物,感受到了地球生活的樂趣。22號在地球上的探險讓她產生了活的愿望。在22號返回靈魂學院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已經獲得了地球通行證。最終,喬,這個不想死的靈魂,扮演著并不屬于自己的角色(博根森博士),卻用糾正混亂人生的熱情完成了許多偉人都未完成的任務。與此同時,22號留在喬身體內的生命感受,激活了已經被喬遺忘的生命記憶。這些記憶使他走出了對生命意義的困惑,放下了生的執念,將通行證還給了22號,拯救了已經迷失的22號,實現了精神的復活。此外,影片著重刻畫了探險中的喬所呈現出的非生非死的獨特狀態。喬因墜入下水道受傷,他的靈魂來到了神秘世界。不過,他的靈魂離開肉體,卻尚未進入生之彼岸,所以他沒有死去。通過月之風等人的幫助,他的靈魂回到了地球,卻不慎投身到了貓的身上,所以他沒有完全復活。死生之間的獨特探險經歷,為喬的精神復活做好了鋪墊。
現代社會的薩滿神話。薩滿源于史前獵人神話,他們為部落提供智慧,治療族人的疾病。在電影中,月之風等人自稱是跨界的神秘主義者。他們實際上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薩滿。“薩滿所特有的這種超乎常人的稟賦, 正是一種超脫凡俗世界而邁進神圣世界的主觀感知調節本領。”[4]就像古代的薩滿,月之風等人神游到神秘世界,拯救地球上迷失的靈魂。在影片的結尾,主人公喬也擁有了穿越日常世界和神秘世界的能力。他重新回到神秘世界,拯救了已經迷失的22號。薩滿是受傷的治療者。薩滿早年經歷過類似精神崩潰的癥狀,通過導師的引導,這些處于精神危機中的個體在更高層面得到復原。[5](P256)薩滿戰勝精神創傷的經歷,使他們擁有指引別人的精神力量。在影片中,有些人無法擺脫自己的焦慮和癡迷,因此切斷了與生活的聯系,成了迷失的靈魂。月之風曾經也是一個迷失的靈魂,他后來從沉迷中覺醒。他戰勝創傷的經歷,使他成為拯救迷失靈魂的星際旅行者。此外,影片還將薩滿的治療儀式和瑜伽的修煉方式融合在一起。喬找到月之風等人,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的靈魂回到在地球的身體中。月之風等人如薩滿般敲鼓、舞蹈,卻要求喬如瑜伽修士般盤腿打坐冥想,以便讓靈魂重新與身體連接起來。他們要喬閉上眼睛,讓自己的能量集中到頭頂的脈輪(Crown Chakra)。此處的Crown Chakra是印度瑜伽的專用術語,意思為“千朵花瓣”。該術語來自昆達林尼瑜伽(Kundalini Yoga)。這一類瑜伽認為,人從頭到腳有七個脈輪,最后一個脈輪就是Crown Chakra。它代表突破一切束縛,與萬物合一,洞悉宇宙奧秘和神秘本源的境界。[1](P116)在月之風等人那里,靈魂只有達到這樣的境界,才能突破兩個世界之間的界限,尋找到自己在地球的身體,從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體中。在具體形象設計方面,影片借鑒了傳統文化。在傳統文化中,薩滿或先知是“神圣的局外人”,處于世俗社會結構之外的“沒有地位的地位”(stateless state)。[6](P117)在現實世界中,他們都是弱小的,沒有地位的;但是,在神秘世界,他們卻是偉大的。他們是偉大的弱者。在影片中,月之風便是此類形象。在現實生活中,他僅僅是一名靠擺弄廣告牌生活的普通人,總被商店老板訓斥;但是,在神秘世界,他卻是迷失靈魂的導師,致力于拯救迷失的靈魂。
坎貝爾認為,“藝術家所必須做的是把原型移譯為活著的當下,一種體現在行動中或內在體驗里的活著的當下。”[7](P217)影片用當下的意象表達永恒的奧秘。它成功打通傳統神話與現代語境之間的壁壘,包容多元傳統,創建了奇特的神幻世界。神話資源成了他們用來打造故事的工具,影片的成功也說明神話資源在這個時代擁有巨大的開發潛力。
二、生命意義的反思與重塑
影片不但試圖建構一個回答生命起源及其歸宿的現代神話元宇宙,而且試圖通過喬的探險,刻畫一幅拯救迷失靈魂的現代心靈地圖。為了尋找讓現代人走出心靈迷宮的方法,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中提出了單一神話。在他看來,傳統神話在現代社會已經支離破碎,人們只能獨自面對眾多心理危機。[8](P101)正因為缺少走出心靈困境的精神力量,許多人被困于內心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迷宮中。他希望為處于困惑中的個體尋找精神救贖之路。[8](P17)運用單一神話及其變體英雄之旅模式的電影,也繼承了這個訴求。《心靈奇旅》便是如此。因此,影片從東西文化交融的語境中展示喬的探險。前半段通過西方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探險,呈現喬追求音樂夢的歷程及其困惑;后半段則通過反思個人英雄主義,探索心靈的救贖等問題。
(一)日常世界里的生命意義
在日常世界,音樂夢是喬的個人神話。“神話,為這個本無意義的世界賦予了意義。神話,是賦予我們存在以重要性的敘述方式。”[9](P2)在喬那里,音樂為他本無意義的世界賦予了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只是擔心,如果某一天我死了,我的生命卻一無所有。”音樂照亮了他的世界,讓他在庸常的、瑣碎的世界感覺到了活著的意義。他一直堅信,“一旦登上舞臺,我所有的困難都將得到解決,你將會看到一個全新的喬。”在他那里,音樂夢是自己從無意義的生活飛躍到重生世界的入口。
因為音樂夢,他的世界被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為謀生而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另一個則是音樂所照亮的夢想世界。如此一來,音樂與職業成為他生命的兩極,他的生命就在這兩極所代表的不同可能性之間搖擺。坎貝爾曾說,“到底我們去追尋圣杯還是荒原?也就是說,你是準備去追求靈魂的創意性探險,還是只追求經濟上有保障的生活?是準備活在神話里,還是讓神話活在你心里?”[7](引言P7)喬便在“靈魂的創意性探險”和“經濟上有保障的生活”之間搖擺。喬在一個學校當兼職樂隊老師。這個懷有音樂夢的人,卻讓音樂成為他謀生的手段。他的職業生涯迎來了轉機,學校決定聘任他為專任教師,這意味著他擁有了有保障的正式工作,然而,這也意味著,為了謀生,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音樂舞臺夢。音樂徹底成為他謀生的工具。
與此同時,另一種可能性也在他的面前展開。他此前教過的一個學生在音樂家多蘿西婭·威廉姆斯的樂隊當樂手,該樂隊缺少一個鋼琴伴奏,他獲得了應聘的機會,并通過了面試,他的音樂夢即將實現。然而,就在這時,他卻掉入了下水道。
(二)神話語境中的生命復歸
影片通過喬在神秘世界(生之前和死之后的世界)的旅程,試圖在更為本源的層次,探討怎樣活著才有意義的問題。在死生之間的神話語境的觀照下,他的音樂夢是否還有價值?
遭遇車禍后,喬的靈魂來到了神秘世界,這個世界是靈魂出生之前的世界,也是靈魂死亡之后的世界。因為他有尚未完成的事業,所以,他不甘心,他拼盡全力重新回歸身體,糾正自己生活的無意義狀態。他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得償所愿。他用22號的通行證,重新回到地球,與他非常崇拜的音樂家多蘿西婭同臺表演,大獲成功;但是,讓他困惑的是,他卻沒有實現自己所幻想的新生,那個全新的自己也沒有出現,實現音樂夢后的生活和此前的生活沒有任何區別。
他發現這個能讓自己復活的音樂夢,僅僅是自己虛構的。如果音樂夢無法帶給他所渴望的新生,那么他所渴望的新生又在何處,生命的意義又在哪里呢?一直以來,喬認為自己就是為音樂而生,但是,因為音樂夢,喬的世界是殘缺的。音樂在喬的世界被過度拔高,而音樂之外的生活卻被遮蔽。他通過了面試,將和自己所崇拜的音樂家多蘿西婭同臺演出。他非常興奮,但是,他在走路時只顧與朋友分享自己的快樂,籌劃未來的美好生活,卻沒能關注身邊的狀況,因此墜入了下水道。在影片中,靈魂如果過度沉迷于生命中的某些高光時刻而切斷與生命的聯系,可能會失去自我,成為迷失的靈魂。他處于與迷失的靈魂同樣的精神狀態。他忽略了音樂之外的生活,跌入了下水道。因此,即使他得償所愿實現了音樂夢,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
音樂家多蘿西婭所講的那條小魚的故事點出了他的問題所在。喬自己就是那條生活在海洋中卻依然在尋找海洋的魚。水便是海洋存在的標志,小魚卻對其視而不見。他也一樣,他忽略了生活,而一味地追求脫離生活的空洞的夢想。
投身到喬的身體上的22號,給了喬重新感受生命的契機。在地球上,通過喬的身體,22號體會到了生命的快樂,披薩餅、棒棒糖、風聲、落葉、媽媽的線團,都帶給了她不同的感受。“你應該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形相,都是同一個永恒者的光芒閃現,因此,你們應該尊重每一個形相,因為他們之中包含著生命的魔法。”[7](P262)在22號那里,每一件事物都是生命樂趣的體現。這些雖然普通卻代表生命樂趣的東西,指向了喬一直所忽略的生活。22號關于生命的感悟,讓他認識到生活中的很多事物都會成為火花,生命的意義蘊含在所有的生命活動中。“所有的道路最終都通向相同的真理。”[10](P25)任何職業都可以實現生命的意義,理發師此前夢想成為獸醫,卻因為當時缺少學費,而成為了理發師,但是他的生活依然擁有意義。音樂只是喬實現生命意義的途徑之一,而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最終消融生活與音樂的沖突,獲得了精神的自由。
喬從困惑中走出,成為兩個世界的主人,擁有了自由穿越兩個世界的能力:“自由地來回跨越兩個世界之間的界限,從時間幻象的世界進入事物原因的奧秘世界再重新回來——既不讓這一世界的原則影響另一世界的原則,但又能通過這一世界了解另一世界——這是主宰者的能力。”[8](P225)憑借這個能力,他回到了神秘世界,拯救了22號。與其說他拯救了22號,不如說他拯救了自己,因為他用22號的通行證回到地球,實現了自己的音樂夢。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的方式,都可能讓他迷失,成為困擾的靈魂;但他在拯救別人的同時,完成了自我救贖。
在影片的結尾,喬的復活暴露了動畫建構現代神話的野心。影片中出現拯救靈魂的薩滿也說明,他們要建構能夠指引人們從困惑中走出的心靈地圖,能夠治療人們精神創傷的現代神話。“我們的故事有治療的能力,能讓世界煥然一新,還能給人們隱喻,讓他們更好地理解人生。”[11](P271)影片通過展示主人公重構人生的故事,呈現給人們一個透視人生的鏡像,讓觀眾能夠通過遠觀別人的故事,修復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