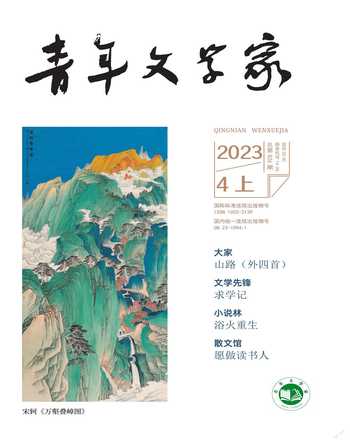父母的愛情
鄧秀瓊
我的父母均出生于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和那個(gè)年代的其他農(nóng)村青年相比,他們的婚戀別無二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始終堅(jiān)信:他們之間是有愛情的!
我聽父親說過,他剛到婚齡不久,媒人便絡(luò)繹不絕,都快把家里的門檻踏破了。前后介紹了好幾個(gè)對(duì)象,可父親始終不滿意。直到遇上了我的母親,第一感覺便是“可以”。我知道,父親不太喜歡夸獎(jiǎng)人,他說的“可以”,便是很滿意了。
在我的記憶中,父母也常吵架,但基本上不會(huì)動(dòng)手。而每次吵架后,冷戰(zhàn)不了兩天,便又和好如初了。母親一旦生氣,父親便開始扮小丑、做怪相、講笑話。每當(dāng)此時(shí),母親都會(huì)狠狠地瞪父親一眼,可奇怪的是,她的那種狠連自己也會(huì)忍不住笑。
在那個(gè)年代,我們家里總?cè)奔Z。可是每當(dāng)外公來借糧時(shí),父親從不會(huì)讓他空手而歸。家里的母豬下了崽,舅舅說先賒賬買兩只,父親也從來不會(huì)拒絕。哪怕家里已窮到連我上學(xué)的費(fèi)用都交不起了,小姨和姨父要出門打工,把不滿兩周歲的表弟送到我們家托管,父親也二話不說便答應(yīng)了。過了兩年,小姨又把剛滿三個(gè)月的表妹送來,并且一再表示:“姐姐和姐夫帶孩子,我們放心!”就這樣,表弟和表妹在我們家待到上學(xué)年齡,小姨才接去廣東上學(xué)。兄妹倆走后,父親還失落了很久。長大后我才明白,父親做的這一切,便叫愛屋及烏。
母親沒有什么文化,但母親總是那么善良。那些年總有人走鄉(xiāng)串戶收“功德錢”(自發(fā)組織的,用于修橋補(bǔ)路,不限于本地)、乞討等,每每遇此,母親總會(huì)多少給些,實(shí)在沒錢也要給人打發(fā)兩碗米。而到青黃不接時(shí),母親總是一個(gè)人吃紅苕,把米飯留給我和父親。她還總對(duì)我炫耀:“我好養(yǎng)活,不像你們爺倆打不得粗。”其實(shí),就她那點(diǎn)兒小心思,我和父親的心里早有一面鏡子,照得清清楚楚。
父母婚后分開時(shí)間最長的一次,是在1995年。那一年,父親隨幾個(gè)鄉(xiāng)鄰一起出門打工。那時(shí),我還不清楚他們口中特別遠(yuǎn)的黑龍江離我們家到底有多遠(yuǎn)。但我知道,父親走后,母親每天都在念叨:“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當(dāng)收到父親的來信時(shí),母親激動(dòng)地用顫抖的雙手遞給我,說:“快, 快念給我聽!”她是那么急切地想知道父親的消息。當(dāng)?shù)弥赣H一切安好后,母親如釋重負(fù),只是埋怨父親離家那么久才來信!我看了看郵戳,告訴母親,父親寄信是在一個(gè)半月以前,她便不再說什么了。
大半年以后,父親回家了。母親見到父親的那一刻,淚水在眼眶里打轉(zhuǎn)。然而,她對(duì)自己的辛苦卻不再嘮叨,好像所有的艱辛都隨著那些淚水被咽下了肚。而父親,對(duì)于那段首次外出打工的歲月,也只是輕描淡寫地用幾句話概括了。然而,從那以后,父母便不愿再長期分離。那些年的農(nóng)村還很貧窮落后,為了供我上學(xué),父親不得不選擇出門打工,而大字不識(shí)幾個(gè)的母親說什么也不讓父親單獨(dú)在外,父親走到哪兒,她便要跟到哪兒。父親進(jìn)廠,她便進(jìn)廠。父親上建筑工地,她便上建筑工地。嘴上說一個(gè)人在家干農(nóng)活兒太辛苦,心里卻是舍不得父親在外獨(dú)自受累。漸漸地,我發(fā)現(xiàn)他們不再動(dòng)不動(dòng)就爭吵,感情越來越好了!一個(gè)盆里洗腳,水燙時(shí)都愿意墊底,而不像年輕時(shí)比誰動(dòng)作快,你踩我左腳我踩你右腳了。
如今,國家的政策越來越好,鄉(xiāng)下的生活也越來越富足了。沐浴在改革的春風(fēng)里,享受著改革開放的大好成果,父母也很知足了,他們不嫌粗茶淡飯,唯慶幸有愛有伴。盡管他們不會(huì)表達(dá),也不曾對(duì)彼此說“我愛你”,但那些幸福時(shí)光依然像那出漿的磨盤,正呼啦啦地轉(zhuǎn)著。
父母的愛情,我不僅看到了,更感受到了,并且悄悄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