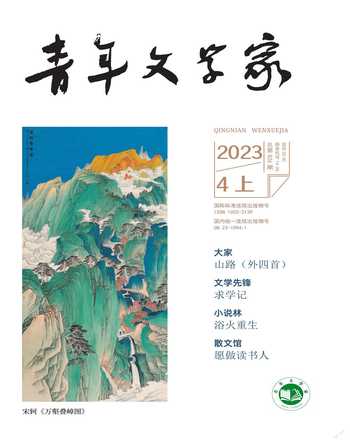一捧紅葉掛心尖
金娜
很多年前,我對紅葉的印象一直覺得就像中國紅顏色一般,鮮艷奪目,耀眼非常。火紅的葉子將那片天空染亮,有了讓人熱血沸騰、噴薄而發的激情在里面。
很多年前的記憶,只局限于小學課本上那篇關于描述香山紅葉的文字,也由此記住了這個叫“香山”的地方。只盼望某天,我可以如愿以償,去看看那火紅一片的山到底是怎樣的。幾十年了,縈繞心間,竟成了一種癡念。
在我的故鄉,除了楊樹、槐樹、柳樹等再普通不過的樹木外,再不見別的稀有樹種,更別說火紅葉子般的觀賞樹木。只因為普通的樹木生命力特別強悍,種植起來,成活率極高。國槐樹不多,皂角樹亦然。在那片只有一百多戶人家的黑土地上,能夠看到幾棵樹齡很大的樹木,已是極限。而在我僅存的記憶里,只記住了鄉村宅院,以及宅院前后那粗大的棗樹、洋槐樹……
離開故鄉三十多年,記憶完全被那一座座老得不能再老的房舍和枯樹所掩蓋。滿眼的滄桑、蕭條,以及陌生的不知身居何處的感官陣陣襲來,讓我那顆渴望回歸故鄉的心,總是由不得自己揪著般的痛。故鄉的蒼老,親人的年邁,都在這依稀存在的老屋里,看到只屬于我們那個年代的模糊印記。模糊了雙眼,更是模糊了那顆歸鄉心切卻又膽怯的心。
小時候的我像頑皮的猴子一樣,為爬上門外的那棵歪脖子棗樹,爬上了四爺家的瓦房頂,踩壞了他家幾片瓦塊,還被洋辣子蟄疼無數次。那時,看著房頂頑劣的我,四爺嚇得不敢大嚷。到如今,我還記得瓦塊破碎的脆響和四爺心驚膽戰的模樣。
故鄉的棗是真的甜,脆甜多汁,讓我每每想起,還一直想流口水。可惜,樹被砍伐,再也不能吃到那脆甜多汁的紅棗,再也不能體會親自攀爬樹上摘棗子的樂趣了。
成年人的記憶,總會在嘗遍多種棗子的味道后,依然覺得家鄉門前的紅棗是最甜的。雖然,如今的棗子也有了曾經的口感,在齊老師那里,我品嘗到了與家鄉味道特別貼近的紅棗。脆脆的,紅紅的,小核,大果。
故鄉的三兩棵國槐不高,結果不少。國槐可入藥,但具體是怎么個用法,小時候的記憶有限,并不記得。我只記得,很喜歡吃國槐角里那個筋道的有指甲蓋大小的硬繭。也算是那個年代里,一道獨有的小零食吧。
在某個陰天,我迷路了。都怪那條路上的國槐角太多了,我惦記著該去怎樣摘下來讓我“憶苦思甜”一下,沒想到,對這個城市一下子沒了方向感,導航也是枉然。那時候的我,嘴角含笑,給兒子打電話,訴說著當下的位置與熟悉的飯店,讓他給我指路。成年人的崩潰和喜劇笑料,在那一刻被我演繹得淋漓盡致。這種內心有半分崩潰,又有半分好笑的別扭情緒,讓我的笑意一直在臉上未消散。路人奇怪地看我,也是帶著善意的笑。那次,我竟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創造出了不一樣的天空奇跡與暖暖的喜悅相伴。
這不,我看到小區里這兩棵掉落的紅楓落葉,落得一地都是深紅深紅的顏色。一片片地撿起,將它們匯集成一小簇,竟有了驚艷片場的嫌疑,暖意撓心,讓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香山紅葉,想起了香山。
自從來到了南陽城,我才知道,太過于遙遠的南陽城與新野漢桑城的距離,真的就像很多年前去大連時,隔海相望的俄羅斯,都不是那么難以想象,且難以到達的。
人,只有在不斷接觸新事物當中,才發現,眼界局限了思維,思維局限了格局。所有的東西,都在自己不斷攀登、追逐新高度,企及目標后才明白—距離的深遠,心來決定。行動力才是決定你的夢想達成的唯一途徑。
未來的某天,我一定要去香山看看紅葉,再看看北京天安門。也由此,由一簇葉片,生出這許多雜亂無章,卻也回味無窮的文字來,都只是對于那段難忘歲月的感懷與惦念。癡念叢生,不由己!葉子雖小,其中深藏的含義卻是深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