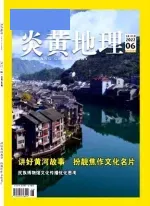宋元時期西域漢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研究
邵明浩 趙平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一帶一路”“文化潤疆”工程的背景下,為證明漢語言文字在西域的通行并未因中原、西域兩地政權(quán)的更迭而出現(xiàn)中斷,以宋元時期西域漢語言文字的使用為切入點,指出漢語作為漢族和其他民族進行交流的方式,漢語使用與通行在宋元時期以及后世有著重要意義,也從語言文字角度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統(tǒng)治與管轄始于西漢。從兩漢至隋唐,雖有魏晉南北朝這樣相對動蕩的時期,但大部分統(tǒng)治中原的王朝始終將西域地區(qū)劃歸在自己的統(tǒng)治范圍之內(nèi)。伴隨著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jīng)營以及同西域間交往的加深,漢語言文字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在西域地區(qū)得到了傳播與使用。
宋元四百多年間,兩個中原王朝對西域地區(qū)的控制力有著較為明顯的差距。宋朝由于周邊政權(quán)的阻隔,無暇顧及西域,但仍舊與西域內(nèi)部各政權(quán)保持往來;蒙元時期,蒙古人結(jié)束了金、西夏、南宋三個中原政權(quán)的分裂割據(jù)狀態(tài),繼漢、唐之后重新于中原地區(qū)建立起大一統(tǒng)王朝,同時恢復(fù)了對廣大西域地區(qū)的統(tǒng)治。漢語的使用與傳播沒有因中原王朝對西域地區(qū)控制力的下降而中斷,也沒有因其他西域語言的通行而消失。宋元時期西域地區(qū)內(nèi)部也存在著政權(quán)的更迭,回鶻人、蒙古人相繼登上統(tǒng)治西域的舞臺,并為漢語言文字在西域的傳播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兩宋時期西域的漢語言文字
早在9世紀中期,由于漠北回鶻汗國的覆滅,部分回鶻人選擇西遷,它們來到西域地區(qū)建立各自的政權(quán),直至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當時的西域地區(qū)存在喀喇汗國、西州回鶻王國以及于闐李圣天王國等政權(quán)。
在分析兩宋時期西域地區(qū)漢語的使用和傳播之前,需要了解一下當時中原地區(qū)的漢語使用情況。不同于兩漢和隋唐,宋朝雖然結(jié)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周邊仍舊存在一些政權(quán),如契丹人建立的遼、黨項人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人建立的金。宋朝與周邊政權(quán)雖存在分歧與對立,但彼此在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上的交往也并不鮮見,漢語的廣泛流通便可以佐證這一點。遼、西夏、金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它們在創(chuàng)造文字的過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漢字的影響。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雖然擁有各自的語言,但并未廢棄使用漢語,因此政權(quán)內(nèi)部掌握本民族語言以及漢語的雙語者甚至多語者的人有很多,如后世建立西遼的耶律大石以及深受成吉思汗青睞的漢文化學者耶律楚材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政權(quán)不同于宋朝,它們與西域地區(qū)接壤,這也為漢語的持續(xù)西傳創(chuàng)造了條件。
這一時期漢語的使用和傳播情況我們主要分為兩個角度來進行探討:其一,中原同西域交往交流的過程中,漢語作為重要的交際工具,為兩地之間的溝通搭建橋梁;其二,西域地區(qū)內(nèi)部存在著相當數(shù)量的說漢語的人口,包括世代生活在西域的漢民以及主動接觸和學習漢語的當?shù)鼐用瘛⑸畟H等。
中原同西域的交往
宋朝由于周邊政權(quán)的阻隔,對廣大西域地區(qū)難以形成有效的控制,因此類似漢唐甚至魏晉南北朝向西域地區(qū)派遣內(nèi)地官員以及駐兵屯田的一系列措施也只能被迫中止,這時兩地間的交流主要依靠互派使臣以及民間使者進行商業(yè)貿(mào)易,漢語則融入于兩地的政治交往及經(jīng)濟交流之中。
回紇(后更名為回鶻)是我國新疆地區(qū)維吾爾族的祖先,早在唐代他們就與當時的中原王朝建立起相當親密的關(guān)系。唐肅宗時,中原王朝通過和親與回紇建立姻親關(guān)系,將寧國公主嫁與回紇的葛勒可汗。由于長久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原和親公主的融入,可見在西遷之前回鶻人已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宋朝建立之后,西州回鶻王國等西域政權(quán)曾多次遣使朝貢與上書,如“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汗,遣都督麥索溫來獻”[1]。又如于闐王使者阿辛的上書中將宋朝統(tǒng)治者稱作“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2]。從上述兩個案例可以看出,西州、于闐等地的回鶻政權(quán)仍舊與宋朝王廷保持著“甥舅關(guān)系”,正如《宋史》所言:“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為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3]。在西域政權(quán)同中原王朝的政治交往過程中,西域使者團中掌握漢語的使臣和譯者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宋太宗也于太平興國六年(981)派遣王延德、白勛等人出使西州,這些來自中原王朝的使臣同樣將漢語帶入了西域。
西域地區(qū)一直是溝通中西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來自中國的商隊源源不斷地進入到西域地區(qū),《福樂智慧》中有:“褐色大地披上了綠色絲綢,契丹商隊又將桃花石錦緞鋪陳。”[4]中國商隊將綾羅綢緞帶往西域的同時,也將漢語言文字帶到絲綢之路上。除了來自中國的商人,近年來新疆地區(qū)出土的宋代漢文錢幣也能反映出當時中原同西域間商品貿(mào)易之繁榮,如中國考古隊于喀什汗諾依古城遺址發(fā)掘出數(shù)量豐富的漢文古錢幣,其中的“政和通寶”“大觀通寶”錢幣為北宋徽宗時鑄造,這體現(xiàn)出宋時中原同西域間仍存在著緊密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漢文錢幣進入西域內(nèi)部,融入西域當?shù)氐呢泿朋w系中。
西域地區(qū)內(nèi)部的漢語言文字
回鶻西遷之后,西域內(nèi)部仍存在著一些漢人聚集區(qū)。高昌地區(qū)從兩漢至魏晉一直是中原王朝經(jīng)營西域的重要節(jié)點,唐朝滅麹氏高昌王國后在此設(shè)西州置縣。由于歷代中原王朝的經(jīng)營,大量漢人官兵和移民進入到西州地區(qū),使西州成為當時西域地區(qū)內(nèi)部漢人聚集區(qū)的突出代表。
宋太宗時,王延德作為中原王朝的使者前往西州,其到達西州之后有以下描述:“用開元七年歷……佛寺五十余區(qū),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jīng)、唐韻、玉篇、經(jīng)音等……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5]可見西州深受唐文化的影響,這也從側(cè)面體現(xiàn)出西州生活著相當多的漢民。以上記載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唐韻》《玉篇》《經(jīng)音》等“小學”經(jīng)典的存在說明當?shù)貪h語文教育沒有因回鶻人的進駐而停止;二是漢語言文字同漢傳佛教相結(jié)合,對西域內(nèi)部的西州等地區(qū)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結(jié)合寺中的漢文佛經(jīng),可知西域僧侶為了閱讀、解釋或是翻譯漢文佛經(jīng)需要主動接觸和學習漢語言文字。例如10世紀~11世紀生活于別失八里的勝光法師將漢文《金剛明經(jīng)》翻譯為回鶻文,其在譯文中就使用了頗多漢語借詞,如“ban”(板)、“bursang”(佛僧)、“hua”(花)等[6]。可見,雖然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區(qū)的控制力有所下降,漢語在西域內(nèi)部的通行和傳播并未因此中斷。
蒙元時期西域的漢語言文字
鐵木真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蒙古人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對外征戰(zhàn)。1209年高昌回鶻亦都護巴而術(shù)·阿而忒·的斤歸順成吉思汗,成為蒙古國的附庸。1279年,元朝軍隊擊敗南宋,結(jié)束了自唐末以來中原地區(qū)的分裂割據(jù)狀態(tài),于中原地區(qū)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統(tǒng)一國家,恢復(fù)了對西域的控制,重啟在唐末就中斷了的西域經(jīng)營事業(yè)。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統(tǒng)治者建立起的大一統(tǒng)朝代,這一時期的通用語言文字主要有蒙古語文、漢語文、波斯語文三種,其中以蒙古語為國語,在此基礎(chǔ)上,元朝統(tǒng)治者嘗試統(tǒng)一語言文字,如創(chuàng)制八思巴文,但在后世實踐中以失敗告終。漢語言文字的使用與傳播在元朝受到當時語言文字政策的壓制,但其在社會通行中仍居于較高的地位。正如徐思益先生所說:“在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里,語言的使用和傳播不決定于當政者的族別和政治態(tài)度,而人口多,文化上占優(yōu)勢的語言總是占主導(dǎo)地位,這是一條規(guī)律。”[7]漢語言文字的社會功能不以統(tǒng)治者的意志為轉(zhuǎn)移,西域地區(qū)也是如此,可以從官方舉措、定居人口等方面進行探討。
官方舉措
蒙古西征相較耶律大石西征,其規(guī)模更加龐大,其組成也更為復(fù)雜,包含蒙古人、漢人、金人、契丹人、畏兀兒人等。《西使記》中記載常德在前往覲見旭烈兀的過程中經(jīng)過一個名為“鐵木爾懺察”的關(guān)隘,其中“守關(guān)者皆漢民”[8],可見當時西征部隊中的漢人不在少數(shù)。在西征的同時,蒙古軍隊為了保障行政與軍事的后勤補給,重新開啟西域地區(qū)的屯墾事業(yè)。13世紀60年代,位于西域的窩闊臺汗國與察合臺汗國公開反對忽必烈的統(tǒng)治,忽必烈在統(tǒng)一中原后將兵鋒調(diào)轉(zhuǎn)西域,為更好地控制畏兀兒地區(qū),元廷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其中就包含在西域地區(qū)開展屯田,“世祖時,以別失八里戍回、漢軍及新附軍五百人屯田哈密力玉速曲之地,又遣侍衛(wèi)新附軍千人,屯田別失八里。”[9]這些進入西域進行戰(zhàn)斗的隨軍和屯墾的漢人士卒,是當?shù)貪h語言文字的主要使用群體。
除軍事措施外,元朝統(tǒng)治者在西域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經(jīng)濟舉措,如設(shè)置軍政機構(gòu)、完善驛站體系、設(shè)交鈔庫等。西域軍政機構(gòu)和驛站的一部分官員、士卒需要從內(nèi)地調(diào)派,漢人官吏自然掌握漢語,如1986年新疆且末縣出土了一批元代漢文文書,其內(nèi)容包括雜劇、書信、名錄等[10]。部分在內(nèi)地生活的蒙古官員出于統(tǒng)治和管理的需要也會主動學習漢語,成為蒙、漢兼通的雙語者。經(jīng)濟上,元朝統(tǒng)治者于西域設(shè)置交鈔庫,“凡鈔之昏爛者,可就交鈔庫倒換。是于畏兀兒地,設(shè)交鈔庫。可見元代鈔票通行于西域”[11],1928年黃文弼于吐魯番發(fā)現(xiàn)“至元通行寶鈔”可以與之相印證。與宋時西域相似,蒙元時期的西域也存在漢文貨幣的流通,漢文貨幣是漢語言文字在當時西域得以持續(xù)通行與傳播的重要物證。
定居西域的說漢語人口
《西使記》中還記載了元憲宗時期西域內(nèi)部漢民的生活狀況:“與別失八里南已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谷”,常德至阿里麻里城,見“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至赤木兒城,該城“居民多并、汾人”[12]。可見元憲宗時的北疆地區(qū)生活著相當多的漢民。此外,常德還隨蒙古軍隊到達取報達國(今伊拉克巴格達),國王合里法“其妃后皆漢人”[13],足見當時漢人分布之廣。
入華西域人
蒙古西征,中西方之間門戶大開,彼此間的人員流動變得活躍,除上文所說的進入西域參與管理、作戰(zhàn)、屯墾的漢人外,于兩地間往來的西域地區(qū)的使者、譯人、僧侶以及至中原供職的西域官員,他們大多學習了一些漢語知識。于元朝政府中任職的入華西域人并不少見,如畏兀兒人阿魯渾薩理通習多種語言,不但精通漢語,且是熟讀漢文經(jīng)典的漢學家。此外,孟速思、廉希憲等入華西域人皆掌握漢語,且家族內(nèi)部漢學氛圍濃厚,足見西州、別失八里等地受漢文化影響之深。
宋元時期的西域地區(qū)作為東西交流的樞紐,多種語言于此通行,這也為西域當?shù)鼐用癯蔀殡p語者甚至多語者創(chuàng)造條件。蒙元時期的翻譯工作具有翻譯內(nèi)容廣泛、涵蓋語種多等特點,入華西域人是當時翻譯隊伍中的主力,如畏兀兒人安藏精通蒙、漢、畏兀兒等語言,奉旨翻譯《資治通鑒》《尚書》《難經(jīng)》《本草》等漢本典籍。此外,阿鄰帖木兒以及上文提到的阿魯渾薩理均為蒙元時期的著名畏兀兒翻譯家。
宋元時期西域漢語言文字使用的影響與意義
張騫通西域后,漢語言文字進入到西域地區(qū)。自漢唐至宋元,其間也有過南北朝、五代十國這樣的割據(jù)亂世,漢語言文字于西域的使用和傳播自始至終未曾斷絕,可謂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壯舉,這也體現(xiàn)出語言文字事業(yè)“事關(guān)歷史文化傳承和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事關(guān)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jié)”[14]。
首先,漢語言文字的使用讓中原地區(qū)同西域地區(qū)間的溝通更加通暢,密切了兩地間的聯(lián)系。宋朝由于地域上的阻隔,無法有效地控制和經(jīng)營西域,但兩地間有著共同的漢文化認同,它們以漢語、漢文為主要工具,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lián)系。元朝疆域廣闊,漢語言文字在保障中原同西域間政令通暢、政策及制度高度一致等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地維護了統(tǒng)治者的政權(quán)。經(jīng)濟上,漢語言文字是宋元時期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語言文字之一,在維系兩地間經(jīng)貿(mào)聯(lián)系、促進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以及維護西域貿(mào)易樞紐地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次,漢語在推動西域發(fā)展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語言將社會生活的模式傳授給學習者,同時也幫助其建立和發(fā)展了與周圍人的各種各樣的社會關(guān)系”[15],以漢語和漢文為中介,進入西域的漢人同當?shù)厝罕婇g的溝通更加便利,加快了漢文化與中原先進生產(chǎn)生活技術(shù)在西域的傳播,從而改變了西域地區(qū)相對落后的風貌,使當?shù)亍邦H似中國”,漢化程度大大加深。
最后,漢語言文字在西域得以持續(xù)通行和傳播,這體現(xiàn)出中原和西域兩地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宋元時期,契丹人、回鶻人、蒙古人等主動學習、借鑒漢文化,以漢語言文字為紐帶,同漢人共同構(gòu)筑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原、西域兩地人民以漢語言文字為聯(lián)結(jié),政治、經(jīng)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彼此認同,最終凝聚起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這對我國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參考文獻
[1][2][3][5]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4]優(yōu)素甫·哈斯·哈吉甫.福樂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6]張鐵山,朱國祥.回鶻文《金光明經(jīng)》中的漢語借詞對音研究[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42(01):135-139.
[7]徐思益.古代漢語在西域(續(xù))[J].語言與翻譯,1993(03):13-18.
[8][12][13]楊建新.古西行記選注[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
[9][11]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0]何德修.新疆且末縣出土元代文書初探[J].文物,1994(10):64-75+86.
[14]國務(wù)院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關(guān)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wù)院公報,2021(35):29-33.
[15]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等.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