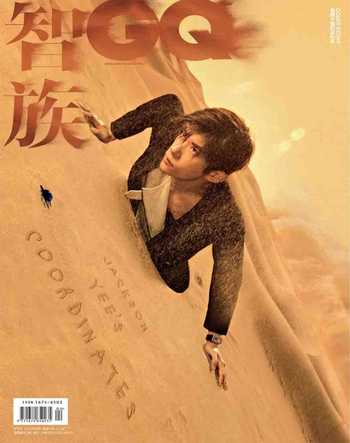石上純也的建筑消解術


建筑家維特魯威在羅馬時代便長久地確立了影響綿延至今的建筑觀:滿足實用、堅固、美觀三要素。建筑是容納人類活動的構造物——在這個以人為主體構筑概念統治的漫長時間里,世界成了人類活動領域與自然領域壁壘分明的世界。我們用四面包圍的高墻驅逐了可能會到來的危險,也同時深深被束縛在自己建造的牢籠里。
自現代主義運動把人從難以照進陽光的房間里釋放出來以后,一代接一代的建筑師們開始抵抗那個古老陳舊,既脫離現實又脫離人愿望的世界觀,把建筑學更加豐滿充盈起來。石上純也是其中最為感性,也最為勇敢的一位。自2004年創立同名建筑事務所以來,在已經獨立執業快20年里,石上純也持續實踐著一件事:在人工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里找到那個沒人見識過的世界,消解人和自然的界限。
風景與建筑,石上純也凝視著它們的交匯之處。

建構風景
世界的原點,是一片蠻荒。
時光流逝,營建工事興起,開始有了房屋、道路、城池,以及隨之聚集起來的人類、動物、植物。這些生命體,以不同的速度生長、擴張著,他們之間的角力決定著風景的面貌。想要靠近而不得,人類與自然對抗的本質使建筑永遠無法成為自然物。但萬物有其此消彼減。人的活動消失之后,建筑衰敗的同時,那受到四季洗禮的斷壁殘垣卻天然地成為風景的一部分,與自然共生共存。
現實里本來需要依賴時間的歷程去賦予人造物的自然屬性,石上純也正在用建筑的方法做出示范,建構風景,創作出一種可居的自然。所以當被問及“從青蔥的學生時代到已經成為蜚聲世界的建筑家的現在, 哪一座建筑讓你最為感到震撼”的時候,石上純也說出早已成為雅典衛城標志性風景的帕特農神廟,原因也就不言而明了。

我們很少看到像石上純也那樣平等地安排建筑和各種環境要素,消除主體與客體之分后呈現出的建筑繪圖。消滅了主次秩序的建筑,空間里常常帶著曖昧模糊的特征,也因此常常令人心生疑惑:這究竟是一個建筑還是一座花園?“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2008年,石上純也將為威尼斯建筑雙年展呈現的日本館取名為“極致的自然:模糊空間的景觀”。這正是他消除內外之分,自然與建筑相交融的絕佳示范。

家與餐廳
從大地里鑿出來的“ 家與餐廳”,是石上純也建構風景的最新力作。這個占地270平米的建筑于去年3月落成,既是業主的家,也是業主經營的法國餐廳坐落之處。設計之初,與建筑師相識多年的業主提出了請求“: 想要一個好像存在了很久的建筑。” 如何表達“存在了很久的建筑”的時間重量和歲月賦予的古舊空間感?石上純也構思出天然、粗礪、不加修飾的“洞穴”的概念,試圖與現實環境剝離開來,創造出由于時間對建筑的磨礪、建筑復歸于自然的感覺。
建造期間,給洞穴建筑內部空間賦形和安裝玻璃給建筑師出了不小的難題。首先,建筑師需要將電腦模型轉化為三維數據,以確定開鑿洞口的坐標。即便如此,圖紙與實際建造仍會因人工誤差、土壤松動等不可抗力存在誤差。挖掘完成后用混凝土為內部空間澆筑出骨架。混凝土凝固、挖除土方模塊后,本應露出的灰色混凝土結構毫無預料地浸染上土壤,也因這個美麗的意外,建筑師改變原本方案,以這個土黃色的洞穴氛圍為起點進行了建筑形象的再設計。
建筑體量雕琢成型后,建筑團隊對場地進行了3D掃描和實際測量,以現實為藍圖再度確認玻璃安裝的數量及坐標以定義建筑內部空間。“家與餐廳”項目里的大約35塊玻璃,沒有任何兩塊是完全相同的。每塊玻璃的形狀還得與洞口的形狀嚴絲合縫,這其中的工作難度可想而知。
自由建筑
建構風景,把建筑變成風景的一部分,是石上純也的建筑觀。自由建筑則是他的建筑宣言。在這里,自由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一個動詞,意即使自由:使拘泥于建筑風格和理論的建筑師自由,使近代以來受困于方盒子之內的建筑自由,使受制于全球化而式微的多元文化自由,使想象自由…… 石上純也在作為建筑師的成長里,跨越了建筑僅僅是為人類服務的思想藩籬,感性地認知到在建筑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之間,是個無限大的世界,而他則要用建筑學把這個無限抽象地提取出來。談及還有什么想要嘗試去做的建筑時,石上純也的目光已經投向了外太空。他說:“雖然現在人類已經可以進行太空旅行了,但無論是空間站或是航天器,仍然只是用最省的辦法制造出來的設備,只能稱作機械。如果有一天,人類的外星移居夢成為現實,屬于月球的建筑文化會是什么樣的?外星基地建筑又會是什么樣的形態?我很感興趣。”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曾精練地概括了詩歌寫作之道:“突破各種理論和教諭,去體驗并感受現實。”這句與建筑毫無關系的箴言準確地概括了石上純也的建筑實踐,反過來,石上純也的建筑充滿了詩性,也正是因為他無視風格、將建筑理論束之高閣,用不同的尺度探索并更新著建筑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