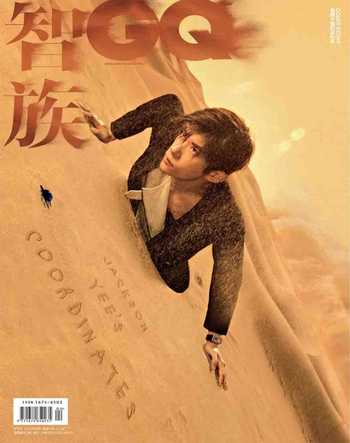去旅行吧,不管去哪里
我有一個總是不高興的同事,名叫賽賽。會議上她總是眉頭緊鎖,眼神充滿懷疑,間歇性以“怎么會搞成這樣啊?”作為她最新社會觀察的落點。
以賽賽的年紀,她還沒法成為一個保守主義者,但她的確對各類變化都相當警覺。我并不總同意她的觀點,但她前陣子發的一條朋友圈,我截取了其中一段,你們看看,是不是還有點道理:
看到博主竹子的一條微博,印象很深。她聊了一個她和老公的思維方式差異,關于“我”的邊界。
竹子說,在她的潛意識里,“我”不僅是我,也是我的行為、我的觀念,甚至是我的家庭、我的文化、我的國家。因為邊界很寬,所以很多對“我”的批評,都會往心里去。
而竹子觀察到,她老公的“我”很窄,“我”是他個人,他的行為、觀念、家庭、文化、國家甚至是更大的事情,是外部。這些外部的事情都可以被客觀地討論。
接下來說的有借題發揮的嫌疑,同時完全沒有攻擊竹子的意思,但這一段觸及到我這兩年問題意識里的一個核心:我們越來越不關心世界了,每天都在“琢磨自己”,跟自己(的感受)較勁。
一開始是有“原生家庭”這詞兒,好像自己(一時)的挫敗都可以用“因為我爸我媽咋樣所以我就這樣了”
來解釋;后來是遇到一公共事件,不關心完整的客觀事實,凈顧著提取一芝麻小點開始剖析“我的感受”;發展到現在,就是完全曲解了“把自己作為方法”和“人是萬物的尺度”,但凡有什么事和自己的個體體驗發生沖突了,立馬就上火。
為什么要搞成這樣呢?人都會遇上困難,但人不是有主觀能動性嗎?這個世界所有發生的事都得和“我”有關系嗎?個體的“我”多有限啊,看到有人做法和自己不一樣,明明是拓展認知邊界的好機會,浪費時間發火,太沒必要了吧?
世界那么大,我們卻把自己當中心,這很荒唐。
就不說“大世界”了。周圍的人也好,客觀事件也好,都有自己的運行邏輯。
放下“我”的心魔,去理解它們,顯然比琢磨自己有意思。
看到這條朋友圈的時候,我人在日內瓦出差,參加Watches & Wonders鐘表展,即將出發去巴黎拍一個廣告。
而此刻是早晨7點54分,我正坐在紐約時代廣場一家酒店打字,加上之前去東京參加愛馬仕的男裝世界大秀,一整月的時間我都在國外東竄西奔。
我知道以上的描述很符合20年前“時尚編輯全球飛,瀟灑光鮮好享受”的刻板印象,但我說“東竄西奔”,不是信口胡來。
以下是同事和我經歷的一些狼狽時刻:
在日內瓦,我們拍攝團隊的制片車被砸了、包被偷了;在巴黎,因為馬拉松趕上巨型封路堵車,我的同事兔子沒趕上飛機,只得坐8個小時汽車趕往目的地;在里斯本,我的一個導演好友被入室行竊;我來紐約的飛機被臨時取消,在機場等了8個小時,好不容易才登上飛機。
這些意外發生的當刻,我都產生了一種之前很少體驗過的情緒:我們出來干嘛,在家待著不好嗎?
老實說,這次出國前,我的包袱也比三年前重:擔心身體吃不吃得消、擔心應對不了突發狀況,以及我最不想承認的,擔心要和陌生人交流。(我甚至還搬出了年齡自我安慰,“年紀大啦,就是想舒服點嘛”。)
結果還真給我和同事碰上了一大堆措手不及。在最焦頭爛額的那一刻,我的感受也和賽賽這條朋友圈呼應上了:“我”現在不好受,世界要完蛋了。
但是真的完蛋了嗎?當然沒有。所有的“狼狽時刻”,都會有另一個后續。
在日內瓦,我們后來去警局報警,這是我們第一次去日內瓦的警察局,很新奇,同時還有好心人告訴我們A警局比B警局效率更高,設計也更好看;我那位在里斯本的導演朋友,終于到了一小時車程外的羅卡角,在懸崖邊的狂風大作中,感受了一把“陸止于此、海始于斯”的超然;而在巴黎,我自己又一次被古舊的“巴黎灰”觸動,加上那天伸手就能觸摸到的厚積云層,讓“春光明媚”多了幾分安謐與素凈。
很難說之前的困難是為了這些美好做鋪墊,但想到英文里的“Travel”由“Travail”(艱苦勞動)演化而來,某種程度上,旅行中的愉悅就是與克服困難相伴相生。這里的困難有身體的勞累,更包括應對認知之外的突發事件的壓力。
在沒有進入“High-tech modernism”之前(這是我從美國文理科學院的出版刊物 D?dalus 里學來的說法) ,我們似乎更能夠接受“走出去,克服困難,然后被另一種美震撼”的等價交換;但在以算法為中心的“High-techmodernism”發生后,我們每天坐在家中,端著一個小屏幕,就能被投喂各式各樣的內容:這些內容披著“外部世界”的外衣,但能被推送到我們眼前的內容,講述角度都是參照我們的固有認知度身定制的。在形式上“多元”的蠱惑下,我們漸漸就誤以為自己能通過屏幕了解一切,沉溺于“不用否定自己固有認知”的舒服,一磚一瓦筑起高墻,以為“我”理解的世界,就是世界本來的樣子。
而沖破這層高墻,或許還是只能靠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出去,碰上些困難再克服它,才能實現。
The world is out there,我們大可以去探秘、去冒險。
這也是我遲來的新2023年愿望:不要安于做狹隘的自己,去成為更寬廣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