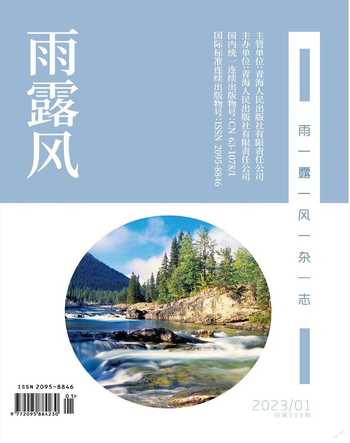淺析《社戲》中的浪漫主義意蘊
《社戲》中,魯迅對于少時看戲的追憶,是建立在當下并不愉快的看戲體驗后,繼而觸發(fā)其回首過往美好生活。當下現(xiàn)實的“灰暗”作為導火索,引發(fā)了魯迅對于“過去”的懷戀,這樣一場試圖跨越時空的追思之旅,促使魯迅在這種維度上感受“人”的生命與存在,這正是浪漫主義精神的內(nèi)核。重點對比《社戲》中的兩種生命狀態(tài),有助于深入理解魯迅創(chuàng)作的思想軌跡,有助于厘清對于魯迅生存哲學的認知。
浪漫主義并非一味反對理性,也并非一味反對現(xiàn)實主義。真正的浪漫主義并非單純強調(diào)感性,而只是強調(diào)情感的重要意義,強調(diào)人性的自由和完善。浪漫主義中包含了一個重要主題——回鄉(xiāng),浪漫主義者批判工業(yè)文明、尋求人類未被工業(yè)污染的牧歌時代,是對于人之性靈的追尋。在浪漫主義者看來,詩性的世界消失了,唯有回歸到“詩意的故鄉(xiāng)”方能獲得人類的救贖和希望。無獨有偶,“故鄉(xiāng)”這個主題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家魯迅那里也有著詩化生存的意味,魯迅的啟蒙思想是建立在人的詩性生存基礎之上的,他強調(diào)人性的自由, 人性的完善。而在《社戲》中,便包含了魯迅詩化生存的哲學思索。
一、現(xiàn)實之“灰暗”
《社戲》的前半部分,是魯迅對近十年來觀戲體驗的現(xiàn)實性描寫,屬于“現(xiàn)實”的部分,寫作視角為成年的“我”;而《社戲》的后半部分是魯迅對于曾有觀戲體驗的回憶,屬于“理想”的部分,寫作視角為童年的“我”。其“理想”部分都是美好的,而“現(xiàn)實部分”則是“灰暗的”,正是由于并不美好的眼前現(xiàn)實,促使魯迅做出了回首過往的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