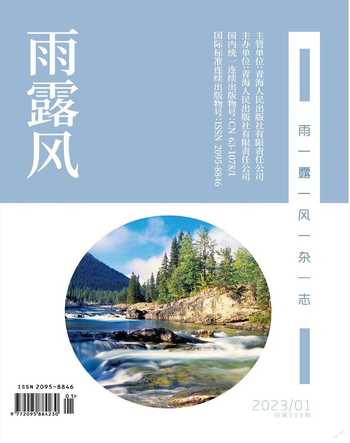顧城詩歌中的現代主義特征
朦朧詩派產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顧城作為朦朧詩派的代表詩人,被稱為當代的“唯靈浪漫主義”詩人。顧城也被稱為以一顆童心看世界的“童話詩人”,在1975年,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生命幻想曲》并奠定了自己的創作風格。顧城的詩歌《一代人》《弧線》成為朦朧詩的經典之作,影響甚廣。他的詩歌具有朦朧詩的象征性、暗示性、哲理性。其中《遠和近》《愛我吧,海》《小巷》充分體現了朦朧詩的特點。這三首詩都寫于1980年,《遠和近》只有24個字,《愛我吧,海》字數稍微多一點,《小巷》也只有24個字。三首詩歌雖然篇幅短小,但詩歌中不僅充滿了朦朧詩的象征性、暗示性、哲理性,還具有現代主義特征,即孤獨感、異化感和荒誕感。
一、孤獨感
現代主義中的孤獨感不是寂寞孤獨,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疏離、冷漠等。《遠和近》一文中的“你”和“我”二者就體現出了現代主義的孤獨感。
《遠和近》:你/一會看我/一會看云/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1]53。這首詩短小,表達的意思卻韻味無窮。“你”在看“我”的時候,又在“看云”,然而,“我”覺得“你”看云的時候很近,看我的時候很遠。這里的遠近暗含著兩層意思,現實距離中的遠近與心理距離的遠近。從這首詩中可得知兩個人是在一起的,他們的距離很近,但是這種物理距離上的近并沒有使倆人在心里距離上貼近,兩個人并不熟悉,因為他們沒有交流。作者在詩中沒有寫兩人的任何語言行動,只通過“看”的行為,描寫二人的表面狀態和實際深層次的狀態。這種油然而生的孤獨感,并不是表面的孤獨寂寞,而是現代主義特征下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是比表面的孤獨更深層次、更絕望、更透徹的孤獨。“你”的兩個觀看對象——云和“我”,一個遠在天邊,一個卻近在咫尺。然而,“我”覺得這遠在天邊的“云”,在“你”的眼里,你們隔得很近;而近在咫尺的“我”,在“你”的眼里,我們卻隔得十分遙遠。
顧城從小就喜歡獨處,性格敏感細膩。1968年,顧城12歲,迫于當時的環境,他不能繼續上學,只好輟學,轉而在家養豬,這給他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是物質生活上的驟變,更是精神生活上的重壓。1969年,顧城和他的父親被下放到農村,然而,顧城不喜歡農場生活,這種在農場里天天勞作的生活和他想象中的生活完全不一樣,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別太大。因此,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壓抑的,他的內心變得更加敏感多思。1977年他重新開始寫作,這首《遠和近》創作于1980年,這時的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有了新的變化。
《遠和近》短短六行,就透露出現代主義特征中的孤獨感,“你”和“我”只是人稱的代詞,但這表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你”看的云本應是遙望無邊的,可詩人卻寫“你看云時很近”,這種近雖然不是空間距離的近,但是一種心理距離的近;而“你”看的“我”就在旁邊,可詩人寫道,“你”看“我”的時候,“我”覺得很遠很遠,這種遠是心理距離的遠,空間距離的近依然無法使得人與人之間縮短心里距離上的遠。“我”和“你”在“互看”中,是一種相互防備的心態,這說明了“你”和“我”倆人在心理上的隔閡,人與人之間有隔閡,不能坦誠交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十分陌生、充滿了不信任、虛偽,充滿了沖突與競爭,失去了人與人之間原本應有的仁愛。人與人在心理上產生了隔閡,像隔著一堵厚厚的墻,這墻使得人與人之間變得無法溝通和交流。人的心靈經歷了一系列波動起伏,人們之間的交往也產生了隔閡,彼此無法溝通交流,互相都不懂彼此,因而格格不入。詩人寫“你”和“我”在空間上的近,寫心理上的遠,這就突出了現代主義特征中的孤獨感。
由此可得,《遠和近》一詩中的“你”和“我”,在一起的現實距離很近,但詩人通過“云”的意象,轉而表達“你”和“我”在心理上的遠,這種“遠”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隔閡,是即使面對面坐在一起也無法彌補的隔閡,也是一種無法用言語交流的痛苦與無法溝通的悲哀。因此,“遠”和“近”的對比更加突出了詩歌中的現代主義特征——孤獨感。
二、異化感
異化指主體所創作的對象,反過來成為壓迫主體、支配主體,與主體相對抗的力量。《愛我吧,海》一詩中就暗含著人被異化的現象。
《愛我吧,海》:愛我吧,海/我默默說著/走向高山/弧形的浪谷中/只有疑問/水滴一剎那/放大了夕陽/愛我吧,海/我的影子/被扭曲/我被大陸所圍困/聲音布滿/冰川的擦痕/只有目光/在自由延伸/在天空/找到你的呼吸/風,一片淡藍/愛我吧,海/藍色在加深/深得像夢/沒有邊/沒有銹蝕的岸/愛我吧,海/雖然小溪把我喚醒/樹冠反復追憶著/你的歌/一切回到/最美的時刻/蝶翅上/閃著鱗片、虹/秋葉飄進嘆息/綠藤和盲蛇/在靜靜纏繞……/愛我吧,海/遠處是誰在走?/是鐘擺/它是死神雇來/丈量生命的/愛我吧,海/城市/無數固執的形體/要把我馴化/用金屬的冷遇/笑和輕蔑/淡味的思念/變得苦了/鹽在黑發和瞳仁中/結晶/但——/愛我吧,海/皺紋,根須的足跡/織成網/把我捕去/那浪等等吻痕呢?/愛我吧,海/一塊粗糙的礫石/在山邊低語[1]38-41。這首詩充滿了異化感。“影子”是詩人自己,是主體存在,但現在“被扭曲”了,“影子”反過來扭曲了“我”,使“我”被異化。接著“我被大陸所圍困”,“大陸”是自身存在但又被主體所創造的,現在“我”卻被“大陸圍困”,客體反過來制約束縛著主體,成為壓迫主體的力量。這樣的“大陸”,是主體自己所創造的社會,這種社會無時無刻不在壓迫著主體,這個主體就是人。人們被自己所創造的客體壓得喘不過氣,被“圍困”,被客體所束縛,這個客體成為與主體相抗衡的力量。人們在與社會相對抗,卻殊不知這種情況是自己一手創造的,自己創造了這種壓迫主體的社會,人們卻渾然不知,人們被“圍困”了,因此,人也就被異化了。后面詩人寫“城市”,這個“無數固執的形體”,卻“要把我馴化”。“城市”本身也是客觀存在的,但同時又是被人們所創造的客體,可是現在,這種客體卻“要把我馴化”。主體在客體面前失去了主觀能動性,只能被客體所壓迫、支配,于是“城市”就“馴化”著“我”。“馴化”一詞多指人對物的訓練、馴服,但是這里用在了物對人上,人被物所“馴化”。不僅如此,這種“馴化”伴隨著的還有“金屬的冷遇”以及“笑和輕蔑”,這就加深了物對人的壓迫性、輕蔑性、加深了客體對主體的冷酷無情,還帶著鄙視的意味。因此,主體被客體所壓迫、支配,而客體成為與主體相對抗的力量,充滿了異化感。
“影子被扭曲”“我被大陸所圍困”“城市把我馴化”,這無不體現著現代主義特征中的異化性。詩人在詩中借助客體,訴說著主體的第二位。詩歌中的“影子”“大陸”“城市”都是作為客體來展現的,這些客體本應該被主體所支配,但現在,客體支配著主體,使得主體別無選擇,只能處于被客體支配的地位。對于“影子”而言,主體是人,人是第一位的,詩歌中卻寫“影子被扭曲”,影子作為客體,現在已經“扭曲”了,那么作為主體的人,自然而然的也被“影子”所扭曲。“影子”是人自己所創造的,人自己創造了枷鎖,現在被這個枷鎖束縛。“大陸”也是人所創造的,人通過行動在“大陸”上生活,然而,現在人被大陸“圍困”。在被壓迫、支配的環境下,人就被異化了。而“城市”也是支配主體的客體,象征著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城市”是主體創造并為主體服務的,它本應該給人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但是現在,“城市”反過來要把主體“馴化”。這是本末倒置,黑白顛倒,主體漸漸地被客體所壓迫、支配,客體成為與主體相對抗的力量,這種力量強大,它壓迫著人,在有形與無形之間都使得人束手無策,沒有辦法反抗這股強大的力量。因此,人失去了主動權,處于被動的地位。
《愛我吧,海》一詩中,詩人用“影子”“大陸”“城市”作為壓迫主體的客體,使得主體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因此,詩歌充滿了現代主義特征中的異化感。
三、荒誕感
荒誕指非常不真實,不符合情理的事。此外,其還引申為人與人之間的不能溝通或人與環境之間的根本失調。《小巷》一詩中就暗含著現代主義特征中的荒誕感。
《小巷》:小巷/又彎又長/沒有門/沒有窗/你拿把舊鑰匙/敲著厚厚的墻[1]48。“小巷”是窄的,詩人加上“又彎又長”暗示著“小巷”代表一種困境,而且這種困境很難沖出,因為它彎彎曲曲且路程長。詩人繼續寫“沒有門”“沒有窗”,這就加深了沖破困境的難度。“門”和“窗”可以使人走出小巷,逃脫小巷,因此,它們代表著希望,代表走出困境的意象。可是詩人否決了這兩條“希望之路”,轉而寫道“你拿著把舊鑰匙”,“鑰匙”本應是打開“門”的工具,但是“沒有門”,這“鑰匙”有何用呢?況且還是把“舊鑰匙”,這里的“舊”象征著舊的一切事物,走出“小巷”就是走出“舊”社會,走出困境,迎接新生活。詩人給人希望又給人失望,給人希望的是鑰匙可以開門,給人失望的是“沒有門”,這也讓人更加絕望。“你”拿著把舊鑰匙,陷入了絕望之境,但是“你”不甘心,還拿著它敲厚厚的墻。“墻”是厚厚的,用鑰匙根本不可能打破,此時的“你”無奈“小巷”沒有“門”,“你”打不開,“你”逃不脫此命運,但“你”還在敲著厚厚的墻,“舊鑰匙”本就破舊,還要去敲厚厚的墻,這是不可能的,這種做法無意于徒勞無獲,什么都不能改變。比如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故事中的主人公西西弗一直推巨石上山,石頭推上去又落下來,他永遠在重復地做一件事,就是不斷地推石頭,這種行為本身是荒誕無意義的。“你”拿著舊鑰匙去敲厚厚的墻,這種行為和西西弗的行為相似,本身缺乏合理性的行為,它是毫無意義的。
在又彎又長的小巷中,拿舊鑰匙敲厚厚的墻是絕望的掙扎,是一種荒誕性體現。《小巷》中的“又彎又長”好比是人生經歷的磨難亦或是在人生中遇到的困境,艱難曲折,“小巷”給人一種一眼望不到邊的既視感,讓人看不到出路和盡頭,使人漸漸失去走出“小巷”的希望。但是詩人并沒有就此放棄逃離“小巷”,他在“沒有門”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拿著舊鑰匙去敲厚厚的墻。此行為頗有魯迅式的對絕望的反抗,雖然詩人確實對絕望進行了徹底的反抗,但這種絲毫不會改變結果的反抗充滿了荒誕性,因此,也失去其反抗的意義。
《小巷》一詩給人一種陌生、荒謬、虛無的感覺,詩歌里的內容是不符合現實且極度缺乏合理性的。因此,《小巷》一詩充滿了現代主義特征中的荒誕感。
四、結語
《遠和近》一詩通過“遠”和“近”以及“你”和“我”,道出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戒備,體現了現代主義特征中的孤獨感。《愛我吧,海》一詩中通過客體“影子”“大陸”“城市”這三者對主體的壓迫和支配,揭示了現代主義特征中的異化感。《小巷》一詩通過“舊鑰匙敲厚厚的墻”的行為,暗含了現代主義特征中的荒誕感。顧城詩歌中不僅只有暗示性、象征性、哲理性,還暗含著現代主義的特征——孤獨感、異化感和荒誕感。顧城以孩子般的語體創作詩歌,注重寓意和象征,帶有某種童話色彩。他的詩歌中包含了幽暗的和深淵式的人性復雜內容,使其單純的表達中蘊含了豐富的信息。他作為朦朧詩派的重要詩人,在當代文學史上敘述新詩潮的發展時,都會把顧城與舒婷、北島相提并論。他用靈魂去感受,用心去觀察,他的詩歌安靜、平緩、沉著,又具有生氣和活力。顧城作為朦朧詩派的一員,其詩歌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詩學意義。
作者簡介:陳湘凝(2000 —),女,重慶開州人,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注釋:
〔1〕顧城.顧城詩集[M].廈門:鷺江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