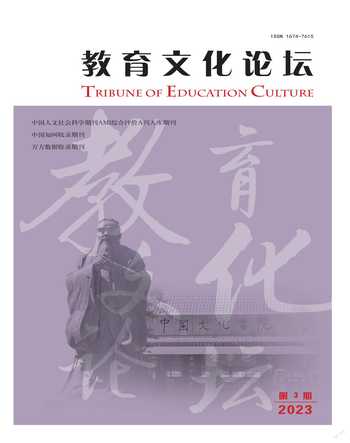二戰后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商業化演進探究
楊九斌 劉媛媛
摘 要:二戰后,隨著學術研究活動的興盛,美國聯邦政府不斷塑形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商業化發展。二戰至冷戰時期,來自美國政府的國防研發資助間接刺激了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發展。研究型大學一方面繼續承擔國防研究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承擔著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為商用、民用的任務,大學科研專利商業化等事宜不斷成為可能。20世紀70年代,出于對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擔憂,聯邦政府出臺相關政策為研究型大學創造了有利的創業環境,掀起了大學科研商業化的高潮。知識經濟時代,加快科研轉化已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時代使命。然而,在商業化實踐中,應警惕科研商業化陷入逐利的危機。審視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商業化的發展,對促進我國大學科研轉化,充分發揮其經濟使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二戰后;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商業化;演進
中圖分類號:G649.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3)03-0080-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8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是美國研究型大學崛起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商業化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建立到二戰之前,研究型大學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尚未積累太多可以商業化的研究成果。二戰爆發促進了研究型大學的發展與壯大,改變了往日大學科研邊緣化的窘境。在這場高度依賴科技的戰爭中,研究型大學充分發揮研究方面的優勢,展現了自身的科研實力,為美國戰爭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基于戰時經驗,聯邦政府意識到研究型大學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無可替代,其強大的研究能力不僅可在戰時用于增強軍事技術,也可轉化為商業成果以提升國家戰后經濟競爭力。戰時研究型大學所積累的科研成果、大學與企業的合作經驗以及戰后聯邦政府對科研發展的大力支持等因素,為大學科研商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
然而,當美國沉浸在戰爭勝利的喜悅之中時,蘇聯向太空成功發射衛星這一事件擊碎了美國想要成為科技霸主的美夢。為應對危機,聯邦政府以前所未有之規模為大學提供資金支持以保障大學科研發展。在國防需求刺激下,伴隨國防需求興起的電子行業也開始進入民用市場。隨著國家對創新活動的愈益重視以及科技園的逐漸興起,大學與企業的互動加深,越來越多的科研發明被不斷投入商業應用,大大推進了科研商業化進程。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國家競爭力以及企業活力的不斷下降,使政府削減了高等教育投入。研究型大學為應對不斷上升的研究成本,滿足自身的發展需求,通過專利轉讓、創辦研究園與孵化器等方式,進行了更多的商業努力。
一、戰爭浩劫:科研價值彰顯,商業化傾向初顯? 美國大學的發展與變革總是與戰爭息息相關。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大學主要是以傳授單一古典知識、培養傳教士為主要任務的傳統小型古典學院,并未成為科學探究的場所。南北戰爭后,美國社會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適應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需求,《莫里爾法案》(The Morrill Act)在1862年應運而生,掀起“贈地學院”的創辦熱潮,開啟美國聯邦政府通過贈予土地支持建立大學的新時代。由于社會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加,19世紀后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將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引入美國后,老牌的殖民地學院以及新建的贈地大學逐漸開始學習德國,在校內開展研究活動,大學科研活動興起。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時期,大學科研規模依然較小,尚未得到學校自身以及聯邦政府的重視,真正從事研究活動的大學鳳毛麟角,教學仍舊是大學的首要工作。如從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畢業院校所占比例來看,美國研究型大學總體科研水平與德國相比相去甚遠。1940年之前,德國人獨攬超過1/4的諾貝爾獎項數量,英國在獲獎人數上排在第二位,而美國僅得到11%的諾獎數[1]。聯邦政府對大學的科研撥款主要限于農業研究領域,除此之外的科學研究幾乎鮮有支持[2]。直到二戰時期,境況才得以轉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前校長普西(Nathan M.Pusey)回憶說:“二戰之前,大學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數量并不大,有研究計劃的大學也不多……來自公共或私人財源的科研資助也很少。”[3]
1941年年末,“珍珠港事件”將美國卷入戰爭泥潭。為盡快贏得戰爭,美國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到這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戰爭當中,政府、企業、大學共負國家使命,齊心協力為贏得戰爭貢獻智慧。為了廣泛動員科研人員,積聚科學家的力量,戰時科技研發的領軍人物瓦尼爾·布什(Vannevar Bush)提議創建國防研究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作為軍隊與科學家在重要研發項目中協調與交流的平臺,其核心成員大多來自美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譬如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長卡爾·康普頓( Karl Compton)、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Institute of Technology)院長理查德·托爾瑪(Richard C.Tolman)等。在國防研究委員會的領導下,軍方將研究任務委托給大學和企業,大學因此得以管理研究項目。聯邦政府的合同和贈款保障了學術研究的不斷進步與增長。大學實驗室成為當時許多科研項目的中堅基地,如麻省理工學院的萊德實驗室(Rad Lab)成功研制出能夠有效探測出德軍U型潛艇的雷達,這項發明成為戰爭中取勝的重要裝備。原子彈、雷達、固體火箭、無線引信這四大最為關鍵的軍事成果,都是建立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霍普金斯大學等多所研究型大學的量子物理學、電子學、無線電通信等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之上[4]。除了對戰爭有直接貢獻的軍事科技成果,在與制藥公司的通力合作下,大學醫藥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基于戰前學術醫學研究人員與藥物公司已有的合作關系,戰時隸屬于科學研究和發展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醫學研究委員會,通過與制藥公司簽訂合同,開發出青霉素、合成抗瘧藥、類固醇和替代性血液制品[5]。
戰爭接近尾聲時,為延續科技領先的局面,開啟未來科學發展的新篇章,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就如何將“科技戰爭”的威懾轉化為國民生產力發出“羅斯福之問”。“羅斯福之問”的核心要點包括:一是如何將戰時以軍用目的開發的科研成果盡快轉為民用,以刺激經濟發展,創社會之繁榮;二是政府應以何種方式資助醫學研究,以對抗疾病;三是政府應如何資助私立與公立的機構(大學)科研;四是政府應當如何在青年中發現并培養科學研究人才[6]。四十多位學界泰斗應邀組成四個委員會,針對這四個重要問題分別進行了討論并形成報告。1945年4月,各個委員會向布什提交最終小組報告,最后由布什親自撰寫了總結報告——《科學:無盡的邊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這份報告對美國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既充分表達了大學科研對于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又預示了將科研與市場聯系在一起的可能性。此外,布什在報告中強調大力資助基礎研究的觀點得到認可,戰后美國政府不斷加強對高校的科研扶持力度,設立了與科研活動密切相關的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國家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等研究資助機構,進一步為日后美國大學科研及其商業化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得益于政府對科學研究的重視以及各科研機構的資金支持,研究型大學的科研事業蒸蒸日上,涌現出豐富的科研成果,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發現了中介子的存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約翰·馮·諾依曼( John von Neumann) 教授主持發明了第一臺電子計算機,麻省理工學院發明了計算機磁芯記憶材料、微波預警系統等[7]。戰時科研成果帶來的豐厚回報,讓美國政府以及部分大學和企業機構對科技成果的轉化表現出濃厚興趣,涌現的一批科技發明經過有識之士的進一步開發后成為民用產品。例如,隨著戰后微電子等領域的進步,雷達的應用范圍不再限于軍事領域,還應用于氣象預報、環境監測等。一些戰時實驗室在戰后繼續存在,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實驗室(Lincoln Laboratory)便是其中典范,促成了日后一批批聲名遠揚的科技公司[8]。戰后零星的商業實踐活動觸發了大學潛在的商業意識,加深了大學與產業之間的互動,象牙塔中開始彌漫商業氣息。科研價值的不斷凸顯,激發了大學將科研成果進行商業轉化的意識。
二、冷戰恐慌:學術實用性溢出,商業化進程推進? 在動蕩的冷戰陰影下,1957年的蘇聯衛星事件給美國全國上下沉重的打擊,造成了極大的恐慌,至此,美國在二戰建立起來的自信被無情擊垮,世界霸主的美夢悄然破碎。恰如托馬斯·邦納(Thomas Bonner)在《高等教育雜志》(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描述:“幾年來,獨立觀察人士一直在警告我們,蘇聯在教育領域,特別是科學教育領域的所作所為,但他們一直在荒野中哭泣,直到1957年10月4日,當俄羅斯人明確表示,他們在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技術的一些相關領域已經超越了我們,從而打破了我們的華麗自負……科學和教育現在成了冷戰的主戰場。”[9]為應對人造衛星危機,加強科學教育迫在眉睫。蘇聯衛星事件不久,《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作為應急法案誕生。此法案頒布以來,國會增撥了大量經費用以發展高等教育,從1958年到1968年,即蘇聯人造衛星之后的10年間,聯邦政府撥給大學的研發資金從3億美元躍升至16億美元,其中用于大學基礎研究的資金從2億美元升到13億美元,增長了7倍[10]。源源不斷的資金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保障,科研事業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研究型大學一方面繼續承擔國防研究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刺激下也承擔著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為商用、民用的任務,社會作用不斷凸顯,大學與市場的交流也愈加頻繁。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二十多年里,乘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東風,來自聯邦政府的大量研究資助投入包括半導體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在內的新興領域之中,科研發明逐步推廣到商業領域,學術與商業的藩籬不斷被打破。
冷戰初期迫切的國防需求,推動了研究型大學通信、計算機、電子等學科的發展,為大學科研商業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斯坦福大學的發展便可窺探一斑。在冷戰機遇下,錯過了二戰紅利的斯坦福大學,一躍成為商業化實踐的領跑者。1944年,斯坦福大學任命電氣工程師弗萊德·特曼(Fred Terman)為院長,這使其在即將到來的電子革命中獲得了“先發制人”的優勢[11]。特曼審時度勢,著力發展對國家具有重要作用的電子領域,通過加強斯坦福大學的基礎電子研究來爭取外來資源,提高大學聲譽。除此之外,在特曼的提議下,斯坦福大學于1951年創造性地通過出租土地吸引科技公司在此發展的方式,在大學校園里建立了斯坦福工業園(Stanford Industrial Park,后改名為Stanford Research Park)。研究園的發展體現了特曼學術——工業合作的愿景[12]。此后,這片土地成為企業的理想選址,瓦利安聯合公司(Vallian Associates)、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mpany)和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成為斯坦福研究園早期的租客,科技公司的創辦也迅速形成連鎖反應——該地區在短期內發展成為世界上電子和半導體公司最集中的地方。大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園區公司得到迅速轉化,斯坦福大學與高科技公司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隨著研究園區的不斷擴張,其所在地圣塔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將經濟發展重心由農業逐步轉移到高科技產業,實現了由農業園區向技術中心的華麗轉身——1971年,一家專門報道半導體工業的《微電子新聞》周刊編輯將其冠以“硅谷”之名。
這一時期,美國國防需求成為硅谷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眾多高新技術公司收到了來自美國軍方的訂單。1958年到1974年間,五角大樓向硅谷的公司采購了10億美元的半導體相關研究成果和產品[13]。硅谷地區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帶動了以斯坦福大學為軸心,加州大學、加州理工大學、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等多所知名研究型大學共同構成的學術創業集群發展。置身于加州地區的科研創業集群,大學與企業之間交往甚密,學術創業活動層出不窮。加州大學為半導體技術與產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加州吸引了大批的科研合同。例如,該校在通信電路與芯片設計軟件方面,創立了集成電路設計及軟件應用的知名公司[14]。20世紀60年代,在1萬美元以上的與國防有關的主要合同中,加州獲得了20%,另外還獲得44%的來自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的分包合同[12]。
除了聞名于世的斯坦福研究園,早期學術商業活動還活躍于為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提供智力支撐的波士頓“128號公路”。硅谷和“128號公路”同樣依靠附近研究型大學的創業活動而聲名鵲起,兩者的發展路徑也常常被世界各地模仿。“128號公路”的振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圍大學的技術創新,其中麻省理工學院的貢獻最大。20世紀6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工程類院系與研究實驗室至少孵化出了175家新企業,其中50家來自林肯實驗室[15]。得益于大學的創新創業活動,短短幾年之內,眾多研究實驗室、老牌公司在此落戶,公路由六車道拓寬到了八車道,為欣欣向榮的學術創業活動開辟了更大的空間,被形象地稱為“美國科技高速公路”。在硅谷、“128號公路”的示范下,北卡羅來納州也著力創辦研究園。二戰之后,北卡羅來納州家具、紡織和煙草三個傳統行業日漸衰落。1958 年 12 月,企業界、學術界、工業界的領袖攜手集資、購買土地,共同建立了以達勒姆市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羅利市的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為智力支撐點的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 the Research Triangle Park of North Carolina,RTPNC)。 隨后,大批企業和研究機構進駐園區。園區在生物醫藥、信息通信、環境衛生及國防科技等領域初具規模,形成了以研發活動為主體的高科技中心[16]。研究園致力于大學與企業的互惠雙贏:企業能夠及時利用高校的人才和技術優勢實現產品創新和技術改造,研究型大學則可以通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孵化器等組織機構將科研成果擴散到園區的企業中去。活躍的商業氛圍吸引了大量風險資本的入駐,為學術、創業營造了良好的融資環境。由此,大學科技園被視為產學合作的重要紐帶、創新創業的大本營,也成為加速大學商業化進程的重要場所。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創辦科技園好處頗多,但在20世紀70年代初,許多大學研究園區難言成功,大多在困境中掙扎求生[17]。
生物技術創業的勃興也是商業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1972年,反導彈條約簽署后,冷戰局勢趨緩,環境惡化以致健康問題成為重要議題。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期望通過推動抗癌運動穩定民心。為此,美國在1971年簽署了《國家癌癥法》(The National Cancer Act),吹響了向癌癥宣戰的號角。為響應抗癌計劃,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于1971年和1972年分別制定了癌癥研究計劃和心臟病研究計劃,促進了研究型大學醫學院的發展[18]。10年之內,NIH在學術研發中的資助比重由1971年的37%左右躍升至1981年的46%左右[19],扮演著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最大捐助者的角色。然而,生物科技發展的歷史并不久,長期以來,“盡管化學、化學工程,物理學和電子學等領域取得了許多進展,最終創辦了一些企業”[17] ,但在生物學領域,這種情況遲遲未發生。DNA重組技術的發現才得以改變這一現實狀況。20世紀70年代,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分子生物學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等科學家從哺乳動物基因組中切割了一個基因,通過將其成功插入大腸桿菌而首創重組技術,為生物科技產業奠定了基礎,由此揭開了生物技術時代的序幕[20]。由于DNA重組技術極具實用價值,在此技術支撐之下,大學醫學研究迅速產生溢出效應。
此后幾十年間,一批基于生物技術的制藥企業在舊金山灣崛起,最為著名的當數DNA重組技術發現者之一赫伯特·博耶教授于1976年創辦的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聯邦政府研發資金的增加以及業界對生物醫學研究成果的興趣愈益濃厚,促使這一時期生物醫學專利申請十分活躍。1968至1970年以及1978至1980年兩個時間段內,非生物醫學大學專利增加了90%,而生物醫學大學專利增長了295%[21]。專利申請的迅速升溫,為大學創造了大量“意外”收入,激發了大學教授的創業熱情。隨著生物制藥產業的蓬勃發展,大學科研機構、生物技術公司、制藥公司及相關服務性機構云集,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初具雛形。幾經發展,依托研究型大學形成了分布在東海岸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華盛頓(Washington)、巴爾的摩(Baltimore)的生物醫藥產業創新集群區,以及分布在西海岸圣地亞哥(San Diego)和舊金山灣(San Francisco Bay Area)的生物醫藥創新集群[22]。在這些創新集群中,產生了諸如默克(Merck)、百健(Biogen)、強生(Johnson&Johnson)、諾華(Novartis)等頂尖醫藥公司,帶動了全美其他地區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受衛星危機的刺激以及科技革命的影響,美國大學通信技術、電子、生物醫藥以及化工等領域加速發展,諸如斯坦福、麻省理工等極具創業意識的研究型大學已悉數通過技術轉移、衍生企業等多種途徑參與商業活動,科研商業化之風日趨強勁。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因政府研究發展經費的大量投入,美國學術研究事業進入蓬勃發展期,大學研究和開發活動也急劇增加。然而,戰爭尚未結束,美國聯邦政府的科學政策依然側重國防及國防需要,政府科學政策、經濟政策中很少提及學術研究所產生的經濟影響[17]。加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在科研商業化方面缺乏立法支持,技術轉移制度不夠成熟,學者對于科研商業化爭議不斷、褒貶不一,亦成為這一時期科研商業化發展的阻礙,以致多數大學仍處于觀望階段,對于申請專利較為保守。
三、經濟絕境:《拜杜法案》頒布,商業化高潮掀起?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了滯脹期,國家競爭力式微。受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規律的影響,1974—1975年,美國面臨著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率在戰后首次達到12%[23]。經濟發展問題引發了民眾對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擔憂,一些主流雜志和報紙紛紛以《正在消失的創新》(Vanishing Innovation)、《創新的衰退》(The Innovation Recession)、《美國創新怎么了》(Somethings Happened to Yankee Ingenuity)為題撰文,憂心當前經濟發展狀況[17]。同時,國內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以“小政府,大社會”理念上臺的里根政府,強調推行市場化和私有化,減少政府對大學的資助與干涉。由此,大學獲聯邦政府資助也隨之被削減,僅僅依靠聯邦資助已經不能維系大學的發展宏圖,這就激發了美國研究型大學通過技術專利和許可方式進行科研商業化活動的動機,大學商業化進入蓬勃發展時期[24]。為了滿足發展需要,大學為政府、企業及社會提供各種服務,以籌集資金,添置設備。
為扭轉經濟頹勢,將科研發現盡快轉變成產品和服務的呼聲越來越強烈[23]。為此,1980 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在紛爭中順勢而出。該法案指出:“法案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由聯邦政府資助之發明專利的利用效率,鼓勵更多的小型企業參與到聯邦研發計劃當中,促進營利組織與承擔研發工作的非營利組織(包括大學)之間的合作……”[25]《拜杜法案》制定之前,大學對于專利申請依舊謹慎:外界對于科研商業化仍抱有成見,認為那是企業的行為;政府始終持強硬立場,認為任何由聯邦資助的研究成果都理應屬于政府;復雜的審批程序增加了專利技術向私人部門轉化的障礙。政府緊握大量專利,卻沒有進行有效配置,實際商業轉化明顯不足。《拜杜法案》頒布前夕,聯邦政府已積累的近28 000項專利中,學術商業化率不到5%[26]。《拜杜法案》頒布后,為適應新形勢,聯邦政府開始鼓勵市場驅動型大學的發展,以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此后,聯邦資助的科研成果的專利權不再是政府部門專有,私人部門、大學也被賦予了享有聯邦資助發明的權利,從而激發了研究型大學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強大動力,大學科研商業化的熱情高漲。法案通過之后,美國大學相繼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全權負責專利、版權許可等事宜。
事實上,早在1970年,斯坦福大學就成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技術轉移辦公室,開創了在大學自行管理專利成果商業化運作的先河。致力于純學術研究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雖是技術轉移的后來者,然而,在歷經了早期商業實踐的失敗后,1986年也建立了專門的技術轉移辦公室[27],加入技術轉移的商業活動之中,而且富有成效的商業活動使其成為巴爾的摩地區經濟發展的引擎。有了政策保障以及負責協調校企雙方的技術轉移管理機構,20 世紀 80 年代之后,美國大學專利許可數量呈現出激增態勢。1974年,美國排名前100位的研究型大學擁有的專利數量為177個,到1984年該數量增加到 408 個,而在1994年專利數量飆升至1 486個[28]。專利轉化解禁之后,大學科技園被視為科研產業集群的重要紐帶,校企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加深。在園區內,大學的科研成果更加通暢便捷地轉化為企業產品,由此吸引大批企業入駐。以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研究園為例,目前共有微電子、電信、生物技術、化學、制藥及環境科學等領域的250家高新企業入駐,每年為園區大學帶來超過3億美元的研發經費[29]。得益于硅谷、“128號公路”、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等早期創建的科技園的成功示范,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科技園的發展已成燎原之勢——1975年之前,僅有10所大學開設了研究園,到80年代中期,已有超過40所大學擁有研究園[30]。原有的科技園因科研商業化活動的持續發展,在規模上進一步擴大,新建科技園的數量亦不斷增多。不僅是研究型大學,傳統意義上的“教學型”大學也紛紛加入興建科技園的浪潮之中[31]。一時之間,美國研究型大學成為了創新創業的溫床[32]。
《拜杜法案》鼓勵大學利用科研創收,大大激活了科研人員的研發活力,提高了他們參與商業活動的興趣。生物制藥行業的接續發展點燃了教授們的創業熱情。1999年,弗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心血管醫學教授喬爾·林登(Joel Linden)和化學教授蒂莫西·麥克唐納(Timothy Macdonald)建立制藥公司,開發治療心臟病、糖尿病、關節炎、癌癥和動脈粥樣硬化等相關腺苷藥物,癌癥研究因此取得重大突破[33]。由于科研人員創業積極性的提高,大學衍生企業的數量實現了快速增長。據統計,1980到1993年,美國高校創設公司達1 013家,并涌現出大批以大學為中心的創新型中小企業集群[34]。美國南部一些城市,如亞特蘭大(Atlanta)、奧斯汀(Austin)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華麗轉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學初創公司。如1986年位于奧斯汀的103家中小型科技公司中,有53家表明它們與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科技公司對于奧斯汀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公司的創始人大多是德州大學的學生、畢業生、教職員工和其他員工[35] 。一向保守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對于商業化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耶魯大學在技術轉化方面態度消極,在促進紐黑文(New Haven)地區經濟發展上無所作為。為了改變現狀,1993年,耶魯大學通過重組合作研究辦公室( Office of Cooperative Research,OCR),加大力度促進技術轉化和商業化。2004年,紐黑文市的生物科技集群已經擁有49家衍生公司,其中有24家公司(約49%)依賴于耶魯大學的科技、思想或者創始人而產生[36]。
隨著美國大學融入商業潮流,大學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更加突出,研究型大學和產業已儼然結成聯盟。這一發展趨勢與相關政策密不可分,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拜杜法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其“可能是美國國會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通過的最鼓舞人心的法案”[37]。除此之外,里根政府踐行“小政府,大社會”施政策略之后,通過的多項法案對促進科研成果商業化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1982年出臺的《小企業創新發展法》(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Law),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技術創新活動,推動小企業在促進聯邦科研成果轉化中發揮自身優勢;1984年出臺的《國家合作研究法案》(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打破了企業之間合作的藩籬,加強了企業間的合作聯系;1986年出臺的《聯邦技術轉移法》(The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和《藥品出口修正案》(Drug Export Amendment),在促進技術轉移方面發揮了法律作用,進一步鞏固了制藥行業的發展。這些法案雖然并非針對大學,但都對大學商業化產生了間接影響。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因特網和生物技術等高科技產業推動了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克林頓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重點發展信息、生物及清潔能源和環境技術產業,為大學與企業的合作創造了更為有利的商業環境[38]。21世紀以來,產業競爭更加激烈,研究型大學作為科技創新的沃土、人才培養的搖籃,對于社會發展至關重要。出于經濟發展要求,聯邦政府持續引導大學進入市場。2009年,奧巴馬政府頒布了高達530億美元的資助法案《美國恢復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其中大部分用于生命科學、能源研究等關系經濟發展的前沿知識研究,使科研成果不斷轉變為驅動經濟創新的學術資本[39]。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價值愈發被重視,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助推器,為美國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經濟貢獻。據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的報告《美國大學/非營利組織發明的經濟貢獻:1996至2015》(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University/Nonprofit Inven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1996—2015)顯示,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經濟回報率巨大,在20年間,學術專利與隨后的工業許可,使美國工業總產值增加了超過1萬億美元[40]。
四、結論
基于國家之需,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國家發展的各個時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僅在戰爭期間致力于軍事項目研發,在和平年代更是起到了提升經濟、改善民眾福祉的作用。據統計,美國80%的新興產業得益于大學的研究成果,如半導體、軟件科技、計算機硬件、互聯網及生物藥劑等[41]。知識經濟社會中學術商業化的價值意義非凡,不僅推動了大學自身的變革,促進了創業型大學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研究型大學提供的智力支持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關鍵參與者,學術與商業日益交織、密不可分。
誠然,大學作為知識經濟的主要知識來源,必然要對社會需求作出反應,大學對外界變化置之不理是不切實際的。通過科研商業化,大學能夠更加深入地融入社會經濟發展之中;適當的商業活動能夠激發科研活力,以幫助大學實現生存之道。鑒于高等教育科研規模的不斷擴展,現代大學只有通過學術商業化等方式獲得大量的經費,才能保障學術研究的順利開展,維系其正常的科研活動[42]。此外,學術創業能夠激活或重啟區域創新活力,助力經濟競爭力的發展與恢復,隨著大學學術商業價值的提升,大學越來越成為各地區發展的經濟引擎。
大學的科研商業化無可厚非,但市場與大學二者屬性不同,目標各異,應當警惕科研商業化活動對大學屬性的破壞。一旦涉足商業領域,大學原本被高歌之科學研究自由難免受到約束。譬如,鑒于商業合同的保密性原則,可能會使科學家以利換義,為保護商業利益放棄自由之發表,隱匿或篡改研究之結果。尤其是那些新興的商業化大學,更有可能為了趕超而大肆鼓勵研究人員追逐知識產權,將學術自由撂置一旁,最終導致本應以興趣為導向的科研工作在商業利益考量之下發生變化。恰如布魯金斯協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所批評的那般:“大學科研商業化導致其對商業回報率的期望值,遠遠超出大眾的預期。”[43]如若這般,大學商業化將難免受挫,期待大學在知識經濟時代作出非凡貢獻也可能事與愿違。
參考文獻:
[1] 喬納森·科爾.大學之道[M].馮國平,郝文磊,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187.
[2]王英杰,劉寶存.世界一流大學的形成與發展[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168.
[3]穆瑞燕.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管理機制探析——以斯坦福大學為例[J].中國高校科技,2017(12):16-19.
[4]高云峰.美國研究型大學與軍事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2004.
[5]TOBBELL D A.Allied Against Reform:Pharmaceutical Industry-Academic Physician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1945—1970[J].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2008,82(4):878-912.
[6]程星.美國大學小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172.
[7]王鳳玉,寇文淑.研究型大學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政策變量——以美國科技政策為中心的考察[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9,18(2):81-87.
[8]ETZKOWITZ H.Entrepreneurial Scientists and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in American Academic Science[J].Minerva,1983,21(2/3):198-233.
[9]BONNER T N.Sputniks and the Educational Crisis in America[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58,29(4):177-232.
[10]格拉漢姆,戴蒙德.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興起:戰后年代的精英大學及其挑戰者[M].張斌賢,於榮,王璞,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47.
[11]ADAMS S B.Follow the Money:Engineering at Stanford and UC Berkeley During the Rise of Silicon Valley[J].Minerva,2009,47(4):367-390.
[12]SAXENIAN A.The Genesis of Silicon Valley[J].Built Environment,1983,9(1):7-17.
[13]王猛.硅谷科技園區的嬗變與經驗——讀《硅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1900—2013)》[J].公共管理評論,2016(1):135-145.
[14]馬丁·肯尼,大衛·莫厄里.公立大學與區域增長:加州大學透視[M].李應博,孫震,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16.
[15]安納李·薩克森尼安.區域優勢[M].溫建平,李波,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18.
[16]牛司鳳,郄海霞.高校與區域協同創新的路徑選擇——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研究三角園”為例[J].高教探索,2014(6):5-10.
[17]BERMAN E P.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28.
[18]游秀麗.戰后美國研究型大學商業化研究(1945—2005)[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0.
[19]MOWERY D,NELSON R.Ivory Tower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M].Palo Alto:Stanford Business Books,2004:43.
[20]孔朝霞.歐盟主要國家生物技術研究及發展概況:—[J].國外醫學情報,1999(2):6-9.
[21]MOWERY D C,Sampat B N.The Bayh-Dole Act of 1980 and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A Model for Other OECD Governments?[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4,30(1):115-127.
[22]江育恒,趙文華.研究型大學在區域創新集群中的作用研究:以美國五大生物醫藥集聚區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5):102-108.
[23]王英杰.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6.
[24]趙俊芳,李國良.美國大學商業化尋理[J].江蘇高教,2011(3):144-147.
[25]范躍進,王玲,苑健.美國科學政策體系評析與借鑒[J].東岳論叢,2017,38(2):26-31.
[26]拜杜法案[EB/OL].(2012-08-01)[2021-07-23].https://baike.baidu.com/ item/%E6%8B%9C%E6%9D%9C%E6%B3%95%E6%A1%88/10653411?fr=aladdin.
[27]FELDMAN M,DESROCHERS P.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Industry & Innovation,2003,10(1):5-24.
[28]王宇翔.20世紀80年代美國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因素探析[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7(5):75-80.
[29]The Research Triangle Park.Who We Are[EB/OL].(2017-11-20) [2022-09-11].https://www.rtp.org/about us/.
[30]羅杰·蓋格.研究與相關知識: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美國研究型大學[M].張斌賢,孫益,王國新,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350.
[31]楊九斌.誰出資,誰擁有?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專利歸屬之爭[J].復旦教育論壇,2019,17(6):97-104.
[32]HANSEN S.Innovations Golden Goose[EB/OL].(2012-11-06)[2022-12-05].http//www.economist.com/node/1476653.
[33]楊九斌,李樂平.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發展與國家創新革命[J].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6(4):108-116.
[34]劉燕影,張冬梅.改變美國的三項科技政策[J].世界科學,2011(7):58-60+64.
[35]SMILOR R W,GIBSON D V,KOZMETSKY G.Creating the Technopolis:High-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Austin,Texa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89,4(1):49-67.
[36]吳偉,臧玲玲,齊書宇.急劇變革中的大學社會服務[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27.
[37]LOISE V,STEVENS J.The Bayh-Dole Act Turns 30[J].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0,2(52):52.
[38]張華勝,彭春燕,成微.美國政府科技政策及其對經濟影響[J].中國科技論壇,2009(3):7-15+20.
[39]楊九斌.學術與商業博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術商業化的艱難抉擇[J].比較教育研究,2021,43(5):29-35.
[40]楊九斌.國家使命與美國聯邦政府大學科研政策演變[J].教育學報,2020,16(3):97-107.
[41]ATKINSON C,PELFREY A.Science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J].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26(4):39-48.
[42]李巧針.淺析博克的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和大學商業化思想[J].中國大學教學,2005(3):56-58 .
[43]COHEN M.“Industry and the Academy:Uneasy Partners in the Cau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Challenges to Research Universities[M].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185.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 as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 flourished,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Cold War, funding for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indirectly stimulated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ose universities. They not only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ense research, but aime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nto commercial and civilian usages, mak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patents and others gradually possible. In the 1970s, out of concern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S. econom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troduced policie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which brought the wave of commercialization for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t has become the miss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commercialization, we should be wary of the crisis of profit-seeking. Look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economic missions.
Key words:post-World War II;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evolution
(責任編輯:梁昱坤 郭 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