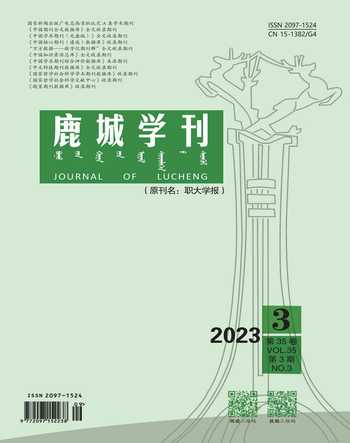永世難忘的師生際遇
“文革”結(jié)束后,高校又恢復(fù)了招生。但當(dāng)時(shí)高校師資中也面臨著一個(gè)嚴(yán)峻的問題,那就是“青黃不接”。有些中青年教師的業(yè)務(wù)水平也亟待提高。于是教育部經(jīng)過調(diào)查,有針對性地提出讓一些老專家來帶中青年教師,并指定有關(guān)高校舉辦進(jìn)修班。這種進(jìn)修班突出了老專家的業(yè)務(wù)專長,分科較細(xì),針對性也很強(qiáng),如南京大學(xué)舉辦的以洪誠先生為導(dǎo)師的“訓(xùn)詁學(xué)班”、中山大學(xué)舉辦的以王季思先生為導(dǎo)師的“戲曲班”便是。其舉辦時(shí)間,大致在1979年至1980年間。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學(xué)舉辦的以姜亮夫先生為導(dǎo)師的“楚辭班”,也就在這一時(shí)期。
1979年秋,姜先生已是78歲高齡的老人了,但接到任務(wù)后還是非常高興。他“覺得這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學(xué)術(shù)研究任務(wù)”,也許是他“最大的一次耕耘”,于是“便打點(diǎn)精神、制定計(jì)劃、準(zhǔn)備參考書、擬定教學(xué)大綱,用全力來完成這一任務(wù)”(見《楚辭今繹講錄·序》)。
1979年9月20日前,十三位學(xué)員全部到齊。他們是:林維純(暨南大學(xué))、郝志達(dá)(南開大學(xué))、張崇琛(蘭州大學(xué))、丁冰(東北師范大學(xué))、王延海(遼寧大學(xué))、姚益心(華東師范大學(xué))、趙浩如(云南大學(xué))、殷光熹(云南大學(xué))、姜宗倫(昆明師范學(xué)院)、呂培成(陜西師范大學(xué))、栗凰(青海師范學(xué)院)、黎安懷(貴州師范大學(xué))、鈕國平(甘肅師范大學(xué))。由于鈕國平1980年復(fù)學(xué)時(shí)再未參加,所以學(xué)界便稱我們是姜先生的“十二門徒”,而姜先生也經(jīng)常說我們是他晚年“結(jié)的一個(gè)大瓜”。
1979年9月24日下午舉行開學(xué)典禮,杭大一位副校長及教務(wù)處胡仲英處長、中文系呂漠野副主任出席。姜先生在典禮上發(fā)表了簡短的講話,明確提出“要綜合研究楚辭”。而且還指出,這樣的研究,“不單是社會科學(xué)的知識,自然科學(xué)的知識也需要”。并以楚辭中的“蘭”為例,勸大家去做綜合研究。又以楚國的大吉日“庚寅”為例,說明楚辭研究也還要懂得民俗學(xué)。話雖不多,但言簡意賅,令學(xué)員們一上來就深受啟發(fā)。
按照教學(xué)計(jì)劃,先生每周講課兩次。一次是在教室上大課,有些杭大的年輕教師也來聽;一次是在先生家圍坐而談,我們也可以插話,氣氛比較活躍。此外,每次上課前都會發(fā)一些輔助講義,主要是先生的有關(guān)文章,有些在課上未能展開的話題便下去看講義。至于個(gè)別輔導(dǎo),隨時(shí)都可以進(jìn)行。
先生還為我們指定了必讀書和選讀書。必讀書中洪興祖的《楚辭補(bǔ)注》是人人都要讀的;其余五種,即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王夫之《楚辭通釋》、戴震《屈原賦注》、劉夢鵬《屈子章句》、姜亮夫《屈原賦注》,再選讀其中的二至三種。選讀書有十五種,即朱熹《楚辭集注》、林云銘《楚辭燈》、胡文英《屈騷指掌》、丁晏《楚辭天問箋》《竹書紀(jì)年》《史記·楚世家》《國語·楚語》《戰(zhàn)國策·楚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艾思奇《中國社會史》、鄧永齡《中國民俗學(xué)》、王國維《觀堂集林》、馬其昶《屈賦微》、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周圣楷《楚寶》,可量力再選讀若干種。每本書讀后可寫出讀書報(bào)告,“各以心得為主,無心得不必寫,有心得可多寫,隨時(shí)交稿集之作為成績”(見《培訓(xùn)計(jì)劃》)。我寫的讀書報(bào)告是《一個(gè)值得重視的〈楚辭〉注本——讀劉夢鵬〈屈子章句〉》,曾得姜先生嘉許。此文稍后發(fā)表于《文獻(xiàn)》雜志(第12輯),經(jīng)壓縮后又作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先秦文學(xué)卷》的一個(gè)詞條。聽江林昌兄說,姜先生后來在指導(dǎo)博士生寫讀書報(bào)告時(shí),還曾以這篇文章作為范文。這當(dāng)然是后話了。
講課開始進(jìn)行得非常順利。姜先生雖然不帶講稿,但文獻(xiàn)的征引,對各家觀點(diǎn)異同的比較,皆脫口而出。而其以清晰的思路,流暢的語言以及親切自然的授課風(fēng)格,將一個(gè)個(gè)深奧的學(xué)術(shù)問題深入淺出地揭示出來,更令聽講者受益無窮。我們?nèi)缇煤抵龈柿兀c(diǎn)點(diǎn)滴滴都舍不得放過,專心致志地聆聽著先生的每一句話。每次下課之前先生總是問我們聽懂了沒有,當(dāng)我們說聽懂了后,先生才微笑著站起來,旋即由兩位學(xué)員攙扶他回家。后來我們覺得先生這樣來回走路很辛苦,經(jīng)與校方交涉,此后每次上課(一般是星期四),便由學(xué)校派車接送。
但在講課進(jìn)行到第七個(gè)星期時(shí),出人意料的事情發(fā)生了。1979年10月27日夜,一名劫賊從姜先生家風(fēng)窗闖入室內(nèi)盜竊。先是刺傷了師母(事后檢查師母為皮外傷),先生見狀抱住劫賊不放,又被推倒在地,造成腦震蕩和尾椎骨折。第二天,二老被送進(jìn)醫(yī)院治療。事已至此,學(xué)校只好決定楚辭班暫停。我們要輪流值班陪護(hù)先生,但先生堅(jiān)決不準(zhǔn),說我們的任務(wù)是學(xué)習(xí),不是陪護(hù)病人。于是我們只好回到原單位,等候復(fù)課的通知。
1980年3月下旬,終于接到杭大復(fù)學(xué)的通知,要求4月5日報(bào)到,4月7日開學(xué)。我按期于4月5日到達(dá)杭大,當(dāng)天就與王延海兄一起去看望先生。先生身體恢復(fù)得還不錯(cuò),見到我們也很高興,連聲說:“你們重返杭州,極不容易,我很高興!”原來先生已經(jīng)知道,當(dāng)時(shí)高校正在評職稱、提工資、調(diào)整住房,人一走,這些全都落空了。而我們?yōu)榱烁辖壬鷮W(xué)習(xí),對此則全然不顧,難怪先生為之動情了。
為了完善我們的知識結(jié)構(gòu),增廣我們的見聞,經(jīng)先生提議,杭大為我們安排了半個(gè)月的訪學(xué)活動。為此,先生又給我們寫了十二封介紹信,介紹我們?nèi)グ菰L江浙一帶的名師同時(shí)又是先生老朋友的十二位著名專家,即南京大學(xué)的陳中凡、程千帆,揚(yáng)州師院的王善業(yè)、卞孝萱,蘇州的朱季海,復(fù)旦大學(xué)的朱東潤、蔣天樞、郭紹虞、陳子展,華東師大的徐震堮、戴家祥,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我去取介紹信時(shí),先生還諄諄告誡我說:“你們一定要認(rèn)真向?qū)<覀冋埥蹋D(zhuǎn)益多師是汝師。”先生之學(xué)術(shù)襟懷,真是令人敬佩。關(guān)于這次訪學(xué)的具體情況,我已寫有《江浙訪學(xué)記》一文,在此就不詳述了。
訪學(xué)歸來后,5月8日繼續(xù)上課,還是每周兩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先生家中。講義的發(fā)放及個(gè)別輔導(dǎo)都照常進(jìn)行。計(jì)自5月8日至6月29日,先生大課又講了六次,即六講。再加上1979年下半年的六講,共十二講。這些課我們每次都有錄音,下課后分工整理。后經(jīng)昆武加注,姜先生審閱,便成了《楚辭今繹講錄》一書。此書由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正式出版后,旋即在楚辭學(xué)界引起轟動,而姜亮夫“十二門徒”的稱謂也便在學(xué)界叫開了。
楚辭班除學(xué)習(xí)楚辭外,姜先生還對我們的古漢語尤其是文字學(xué)與音韻學(xué)進(jìn)行了補(bǔ)課。這樣的大課也講了有五六次。先生將深奧難懂的音韻學(xué)知識(如“等呼”等)用很淺顯的語言表達(dá)出來,令我們茅塞頓開。先生還給我們介紹了最為精妙的太炎先生的《成均圖》,并謂“章太炎先生的《成均圖》是科學(xué)的,它告訴我們?nèi)绾握莆胀ㄞD(zhuǎn)的規(guī)律”(見《漢語大辭典》浙江省編寫辦公室編《漢語散論》)。三十年后,我考證《倉頡書》28個(gè)字的讀音,正是得益于太炎先生的《成均圖》。
總之,在楚辭班學(xué)習(xí)期間,用一句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收獲滿滿。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先生教會了我們一種先進(jìn)的、行之有效的治學(xué)方法。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點(diǎn):
一是綜合研究法,即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方法。《楚辭》是一部百科全書,其中既有著豐富的楚文化史料,也蘊(yùn)含了亞洲乃至環(huán)太平洋文化的許多重要信息。因此,對《楚辭》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文學(xué)的層面,而應(yīng)該全方位地展開。這方面,先生的《楚辭通故》已為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樣。我此后對《楚辭》之“蘭”的辨析(《楚辭》中“蘭”字凡四十二見,包含了佩蘭、澤蘭、木蘭、馬蘭、蘭花五類),以及對楚騷詠“蘭”文化意蘊(yùn)的探微(即楚地之土宜、健身之良藥、王者之香草、詩思之淵藪),都是受到先生啟發(fā),并沿著先生的路子走下去的。我的《楚辭文化研究》一書,從哲學(xué)、政治、教育、美學(xué)、文學(xué)、歷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學(xué)的角度對《楚辭》所作的研究,實(shí)際上也是對姜先生綜合研究方法的一次實(shí)踐。崔富章先生讀后說“有老夫子之風(fēng)”,這既是對我的鼓勵(lì),同時(shí)也表明他看出了我對姜先生綜合研究方法的繼承。
二是“三重證據(jù)法”。自王靜安先生提出用“地下之材料”以“補(bǔ)正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jù)法”以來(見其《古史新證》),學(xué)界無不稱贊。姜先生則在此基礎(chǔ)上又加入“民俗”一項(xiàng)。他不但在講課中經(jīng)常強(qiáng)調(diào)從民俗角度切入以研究楚辭的重要性,并給我們指定了幾種民俗學(xué)方面的參考書,而且在《九歌》研究中還引用了大量的民俗資料。例如他在講《國殤》時(shí),便引后世戲曲習(xí)俗中的“打加官”來說明該詩是“用來鼓舞戰(zhàn)士的”。民俗是民間流傳的活史料,雖未形成文獻(xiàn),但其中往往保存有古代人民生活的影子。先生雖未明確將他所注重的民俗與“二重證據(jù)”并列,但我們在私下里實(shí)已合“民俗”與“二重證據(jù)”為“三重證據(jù)法”了。我后來寫作《楚人卜俗考》及《說“姱女”》幾篇,便著意運(yùn)用了這一方法。
三是比較記憶法。我因驚異于先生超常的記憶力,就問先生如何記得住那么多的楚辭文獻(xiàn)。先生說靠比較記憶,即針對某一問題,比較各家之說的異同。這樣文獻(xiàn)就活起來了,而不再是刻板的教條。我嘗試這樣做了,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對《離騷》之“求女”及“兩上昆侖”,我將自王逸以來,下迄唐人、宋人、明清各家,以至聞一多、游國恩、姜亮夫諸先生之說梳理一遍,明其異同,不但問題搞清了,連各種版本的要點(diǎn)也都記住了。
應(yīng)該說,姜先生的這些治學(xué)方法不但可應(yīng)用于楚辭,對古代文學(xué)的其他作品也同樣是適用的。我從中西交通的大背景以及宗教、民俗、新聞等角度對《聊齋志異》所作的綜合研究,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diǎn)(見拙著《聊齋叢考》)。我后來在治學(xué)和指導(dǎo)研究生時(shí)所倡導(dǎo)的“大文化視野下的古代文學(xué)研究”,也正是在姜先生“綜合研究法”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并服膺終生。
楚辭班經(jīng)歷了前后兩個(gè)階段的學(xué)習(xí),終于要結(jié)束了。1980年6月28日上午,杭州大學(xué)舉行了楚辭進(jìn)修班結(jié)業(yè)典禮,校系領(lǐng)導(dǎo)、姜先生及全體學(xué)員都參加了。姜先生在典禮上發(fā)表了充滿深情厚誼的講話。他說:“我因遭劫賊擊傷住院,校方?jīng)Q定暫停授課,讓學(xué)員返校聽候復(fù)課通知。復(fù)課通知出去后,我們同學(xué)是否有興趣再來?結(jié)果同學(xué)們都來了,甚至有的在校還有課,又在‘工調(diào),涉及職稱、工資、房子……什么都不顧,丟掉就來了…..中斷后又續(xù)上,續(xù)得毫無痕跡。可以向教育部反映,全國有沒有這樣的班?大家多少都看到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才來這里學(xué)習(xí)的。在杭大學(xué)習(xí)期間,用功是不用說的…..我八十歲了,能結(jié)識你們這么多朋友,是世界上少有的事,我深感慶幸!”最后先生還鼓勵(lì)學(xué)員們說:“你們繼續(xù)走,我跟著你們走!”(姜先生的講話系根據(jù)殷光熹兄的記錄)既流露了先生一貫的謙虛與真誠,又充滿了對學(xué)生的厚愛和熱切的希望。
在結(jié)業(yè)典禮上,繼姜先生的講話后,我也情不自禁地做了一次發(fā)言,主要是講從姜先生那里所受的教誨以及參加楚辭班的收獲。我雖事先毫無準(zhǔn)備,但從來都沒有做過那樣酣暢淋漓的發(fā)言。我講話時(shí),先生一直在頷首微笑。我知道,先生對我們這一班學(xué)員的刻苦學(xué)習(xí)、心無旁騖,是十分滿意的。典禮結(jié)束,我送先生回家。在回去的路上,先生又告訴我說,我寫的讀劉夢鵬《屈子章句》的讀書報(bào)告他已閱,寫得好,主要的東西都抓住了,并讓我再壓縮一下,作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一個(gè)條目。先生啊先生,您對弟子的學(xué)業(yè)真是無時(shí)無刻不掛在心上。
結(jié)業(yè)典禮后,分別的日子就要來臨了。正當(dāng)我們幾個(gè)班委(郝志達(dá)、林維純、殷光熹、趙浩如、張崇琛)在商量如何答謝恩師時(shí),姜先生卻派他的女婿徐老師通知我們,說姜先生要在“樓外樓”飯館宴請我們楚辭班全體學(xué)員。這真是令我們喜出望外。自古學(xué)生結(jié)業(yè),只有學(xué)生請老師的,哪有老師請學(xué)生的?我想先生這一破例的做法,既體現(xiàn)了他對師生情誼的高度重視,同時(shí)也隱含著他對我們這一班學(xué)員的極好印象。宴會上我們頻頻舉杯向先生致謝,并祝老師健康長壽。而姜先生也顯得格外開心,一直慈祥地看著每一位學(xué)員。先生還再次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們回單位后,要努力學(xué)習(xí)和工作,今后學(xué)習(xí)上如有什么問題亦可隨時(shí)給他寫信,繼續(xù)切磋。
為了能同先生在一起多待些時(shí)候,6月30日,我們又請先生到黃龍洞喝茶,先生也高興地去了。先生一邊喝茶,一邊還在同我們談學(xué)業(yè)。他要求我們回去后每人寫一篇有關(guān)楚辭的文章,明年交來,由他出集子。他還告訴我們,各位的結(jié)業(yè)鑒定也已經(jīng)寫好,下午即可去取。
下午,我如約來到先生家,將十二位學(xué)員的結(jié)業(yè)鑒定取回,先供大家傳閱,然后再交杭大簽注意見寄回原單位。可以看出,我們與先生相處的時(shí)間雖然不是很長,但先生對每個(gè)人的性情及治學(xué)特點(diǎn)都了如指掌,且皆勉勵(lì)有加。其中關(guān)于我的一份是:
張崇琛同志是個(gè)博涉群書的中年教師。這是一個(gè)最主要的讀書方法。專門只搞一、二門,自然容易為功,但成就必然有限。由博返約,然后能切實(shí)掌握所要掌握的東西,這即是近年來所盛傳的綜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要素。他讀書也非常細(xì)心老實(shí),他最近所寫的一篇《讀劉夢鵬<屈子章句>》的讀書報(bào)告,看來他所以能深切了解劉書的長處,同他博涉與細(xì)心兩事分不開。是我們隊(duì)伍中后起之秀。
姜亮夫1980年6月30日
1980年7月4日晚,我去姜先生處話別。先生很鄭重地對我說,希望我能來杭大,做他的助手。我聽了當(dāng)然非常高興。但我知道,調(diào)動的事必須征得蘭大的同意,所以就跟先生說我一定努力爭取。誰知回校后費(fèi)了九牛二虎之力,蘭大還是不肯放行。我寫信告訴先生,先生又說讓我先去,由他來給我發(fā)工資。我知道先生這是在仿當(dāng)年顧頡剛與童書業(yè)及譚啟驤之例,但時(shí)代不同了,高校教師均須納入體制之內(nèi);而且,我又怎能忍心去占用先生的工資呢!所以事情終未辦成,我也只能以此為終生的遺憾了。
(責(zé)任編輯 蔚紅霞)